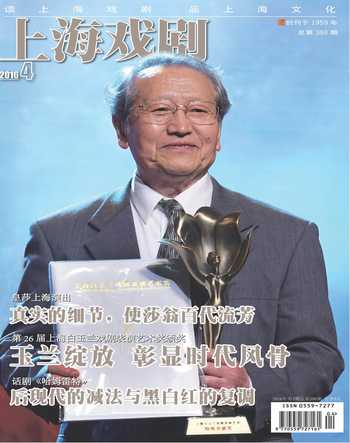不约而同:音乐的笼罩
郭晨子
2016年,似乎无论如何也逃不掉莎剧了;莎剧中,又怎能绕得过《哈姆雷特》?去年六月,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德国邵宾纳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在天津大剧院亮相;2016年元旦,由法国著名导演、曾任巴黎国立戏剧学院院长的丹尼尔·梅斯基氏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2级蒙古班的学生导演了又一版《哈姆雷特》;3月10日至13日,曾在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活动中艳惊四座的立陶宛OKT剧团的《哈姆雷特》在沪上演,该剧导演为奥斯卡·科尔苏诺夫,他也是剧团的创办者。
这些“哈姆雷特”,早已丢弃了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式的阴郁与优雅,代之以狂躁乃至粗俗,像熔岩马上就要喷发的火山。如今看《哈姆雷特》,看的也不仅仅是所谓哈姆雷特的犹豫和最终酿成的悲剧,而是着意于某些特定段落的处理,如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出现的位置和次数,如“戏中戏”的演绎方式,如“决斗”一场的表演,甚至是看一人扮演多角时角色分配中导演的动机,总之,看的是不同导演对《哈姆雷特》的不同解读。
“不约而同”,欧陆导演们都选择了用非常现代的音乐来应对古老的《哈姆雷特》。奥斯特玛雅的版本以开场最为人称道,他把老国王的葬礼放在全剧之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曲”——在全剧结构中是这样,在音乐上更是一段完整的序曲。由几乎没有旋律的长音进入,影像为巨大的哈姆雷特面部特写,“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这段“序曲”中,这也是仅有的台词。随着表演区移至舞台前端的墓地,音乐渐渐变得比之前复杂,但仍是少旋律感的弹拨节奏。再接下来,演员当众举起水管下雨,肮脏的泥土成了挣不脱的、更加肮脏的泥泞,掘墓人分别把铁锹逐一递给王后等人,或敷衍或惊恐或沉重,各自的应对显示出与死者的人物关系,哈姆雷特索性拒绝了铁锹而是自己抓了一把泥土洒在父亲的棺木上。此刻的音乐在不断重复的节奏中唤起难奈和不安,其轻重配合表演,同时电子合成器发出犹如幽冥之地回旋的风声,冰冷的死亡之外平添了阴谋的气息。终于,棺木落入坟茔,可就在“安”葬的这一刻,掘墓人失手,棺木不像样地倾斜着,音乐到了这一段落的高潮。不祥、压抑、诡谲、暗示风暴即将来临……“序曲”既呈现又规定了全剧的基调,和剧中移动的金属幕帘有相匹配的质感。而在紧随其后的“婚礼”一场,铜管乐器奏出俗气的欢乐,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和不少德国戏剧一样,该剧有专职的作曲。剧中还用了迪斯科舞曲、HIPHOP,奥斯特玛雅本人也曾在青春期叛逆退学加入了一个朋克乐队。他担任邵宾纳剧院的艺术总监以来,剧院的戏越来越受到年轻观众的喜欢,不知和他擅用手术刀一般锋利的音乐是否有直接关系,他用音乐划破生活的表象,解剖病灶的形成。
丹尼尔的《哈姆雷特》舞台上是最简洁的,既没有奥斯特玛雅的“豪华”移动轨道、金属幕帘和现场投影,也不似科尔苏诺夫用化妆间的镜子和镜像映射间“打哑谜”。他用的只是普通的椅子、餐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床。奥菲利亚闺房中的床意味着少女的童贞和纯洁,王叔与王后的眠床指向纵欲和淫逸,哈姆雷特也有一张床,却没有安适平静的睡眠……区别于奥斯特玛雅用六名演员演绎《哈姆雷特》,如王后和奥菲利亚由一名演员扮演的路径,区别于科尔苏诺夫让一名演员扮演父王和叔父,丹尼尔独具匠心地增加了演员。他时而让两名男演员都扮演哈姆雷特,一个是另一个的灵魂出窍,时而让两名女演员都扮演奥菲利亚,另一个是本来一个的放大和加强。相形之下,丹尼尔对文本的改动最小,他用转场音乐带动和加快了全剧的节奏!
蒙古族同学找来的一段马头琴音乐最终为丹尼尔选用。这马头琴奏响的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悠扬或凄怆,而是齐奏出一种节奏感十足的模进,一种大祸临头的紧迫感,一种重力加速度下的坠落速率。每当转场时音乐响起,就预示着哈姆雷特即将被卷进更黑暗、更无力挣脱的漩涡。转场音乐像是抽向旋转陀螺的鞭子,让陀螺转得愈发疯狂。如果说这一版《哈姆雷特》最忠实于原著,不断重复使用的转场音乐是一枚“快进”键,让全剧免于陷入堆砌修辞的言语,更有效地使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国成了某种社会模型和缩影。和剧中演员的蒙古族服饰相得益彰,《哈姆雷特》无关时代、国别和民族,时间越久越是一则寓言。
科尔苏诺夫版的《哈姆雷特》视觉上当然形成了体系,镜子的映射与反射、剧中人的当众自敷白面和当众卸妆、白色的鲜花和红纸、红鼻子、红血浆,各有隐喻。而在音乐上,全剧中不时响起的是噪音!
的的确确的噪音,刺耳难听又无可逃避。它“神出鬼没”,总是“莫名其妙”地响起,在哈姆雷特决意等待鬼魂时,在导演将哈姆雷特写情书、奥菲利亚读情话和波洛涅斯把信拿给王后、王叔看并置在一个场面时,以至于无法回忆和记述每一次噪音出现的契机,噪音简直像无时、无处不在的……噪音也是一种音乐,一种比悦耳之音更难忘的音乐。它也是暗示,暗示不为人知的秘密之存在,暗示秘密终究暴露时,不管对秘密的制造者来说还是对秘密的发现者而言,都难免惊慌失措、避之不及。它自成象征,它既是喻体又是喻意,它是所有人都不愿听到、所有人又都听到过的,是摆脱不了的麻烦,且总在猝不及防时突然响起,在放松警惕后再度来袭,它像是魔咒,边告诫“一切才刚刚开始”边诅咒“一切永远不会结束”,它像是暗中窥视的命运之神,又或许,生命不过是一团噪音。当噪音成为美学,“人”早已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至多是造物主的一个玩笑罢了,不可理喻的噪音正像存在本身一样荒谬。
在奥斯特玛雅、丹尼尔、科尔苏诺夫的诠释下,在当代舞台上的《哈姆雷特》中,种种语汇的创造都使观众意识到:疯狂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他周遭的世界、他周遭的所有人!佯装疯癫的哈姆雷特并未丧失清醒,自诩理智的其他剧中人早已神志不清。这其中,音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虽然在剧本中常常写到“喇叭奏花腔”(朱生豪译本),莎士比亚一定不会想到,在他辞世400年后,《哈姆雷特》的搬演中音乐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竟然和他的台词一样共同诉诸观众的听觉。而莎剧在当代的魅力,也产生自莎翁文本和当下呈现中的弥合与割裂、重叠与反差。音乐像手术刀、像推进器、像搅拌机,哪怕是“生存”不得“毁灭”不了的噪音,一旦降临,就是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