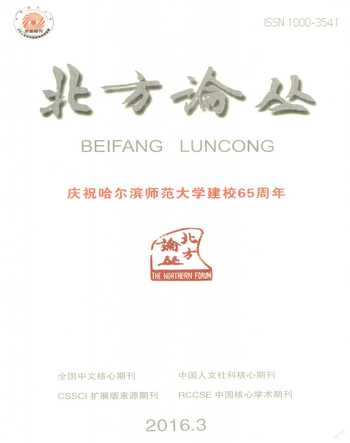陈柱散文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及文学史价值
梁艳青
[摘 要]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陈柱,一生著述甚丰。他的散文研究述及中国散文史、散文分类、散文创作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出于矫治时弊的意图,陈柱以“学术”内质和“文学”外式的体用关系构建了散文理论的基石;以此为基础,他尝试以“文言”和“质言”划分散文体类,探索归纳出中国散文的内部类型;与他的散文理论相呼应,陈柱将六经视为后世文学的源头,提出“体尊质衰”的散文史观。他将后世散文之弊归因于“尊体”的结果,主张以先秦文学为散文范本。陈柱以融汇经史子集的广阔视野来审视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后来的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史书写。
[关键词]陈柱;散文;文质论;体尊质衰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40-06
Abstract: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prose history, there are large number of scattered prose views in the the writings of Chen Zhu. They clearly show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rose theory. Due to the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e, Chen Zhus prose study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refinement and substance. He thought that academic is essential and literature is manifestation of it. He tried to divide the prose into two categori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refinement words and substance words which summarized the types of internal Chinese prose. That coincide with Chen Zhus prose theory, the six classics were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the later literature. Chen Zhu thought the prose development history is a course of more refinement and less substance. He spoke highly of the pre-Qin period works. He blended together all Cano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d explored the law of Chinese prose history development. His research inspired and promoted the later Chinese prose research .
Key words:Chen Zhu; Prose; concepts of refinement and substance; more refinement and less substance
陈柱(1890—1944年),民国时期国学大家,尤以诸子学见重于世。散文研究方面,陈柱著有中国第一部散文史著作《中国散文史》,有开先之功。此书之外,他还著有《文章论》《四十年来吾国文学之略谈》《讲陆士衡文赋自记》《论作文模拟变化之法》《韩文研究法》《大学校教授国文之方法》《与友人论文书》《与叶长卿教授论文书》《茹经堂文集序》等,述及中国散文史、散文分类、散文创作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散文理论体系。他的散文研究为总结中国散文发展规律、启发民国以至于现在的中国散文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简言之,他的散文研究体系及价值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一、“学术”内质与“文学”外式体用对应
文质论是陈柱散文体系的基础。在他看来,治化学术是散文的内质,文字表达形式是散文的外式,两者是体用关系。他在《中国散文史序》中说:“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1] (p.1),“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1](p.2)治化、学术是陈柱从文学角度对秦以前时代的认识,时间分别对应上古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陈柱认为,治化、学术时代奠定了后世文学的规范,因此,他以治化、学术论定散文,以及文学的内质,以此为基础判定文学的价值。“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2](pp.3-4)他认为,文章是治化、学术的文字表达形式,是依附于治化学术这样的内质的。
陈柱关于文质的观点与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文”的本义是“文饰”,文学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文饰:“盖文之为义,不外文饰,如上图天文地文,此天地之文饰也。自人文以降,重乎人事,礼乐行政一切文武之事,人事之有文饰者,故谓之文。就文武论,文教之事,尤其有文饰者也,故离武而谓之文。自兹以降,至于载籍,文饰之文,其文饰愈严,其称文亦愈严。文集之文为文人专尚文饰之作,比于其他典籍,文饰尤甚,故比较而又专称为文。”[3] (p.181)在他看来,文学与其他知识一样,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文学的内质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将认知用文字方式表达出来则构成了文学的外式。后来文学从广义的文饰中独立出来,渐渐固定为文字形式,进而被限定为文人的作品,但究其本原,依旧是以治化、学术等为内质,文字形式为外式。
首先,陈柱认为,散文的内质对外质具有决定作用。从文学的发源看,六经是圣贤治化之文,治化的内质发乎文字,成为后世文学的源头:“后世文体,皆原于六经,而《尚书》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2](p.5)可见,散文在发生之初,文史尚未分立,只是如实记录圣人治化的文字,作为外式的形式因素完全是由表达内质的需要而选择的:“盖三代之世,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2](p.4)
陈柱认为,作品的成就和价值主要是由内质决定的。陈柱指出,六艺是人文的开始,记载的是圣贤的治化之功,布达治化的崇高内质使其成为后世文学的源头,奠定了人文包括文学的规范。他将秦汉之前的散文作为最高标准和后世的取法对象,在论述具体作品时也更注重对内质的评价。他在论述《禹贡》一文时,以治水的功绩论定文字的价值:“此禹勤苦之精神,牺牲一己之幸福,以求国家与民族之安全,其功绩最为伟大,故《禹贡》一篇,遂为千古最伟大之文章焉。”[2](p.16)他论孔子时认为,孔子的《春秋》成就最高,不是因为文辞多么出色,而是因为该著作是正名之作,最重攘夷狄与大复仇之义。而后世文天祥、岳飞等人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也因为凸显了爱国情怀,得到他的高度评价。他论两汉散文,认为与专门为文的辞赋家相比,奏疏的成绩因其政教功用而更胜一筹:“两汉之世,专欲为文人者惟辞赋家耳,若著散文者则以奏疏为最工,此则以政教为本,而非专欲为文者也。”[2](p.149)他还称道长于赋体的陆机所作《闲居赋序》《吊魏武帝文序》两文,认为文章取法《史记》,语言上虽然没有大量的铺陈,比较内敛,但在情绪表达上则相当饱满。他论韩愈的散文,认为昌黎文章内质与外式相互契合而成就最高:“皆理足辞充,沛然莫御,故语不必求奇,字不必求险,而文义深粹,自为杰作,所谓诚于中形于外者也;此自孟子得来,韩文此类于文为最高。”[2](p.203)论王安石文以经国之心迹而实现了文章之美:“荆公之文,则纯乎大儒经国之言,古来言治道之奏疏,此其最美者也”[4]。可见,陈柱选取和论述对象时往往以作品的内质作为标准,并以其为主要标准衡量文学价值。
内质既然起到决定作用,则散文创作中选择什么样的外式就应依据内质的表达需要而定,即做到体用相应。他论沈约的三篇散文成功之处在于根据表达需要选择了合适的外式:“《难神灭论》纯乎笔也;《弹芭蕉文》,纯乎文者也;《谢灵运传论》介于文与笔之间者也。《难神灭论》专主乎理胜,言贵精刻,无取乎华辞,故宜乎笔也;《弹甘蕉文》乃寓意抒情之作,味贵深长,不宜过于质直,故宜乎文也;至于《谢灵运传》意在论文,直抒胸臆,故贵乎文笔之间也。六朝文人,明于文章之体用如此,岂可以宗师唐宋古文之故,而遂尽斥六朝文为靡丽哉?”[1](p.191)进而澄清在靡丽之风盛行的六朝文学中,文人明晰文章体用,依据内质表达需要安排外式之浓淡,并不一味崇尚华丽。在他看来那些不刻意注重文体、技巧等文学规范,内质自然外化的文章成就最高。比如上古之文:“天地万物之情,非有虚淡而无华丽,非有华丽而无虚淡,则古圣人之文,又岂能若有或无于其间哉?”[5]他肯定老子之文也缘于此:“《老子》全书对偶最多,此岂有意作对仗哉?以其学理本如此而。”[2](p.30)他对后世帖学家散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贴学家不热衷于追逐人工之巧,“书者随意写之,作者随意出之,原不期人之刻之也;故其字与文一任天而行,极自然之致,与钟鼎石刻之文学家适极端相反”[2](pp.172-173)。他称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事文采味自隽永”[1](p.177);《十七帖》“绝不修饰,而味之隽永,乃古今两无” [2](p.175)。
当然,陈柱也注意到了相同的内质,也存在着艺术差异。他指出:“古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治文,记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最工者,莫如《甘誓》。”[2](p.6)决定文学作品艺术差异的,是写作者能否用文学的思维去观照写作对象。他在论《轮人》一篇时指出:“此记制轮之事,为最机械、最无情之事,而写出工人之为,欲其器之工之情,跃跃如见。可见题材有文学情绪与否,实视作文者主观而异。”[2](p.24)作者的文学修养也是滋养内质的手段,因此外式如何,最终还是由内质决定,而且他散文研究的精力也主要放在对内质的讨论上。
其次,陈柱关于内质与外式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内质是人对世界的认知。从时代发展和现实创作看,内质不但包括圣人布达治化的功德、学术思想,性灵才思、情、气、创作者的品性修养和道德学问等,能够涵养内质的诸多因素他都非常重视。陈柱都将之视为作品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与音韵辞藻等作品的外式相比,内质充盈才是根本,外式才会有所附丽。
春秋战国及其以前,以治化与学术为内质,这是先秦时代所独有的文化资源。之后,效仿古圣先贤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学问识见等都成为后世治化学术内质的流脉。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不同的内质,如认为要想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以文道贯,才能有所成就,反之则欲工文而不达:“作者固当于神求之,不当于貌求之。而论文者亦当以神取之,不当以貌论之也。古圣贤之文章,惟道之传……西汉以后,学者竞相为文,而不知为文之本” [6];他还认为“作文最重才思……然古人有患才多之说,则质于不立之故,正才小之过也”[4]。他在《与吕日侔论学书》中说:“若夫诗文则道德学问之发于文字者而已。未有道德学问充于内,而其诗文不工者也。”他提出只有努力学习古代圣贤的言行,躬行圣人之道,去鄙除陋,方能有较大的成就:“学者不欲大成则已,苟欲大成,则先要立志高尚,而继之以博学。”[7]学识对文章也有很大影响,他认为归有光文因志识缺陷难有成就:“震川之于文,亦不过如昌黎韩子所谓‘蕲胜于人,而取于人者尔。其志即小,其识亦卑,则其文又乌足以有闳奇伟力之观哉?”[8]( p.42)又论人品影响文品:“夫文之有品,则必以其人品之高下为极则”[9]。可见,他在评定散文价值时,以内质为主,但并不拘泥于一种,能够增加创作者和文章内涵的品质,都是作文的需要。相反只专著字句辞藻,则是舍本逐末之举,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圣人之道废而不讲,惟互相模拟,以浮靡相高,万首同声,千篇一意。”[6]
从历史上看,“文”与“质”是我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对重要概念。《论语》中有“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的说法,首次对举了“文”与“质”,提出文质中和之说。虽然道家、墨家等从自己的学术系统出发对文与质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流传和影响较大的还是儒家致中和的文质观。此论经由两汉至于六朝,演变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中唐以后,孔子的文质观逐渐地淡出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至于清代,章学诚提出文生于质,重提文质的关系,近代章太炎、唐文治等都曾经用文与质论文,但均未形成相应的体系。受章太炎、唐文治影响,陈柱对文质论进行了新的理解和应用,将文质关系作为考察散文性质、分类以及散文史的基础。陈柱关于散文内质与外式的论断,是他用文质论研究散文的结果。其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并没有超出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范围,不过更加系统深入。他对治化、学术、经世、爱国、道德、学问等内质的强调,赋予文学内质更丰富的含义,以之衡量散文的价值,丰富了散文研究的视角。
文质论是陈柱散文理论的出发点。他以文质论为基础梳理散文史,衡定散文价值时,着重强调内质的决定作用。当然,他也注意到了创作者的文学造诣对外式的作用,论及散文的形式美。他在《讲陆士衡文赋自记》《文章说》《文心雕龙增注序例》等文中详细论述了文章的口耳心目之美、声韵辞藻之美。但形式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没有充盈的内质,外式之美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
与此同时,陈柱对散文内质的强调也具有救治时弊与文弊的现实意义,与近代以来文学新民,立人等思想有相通之处。当时之世,重科学轻国学,崇知识忽道德,陈柱认为为文是培养志向,灌输道德的很好的途径:“为今之计,最宜乎讲授国文之时,特为注重于道德之发挥,使学生咸了然于道德 ,于国家盛衰,人生安危有极大之关系。”[10](p.49)他认为:“学作文者,当有责任心也。人之求学在乎立人立己,达己达人。”[10](p.39)可见,陈柱对散文的认识是坚守旧学的海归学人欲以经史矫正时弊的学术选择,包含一定的济世意图。
二、尝试“文言”与“质言”的文章分类
陈柱试图将文章分为文言和质言两类:崇尚语言文华的作品为文言;崇尚言辞质朴的作品为质言。他说:“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与无韵文二种。”[1](pp.2-3)在他的散文理论框架之下,除了诗歌之外,几乎有的文字作品都可归于文言或质言,之后再按照有韵和无韵继续划分子类。
陈柱提出文言和质言之分,缘于他不满传统的文体分类方式,认为此前以骈文与散文、文与笔来划分文类的做法不够科学。前者注重的是句式上奇偶的变化,后者注重的是音韵上的划分。在他看来,无论句式还是音韵,都只是形式上的差异,不能说明文类之间质的区别。在他之前,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即以文与质来区别骈文和散文,“散文尚质,骈文尚文,观骈散之分合,亦可见文质之升降也。”[11](p.186)此说较陈柱《中国散文史》早30年,陈柱文学史中多处引用林著,或是受了林的影响。不过林著是从语言的文华与质朴来区别骈文与散文,陈柱则将文言与质言做了近似于文体的应用。
首先,他先从字义上指出了“骈文”“散文”作为文体的名称是不合理的。陈柱考证“散文”一词最早见于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但应用为文体之名则盛行于清代,是清代骈文家常用的术语。在陈柱看来,“骈”“散”本义分别是骈合与离散,并不能用以对应文学体裁:“盖取其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耶?故有正名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矣。”[2](p.2)
其次,建立在句式奇偶基础上的骈文与散文之分并不科学。他提出骈散、奇偶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自然法则,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尤其是从文学的发展历程上看,最早的作品中并没有骈散区分:“天地万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2](p.3)由此看来,后世历史上长期以来,以骈散区分文体的做法有失妥当。实际创作中,两者往往互相依存,相互影响,很难一而二之。他论公孙龙子之文,“最为明辩而瘦削,五篇之文绝无华辞,然偶遇语却甚不少,可见无纯粹散而不骈之散文也。”[2](p.75)他论汉代散文受辞赋影响而形式华丽:“西汉文章之盛,而文质得中也。其所以如此者,盖不特辞赋为汉文之特色,为受《楚辞》之影响而已;即其书疏等散文,亦莫不渐受辞赋之影响,而日趋于富丽,如贾生司马相如之徒之所为也。”[2](p.100)
他认为将骈、散作为文体来静态的划分文学作品,不如将骈文与散文作为创作倾向而动态讨论文学发展过程中两者的相互角胜。他将文学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渐盛时代,六朝初唐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 。骈文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以至于四六专家,八股时代,凡为散文骈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响。”[1](p.1)
此外,陈柱认为,以音韵为标准的文笔之分,也缺乏足够的有效性。相对于更加华丽的有韵之文,无韵的文字被称为笔。在他看来,以有韵与无韵来区别文体,显然不够精准。他分析了钟鼎家文与周秦诸子之文,认为并不能因为用韵就将其归入韵文,“此等文或有韵或无韵,然其体仍当属散文,不能以其有用韵质语句遂谓其非散文,犹周秦诸子之文,亦时有韵语,而不得以其为韵文也。”[2](p.89)而且韵文之中,实则包括很多文体,如诗、赋、骈文等。倘若在实际运用时把文、笔作为文体概念将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当时所谓文,犹今日所谓诗赋也,当时所谓笔,犹后人所谓文也。广义言之,当时之所谓文者,犹后世所谓诗赋骈文也;当时所谓笔者,犹后世所谓散文也。”[2](p.169)
陈柱之前,章太炎曾经有文言与质言的提法,用以区分文与质的离合,“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烈。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12](p.215)章太炎认为,文与质是对立的,文辞害质,与陈柱文与质互为体用的观点不同。而且陈柱提出的文言和质言是从文类划分的意义上来说的,希望以之代替此前的文章分类,这也是陈柱散文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他曾经以文质来区别散文创作流派。在论及晋代至南北朝散文时,即以文华与质朴将其划分为藻丽派、帖学派、自然派、论难派、写景派,这种命名创作流派的方式明显来自于文质对称的文类观念。
遗憾的是,陈柱对文言与质言之分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述。至于文言和质言到底包含哪些当时的文体,他的《中国散文史》及其他著述中均未见继续阐述。在他的散文研究专著《中国散文史》中,从书名到具体论述,都没有使用文言和质言的概念,而是因循时俗,仍然沿用散文、古文等已有的概念:“吾今于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宜,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前括。”[2](p.3)从他散文史涉及研究对象看,文言与质言所共同构建起来的作品不全然是文学作品,而是广涉经史子集,已经超过了当前的散文文体范围。从他的编纂实践看,他的文集《守玄阁文稿选》《待焚文稿》等也仍然沿用传统的划分方式。总体看来,陈柱提出的文言与质言之说只是初步的理论探讨,且用文言和质言来划分文体,实际操作中显然也失于笼统。
民国以来,或参照西方的价值体系,或结合新近的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学进行重新书写与评定的做法蔚然成风。关于散文文体的探讨,郑振铎曾在1927年编辑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刊集中编发了多篇讨论文章,汇聚了有关散文文体意见。有陈衍《散体文正名》、严既澄《韵文与散体文》、唐钺《诗与诗体》等。另有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中国文学概论》、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等专著都涉及散文文体的讨论。整体来看,大家对骈文、散文的划分方式并不完全认同,但却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仍然延续骈文与散文的分类习惯。陈柱从文质论出发,提出用文言与质言代替骈文与散文的分类,显然是文体讨论中一个具有探索意义的声音,值得关注。
三、“体尊”与“质衰”的散文史观
基于文质论为核心的散文理论,陈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文史观。他认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是一个“体尊质衰”的过程。“体尊”是指文学逐渐自觉,后世越来越看重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注重文学的技巧,文学的地位越加尊崇,外式愈加发达。“质衰”是指文学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人们专注于文学和技艺,忽略了内质的修养,本末倒置造成了文学徒有其表。他说:“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扑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兹以往,士人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倡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学术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合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1](p.2)陈柱认为,文学之质本于治化、学术,秦以前正因没有专门的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文学的外式才能自然而然地由内质生发而出,成就了无法超越的繁盛时代。及至后世,文学渐渐自觉、独立,成为专门的学科而备受重视,技艺日益精巧,然而,却越来越偏离内质,舍本逐末,最终体尊质衰。
从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看,陈柱认为,文学尊体的过程与学术进化、学科细化有关。文学本是对世界的文饰,随着学术的日益进化,学术分科愈加精严,于是出现了文笔之分,文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且范围日渐狭窄。他说:“文集之文为文人专尚文饰之作,比于其他载籍,文饰尤甚。故比较而又专称为文,然文集之文有韵无韵之别,有韵之文,文饰尤甚,故以无韵为笔,有韵为文,又岂得谓之谬论。再进一步而言,则有韵之中,有骈文与诗乐之别,诗之音韵,又比骈文为文饰,故文之一字又可专属于诗,亦岂过言也哉?是故以人类之进化而论,文明愈进,学术愈专,而分科亦愈严,则文学之范围惟诗而已。”[3](pp.181-182)
从文学发展的内部看,陈柱认为,体尊质衰是文质分离的结果,散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过于重视自身的独立性,精于“文学外式”的修饰,忽略了内质的修养而变得空疏。他认为,为文要取法两汉以前,去除以文为文的观念:“今文自魏晋以降,多以文为文,而不以道为文,宜返乎两汉以前之以道为文,以政教为文也。就外式而言,则今之魏晋以来,多拘声病,尚古典,多模拟,皆文之桎梏,宜返于两汉以前之不拘声病,不尚古典,不相模拟,乃得自由也。”[13]而后世之文在以文为尊的思路之下,往往忽略了文学的内质修炼,在创作中只因袭了古人的相貌而遗失了精神,加剧了体尊质衰的历史:“拟似者固非古人之大病,病在似其貌而遗其神,袭其意而规其貌。如魏晋以后之七。崔蔡以后之难,斯足贱耳。”[6]
体尊质衰的史观在陈柱的散文研究中,体现为明显的尊古倾向。如陈柱认为,六经是后世文体的源头,尤其是《尚书》,开创了记言和记事两种文体。此外,孔老之文开后世骈文先河,《左传》开后世史家先河,其他诸子之文系后世集部所本。这不仅仅是从文体而言,具体写作方法上这些不能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品也是后世的楷模。如《尚书》、金石文是后世史书作法的样本,影响了后世的散文义法。而抒情与叙事散文,则《庄子》与《史记》最成功:“自来以散文而最善言情者,于战代有庄周,言哲理而长于情韵;于汉有司马迁,述史事而擅于风神。自此而外,多莫能逮。”[2](p.258)
同时陈柱还特别重视散文创作的源流传承,常常以尊体之前的先秦文学为范本,对散文进行追源溯流的批评。如他认为:“孟子之文富有古文化,为后世之古文家之祖;荀卿之文富有骈文化,为后世骈文家之祖。韩昌黎之抑扬顿挫学孟子,而句奇语重则法荀卿。”[2](p.64)论诸子之文的流传,“汉之董仲舒刘向,儒家兼阴阳家之文也。法家兼兵家之文也。司马谈迁父子,道家兼史家之文也。徐乐、晁错、赵充国、严安,纵横家之文也。杨王孙,墨家之文也。淮南子,杂家之文也。”[2](p.45)又如论曹植的寓言《籍田说》:“此寓言之文,上承庄列,而秦汉已少见之。后世古文家,韩柳亦尝为之,柳宗元所为,尤与子建为近。”[2](p.156)论柳宗元散文“子厚之文,论辩体多从韩非得来”[2](p.211)。论樊宗师文《绛守居园池记》:“此等文体盖上法古钟鼎文字,而下法班固《书秦始皇本纪后》者也。”[2](p.234)论白居易文“乐天之文盖学陶渊明,其《醉吟先生传》即拟《五柳先生传》而能扩充之者也”[2](p.236)。论王安石文“盖以礼家而兼法家之精神也”[2](p.248)。论民族主义文学“后世民族主义之文学,盖莫不本于《春秋》。”[2](pp.166-277)他还在《论作文模拟变化之法》《韩文研究法》《证韩篇》等文中,分析韩愈的文章如何从古代的作品中取法借鉴,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承认中国散文发展体尊质衰历史的同时,陈柱也肯定后世之文有超越前世之文的可能,但这种超越并不是文学技巧上的成功,而是重视内质的结果。除去上文中强调滋养文章内质的途径之外,他还结合时代发展提出振兴散文的方案:即要立足于当前的时代,广泛吸收新时代所独有的新精神,新理论,新名词,让作品充盈时代气息,创造出新时代之文学。他在《与叶长卿教授论文书》中说:“居今之世,为今之人,则今日之事物,皆当以入吾之文。则今日之新名词与夫新造之字,其不乖六书之义例者,皆不当避也。”[14]在《答某前辈论文书》中说:“辅之小学,参之以科学,斯足超乎众流耳。”[5]主张同时吸收传统文学和西方的科学观念,创造出不同于古人的新文学。
虽然陈柱所探讨和创作的仍旧是文言文,但他努力创造新时代文学的观念则顺应了新文学运动的潮流。主张融汇中西以推进文学发展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如叶恭绰所言:“自民国以后,真是新建设时期及国难严重的时期,许多人提倡我们应仿效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而建立一种中华民国的新文艺。”[15] (p.110)叶长卿也从严复的作文经历中,看到了西方文化对散文创作的促进:“严又陵先生初习文辞未能通达,后居英伦治逻辑学文境大进。”[16]可以说,在以白话文为语言介质的新文学之外,陈柱等人也在努力寻求古文的变革,虽然他们的理论研究多于创作,但也代表了坚持以文言写作的旧式文人在新旧交替时代的文学传承与变革的观念,对于全面客观地书写民国时段文学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所论,陈柱的散文研究体系以“文质论”为基础,他的文类划分方式、体尊质衰的发展史观等诸多理念都不同于现代以来从审美、文学特质等方面认知文学的观点。他没有否认文学从经、史、子部中析出进而确立了独立的身份,不断完善自身的历史趋势;他也没有单独关注文学独立于内质的之外的所谓“外式”及其发展规律,而是将其容纳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作了淡化处理。
由于西方学科分类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引进,陈柱在书写第一部中国散文史及散文研究的有关文章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梳理、解读、评估中国散文的本质、构成、起源和发展历史等问题。他在诸多散文研究著述中对上述问题均有所涉及,但有些尚未深入讨论。作为在经史子集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且多有成就的学者,陈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融汇经史子集的广阔理论视野来审视 、梳理中国散文发展的历程。他在文质论的基础上,对散文性质与分类予以全新的理论探讨,将文质论推演到了文类范畴,并以文质论为标准在中国散文史中确立并蕴含了体尊质衰的散文史观。此于其所处的时代已是难能可贵的开拓,他的成果对于文学史、史学史和散文研究史也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参 考 文 献]
[1]陈柱.中国散文史:序言[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陈柱.中国散文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中国学术讨论集(二)[M]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8.
[4]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J].学术世界,1935(1).
[5]陈柱.答某前辈论文书[J].学术世界,1935(1).
[6]陈柱.答南洋公学母校校长唐蔚芝先生论文书[J].学术世界,1935(1).
[7]陈柱.与吕日侔论学书[J].学术世界,1936(2).
[8]陈柱.书曾文正公集· 待焚文稿:卷五[M] .十万卷楼丛书,1933.
[9]陈柱.与友人论文书[J].学术世界,1935(1).
[10]陈柱.国学教学论[M].上海:中国学术讨论社,1926.
[11]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上海:武林谋新室,1910.
[12]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3]陈柱.四十年来吾国文学之略谈[J].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1936.
[14]陈柱.与叶长卿论文书[J].学术世界,1935(1).
[15]叶恭绰.遐庵谈艺录[M].上海:太平书局,1961.
[16] 叶长卿.与陈柱尊教授论文书[J].学术世界,1937(2).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