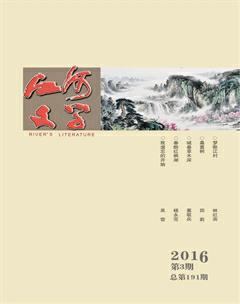桑葚树
田莉
一
我走进院子里时,父亲正在砍伐那棵桑葚树。他敞开那件穿了几年的旧棉袄,吃力地弯着腰,抡起斧子,砰砰地向树干剁去。初冬的树早已掉光了叶子,土地僵硬,树干也僵硬。他不要命地剁着它,树剧烈摇晃着,就要砍断了,死了。我的心里阵阵疼痛,我从后面抱住父亲,我知道这是徒然,就放肆地哭起来。
“哭,你就知道哭!还不是它害了我们这么多年?还不是它让你哭了这么多年?我早就想砍它了,我怎么早没想到砍它呢?我真后悔……”父亲气愤地呵斥我。
我松开了抱住他的手,我无法阻止父亲。他一说话,我就止住了哭声,我不敢哭得太放肆。这些年,我的确哭得太多了。我擦擦眼泪,从他手里接过斧头,狠狠朝树劈去。每劈一下,我的泪水就涌出来一些,它们掩盖在斧劈声里,仓惶坠落。显然我比父亲有力气,一会儿树就倒下了,发出生硬的脆响,枝条们断了,似乎也划破了小院的上空。
父亲长舒一口气,抹了抹额头,说:“我砍了好几天了,斧子再快,没有几天功夫,也是砍不倒的。”
是啊,这棵树二十年了,实在太高大了。它每年结出紫红的桑葚,我对它有特殊的情感。小学毕业后,我陪父亲种地,十五岁后就去打工了。
爷爷是嗑巴嘴,外号“结巴老八”。他常趁家里人外出干活时欺负我娘,我两三岁,娘在家看我。晚上我娘会悄悄把白天的事告诉父亲,他却不敢问爷爷。
是的,我恨他们,无知的父亲,狠毒的爷爷。
家中祸不单行,先是爷爷打死了我娘;后是我大娘病死了,不久大爷也死了;我堂姐红燕失联了。
有个风水先生指点父亲,说你院中不该栽桑,否则丧事不断。
二
我扔下斧头,我俩一屁股坐地上,父亲重重叹了口气,说:“这些年,要不是你爱吃桑葚,早该下手了。这不是迷信,后来我想起那人说的话,有道理。我们家破败离散,是风水不好。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这两年我的身体也不好,经常吃药,我帮不上你。就担心你以后怎么娶个媳妇……”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语调越发苍凉,使我心底也徒生出不属于青春的沧桑。我抬头看天,一平如展,头上连只鸟雀也没飞过。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哪是为了吃葚子?是怀念娘。我是围着树长大的。
父亲把头埋进膝间,他觉得我过于沉默了,很快又扭过头问我最近有什么收获,是怎么想的。我尽量装出淡定平和的样子,看他一脸期待,又一脸沮丧,就胡乱搪塞他说在外还算可以,只是没有技术,赚钱就少,身体倒是没有毛病。
“我是说你这么大了,谈对象了没?”他沙哑着嗓子,打断我。
一小股烟草味钻入我的鼻孔。我一下子就寻到了南墙根下的一捆干烟叶。种烟,还是我娘教他的,在我记忆中她只种过一回。
想起去年葚子熟了,我不在家,父亲摘下来晒干。年底我回来了,他拿出来给我泡水喝,他没看见我的眼泪也落进水里了。
亲人之间,最能戳到人的痛处,这正是我的忧伤。像我这般穷苦,找个女人过日子,谈何容易?但他这么问了,我也不愿年迈的父亲听到更多坏消息,娘死后,他极失落。爷爷死后,他有类似于精神分裂和抑郁的症状。我只有撒谎说工厂里有个女孩对我有意思,我对她没感觉,以后再说吧。
“该抓住机会的不能放过!趁年轻有力气,多挣些钱,这几年地承包了,我种不动了,以后也怕帮不上你。怎么我也得攒一点钱。我可不愿意你到四十岁还是光棍儿,别跟我一样。”
父亲气愤起来,咳嗽气喘。使劲抓起一把土,投向一只觅食的母鸡,吓得它咕咕叫着跑开,扑棱一下飞到墙上去了。接着又跳上屋顶,奇怪地看着我俩。
这个院子,积怨太深,阴气太重。亲情?这个概念于我来说很虚幻。如今,院里只剩下两个同样孤独的男人,几只自己刨食的鸡。我的仇恨,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减少。
三
这让我想起以前。娘喂了几只鸡,一只就是这样的芦花鸡。在院子的角落有个鸡窝,它们白天出来觅食,下午或傍晚会“咯咯答”地叫唤着。娘就扔一把谷子米给下蛋的鸡,我捧着一只温热的小鸡蛋,让娘用炒勺给我炒了吃。那个好吃啊,香咸适口,现在想到我的口水就下来了。一个勺子,仅炒一个蛋,娘看着我蛋白蛋黄都吃了,就开心地笑。
这样开心的时间屈指可数,爷爷就像生存在我们中间的敌人,每天碎碎念,有没完没了找不完的茬。
他一棒子打死我娘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无助、恐惧、绝望缠绕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原谅他?
我十三岁时,他才死。他怎么活了那么久?
三岁的我,由大娘管着,父亲重新做回光棍的日子。我五岁时,大娘死于急性病,大爷也成了一个人。他的女儿红燕十八岁了,跟镇子上一个男人好了。大爷不同意,说红燕太小,过两年要明媒正娶才行。不过最终男人还是拐跑了她,大爷气不过,不久也撒手归去。
红燕自此失联,大爷一家死的死,走的走,空了院落。
没有女人的家就散了,我又回到自己家,跟爷爷跟父亲在一起。大娘死后,我吃不饱穿不暖,破衣烂衫,泥孩子一个。
我在背地里骂他“老不死的”。我骂了好几年,他还没死。那一年,我都十岁了,故意让父亲听见我骂。
父亲要打我,他一脚把我踢趴下了,我吃了一嘴土,十指抠进土里。我发誓以后有机会杀了爷爷。
我哭起来,大叫着:“老不死的,早晚宰了你!”
父亲说:“有完没完?人各有命。”
“叫我怎么原谅他?我不会的!”我大叫着爬起来,怒视他,“娘的死,你也有责任!你从不关心她!你没有良心,爷爷没有人性。”
“畜牲!”他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嘴角渗血。
我跑了,我跑到镇子上,那天正是个集市。我在一个包子铺前驻足,松香的包子味,让我的肚子不知好歹地叫起来。我的嘴干了,没有唾沫,我眼馋那蒸笼里的包子,怎么才能吃上一个呢?
我不远不近地蹲在附近,若无其事地用手在地上划拉着,这样我空空的胃还好受点儿。我决定无限期地蹲下去,哪怕饿死了,正好去见九泉下的娘。
集市上的人逐渐稀疏,嘈杂声陆续散去,我的腿麻了,没有力气继续蹲着。我躺下,但眼睛不敢闭上,一个个人影晃过我左右,真希望拿着零食的人们施舍一点给我,可是没有。我眼巴巴地看他们走远了,不远处有只狗,坐直身子盯着我。它在想什么?它伸出了舌头,张嘴打个哈欠,收回舌头。我猜不出它的动机,我在它眼里就是个黑白图像,听说街上的狗很凶,像街上的人一样,有比村里高高在上的感觉。人们把“镇上”称为“街上”或“乡里”,村里要高看镇上的人,因为是镇。
现在这只狗会不会看我不顺眼,突地跑来咬我,或者把我当小叫花子吃了呢?我不敢动,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会招来它的撕咬。
“松松,松松……起来——”忽然有人唤我的名字。
“我是红燕姐姐,想想。你今年十岁了,长大了,可我还认得你。”
堂姐?她不是跟镇子上一个男人私奔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都快不记得了。我娘死了,大爷也死了。”
她没回答我。
我声音低下去,坏消息不能大声说。
她没哭,反而笑了笑,说:“我在对面看着你,越看越像你。喏——走得再远,总要回来的不是?哦,对了,你没吃东西吧?我去买包子。你跟我回家。”
那只狗跑向她,像只肥硕的黑绵羊。它摇摇尾巴,她拍拍它的头,丢给它一只刚买的包子。很奇怪,它并未冲我不怀好意地吼。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回来一阵子了,但不能回村里,叫人说闲话。以后我还会走的。”
那是我唯一一次遇见她,也是最后一次。屋子里就我俩。
她给我洗了手洗了脸,又给我找了套小孩衣服,叫我换上。说是别人送她的,正好你穿着合适。
她摇头叹息,倒杯水给我。又说:“一家人好好的就散了,都不在了,回去干嘛呢?清明节得上坟了,不然,你大娘大爷地下有知,也不会原谅我……有什么意思呢?”
她伏在我对面的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抽泣起来。她哭了,我心酸得很,一下子觉得吃饱了。
不久,她抬头问我:“哦,你跑出来,家里知道吗?”
“家里?哪有家啊。你是说爷爷和我爹吗?他们不管我。”
“你可要好好学习呀!起码你把村小学读完,不然,外出打工,连个字也不认得……”
我点了点头。
走的时候,堂姐送了我一段路。在路上,我问她当年为什么爷爷老打我娘?她说爷爷脾气不好,你娘并不伶俐乖巧,但我也不很清楚,我要看见,早就去拉住他了。
她欲言又止,停下,说:“我告诉你个秘密,不过你不能回家问你父亲。这是真的,你娘,是爷爷给你爹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每年计生站查户口,你娘都藏到地窖里,她没有户口。那年你爹四十岁。他把队上的机磨房收购了,给全村磨各种面粉,邻村的也来。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忙活加工面粉。他有的是活干,日子也不错。
磨房在前院,桑葚树在后院。当时家里还景气。
买了你娘,你爹起初拿着当个宝,走哪里带到哪里。村里人看得清楚,说老八的老二又抱着小媳妇去树林里玩了,说老二载着她去赶集了,又说她跟着老二去麦田浇水了。好不容易得个女人,怎么舍得打她?
估计你娘精神受了刺激。她从未想过要逃跑。她知道家在四川江油,在长江对岸,很穷。有个弟弟,还有个蹲监狱的老公。刚来不久,你娘生下一个孩子,死了。之后,有了你,她不想逃走,因为你……”
我惊愕地听她说我娘的经历。然后她塞我手里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名和人名:四川江油中坝镇,王秀兰。
她再三叮嘱我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你姥姥家的地址,你长大了要去找她,跟她说说你娘的遭遇。你投奔你姥姥家吧,起码,你还有个舅舅。
这真是个天大的秘密。父亲从没说起过这个,是的,他无法交待娘的死。
我还得回到那个一刻也不想呆的破家。一个老男人,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小男孩。
在村口,遇上我爷爷。他追问我:“松松,你哪去啦?怎怎怎,怎么也不说一下?急死我了。你你你——站住!”
我在心里骂:“急死你才好。”
我在前面跑,他是追不上了。老了还叫人厌烦。
四
“人是自由的,人是不能逼的……你以为现今还能跟以前一样?还能买个媳妇?”我不得不反驳他。
如仇人的亲人,分裂着我的情志。我也有淡淡的抑郁,或许吧。有时我会发呆,呆呆地看地,呆呆地望天。
他沉默着,突然抬头驳斥我:“女人嘛,上了床,生了孩子,绊住她过日子,还不都是那回事儿?自古以来,人性是一样的!”
父亲继续着他的理论。
可能,村里那几个买来的女人,智商大多存在问题。不然,哪会逆来顺受?有的知道跑,但是瞎跑,不远就被追回来了。从此就被更紧地看管,甚至用脚链拴住。比如湖北来的女人,成了“小迷糊”媳妇。他并不真“迷糊”,把女人看得可紧,只一次逃跑的动机,就把她拴住。平时他下地干活,把她链在门廊下,久了,就有点疯了。人们尽量不路过他家的门廊,因为见了人她就胡说八道,说上不了台面的话。大姑娘羞红了脸跑开,男人们逗她玩儿。她会告诉他们夜里“小迷糊”的表现,怎么怎么厉害,怎么差点折腾死她。他们不怀好意的欲望被挑逗起来,叫她脱裤子看看,她就真脱。这事儿很快被“小迷糊”知道了,他打了她,就把她锁进屋里,再见不到人了。
再比如四川来的“秃子”媳妇,外号叫“秃子”的男人又丑又穷,家里长辈凑钱买了个四川女的,她自己说才十八岁,外出务工被骗。辗转几次被拐至这里,她说既然来了,就安心过日子。平日里很勤快,对男人也体贴入微,秃子觉得她很听话,就放了心。结果有一天深夜她趁上厕所出逃了,当然没跑多远,因为人生地不熟,她只跑到镇子上,还没截到一辆车,就被秃子一伙人追上了。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哭叫,惊醒了半夜中的村庄梦。狗吠了,鸡鸣了,牛羊也骚动了。
秃子把她拽倒在地,揪着头发扇她耳光,边扇边问:“还跑吗?”
女人学着当地话,答:“不跑了,再也不跑了!我发誓!你别打了……”
男人住手,说再跑就打断你的腿。村里人听了哈哈一笑,都各回各家了。
那时我已经没有娘了,但我也爱看热闹,喜欢女人被捉回来,以喜剧收场。
此时父亲会唤我回家,捧一把桑葚,哄我不乱跑。他吓我说:“外面有偷小孩的。别乱跑啊。”
五
那天,爷爷又打我娘了。快中午了,村里人都去镇上赶集了,我父亲也去了。
我娘跑到后院,我抱着娘的腿哭,爷爷推开我。我想抢他手中的扫把,他把我扔到鸡窝上。我坐漏了下蛋的窝,坐破一只蛋。鸡们大叫着逃离现场,父亲又不在家。我看见,爷爷凶神恶煞的样子,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扔掉扫把,又抡起一把铁锨,拍在我娘头上,我娘依在桑葚树上,顺着树干滑下,腿抽搐几下就不动了。然后他骂骂咧咧地把家什搁在墙根下,余气未消似地出了门。
我趴在娘身上大哭,她用尽全身力气,只说了一个字:“去……”就不行了。
这之前,隐约记得,娘在夜里也向父亲告诉过爷爷在家怎么对她。因为父亲钻进娘被窝的时候,她说了她很疼,腰有於青,屁股紫红,阴部也被烧火棍戳了。
这个记忆,对我很深,应当不是我的想象。父亲不追究爷爷的责任,这是他的罪过,他虽没有直接虐待我娘,却也是不管不问,是帮凶。
从此,磨房也关闭了,再没有人来加工面粉。后来那些机器父亲卖掉了,把前后院通开,改成一个大院子。桑葚树长得很欢,扑扑棱棱几乎要占满整个庭院。家里冷清了,再也没有推着车子加工面粉的人。
我的恨太多太长,我无处发泄的恨啊。无时无刻不叫我觉得:我活着,是多余的。我既无法杀了爷爷,又无法害了父亲。
六
冬天的地太冷,但我们把地捂热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聊聊过往。还有,我从堂姐那听来的往事。多少年了,我才长到这么大?
一个“去”字,娘抬起一只手臂,吃力地指着远方,含恨而去。她又想让我去哪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画面愈加清晰。
我没有告诉他们堂姐在街上,她也没来家里,直到爷爷死,也没露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或许她早已不在街上了。
不过现在我可以大胆地和他聊聊堂姐了。我说前几年我见过红燕,她住在街上。
他猛然站起来说:“不可能!她早去东北了,不回来了。”
“就是她。”我不想跟他啰嗦。
“说吧,跟我讲讲我娘,我那时太小。”
父亲坐到树干上。我也拍拍尘土,坐到树干上。我们都觉得这样坐才舒服些,情绪稍有平和。我看到天上的云朵幻化成一堆泪珠,啪嗒啪嗒落在我脚边。
他似乎早有准备,告诉我说:“……红燕说得对,你娘是买来的。她头脑笨,不灵光。你爷爷一棒子打死她,我能怎么办?送他进监狱?这样你娘的身份也暴露了,我也犯法了。谁来管你呢?我们全家都完了。我愿意她活着,再生一个跟你作伴。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有恨,可恨不能化解问题,你还是别恨了。你爱吧,爱你自己,爱我,爱你所爱的人。你的路还长,我老了,不知能否熬得过这个冬天。”
我知道,买来的媳妇是黑户口,没名没姓,谁去追究?村长也偏向自己人。我也不知我们这几个外来女人生的小孩是如何上的户口,但她们却是隐形人。
我荷包里的纸条不知揉烂了多少次,扔过多少就抄写过多少,现在它就在我的贴身内衣里,必要时我马上取出来给他看看。证明他这些年隐瞒的真相,不让我找到娘的娘家。为了寻根,我在四川呆了两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在体会娘的故乡的气息。
我有无数次机会,到当地派出所打听,只要我拿出身份证,问有没有一个叫王秀兰的人,就能找到姥姥家。无论他们愿不愿帮忙找,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意义了。多少年我都想找到娘的娘家,找到娘的来处,就像发誓追到厂子里那个并不喜欢我的女孩一样。是我自作多情地寻找着温暖,最后我才接受我是无根的浮萍这样的现实。我早忘了我娘的模样,她连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徘徊在那个镇子上,每一张都是陌生的脸。
这些,父亲一点也不知道。
七
“你去找找你姥姥家吧,我给你地址……”父亲颤抖着从棉袄里摸出一个小纸片递给我。
“你不要去,不要去。那个地址是假的,电话也是假的。”一个女人突然闯进院子,她就是“秃子”媳妇,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安分得很。
“我一直在墙外偷听你们说话。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她补充说。
真是个意外。
“为什么?”我和父亲同时发问,都错愕了。
“说实话,红燕的地址也是我给的,本来,我是想让松松有个成长的盼头。我跟松松娘家离得不远,这些年我回去过几次,她娘家穷得很,又没钱找闺女,不几年就死去了。在这期间,我见过她娘一次,她抓着我的手,急急问我王秀兰的消息。我不能说实话,她死在异地,她娘会没了盼头。我只好说谎,说帮她寻找,一旦有消息就告知她。可她,没多久就急死了。都怪我,欺上瞒下……你们恨我吧。”
“这是真的吗?”
“真的。劝你别去了,白跑。”
说完她就哭着跑了。
我从衣服里掏出从前的纸条,对比看了两个纸条,父亲的纸条上只是多出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立刻用手机打过去,说已关机。
父亲说:“别听她的。若是假的,她干嘛要告诉我?你该去一趟,不管真假。我老了,不然死也不安心。你在这里多孤单,如果那边好混,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他唯一絮叨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当他说到“死”时,我有点伤感。
我决定明天就回厂子,再干上两个月,本来我就请了一天的假。多积点钱就去那个村庄,不为什么,倒像跟人赌一口气。
父亲又往我包里装干葚子了。他把葚子叶也塞包里,说:“好儿子,这是最后的葚子了,你在外照顾好自己。”
我头一回看到他哭泣得不成样子。头一回拥抱了他。这么亲密的举动对于我们也是头一回。
八
这期间,我多次打那个号码,都是关机。
我才走了一个月,秃子媳妇给我打手机说我父亲暴病死了。这些年,没人愿和父亲来往了。
我回家奔丧,我也没想到我哭得那么凶。原来我心里还是在乎父亲的。可这些年,我没给他买过一件物品,哪怕一支烟。
他给我留了遗嘱,上面说要埋在桑葚树南面,因为你娘也在,她死后没有火化,一直都在树北面。所以,这棵树是不能刨根的。现在村里没有荒地,庄稼地里的坟也被铲平,都种上了粮食。村里再也没有勤劳的农民安心留守着土地,被承包后的田地在别人手里,他们擅自作主,为了多种点儿东西,一个个坟茔的面积也被利用。
父亲的决定是对的,他们留在自家院中,暂时守护着一个别人动不着的地方。
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惊呆了。
我仿佛看见娘给我吃着一把把的桑葚,紫红的甜水溢出嘴角,染了衣服。娘冲着我傻傻地笑,鸟雀也来争吃,云朵也跑到我手中来了。疯长的树,我快搂不过来了,荫翳了后院。
我的脊背麻麻冷。空荡荡的院子,砍倒的树父亲肯定是卖了。秃子一家来帮忙料理父亲的后事,他们还交给我一沓新旧不一的钞票,说是你爹的全部家底儿了。他女人还是说:“忘了吧,我知道你没去。这样好,不去翻旧历……”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我好奇地问她。
“我猜的。去了也找不到,白跑,能咋地?”她的声音软下来,像掉在地上的一颗烂熟的葚子。
我没理会她。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就上路了,我要跟着思路走。
在火车站,我买了去目的地的票,是晚上八点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供我消磨,于是我就给那个心仪的女孩打电话,她不接;发短信,好几条,她也不回。然后我又想起那个重要的号码,再打,通了。我的心砰砰跳得极快。我还没想好怎么说,说什么。
“喂?你是?”一个女人。
“我是松松,我,我找王秀兰。”我只好这么说。
“哦,松松啊,你在哪?”
“火车站,八点开。我要去找姥姥。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名字?”我来不及想什么。
“我是红燕姐。你别来了,真的,没意义了。”没想到她这么说。
“为什么是你接电话?这到底是谁的号?从前你不也是劝我来的吗?”急死我了。
“……你别问了。事实不是这样。我也被卖掉了,可能打过这个电话,以后你也找不到我了,连我自己下一站在哪里也不清楚。实话说吧,你娘,是被你姥姥卖出去的,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我说过,你娘有点傻。旧帐找谁算?你姥姥也不在了……反正,接过这个电话,不知我还能否活着……世界很疯狂,我们太无能为力了。松松,原谅我,我帮不了你……”
她好像哭了,哭得不能再说了。
挂断了。再打,停机。直到检票了,还是停机。我在犹豫,这一切是否是真的?还要不要去?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突然也想放声大哭。我的全身都在燃烧。
九
我还是上车了。觉得一切都是假的,谁的话也不要信,就像父亲说的,最好亲自去一趟。现在我成了个孤儿,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即便前方是火海,我也下了。趁着自己还没疯掉之前,先平静下来睡一觉。我没吃东西,我的胃被一个个疑问塞满了。
听说江油是历史名城,李白的故乡,有李白纪念馆,我打算去看一看。小学的时候,老师说“诗仙”的诗最豪放了。我最喜欢那首《静夜思》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想着将要抵达的远方,怎么也豪放不起来,我是个没有故乡的人。
我睡着了。
火车在夜里,奔跑得很快,它把我带到一个开满鲜花的草原上,我看到了厂子里那个不给我回短信的女孩。
我笑着醒来。听见广播说:旅客您好,下一站列车抵达绵阳,有下车的请提前做好准备。
哦,哦!广元站早过,江油站也刚过。我该怎么办呢?该死的梦!
急得我想尿裤子。于是我就进了厕所。其实我没有尿出来,我反锁了门,砸了小窗户,因为窗户太小,我跳不出去。我又回到座位上。可很快就被乘警带走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搞破坏?
我又哭又笑,说你们把我拘留了吧,关了我吧。我精神出问题了。
其实,我很想打开车厢里的大窗户飞下去的,因为有太多人,我不敢动手。
他们不相信一个真正的疯子会说自己出问题了,最终把我铐起来,说到绵阳站送派出所。
好吧,好吧。这正是我期待的。
责任编辑: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