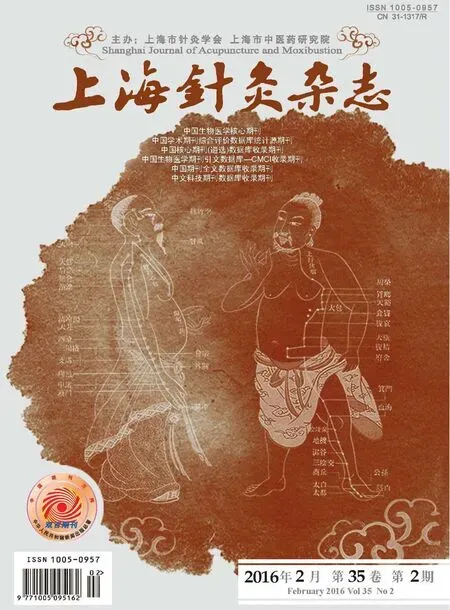靳三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痉挛性偏瘫临床观察
徐世芬,顾金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上海 0007;.上海市奉贤区中医医院,上海 0400)
靳三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痉挛性偏瘫临床观察
徐世芬1,顾金花2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上海 200071;2.上海市奉贤区中医医院,上海 201400)
目的观察靳三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以及单独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患者临床疗效,探讨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最佳方案。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71例患者按简单随机对照的方法分为两组,治疗组(靳三针加康复训练治疗)36例,对照组(康复训练治疗)35例,两组疗程均为28 d。治疗前后应用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NDS)、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疗效评定量表(ADL)、四肢简化Fugl-Meyer运动评分(FMA)及功能综合评定(FCA)进行两组的疗效评价。结果两组治疗后均能不同程度地改善中风后痉挛性偏瘫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痉挛程度、日常活动能力及运动能力评分(P<0.01)。治疗组在上肢FMA评分的改善方面未见明显差异(P>0.05);而在NDS及下肢FMA、ADL、FCA评分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1)。结论靳三针疗法配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痉挛性偏瘫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针刺;中风后遗症;偏瘫;肌痉挛;靳三针疗法;康复训练
[Abstract]Ob 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of Jin’s three-needle acupuncture plus rehabilitation and using rehabilitation alone in treating post-stroke spastic hemiplegia,for seeking the optimal treatment protocol for this problem.M ethod Seventy-oneeligible patients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36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group(intervened by Jin’s three-needle acupuncture plus rehabilitation)and 35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intervened by rehabilitation),28 d as a treatment course in both groups.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Neural Defect Scale(NDS),simplified Fugl-Meyer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FMA),and 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FCA)were adopted for evaluat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Result A fter intervention,the NDS,spastic intensity,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andmotor function were improved in the two groups to different degrees(P<0.0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aring the improvement of FMA(P>0.05);the NDS, FMA,ADL,and FCA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ConclusionJin’s three-needle acupuncture plus rehabilitation can produce a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post-stroke spastic hemiplegia.
[Keywords]Acupuncture;Post-stroke sequelae;Hem iplegia;Muscular spasm;Jin’s three-needle therapy;Rehabilitation
中风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我国脑血管病发病率为120~180/10万,死亡率为60~120/10 万,幸存者中50%~80%留有运动功能障碍[1],且绝大多数患者都遗留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其中中风偏瘫痉挛状态约占80%~90%[2],国外报道为65%[3]。本研究探索了康复疗法及靳三针配合康复疗法治疗该病的疗效及各种疗法的差异,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临床观察中风后痉挛性偏瘫76例,均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或神经内科的住院患者,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分为治疗组(靳三针疗法加康复训练治疗)38例与对照组(康复训练治疗)38例。其中治疗组脱落2例,对照组脱落3例。共71例患者纳入统计,治疗组36例,对照组35例。治疗组中男28例, 女8例;年龄最小42岁,最大75岁,平均(60±10)岁;病程最短15 d,最长90 d,平均(50.39±22.52)d。对照组中男24例,女11例;年龄最小51岁,最大75岁,平均(65±6)岁;病程最短15 d,最长90 d,平均(47.75± 22.63)d。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病灶”的部位及大小经统计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标准采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订的《中风病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试行)[4]。西医诊断参照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5]。肢体瘫痪分级标准参照Brunnstrom六阶段分期标准[6]。
1.3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脑梗死诊断标准;②符合中医中风病诊断标准;③Brunnst romⅢ-Ⅴ期;④脑血管意外发生在颈内动脉系统,经过头部CT或MRI证实;⑤小于两次的中风(包括两次),且发病时间15 d至3个月;⑥年龄40~75岁,性别不限;⑦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NDS)中肢体功能缺损评分累计≥10分;⑧患者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者;⑨知情同意者。
1.4排除标准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逆性神经功能缺损(RIND) 等;②Brunnst romⅠ~Ⅱ期;③经检查证实神经功能缺损由脑肿瘤、脑外伤、脑寄生虫病、心脏病、代谢障碍等疾病引起者,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⑤中风次数≥3次者;⑥合并心、肝、肾、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疾患者。
2 治疗方法
2.1对照组
康复训练方案主要依据卫生部规划教材《康复医学》第3版[7]制定,以达到降低肌张力,抑制痉挛模式,诱发分离运动等康复目标。
疗程28 d,康复治疗每星期5次,休息2 d再继续治疗,共治疗4星期。
2.2治疗组
在以上康复训练治疗的基础上加靳三针疗法。
头针取颞三针;体针取上肢挛三针(极泉、尺泽、内关),下肢挛三针(鼠蹊、阴陵泉、三阴交)。失语加舌三针;口角歪斜加口三针(地仓、迎香、夹承浆);腕关节严重痉挛加腕三针(阳溪、阳池、大陵);踝关节内翻加踝三针(太溪、昆仑、解溪);上下肢痉挛无法伸展加开三针(水沟、涌泉、中冲);指趾浮肿加八邪、八风。肝阳暴亢加太冲(双);风痰阻络或痰热腑实加丰隆(双);气虚血瘀加足三里(双);阴虚风动加太溪(双)。
患者取仰卧位,嘱患者放松,使用0.30 mm×25~50 mm针灸针,75%乙醇棉球皮肤常规消毒后进针。颞三针取患侧,采用快速进出针,快速小捻转间断平补平泻方法。首先垂直刺入皮下,达帽状腱膜下后,以15°角的针刺方向沿皮轻微、快速、不捻转刺入30mm,得气后以180~200次/min频率捻转2 min,分别在进针后第10分钟、第20分钟、第30分钟动留针3次,共留针30 min。上肢挛三针,极泉进针时注意避开腋下动脉直刺入30~35 mm,以上肢抽动为度;尺泽、内关均直刺入15~20 mm,以手指末端抽动或麻木感为度。下肢挛三针,鼠蹊在腹股沟动脉搏动处外侧进针,向居髎方向刺30~35 mm,以针感向下肢末端放射为度;阴陵泉向阳陵泉方向透刺30~35mm;三阴交沿胫骨后缘向悬钟方向透刺30~35 mm。腕三针阳溪、阳池、大陵分别直刺入15~20 mm;踝三针太溪、昆仑、解溪分别直刺入15~20mm;开三针水沟、涌泉、中冲分别直刺入5~10mm,水沟进针后用雀啄法,以患者流泪为度;八邪、八风分别直刺入10~15 mm。
疗程28 d,每星期针刺5次,休息2 d再继续针刺,共治疗4星期。
3 治疗效果
3.1观察指标
3.1.1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采用神经功能缺损量表(neurologic defec tscale,NDS)[8]。该量表包括8个维度,分别是意识、水平凝视功能、面瘫、言语、上肢肌力、手肌力、下肢肌力和步行能力。其意识维度分为两项提问、两项指令、强烈局部刺激3个条目,其余每个维度均为1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实际情况赋值6分。合计总分最高45分,最低0分。
3.1.2偏瘫侧肢体运动功能评分
采用四肢简化Fugl-Meyer功能量表(simplified Fugl-Meyer motor functional assessment,FMA),是1975年瑞典医生Fugl-Meyer等人在Brunnst rom评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目前国内广泛使用,Fugl-Meyer量表中对肢体的功能活动进行详细的量化评价,Fugl-Meyer量表分值越高,肢体功能活动越好。由于上下肢体功能恢复进程的不同,因此将四肢简化Fugl-Meyer评分分为上、下肢分别统计分析研究,上肢总分66分,下肢总分34分[9]。
3.1.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 tivity of dai l y l iving scale,ADL),Bar thel指数产生于50年代中期, 由Florence Mahoney和Dorothea Bar thel设计并用于临床,60年代中期文献报告正式称为Bar thel指数。合计总分最高100分,最低0分。Bar thel指数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研究最多的一种ADL评定方法[10]。
3.1.4功能综合评定
采用 功 能综 合评定 量表(funct ional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FCA),是根据功能独立性评定(functional independent measure,FIM)量表和综 合 功 能 评 定 法 (comprehensivefunct ional evaluation,CFE)的内容,具体内容包括两大类,一是运动功能,包括自我照料(进食、修饰、洗澡、穿上衣、穿下衣、用厕)、括约肌功能、转移能力、行走能力;二是认识功能,包括交流(视听理解、语言表达)、社会认识(社会交往、解决问题能力、记忆),共分为18个小项。本研究仅选用了功能综合评定量表的运动功能部分,共13个小项,每个项目最高评分6分,最低评分1分,运动功能部分总分78分[11]。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目前采用该量表作为脑卒中后功能评价方法的文献尚不多,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了其比较好的应用价值,与国外的同类量表比较更适应中国的国情[12-13]。
3.2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3.3治疗结果
3.3.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DS比较
由表1可见,两组治疗0 d、14 d N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28 d NDS评分比较,治疗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两组治疗14 d、28 d NDS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28 d NDS评分与治疗14 d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NDS评分比较 (±s,分)

表1 两组治疗前后NDS评分比较 (±s,分)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与治疗14 d比较2)P<0.01;与对照组比较3)P<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4 d 治疗28 d治疗组 36 13.44±2.35 8.72±2.191) 4.83±2.061)2)3)对照组 35 14.50±3.33 10.83±2.791) 8.00±2.911)2)
3.3.2两组治疗前后四肢简化Fugl-Meyer评分比较
由表2可见,两组治疗前上肢Fugl-Meye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14 d、28 d上肢Fugl-Meye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14 d、治疗28 d上肢Fugl-Meyer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28 d上肢Fugl-Meyer评分与治疗14 d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2 两组治疗前后上肢Fugl-Meyer评分比较(±s,分)

表2 两组治疗前后上肢Fugl-Meyer评分比较(±s,分)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与治疗14 d比较2)P<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4 d 治疗28 d治疗组 36 33.81±10.04 43.53±14.571) 54.67±12.441)2)对照组 35 31.89±10.90 39.83±12.631) 48.33±12.611)2)
由表3可见,两组治疗前下肢Fugl-Meye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14 d下肢Fugl-Meye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28 d下肢Fugl-Meyer评分比较,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两组治疗14 d、28 d下肢Fugl-Meyer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28 d下肢Fugl-Meyer评分与治疗14 d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3 两组治疗前后下肢Fugl-Meyer评分比较(±s,分)

表3 两组治疗前后下肢Fugl-Meyer评分比较(±s,分)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与治疗14 d比较2)P<0.01;与对照组比较3)P<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4 d 治疗28 d治疗组 36 20.89±4.72 26.11±6.041) 30.11±5.081)2)3)对照组 35 19.50±3.66 23.11±3.981) 26.38±4.721)2)
3.3.3两组治疗前后ADL比较
由表4可见,两组治疗前ADL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14 d ADL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28 d ADL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两组治疗14 d、28 d ADL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28 d ADL评分与治疗14 d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4 两组治疗前后ADL评分比较 (±s,分)

表4 两组治疗前后ADL评分比较 (±s,分)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与治疗14 d比较2)P<0.01;与对照组比较3)P<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4 d 治疗28 d治疗组 36 58.89±15.72 78.33±15.491) 90.00±8.781)2)3)对照组 35 48.06±20.08 65.00±12.651) 76.94±15.131)2)
3.3.4两组治疗前后FCA评分比较
由表5可见,两组治疗前FC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14 d、28 d FCA评分组间比较,治疗组FCA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1)。两组治疗14 d、28 d FCA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28 d FCA评分与治疗14 d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5 两组治疗前后FCA评分比较 (±s,分)

表5 两组治疗前后FCA评分比较 (±s,分)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与治疗14 d比较2)P<0.01;与对照组比较3)P<0.01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4 d 治疗28 d治疗组 36 47.61±13.45 61.06±9.151)3) 69.89±6.481)2)3)对照组 35 38.83±13.52 49.11±8.531) 58.17±10.721)2)
3.4安全性评价
经安全性评测,本研究在实施过程中未出现不良反应。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选取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患者。现代医学认为痉挛性瘫痪是由于上运动神经元,即中央前回运动区大锥体细胞及下行锥体束病变所致;主要表现为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浅反射减弱或消失,出现病理反射等[14]。中风偏瘫明显的痉挛约出现在发病后3星期,痉挛一般持续3个月左右[15]。痉挛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倾向于两种机制[16],即反射介导机制或称牵张反射相关机制和非反射介导机制或称非牵张反射相关机制。一般认为中枢抑制的减弱是导致痉挛发生的重要机制。
现代康复医学认为,针刺作为一种适宜的外周刺激,通过特殊的外周感觉输入方式,形成有功能的突触联系,调整神经反射环路中各个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促进脊髓运动神经元的可塑性变化,改善局部肌肉的肌张力,提高了再生神经的协调性运动支配能力[17-24],从而抑制低级中枢控制的异常活动,实现高级中枢控制的独立活动。因此,通过针刺诱发出的随意运动或通过针刺调整后的运动模式会增强神经反射及功能重组的效果。在痉挛期,通过刺激肌腱感受器,还可以使神经冲动经向心径路传至脊髓中枢,抑制肌肉痉挛,并使皮质下中枢发生代偿作用,使患者的步态、行走能力有所改善[25]。研究表明,针刺通过刺激脊神经根及交感神经,激发了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分泌,使脊髓前角的兴奋性降低,牵张反射减弱;同时通过神经将针刺激不断传入,经传导束促进脑血管侧支循环建立,改善脑组织的缺氧状态,促进脑细胞的再生及功能重组,解除痉挛状态,恢复肢体功能[26-30]。此外,针刺对中风后偏瘫患者的血液流变学、血脂和血糖、血栓素与前列环素系统和体感诱发电位等均有影响。
靳三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靳瑞教授在传统针灸学基础上借鉴吸收现代医学内容,使得传统针灸配方更趋于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靳三针的有效性已经通过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找到了理论依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在各种脑病的治疗上体现了其独特的优势[31-33]。本研究显示,两组NDS、四肢FMA、ADL、FCA评分组内比较,治疗14 d明显优于治疗前(P<0.01),而治疗28 d明显优于治疗14 d(P<0.01)。治疗14 d两组组间比较未见明显差异。治疗28 d,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在上肢FMA评分的改善方面未见明显差异(P>0.05);而在NDS、下肢FMA、ADL、FCA评分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P<0.01)。靳三针配合康复治疗中风后偏瘫痉挛状态疗效显著。本研究在治疗14 d组间未见明显差异可能与观察周期较短,累加效应未能体现有关。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对试验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有待以后大样本的深入研究来验证该结果。
[1]侯熙德.神经病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08.
[2]周天健.康复技术全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801-802.
[3]M cGruke JR,Harvey RL.The prevention andmanagement of complieationsafter stroke[J].PhysMed Rehabil Clin N Am,1999,10(4): 857-874.
[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55-56.
[5]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 1996,29(6):379.
[6]Brunnstrom.Movement therapy in hemiplegin.A neurophysiological approach[M].New York:Harperand Row Publishers,1970:5.
[7]南登崑.康复医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11.
[8]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382.
[9]桑德春,纪树荣,张缨,等.Fugl-Meyer量表在社区脑卒中康复疗效评定中的应用[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7,22(3):245-246.
[10]巫嘉陵,安中平,王世民,等.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研究[J].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09,9(5):464-468.
[11]胡永善,吴毅,范文可,等.功能综合评定量表的研究(一)量表设计[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2,17(1):35-38.
[12]方军,胡永善.功能综合评定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02,24(7):424-425.
[13]范文可,胡永善,吴毅,等.功能综合评定量表效度的研究[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3,18(6):325-329.
[14]王维治.神经病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65.
[15]王茂斌.偏瘫的现代评价与治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59.
[16]卓大宏.中国康复医学[M].第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68-671.
[17]王富平.针刺配合运动再学习促进脑卒中患者肌张力恢复[J].中国临床康复,2003,7(25):3532.
[18]李小兰.针刺结合隔药灸经筋结点治疗中风后肢体肌肉挛缩乏力临床研究[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5,37(12):1086-1090.
[19]杜小娜,熊佐玲,陈东梅.排针疗法针刺拮抗肌治疗中风后肌张力亢进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医药科技,2015,(5):556.
[20]庄志江,张丽红.针刺治疗脑卒中后下肢痉挛54例[J].中国民间疗法,2015,23(1):13-14.
[21]陈杰,高欣,李顺铭.针刺联合康复疗法治疗脑卒中后的肌张力增高[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5,19(B05):6.
[22]李作伟,李平,李英艳.巨刺针刺法治疗脑卒中后肌张力障碍的应用研究[J].内蒙古中医药,2014,33(16):85-86.
[23]姚庆萍,魏丽.醒神通络针刺法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60例临床观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4,35(12):52-54.
[24]何威.针刺治疗中风后下肢肌张力增高临床观察[J].实用中医药杂志,2014,30(11):1055-1056.
[25]吴毅,安华,施桂珍,等.常规康复治疗结合神经肌肉电刺激对脑卒中患者的疗效观察[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4,19(1):25-27.
[26]于学平,齐欢,黄昕.电针夹脊穴治疗中风偏瘫痉挛状态临床疗效观察[J].针灸临床杂志,2007,23(10):21-23.
[27]王雪飞,王少松,王麟鹏.早期针刺王氏夹脊穴治疗脑卒中后痉挛50例[J].环球中医药,2015,8(6):751-753.
[28]王琳晶,王玉琳,王春英.针刺夹脊穴配合巨刺治疗中风偏瘫痉挛状态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医药学报,2014,42(4):124-126.
[29]纪哲,申鹏飞.芒针针刺夹脊穴与督脉穴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J].黑龙江中医药,2014,(2):61.
[30]王雪飞,赵因,王麟鹏.早期针刺夹脊穴治疗脑卒中后痉挛的机制探讨[J].吉林中医药,2015,(4):421-424.
[31]魏文著,阮永队,宁晓军.温阳益肾健脑方合“靳三针”治疗皮层下动脉硬化性脑病21例[J].河南中医,2009,29(10):991-992.
[32]徐明学.靳三针治疗脑病先天愚型的成果[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4,(2):79.
[33]王洪涛,陈凡.靳三针疗法结合语言康复训练治疗脑中风失语症的疗效[J].实用医学杂志,2015,31(3):482-484.
C linical Observation of Jin’s Three-need le Acupuncture plus Rehabilitation for Post-stroke Spastic Hem ip legia
XU Shi-fen1, GU Jin-hua2.1.Shanghai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0071,China;2.Shanghai Fengxian DistrictHospit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hanghai201400,China
R246.6
A
10.13460/j.issn.1005-0957.2016.02.0153
1005-0957(2016)02-0153-04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课题(14401930900)
徐世芬(1975-),女,副主任医师,Emai l:xu_teacher2006@ 126.com
2015-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