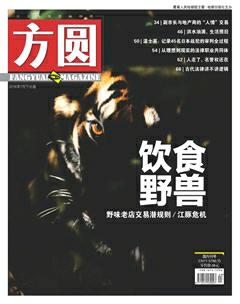从理想到现实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侯学宾
选拔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打通法律职业间流动的障碍,但未能在积极的意义上增加司法官职位的吸引力。因此,这个选拔办法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实效更多地在它之外的因素
让律师去当法官,让教授去当检察官,这样的情景过去只出现在美国律政剧中,现在在中国却要变成现实。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下面简称《选拔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该选拔办法从今年6月2日起生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一个想象的法律职业群体,一个凝固的法律职业群体,一个撕裂的法律职业群体,都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只有经由制度的形塑才能价值、知识、事业和技能上的“共同体”。这项改革的推行就属于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努力,也是将法律职业共同体从想象推向制度的关键性努力。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从业者在法律实践中的共同努力,法律职业者之间的良性流动不仅仅能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与专业化,也能促进法律职业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更能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但是这个良好开端并不一定就能产生良好的结果,真正地将现有的单向流动走向多向流动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
“法曹”之间的撕裂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法律职业主要成员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逐步建立规范的制度,但是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流动一直受到各种限制。
作为司法官的法官、检察官有专门的遴选任职制度,律师有律师资格考试制度,而法律教育者则通过科研院所系统进行选任管理。法律职业者之间的流动只是零星的存在。法律职业群体内部的流动不畅导致现在依然存在的“撕裂”现象。
这种“撕裂”体现在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却在知识生产与共享上相互“指责”。俗称“法曹三者”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一起指责承担法律教育与培训的教育者不了解实践、脱离实践,无法为法律实践提供优秀人才,而法律教育者也质问法曹三者没有贯彻法治观念,无视法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扭曲了从文本到现实的法律规则。
在法曹三者之间的,相互的流动也存在阻隔,大多数是从法官、检察官向律师的单向度流动。这种流动导致在朝法曹与在野法曹之间的撕裂,法曹三者之间也是互相指责,不仅在他们之间未能形成基本的法治共识和意识形态,而且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近日在广西“撕裤门”,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侧面。原来,6月3日,网上曝出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吴良述律师到南宁市青秀区法院申请立案期间诉称被殴打和撕扯事件。从吴律师在法院门口的照片上看,裤子撕坏,内裤外漏,敞胸露怀,尤其是单条腿的裤腿全裸,但是气质形象十分犀利,颇具T台走秀的舞台感。此事引发律师和法院的互相指责,律师被指责作秀,法院被指责滥用强制手段。
从“想象”到“制度”
面对法律职业群体内部流动不畅导致的困境,我国的司法改革开始逐步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流动。
这种内部流动首先在法官与检察官之间展开。199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法官、检察官相互调任不需参加调入方初任考试的通知》,规定“法官调入人民检察院担任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或检察官调入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不需参加调入方初任考试,经考核合格后,即可依法任命相应的法官、检察官职务”。
与此同时,尽管法律并未禁止律师流向法官,但从律师中遴选法官和检察官在实践中出现令人困惑的现象。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都没有单独设置从律师中遴选司法官的规定,只要符合法定的任职资格,律师也可以成为司法官。
在顶层设计的司法改革文件中,律师流向司法官的改革显得飘忽不定。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提出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从律师和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和《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不再单独提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规定,而是改为从其他优秀法律人才中选任,而措辞也从逐步建立,变成了逐步推行和原则上择优录取。
在顶层设计的具体制度上,律师流向法官的改革也是姗姗来迟。在参加法官遴选的公务员考试中,律师的经历和经验不仅没有优势,而且面临资格上的限制。一直到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才对《法官法》中的“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解释为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也在此列。但是2002年开始实施统一司法考试,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将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视为基本资格。这项规定实质上将2002年之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律师排除在候选范围之外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联合发布《关于将取得律师资格人员列入法官、检察官遴选范围问题的通知》,将已经通过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职业律师视为已经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由此可见,律师流向司法官的路途总是走得磕磕绊绊。
总之,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从律师中遴选司法官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有学者总结到,从2000年到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从律师和法学教育者中公开招考了22名法官,其中律师数量远少于法律教育者。2014年,上海市首次探索从律师和法律教育者中选拔高级法官和检察官,知名律师商建刚被选任上海市二中院三级高级法官。这种零星的实践在地方法院中存在,但是都未能形成一种常规性和制度性选拔方式。
外国法律职业间的流动模式
《选拔办法》的出台是对党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任务的具体化和制度化,也是改变我国法律职业之间的流动模式。
是不是一定要从律师、法律教育者中遴选司法官,世界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并不相同,不同的法律职业间的流动模式背后有不同的法律职业理念。
在英美等国家,司法官的任命更为强调法律经验,因此在律师与法官之间具有一脉相通的流动模式,具备律师资格是担任法官的必要条件。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法官的任职资格原则上包括三个条件:第一,美国公民;第二,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第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并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在英国,除了治安法官以外的所有法官都是从参加全国四个高级律师公会或者初级律师协会的律师中进行遴选,不同级别的法官所需要的从事律师工作的年限也不同,越是高级法院要求的工作年限也越高。这种一元化的法曹流动模式使得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意识形态更容易同质化。
而在德日法等国家,司法官的任命更为强调专业知识,因此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流动并不像英美那样紧密。诸如德国的法律教育系统更倾向于培养法官,在法律大专院校之间的培训课程高度一致,因此在德国有律师工作经验并不是担任法官的必要条件,而是要求接受三年半到五年的正规法学教育,并通过两次严格的国家考试,才能取得候补法官的资格,取得法官资格后才能去申请律师资格。在法国,法官的任职资格更为强调接受大学四年的法律课程,并通过政府主导的考试,考试合格后进入国立法官学院进行为期三十一个月的专业培训。检察官的任职资格和法官基本相同,律师资格的获得则要在具备大学法学四年毕业证书或者同等学力证书后,接受地区职业培训中心为期十八个月的培训,再去考取律师资格。因此,在德法等国,司法官与律师在获得基本大学法律教育后就“分道扬镳”,接受不同的培训,走入各自的岗位,这也造成了法律职业内部的“割据”。
法律职业间不同流动模式的形成和每个国家的法律变迁与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而言,律师与司法官之间的多向流动是最有利于形成法律职业精神的制度设计。因此,即使在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借鉴英美的一元化法曹模式。诸如在日本,法曹三者被认为是日本法治建设的三大支柱,但由于法律职业间流动模式承袭德法,法律职业共同体分裂成在朝法曹与民间法曹,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步变得紧张。在1988年,日本的临时司法委员会提出拟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议案,要求从具有十五年以上实务经验等资格的律师中每年选任20人任命为法官。
制度性多向流动的难题
《选拔办法》的出台预示着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迈出良好的开端,但是真的发挥实效却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是司法官的职位对律师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选拔办法》的出台和法官离职潮形成强烈的对比。有学者统计,在2008-2012年间,平均每年流失法官67人,2013年流失法官74人,并且大多在40-50岁之间,属于业务上的骨干力量。在2008年到2012年6月,江苏全省法院流出人员2402名,其中法官1850名。尽管不是所有离职的法官都会去做律师,但是依然能看出单向流动的频繁性。
《选拔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打通法律职业间流动的障碍,吸引更多的优秀律师人才进入司法官队伍,但是这种措施只是在消极意义上允许流动,而未能在积极的意义上增加司法官职位的吸引力。因此,这个《选拔办法》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实效更多地在它之外的因素。
尽管在世界各国,法官的薪俸都无法与律师的收入相比较,但是法官薪俸依然在整个国家公务人员体系占据较高的水准。在英国,高级法官的薪酬高于政府大臣,大法官的年薪甚至高于首相,其他各级法官的年薪也相当可观。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薪俸与副总统相等,联邦法院的法官与国会议员、政府内阁官员的工资大体上相当。日本的宪法与法官工资法明确规定最高法院院长的薪俸与内阁首相、国会两院议长相同。与之相比,我国法官与检察官的薪俸在整个公务人员体系中都处于较低的位置,很多法官、检察官离职中的经济原因占据很大比重。在此意义上,薪俸对律师流向法官几乎没有吸引力。
即使法官的薪俸对律师并无太大吸引力,但是很多国家的律师依然原因去做司法官,这是因为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官的权威和社会地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我国的司法机关面临着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司法权威不足,司法公信力遭到质疑,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尚未得到完全保障;司法官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受到尊崇的社会地位,职业荣誉感不足;司法的行政化与地方化导致法官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尤其面临着严重的职业风险。司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影响着司法官职位对律师和法律教育者的吸引力。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在《选拔办法》答记者问中,提出要为选拔优秀人才设置“高门槛”,在司法官职位缺乏吸引力的情况,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制度预期目的和实践效果出现较大的偏离。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在法律职业之间形成良好的流动或者互动,需要在制度上进行良好的设计,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真的从“想象”走向“制度”,需要不仅仅是流动模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整个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