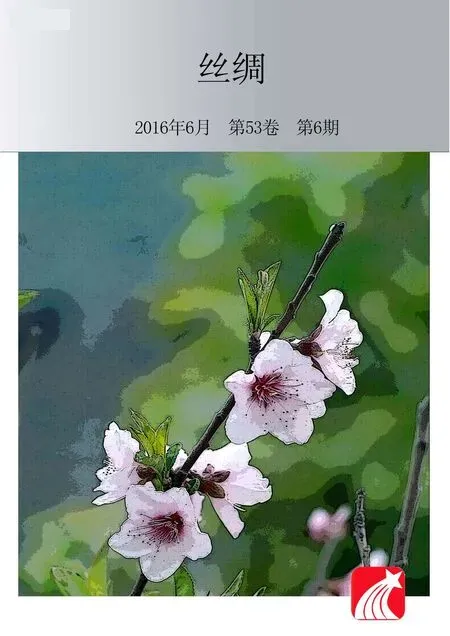中国传统服饰色彩之红色系染色工艺及显色探析
赵志军, 徐 菲, 王 慧, 杨晓华
(1. 齐齐哈尔大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沈阳 110136;3. 日内瓦大学 自然科学学院,瑞士 日内瓦 CH-1211 Genève 4)
中国传统服饰色彩之红色系染色工艺及显色探析
赵志军1, 徐菲1, 王慧2, 杨晓华3
(1. 齐齐哈尔大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沈阳 110136;3. 日内瓦大学 自然科学学院,瑞士 日内瓦 CH-1211 Genève 4)
摘要:中国传统服饰色彩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影响较为深远,但传统色彩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文章以大红色、小红色,以及相关色彩莲红色、桃红色、银红色、水红色、丹矾红共7种传统服饰色彩为例,对其染色技艺、染材、染液、色名、色彩等进行研究整理,并通过染色实验确定了最终的染色工艺及其L*、a*、b*值的大致范围。结果显示,大红色和小红色两者显色清晰、饱和度较高,为明度不同的对立色。其中大红色呈鲜艳的红色;小红色和丹矾红色相接近,均呈深红褐色,为同色、同技而不同名的色彩;其他4种色彩均与色名描述相符。染色后对7种色彩试样进行耐洗色牢度和摩擦色牢度测试,大红色、莲红色、桃红色、银红色、水红色皂洗牢度中的褪色为1~2级、沾色为3级,摩擦色牢度为3级以上,不能满足现代服装服用色牢度要求;小红色和丹矾红均达到3级以上的标准,可满足现代服装服用色牢度要求。同时通过调整媒染剂的用量可改变小红色和丹矾红的色相,使之呈鲜艳的棕红色,其改良结果与小红色、丹矾红同样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服饰色彩;染色技艺;植物染色;大红色;小红色;色牢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色彩是汉民族文化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字把色彩描绘成约定俗成的形象,使其在民族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突出性,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色彩发展的演变历程。透过丰富多彩的色彩词汇,不仅让大家认识客观事物的属性,而且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内涵。
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色彩像红色这样为人们崇尚,清代女刺绣工艺家丁佩在《绣谱》中记载:“颜色中之极绚烂者,红是也,极贵重者,亦惟红。”可见当时对其评价之高,远胜于其他色系。但由于红色体系庞大,从汉民族重具象、重直觉的思维方式来看,绝大部分色彩词运用“以物呈色,观象知意”的表达方式来构词,数量庞大,而又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时又受心理感受和色彩词的数量限制,很多色彩存在一定的模糊性[1]。只有深入研究古人造色识色的过程,并通过染色实验,明其意,断其色,确定色彩的显色范围、染色工艺、社会内涵、应用价值等,才能使研究成果不局限于文化运用上,还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纺织行业和古物复原等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支持。
中国是一个尚红的民族,对红色情有独钟。本文以“大红色”“小红色”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大红色是红色系中最经典的色彩,从古至今其应用与价值一直处于色彩之首,但对其染色技艺与显色情况却鲜有报道,揭示大红色的显色情况让大家一探究竟尤为必要。小红色与大红色似乎存在一定的关系,对于这个比较神秘的色彩,在印染史上仅记载过一次,但这一次却为传统套染技艺提供了重要信息,其染色工艺既科学合理又精彩绝伦,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结晶的代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对其深入研究可揭开明代流行色彩“丹矾红”的显色情况,并为其他套染色彩提供技术参照。
1 染色工艺
1.1染色文献记载
大红色在古代文献中多有出现,但记载染色工艺的文献目前仅查到四部著作,分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清代染织局档案的《乾隆十九年分销算染作》[4],以及在清代民间流传的清抄本《布经》[5],文献记载的朝代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传统染色技艺达到高峰的时期。从四部著作的记载可以看出染色工艺存在不同,《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偏重于染色工艺的记载,如“浅深分为两加减而成”,说明通过浸染的次数可增加色彩的深度;《乾隆十九年分销算染作》和《布经》偏重于染材及详细用量的记载,为染色工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数据。小红色仅出现在元末刘基的《多能鄙事》[6]中,也是现今对染色工艺记载最详细的染色文献[7]。“丹矾红”为明代上流社会的流行色彩,染色工艺仅见于《明会典》(卷二百一)中[8],文中记载的染材和用量与小红色极其相似,考虑小红色可能就是“丹矾红”或色相相近的色彩,将通过染色实验来确定两者的关系(表1)。

表1 大红色与小红色染色文献一览
注:宋应星把乌梅水和碱水顺序弄颠倒了,应该是“用碱水煎出,又用乌梅水澄数次”。
1.2染色工具和材料
1.2.1染色仪器和设备
HH-4数显恒温水浴锅(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pHS-2C型酸度计(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5102型电子天平(常州第一纺织设备有限公司),SW-12AⅡ型耐洗色牢度实验机(温州大荣纺织标准仪器厂),Y571L型染色摩擦牢度仪(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计算机测色配色仪(CrelagMaebethTMCol-orEye@2180UV,中国台湾瑞比公司)。
1.2.2植物染材
红花(产地西藏)、黄栌、黄檗、姜黄、槐花、栀子、苏木,均购于中药店。
1.2.2.1红花
红花,菊科植物红花的干燥花。红花是人类使用最主要的红色染料之一,以西藏所产的红花最为著名,即藏红花。红花染“真红”是从唐代开始,之前所染红色均含有黄光,这是因为红花中含有两种色素,一种是红花素(Carthamine,遇热则分解),其含量较少,仅占0.5%左右,可溶于碱而不溶于酸,采用酸或酶水解后,可染红色,是古代极为著名的染料[9](表4)。一种是红花黄素(Safflower yellow),含量较多,占30%左右,可溶于酸及水而不溶于碱,直接染色呈中黄色,微偏红;与白矾媒染呈黄色调;与皂矾媒染呈灰黄色调,见图1。图1中,红花→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1 红花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1 Carthamus Tinctorius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2黄栌(芦木)
黄栌,为漆树科植物黄栌的干燥木材。《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唐颜师古注:“栌,今黄芦木也。”黄栌木材呈黄色,古代常作为黄色染料。关于染色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初朱橚的《救荒本草》,即“木可染黄”。在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有记载。黄栌直接染色呈亮黄色;与白矾媒染呈黄色调,其中后媒染呈浅灰黄色,微偏绿;与皂矾媒染呈灰黄色调,其中同媒微偏绿,后媒呈灰黄色,见图2。图2中,黄栌→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2 黄栌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2 Cotinus Coggygria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3黄檗
黄檗,为芸香科植物黄檗的干燥树内皮。黄檗本身是一种中药,具有杀菌、解毒、消炎等药效,在古代常用于染织品和纸张,不但可以着色,还可以防腐防蛀,便于长期保存。黄檗易溶于水,与纤维有较高的亲和力,直接染色呈鲜黄色;与白矾媒染呈黄色调,其中后媒染呈浅灰黄色;与皂矾媒染呈灰黄绿色调,其中后媒呈土黄色,微偏绿,见图3。图3中,黄檗→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3 黄檗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3 Phellodendron Amurense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4姜黄
姜黄,为姜科姜黄的干燥根茎。《本草纲目》说:“近时以扁如干姜形者为片子姜黄,圆如蝉肚形者为蝉肚郁金,并可浸水染色。”《南城县志》亦说:“南城种姜黄如种菜畦,其根染黄,商贩他处,颇为民利。”说明姜黄染色颇受欢迎。姜黄属直接染料,亦含媒染基团,色光鲜嫩,唯不耐日晒。姜黄直接染色呈柠檬黄;与白矾染色呈黄色调,其中同媒略灰;与皂矾染色呈灰黄色调,前媒、中媒略灰,后媒较深,见图4。图4中,姜黄→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4 姜黄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4 Rhizoma Curcumae Longae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5槐花
槐花,为豆科植物槐树的干燥花。用于染材最早见于宋代寇宗奭撰的《本草衍义》,即“槐花,今染家亦用。收时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黄滓,渗漉为饼,染色更鲜明,治疗肠风热,泻血甚佳,不可过剂”。之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有记载:“凡槐树十余年后方生花实。花初试未开者曰槐蕊,绿衣所需,犹红花之成红也。取者张度笃稠其下而承之。以水煮一沸,漉干捏成饼,入染家用。既放之,花色渐入黄,收用者以石灰少许晒拌而藏之。”槐花既是黄色染材,又是染绿色和红色的打底色。当槐花为黄色染材时,直接染色呈浅灰黄色,与白矾媒染呈黄色调,皂矾媒染黄绿色调,见图5。图5中,槐花→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5 槐花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5 Flos Sophorae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6栀子
栀子,为茜草科植物栀子的干燥果实。栀子是中国较早染黄色的植物染料,在周代,皇帝祭祀所穿的“鞠衣”就是由栀子所染。栀子染黄色比较鲜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为皇室或贵族使用,一般庶民不得使用。栀子属于直接性染料,无需媒染剂也可染色,煮染或媒染可增强色牢度。栀子直接染色呈鲜黄色,与白矾媒染呈黄色调,与直接染色所呈色彩区别不大,与皂矾媒染呈黄绿色调,其中同媒呈较深的黄绿色,见图6。图6中,栀子→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6 栀子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6 Gardenia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2.7苏木
苏木,为苏木科植物苏木的干燥芯材。苏木原产东南亚和中国岭南地区,约魏唐之间跨过岭南进入中原,对中国染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古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用于染色最早见于西晋时期《南方草木状》:“苏枋,树类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绛,渍以大庾之水,则色愈深。”苏木是一种典型的媒染染料,在不同的媒染剂中能染得不同的色彩,古人常用来染红色、紫色或套染橙色、深蓝、褐色等,涉色领域比较广泛,其工艺比较简单,便于操作。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了染复色不可缺少的基础染材,如土红色、椒褐色、小红色、玫瑰紫、沙石色等。苏木直接染色呈橙黄色,与白矾媒染呈紫红色调,与皂矾媒染呈蓝紫色调,见图7。图7中,苏木→直接染色效果→与白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与皂矾媒染效果(前媒→同媒→后媒)。

图7 苏木染材及其基础染色显色效果Fig.7 Sappanwood dyeing material and its basic coloration results
1.2.3染色助剂
明矾(又称白矾,硫酸铝钾,分析纯,哈尔滨化工化学试剂厂)、无水碳酸钾(又称钾碱,代替碱和生炭灰,分析纯,天津市四通化工厂)、黄丹(又称铅丹,购于中药店)、柠檬酸(代替乌梅汁,分析纯,天津市北方天医化学试剂厂)。
1.2.4染色面料
真丝双绉(平方米质量90 g/m2),尺寸为10 cm×10 cm。
1.3明清时期度量衡计量单位换算
明朝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朝政府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度量管理制度,这在明官修的《明会典》和《大明律》中多有记载,政府规定民间市场贸易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同,并且要经官方校验印烙后方可合法使用,否则按律治罪[10]。从现存文物的角度研究,明代的衡量单位量值已基本明确,明清的容量单位是一致的,清代有尺原器留存至今,数据比较确实可靠,即1 L为1 035 cm3,转化为毫升为1 035 mL;明清时期的质量单位与前代略有区别,即1斤等于16两,1斤在591~596 g,平均1斤约594 g,1两约37.1 g。
《多能鄙事》中用于提取染料色素的染具多为普通碗、杯等。明代碗的盛水容量一般比1升小,1升为1 030 mL,一碗大约在515~1 030 mL,小于515 mL染液不便于面料浸染和操作,故设定一碗为772.5 mL。
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古今度量衡的转换比例,推算出染料比例,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

表2 大红色、小红色及丹矾红染料比例
1.4萃取色素
1.4.1槐花萃取工艺
文献记载“将槐花炒令香”,就是将新鲜的槐花炒干直到有香气发出,之后“碾碎”,便于萃取色素。将“以净水二升煎一升之上”,又《本草衍义》记载:“槐花,今染家亦用。收时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黄滓,渗漉为饼,染色更鲜明,……”可见萃取工艺为将炒好的74.2 g槐花碾碎,放入2 070 mL水中,大火加热至沸,之后关小火持续煎取,煎至1 200 mL待用。
1.4.2苏木萃取工艺
根据文献记载,取148.4 g苏木,处理成碎片,放入1 545 mL(即两碗)水中,大火加热至沸,关小火煎至1 200 mL,定为苏木头汁,待用。将头汁碎渣放入约1 158 mL(即一碗半)水中,继续煎取,煎至约580 ml,倒入烧杯中待用。将第二次煎取剩渣放入1 545 mL(即两碗)水中,煎至约773 mL,与第二次染液混合,定容至1 200 mL,定为苏木二三汁。
1.4.3红花萃取工艺
红花萃取工艺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见表3。从文献来看红花饼的制作方法最早见于西晋时期,到明代记载更为详细。总的来看都是运用相同原理进行萃取,即利用红花中含有的红色素(即红花甙)溶于碱而不溶于酸的化学特性来保存红色素。
取500 g红花,洗净后捣烂,浸入pH值为4~6的冷水中进行淘洗,放置一夜,用布袋绞挤黄色素,重复以上操作步骤,直至完全去除黄色素。用布覆盖去除黄色素的红花,放置一夜,使之发酵,制成红花饼。取一定量的碳酸钾放入5 L冷水中,调pH值为10~12,放入红花饼,搅拌、揉搓后静置一夜,次日将布袋绞挤得黄橙色溶液。重复以上操作一次。将两次所得溶液混合,放入一定量的柠檬酸调pH值为4~6,即为红花染液,呈桔红色,待用。将一定量柠檬酸加入2 L净水中,调pH为4,为发色染液,呈红色,待用,见图8。图8中,红花饼→提取过的红花饼→红花染液→加酸后的红花染液。

表3 红花萃取工艺文献一览

图8 红花饼及红花染液Fig.8 Safflower and Carthamus Tinctorius dye liquor
1.4.4黄栌、黄檗、姜黄、栀子萃取工艺
黄栌、黄檗、姜黄、栀子均为打底染材,文献未说明萃取工艺。从染材性质看,均溶于水,皆可采用“煎取法”。取100 g染材,放入1 L水中,大火煮沸后调至小火继续煎取,煎至600 mL染液待用。重复以上操作一次,将两次染液混合,共1 200 mL,留作实验备用[13]。
1.5染色工艺
1.5.1大红色染色工艺
大红色为酸性染色工艺,在染色时利用红色素在酸、碱溶液中的不同溶解度,在酸性条件下,使其在纤维上固着发色。染色效果的关键在于对红色素的质量浓度、浸染次数和浸染时间的控制。
染色条件:一浴,染色时间30 min,pH值为4~6,二浴,染色时间20 min,pH值为4。发色染液质量浓度为1.5 g/L,红花染液质量浓度为25 g/L,黄栌、黄檗、姜黄染液质量浓度约为83.3 g/L。
操作步骤:第一步,将面料放入200 mL打底染液中,浸染30 min,水洗,待用。第二步,将面料放入红花染液中,浸染30 min,染后水洗,放入发色染液中浸染20 min,水洗,风干,为一次染色。再根据实际需要色彩重复以上步骤。
《天工开物》记载“莲红、桃红色、银红、水红色:以上质亦红花饼一味,浅深分两次加减而成”,可见每种色彩需要浸染次数不同,以每浸染二次为一种色彩,染大红色则需更多次数。本文共设计了4种染色方案(表4),分别为直接染色1种,黄檗、黄栌、姜黄打底各1种。

表4 染色操作及结果
1.5.2小红色染色工艺
1.5.2.1染色温度
染色温度对植物染色极其重要,色相的变化、明度的深浅、牢度的坚固都与温度有关,控制合理的温度决定着染色的最终效果与成败。文献中有两处对温度有明确描述,分别为“以沸汤一碗化开解余矾”“将头汁温热”,但无具体数据记载。一浴温度,从前文记载可以推断,煎取后滤去渣,然后下白矾,工艺过程动作流畅,时间较短,煎出染液的温度一般在90~100 ℃,之后使用工具进行“搅匀”,在这个过程中,温度下降较快;最后下绢帛的温度大约在50~70 ℃,这个温度区域对染色结果的影响并不大,故设定为60 ℃。二浴温度,首先是沸汤化余矾,由于温度较高,白矾化得较快,温度略有下降,再入黄娟,浸半时许,在这个过程中温度不断下降,一直处于变化状态。长时间浸在矾水中,从高温到低温只会影响上矾的速度,对染色结果的影响不大,故设定温度为60 ℃。三浴温度,煎取第二汁后暂存储,等煎取第三汁与第二汁合在一起,此时第二汁温度已下降,第三汁温度较高,混合后温度在60 ℃左右。入黄丹后“搅极匀”,温度会有所下降,再浸片刻“提转令匀”,温度逐渐降低,古人在此处并没有强调加热或保持恒温,说明染色温度低于60 ℃的条件下也可操作,故考虑染色的稳定性,设定温度为60 ℃。四浴温度,文献记载将“头汁温热”,同时“急手提转”,可见温热的程度用手便可操作,温度不会超过60 ℃,浸半时许,温度不断降低,也不影响染色效果,故设定温度为60 ℃。
1.5.2.2染色时间
染色时间与染色温度一样重要,对染色结果起决定作用。文献在记载小红色关键的染色步骤上也有详细说明,如二浴时间“入黄绢浸半时许”、三浴时间“浸片时扭起”、四浴时间“急手提转,浸半时许”,唯独没有对一浴时间进行说明。经实验观察,面料入一浴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产生同媒效果,呈鲜黄色,时间达到30 min后并无明显变化,可见文献没有特意强调,说明一浴时间的长短对染色结果影响不大,而且一浴染色主要以黄色打底,是古人为节省染材讨便宜的技法。二浴时间较明确,为半时许(1 h),较长时间的浸染可以使面料上矾充足。三浴时间为片时许,略有争议。片时也叫片刻,一刻为15 min,按此说法片时就是15 min,同时“片时许”也表示很短的时间,故不改变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设定5种不同时间进行测试,1 min与5 min时间点的染色结果较为灰暗,不如长时间明亮,20 min与15 min得到的染色结果接近,几乎没有变化,故结合文中“其色鲜明甚妙”的描述,片时推断为15 min。四浴时间为1 h,长时间浸染有利于使面料上色达到饱和,增加色牢度。丹矾红,在四浴浸染中共设计了6种时间的染色方案,随着时间的增加,所得染色结果略微加深,但并不明显(表5)。

表5 三、四浴不同时间显色结果
1.5.2.3染色手法
古代染色均采用手工操作,手工在染色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必要的手法能够使面料着色均匀、色彩层次丰富。文献在三浴和四浴中对此多有记载,如三浴需“搅极匀”“提转令匀”“扭起”,四浴需“提转六、七次,扭起”,这说明染色已经达到了高潮阶段,为了实现上色效果,需达到“匀”“准”“牢”,这种巧妙设计体现了先民高超的智慧。
1.5.2.4染色工艺
小红色的染色工艺为媒染法和套染法。媒染法,利用媒染剂中的金属盐与染料分子中的配位立体结构进行络合,一方面可以改变所染色彩的纯度和色相,另一方面可以对所染织物上染率和色牢度等产生很大的影响。传统的媒染法根据媒染的前后顺序分为前(预)媒法、中媒法、后媒法、同媒法4种方法。套染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植物染料套染或拼色而染的工艺[14]。
操作步骤:依次入一浴、二浴、三浴、四浴,最后水洗,阴干。
染色条件:按照古代文献记载的染材比例进行换算,设定染缸所用染液标准为200 mL,使用明矾约6.2 g,黄丹6.2 g。槐花质量浓度为62.8 g/L,栀子质量浓度为83.3 g/L,苏木头汁质量浓度为123.7 g/L,浴缸温度60 ℃,浸染时间无说明均为30 min,二浴明矾水质量浓度无说明均为31 g/L。
针对文献记载共设计了5种染色方案(表6),其中大红色、小红色复原染色方案各1种,无槐花打底染色方案1种,改良染色方案各1种。

表6 染色操作及结果
2 染色结果
2.1大红色
从大红色的构词形式来看,属于“修饰词+红+色”的类型。“大”表示颜色程度,即红色系中饱和度最高的色彩。在《天工开物》中也有描述,如“澄得多次,色则鲜甚”,说的就是提高色彩饱和度的办法,大红色需多次浸染才能得到。据《天工开物》记载,在浸染的过程中,每浸染2次可以得到莲红色、桃红色、银红色、水红色,其色相也不难理解,连红色、桃红色、银红色属于比喻构词方式——“事物+红+色”,由红色联想到与“红”色相关的事物就与此比较。水红色属于“修饰词+红+色”的构词形式。莲红色,像荷花(莲的花)那样的中绛红色;桃红色,像落叶乔木桃树粉红色花那样的颜色;银红,是粉红色颜料加银朱调和而成的鲜红色;水红色,水表示浓度,即含有大量水分感觉的淡红色,见图9。图9中,水红色(L*:75,a*:26.8,b*:3.2)→银红色(L*:63.4,a*:47.2,b*:4.2)→桃红色(L*:58.2,a*:56.6,b*:11)→莲红色(L*:51.4,a*:62.8,b*:20.4)→大红色(L*:47.8,a*:70.2,b*:50.8)。

图9 水红色、银红色、桃红色、莲红色及大红色显色效果Fig.9 Coloration results of water red, silver red,peach red, lotus red and big red
染色分析:红花直接染色方案,随着浸染次数增多,色光逐渐偏红光,最后达到鲜艳的红色。依次可见,浸染1~2次可得水红色,浸染3~4次可得银红色,浸染5~6次可得桃红色,浸染7~8可得莲红色,浸染9~14次可逐渐得到大红色。黄檗、黄栌打底染色方案,在浸染的过程中面料显色效果比较接近,但在发色的过程中会游离出黄色素,随着浸染次数增多而减少。姜黄打底染色方案,前几次浸染出现染色不均现象,在后期得到改善。4种染色方案达到10次以上,显色效果逐渐接近,最终都能达到大红色,但直接染色方案效果最佳,色彩更为纯正。打底染色方案不能得到莲红色、桃红色、银红色、水红色。
大红色,文献明确记载色相约在宋代,宋之前色相呈橙红色,这与红花中含有黄色素,提取不净有关。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抄》(卷一)中有记载“以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亦曰干红”,可见这个时期工艺成熟,提炼纯净,已很少含有黄色素。《天工开物》记载:“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饼然后用,则黄汁净尽,而真红乃现也。”说明在明代乃至清代,红花的提取和染色更是技术娴熟,所染色泽纯正,并形容为真红。大红色服饰代表上层社会,多为身份和权贵的象征,亦为明清时期结婚喜庆用色。
2.2小红色
从小红色的构词形式来看,其含义与大红色正好相反,色相也有很大差异,所染的小红色呈深红褐色,如图10所示。图10中,一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二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三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小红色(L*:22.6,a*:39,b*:12)。

图10 小红色显色效果Fig.10 Coloration results of little red
染色分析:一浴,少量白矾与槐花进行同媒,可使面料上色均匀,呈鲜黄色,此步称为打脚(打底),古人认为此法可讨便宜,节省染材的消耗,同时对最后色泽影响不大;二浴,大量白矾进行媒染,进一步使面料上色均匀,此步既是槐花的后媒,又是苏木的前媒,由于上矾量大,面料呈稍浅的鲜黄色;三浴,使用浓度较稀的苏木二、三汁混合染液与黄丹进行同媒,黄丹起到调整色相和促进媒染的作用,使面料呈灰橙色,同时也是苏木头汁的前媒;四浴,面料上残余的白矾和黄丹再与苏木头汁同媒,使染色达到高潮,形成小红色,面料呈深红褐色。
小红色出现在元末时期,据沈从文先生说:“元代法律制定,官吏和平民只许穿棕褐等暗色,正由于禁令限制,反而促使广大劳动人民就地取材,创造了种种不同褐色。”[15]可见元代民间服色最大的特点多为褐色系,他们将此色发展成许多不同褐色,甚至将褐色染成由浅而深达20种之多的色相。《多能鄙事》记载的其他色彩,如枣褐色、椒褐色、艾褐色、明茶褐色、暗茶褐色、艾褐色、荆褐色、砖褐色、皂色等,多为深或灰的褐色,几乎没有鲜艳色彩,这些色彩都在元代禁令限制之外,说明《多能鄙事》所记载的色彩极可能为民间流行服色。因此小红色极有可能是褐色系中的一种,文献描述“其色鲜明甚妙”,推断“小红色”要比其他褐色要鲜艳一些,正如所染的小红色一样,呈鲜艳的深红褐色。
2.3丹矾红
从丹矾红的构词形式来看,“丹”指黄丹,“矾”指白矾,丹矾色即是使用黄丹、白矾为媒染剂所染而成的红色。所染的丹矾红呈深红紫色,如图11所示。图11中,一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二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三浴显色效果(未经水洗)→丹矾红(L*:16,a*:36,b*:11)。

图11 丹矾红显色效果Fig.11 Coloration results of cinnabar red
染色分析:由栀子的基础染色可以看出,栀子无须媒染即可得到鲜艳黄色。白矾在此工艺中主要与苏木发生媒染而达到显色的作用。前三浴的浸染效果较小红色鲜艳一些,四浴的显色结果与小红色比较接近,略深一些。
丹矾红,在明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最早出现在弘治《徽州府志》中,即“永乐元年重建,正厅库房各三问,东西两堂机坊十一间,东西染房六间,门房五间,改造细绢,今岁造深青、黑绿、丹矾红三色,光素芝丝”。文献描述也常见于农户织造丹矾红进贡朝廷,朝廷将此色定为高贵色彩,规定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可用此色。同时朝廷常将丹矾红织物作为赏赐赠与西藏佛教高僧,甚至也作为颁赐礼品流传到日本等。由此可见,丹矾红在明代大受重视,也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流行色。在清代文献中却很少见此色名,极有可能像“小红色”的命运一样,保留了工艺更改了色名或解禁此色,并消失于民间,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3 显色关系及色牢度检测
3.1大红色、小红色和丹矾色之间的关系
3.1.1大红色与小红色的关系
根据大红色和小红色染色实验所呈现的结果来看,大红色为红色系中最饱和的鲜艳之色,小红色为红色系中最饱和的深暗之色,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大”与“小”的对比一样,也许这就是古人对小红色的理解,见图12。图12中,大红色→小红色。

图12 大红色与小红色显色效果对比Fig.12 Coloration comparison of big red and little red
3.1.2小红色与丹矾红的关系
小红色只出现在元末时期,犹如昙花一现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古代文献上也少有记载。丹矾红也出现在元末,在明代也多有记载,而清代却少有记载,两色所用染材除栀子之外其他染料比例相同(表2),染色的结果也非常接近,只有改变媒染剂的用量和染色时间才能适当改变色相。以上说明丹矾红就是小红色或丹矾红继承了小红色的染色工艺,并取代了小红色,见图13。图13中,小红色(L*:22.6,a*:39,b*:12)→改良的小红色(L*:32.8,a*:50.6,b*:24.6)→丹矾红(L*:16,a*:36,b*:11)→改良的丹矾红(L*:33.4,a*:49.8,b*:30.2)。

图13 小红色与丹矾红及改良显色效果对比Fig.13 Coloration comparison of little red, cinnabar red and improved red
3.2染色色牢度的检测
耐皂洗色牢度:按照GB/T 3921—2008《纺织品 色牢度测试 耐洗色牢度》标准测试;耐摩擦色牢度:按照GB/T 3920—2008《纺织品 色牢度实验 耐摩擦色牢度》标准测试。由表7测试结果可见,大红色、莲红色、桃红色、银红色、水红色共5种色彩试样的皂洗牢度中的褪色为1~2级、沾色为3级,摩擦色牢度为3级以上,不能满足现代服装服用色牢度要求;小红色、小红色(改良)、丹矾红、丹矾红(改良)共4种色彩试样的耐洗色牢度和摩擦色牢度均达到3级以上的标准,能够满足现代服装服用色牢度要求。

表7 染色色牢度的测试结果
4 结 论
大红色和小红色都是传统服饰色彩的典范,通过深入研究,建立了大红色、小红色及其相关5种传统服饰色彩的工艺参数,并明确了大致的显色范围。对染色结果的分析与比较,证实了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演变历程,同时从古代文献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大红色、小红色及丹矾红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使其再次重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对染色色牢度的检测,证实了部分色彩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有利于植物染色得到永续而广泛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伍铁平.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2):88-105.
WU Tieping. Theory of color words and its fuzzy properties[J].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1986(2):88-105.
[2]宋应星,钟广言.天工开物[M].北京:中华书局,1978:113-122.
SONG Yingxing, ZHONG Guangyan. Tian Gong Kai Wu[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8:113-122.
[3]方以智.物理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57.
FANG Yizhi. Wu Li Xiao Shi[M].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37:157.
[4]王业宏,刘剑,童永纪.清代染织局染色方法及色彩[J].历史档案,2011(2):125-127.
WANG Yehong, LIU Jian, TONG Yongji. In Qing dynasty, dyeing and weaving Bureau dyeing method and color[J]. Historical Archives,2011(2):125-127.
[5]李斌.清代染织专著《布经》考[J].东南文化,1991(1):79-85.
LI Bin. Qing Dynasty dyeing monographClothby test[ J]. Southeast Culture,1991(1):79-85.
[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168子部:杂家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9.
ContinuationofSiKuQuanShuCodification Committees. Continuation of Si Ku Quan Shu 1168 Zibu: the Eclectics[M]. 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6:49.
[7]赵丰.《多能鄙事》染色法初探[J].东南文化,1991(1):72-78.
ZHAO Feng.DuonengBishistaining method[ J]. Southeast Culture,1991(1):72-78.
[8]赵其昌.京华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25.
ZHAO Qichang. Beijing Sets[ M]. Beijing: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8:225.
[9]孙云嵩.植物染色技术[J].丝绸,2000(10):24-29.
SUN Yunsong. Dyeing technology vegetable dyes[J]. Journal of Silk,2000(10):24-29.
[10]卢嘉锡,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11-415.
LU Jiaxi, QIU Guangm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M]. Beijing:Science Press,2001:411-415.
[11]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186.
LI Fang. Taiping Yulan[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60:3186.
[12]贾思勰.齐民要术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16.
JIA Sixie. Qimin Yaozhu[M]. 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9:316.
[13]孙云嵩.黄色植物染料及染色[J].丝绸,2003(1):31-33.
SUN Yunsong. Yellow vegetable dyes and dyeing[J]. Journal of Silk,2003(1):31-33.
[14]赵志军,刘剑虹,徐菲,等.中国传统服饰染色技艺之褐色系复原研究[J].丝绸,2015,52(3):31-36.
ZHAO Zhijun, LIU Jianhong, XU Fei, et al. Study on dyeing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brown color series recovery[J]. Journal of Silk,2015,52(3):31-36.
[15]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分社,1981:395.
SHEN Congwe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othing[M]. Hongkong:Hongkong Business Bookstore,1981:395.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16.06.005
收稿日期:2015-10-21; 修回日期: 2016-05-11
基金项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指导性项目(201505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5YSE03);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社科类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2014W-M22)
作者简介:赵志军(1979—),男,讲师,主要从事草木染艺术、装饰艺术设计的研究,为“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成员。
中图分类号:TS1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003(2016)06-0020-12引用页码: 061105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color-red color series dyeing process and coloration
ZHAO Zhijun1,XU Fei1,WANG Hui2,YANG Xiaohua3
(1. College of Art & Design, Qiqihar University, Qiqihar 161006, China; 2. College of Design & Art,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3. Facult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Genève, Genève CH-1211 Genève 4, Switzerland)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color has influenced modern costume design significantly, but traditional color itself has certain fuzziness. This paper takes 7 traditional costume colors (including big red, little red, lotus red, peach red, silver red, water red and cinnabar red) for example and studies their dyeing techniques, materials, additives, code and colors. Besides, the final dyeing process and the rough range of L*, a*, b* are confirmed through dyeing experiment. Final result shows that big red and little red have clear coloration and high saturation, and they are opposite colors with different brightness. Big red is bright red, while little red is more close to cinnabar red which is more bronzing, and they are the same color, same dyeing technique but different color code. The rest 4 color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codes. Washing and rubbing fastness tests were done for the 7 colors after dyeing.The result shows that fading level of big red, lotus red, peach red, silver red and water red is 1~2; their staining level is 3; their rubbing resistance level is above 3, and all of them cannot meet the fastness requirement of modern costume design. Little red and cinnabar red is above level 3 which can satisfy colour fastness requirement of modern costume design. By adjusting dyeing additive dosage, it can change the deepness of little red and cinnabar red to make them more brownish and more applicable. The improvement result also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like little red and cinnabar red.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s; dress color; dyeing technology; plant dyeing; big red; little red; color fas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