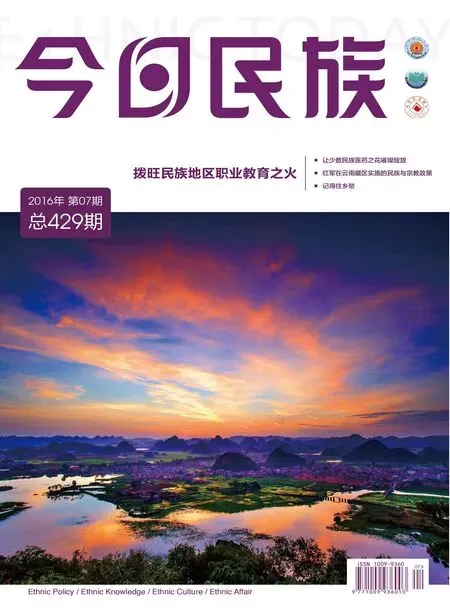从“边缘”看历史读《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文·图 / 龙成鹏
从“边缘”看历史读《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文·图 / 龙成鹏

编者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是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名著,1997年在台湾出版,2006年在大陆出修订版,2013年出全新修订本,在知识界一直很畅销。被评价为“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典范”,读这本书,可以了解最近民族研究领域的部分声音。
气候变迁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对中国民族的认知,当代学者从民族史的角度提供了很多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中,我们熟悉的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理论最早公开发表是在1988年,引起学界巨大反响。
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与另一个学者苏秉琦的比较类似。考古学者苏秉琦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梳理出一条中国文明的发展模式:从空间上,他主张是“满天星斗”而不是黄河流域一枝独秀;从发展阶段上,他细化出“古国”(尧舜禹时代或更早)、“方国”(夏商周)到“帝国”(秦汉以后)的三步曲。某种程度上,苏秉琦的观点可以视为“多元一体”的考古学版本。
有费孝通和苏秉琦的观点为参照,我们对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对中国民族提出的另一个解释体系,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先从具体的问题入手。中国的早期文明,无论是费孝通还是苏秉琦,似乎都同意它是从涓涓细流发展成大江大河的过程,是综合不同的区域文明,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好像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在《华夏边缘》一书中,王明珂补充了一个特别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
在《华夏边缘》的第二部分,用3章来阐述这个细节。王明珂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中国北方,从西北到内蒙古再到华北一线,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发展程度较高的农业文明。但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这个区域发生了重大变故,他们从农业逐步转向游牧,出现了文明的“衰退”。
有一个典型例子。青海河湟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马家窑文化,这个文化受著名的仰韶文化影响,也是定居的农业文明。但经过齐家文化,到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时,这个地方已经游牧化,养羊已经普遍地替代了养猪。
这个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王明珂认为是气候变迁。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开始了持续一千多年的干冷化,直接导致了上述地区逐步放弃农业而转向游牧,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个转变得以完成,并造成了一系列民族史上的后果。
王明珂把公元前1000年前后上述地区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视为中国民族史的一个重要转折,这种转折就是,华夏民族的疆界沿着农业与游牧这条生态边界开始形成,而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华夏民族的认同以及与边界之外的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
从先秦考古文献中梳理早期民族史材料,是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考古材料只能说明它是人类的遗迹,但却不能告诉你它应当属于什么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族有它客观的一面,但也有主观的一面,主观的一面,主要是民族的认同,认同什么时候出现?只有跟“外人”或者“他者”有接触,并反观自己时,认同才出现,这个人群才会意识到我是什么族或者什么人。
王明珂认为,华夏民族这个集体认同的出现,是春秋时代的事情。他从历史文献中也找到了若干证据。在西周时期,中国北方,并没有华夏与其他民族的区分,西周崛起于西部,在它西边的“戎”就是它的盟友。但到公元前771年,一个事件打破了这种联盟的关系(彼此矛盾也许更久)。这就是西周王都,被西方的“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其余王室成员被迫东迁。这个时间点,是东周的开始,也是春秋的开始。而此时的戎狄入侵,也并没有结束而只是一个开端。此后春秋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尊王攘夷”,而“攘夷”的背后,就是华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华夏民族的认同与近代转型
从春秋时代形成的华夏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晚清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才逐步瓦解。看到西方人,看到另一种“他者”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重新调整历史上的“华夷之辨”,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认同,一种包含了华夏与周边民族的认同。这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起源。
《华夏边缘》一书,对上述历史演变,都有涉及。在该书的第三部分,王明珂用4章的篇幅阐述了华夏民族向四周扩展的历程,在第四部分,用2章的篇幅回顾了近代民族主义影响下,传统的民族观念如何向近代转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的迁徙经常被关注,但华夏民族向四周的扩展,却容易被忽略。比如羌人,在商周时代,活动范围是在陕西黄河流域,但到东汉、魏晋时期,羌人已经一部分“迁徙”到了新疆的天山南路。这种迁徙,经常成为民族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王明珂认为,羌人的“漂移”,其实反映的不是羌人的实际迁徙,而是华夏族群的西扩。换句话说,羌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民族称呼,而只是一个西方异族的模糊的指称,羌人所在的位置,就是华夏民族的边疆(他用“边缘”这个词),这个边疆,也可以视为文化的边疆。相比春秋时代,秦汉时期华夏的疆界已经超出了农耕与游牧的生态疆界,变得更具包容性。
华夏的扩张,并不单纯是武力征服的过程。王明珂花了很大篇幅,讲历史记忆如何使得华夏的疆界向东北、东南、南部扩展。典型例子就是“泰伯奔吴”的故事。
泰伯奔吴,说的是春秋时代的吴国王室是周人的后裔,而且是主动放弃王位的泰伯的后裔。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因为周文王的爷爷看好周文王,想让他成为未来的接班人。但周文王的父亲不是长子,所以,按规矩,不能顺利接班。于是泰伯就主动放弃王位让给弟弟(周文王的父亲),跑到了荆蛮地区,文身断发,主动变成“野蛮人”。荆蛮后来就变成春秋时代的吴国。
王明珂认为,这个故事,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但可以视为历史记忆,通过这个历史记忆,原本被华夏视为“野蛮人”的吴国,主动认同为华夏,于是华夏的边缘得以扩展。
华夏的认同,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争夺正统。“泰伯奔吴”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吴国对正统的窥觑:泰伯这支原本是正统,但他放弃了。此外,“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同样可以看成是对正统的争夺。争夺正统的后果,就是强化了华夏的认同,强化了华夏文化优越性这种观念。
假借历史记忆来完成华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故事,云南的“庄蹻王滇”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华夏边缘》一书中,王明珂并没有具体阐述,但在几年前的一个讲座中,他提过这个例子。
楚国的庄蹻,在滇池边建立了滇国,此后滇国被汉武帝灭,但王室被保留。因为楚国的这层渊源,古滇国与中原的汉王朝,具有比云南其他部落、王国更亲密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的评论部分就暗示,正是因为楚国后裔这个身份,滇王具有某种优越于云南其他部落的德行,所以也得到了汉武帝的庇护。
对中国民族的近代历史,王明珂的研究,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民族有很多启发。他并没有割裂历史与近代的联系,而是视为一种延续。通过近代民族主义的洗礼,中国把过去与华夏对立的“四夷”转换为“少数民族”,华夏变成汉族,华夏与“四夷”从概念上的分裂走向融合。
王明珂从个案入手,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描述。他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了民族知识的生产在促进近代民族观念转型过程中的意义。他的案例之一,是1928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史语所倡导下,民族学者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这些调查,所汇集的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细节,为构建中华民族奠定了历史根基。
王明珂描述的史语所,跟云南的民族研究的确有密切关系。1928年,史语所成立不久,就派出杨成志到云南调查,杨成志是第一个到云南开展调查的民族学者,所以,1928年也被视为云南民族学的开端。
王明珂从民族学知识生产(民族学调查)的角度,分析近代民族观念的转变,还留下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实际上,1949年后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都是同样类型的文化工程,对于我们塑造今天的民族格局(知识上或者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谈论民族时,今天的学者在谈论什么
《华夏边缘》在台湾出版于1997年,2006年引进大陆。台湾版出来后,我曾经读过一次,还写过书评。现在重读,跟过去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过去,关注的是王明珂对传统民族史的“解构”的一面,但现在,看到他的更多“建构”的一面。
王明珂是台湾学者,早期的学术经历比较叛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的是羌族。1994年,开始到羌族地区调查,《华夏边缘》是成果之一。
《华夏边缘》一书可以视为他对羌族长期研究之后,由点向面,从羌族进而中华民族的一次尝试。该书的一个关键词汇是“边缘”,“边缘”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研究视角或者研究策略。为了弄清楚中国人是什么,中华民族怎么来的这样的问题,王明珂从中国的“边缘”(华夏的文化边界)入手,从“边缘”的变化看中国整体的变化。
这个研究角度,跟以往的民族研究,有很大不同,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中心,是起源。王明珂选择从“边缘”入手,解读中国民族史,其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有一个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所以,要描述一个民族时,他的方式,不是描述这个民族有什么文化特征,具有什么样的“本质”,而是描述它的“边缘”,它在边缘之地,与他者发生文化接触时的各种际遇,研究它怎么看待,怎么区分其他民族,其他民族怎么看待它。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民族学上,有一个通俗的现象,叫“面对他者,自觉为我”,你有什么特征,你开始是不知道的,只有与他者相遇,你才在对比中发现自己的区别。这就是“边缘”的优势。
而且,这个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表面看是一种文化(比如,用服饰区分与周边另一个族的区别),但再往里分析,则是一种族群认同。你的文化(包括对历史的记忆),不过是为了建构或者维护某种认同时的工具。认同是流动的,所以,民族的文化表象也是会改变的。
这种现象,以及对认同的强调,是《华夏边缘》这本书的理论背景。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王明珂用3章的篇幅描述了当代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及民族史研究中的边缘理论。王明珂是一个十分前卫的学者,很有理论野心,所以,他想从这些不同领域的理论中总结出一个体系,用来解读中国复杂的民族历史。
简单说来,王明珂的理论背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认为民族(他用族群这个概念)是一个认同现象,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追溯下来就有着某种本质的共同体。他把这个观念带入到历史研究中,就得出与过去很多民族史学者不一样的发现。
另一个是认为历史材料不是客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物。找到真实的材料,证明历史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并用来描述民族历史的细节,是传统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但王明珂认为,民族史的材料,在客观性之上,还有一个认同的因素,认同有主观的一面,所以,经常有“造假”。他把历史材料,视为历史记忆,而历史记忆可以因情景、因认同而改变。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王明珂对传统历史材料的解读,又显得与众不同。
王明珂对羌族的研究,最初是想要解构羌族,认为它是一个被创造的民族。但是在田野调查之后,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初衷。在不久前,上海的一次讲座上,他再次举了在田野中的一个例子。
他在川西北做羌族的调查,有一次访问一位老人。老人讲他们的村寨常常生活在一种恐惧中,因为总是怕下游的汉人和上游的“蛮子”来欺负他们,这个老人就讲了很多过去的暴力故事,然后突然笑着说道:“那是因为过去没知识,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民族。”王明珂说,“大家现在听了很好笑,可是我当时听了寒毛直竖,我在干什么?难道真的需要解构这种概念和知识吗?”
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民族以及如何看待它的历史,王明珂提到的这个故事,已经提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来认识我们今天的民族,来理解我们今天的民族工作,如果创造历史是一个中性词,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今天,我们今天做的应当就是创造历史。
(责任编辑 赵芳)
王明珂是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学生,所以对考古材料十分熟悉,他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北方考古材料反映出的这一重大变迁。这些材料,有一部分被苏秉琦用来证明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但这些考古遗址背后的人群,后来如何成为中国人,苏秉琦并没有涉及。而王明珂刚好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