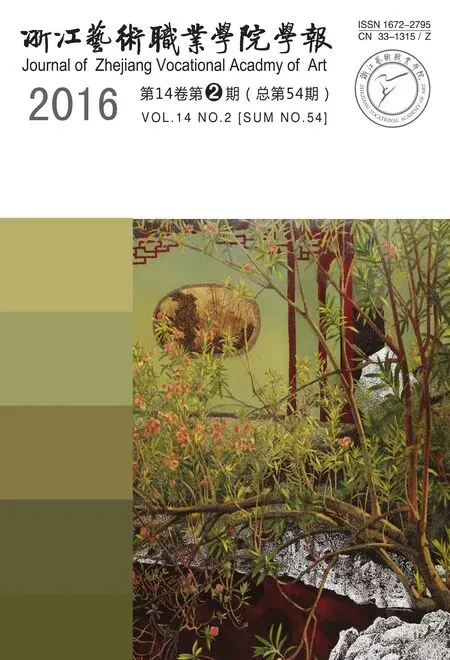中国民间剪花的当代活化与设计路径∗
王 怡 陈 青
中国民间剪花的当代活化与设计路径∗
王 怡 陈 青
中国民间剪花其艺术语境的缺失是当下中国都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之一,如今对其在 “与古为新、中体西用”指引下,以设计的观念驱动进行活化与都市再生成为了有效路径之一。在此从视觉传达设计实践角度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剪花艺术形式,通过最具民众基础的 “设计”的方式,展现其置身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 “新民俗”,实现剪花通过视觉活化与创新设计回归当代中国民间、都市再生的可行性策略。
民间;剪花;活化;设计;路径
剪刻镂花在中国具有千余年的历史,伴随着造纸术的改进成就了剪花这种以薄材镂空为主要手法的艺术形式所独具的魅力。民间剪花是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民俗生活中自发创造、流传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民众乡土生活的一部分。剪花从吉祥题材、民间创作、器物运用等方方面面都浸润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与农耕生产方式中,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剪花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显著 “中国风”指向的形式语言。如今,随着外部大工业时代机器生产的普及加速、全球一体化的兴盛以及中国内部三十多年间持续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1],导致了以剪花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生长土壤日趋贫瘠的不争事实。
梳理中国民间剪花的发展流变不难发现,身居 “传统”的剪花在千年历史中一次次为顺应时代与时尚而不断有机更新,彰显其形式与风格变化过程中的主动适应性。如今剪花在主动适应的转化过程中,也存在着极具当代价值的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一、中国民俗剪花之新 “困境”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国内学院派艺术家一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长期被机械化生产、现代化生活方式边缘化了的民俗剪花艺术保护与传承工作。综观中国当代民俗剪花现状不难发现,生活于学院派中的造型艺术家们,往往视民俗剪花为 “民间艺术”或 “文化遗产”[2],但在以 “文化遗产”冠名下的对中国民俗乡土剪花侧重 “保护性”的传承,也逐渐展露出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3]。
首先,如今在造型艺术家占据话语权与风格主导的学院派中,去竭力塑造源于乡土民俗的剪花可能性有几多?乡土剪花艺术是中国基层百姓 (多为农民),依照千百年形成的自然生活方式,选题上大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形式上不拘泥于技法限制的自发性创作与装饰。而今其民俗与乡土的精神本质是否能在学院派的氛围里真正被艺术化的创作出来,并追随民俗剪花的精神本质传承下去?当今学院派与民俗乡土剪花联袂的成果,大部分是以西方造型语言占主导的、纯艺术化特征明显的当代视觉艺术作品,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俗乡土剪花质朴的装饰语言体系,以及其中作为最广泛群众基础的 “民”在此则无意中被弱化了。其次,当代众多由学院派艺术家创作的、纯艺术化了的剪花与中国快速消费市场并无直接接轨,原本民俗剪花的 “民”或群众基础,在上述当代艺术作品中通常所剩寥寥。可以说,当代学院派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是中国民俗剪花在当下艺术化了的 “再生”可行路径之一,却因侧重点不同,缺失了与当代最广泛都市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众基础这一先天缺陷,尚不足以成为主流,或许无意间促成了当代民俗剪花发展的新 “困境”。
二、当代民俗剪花之时尚际遇
民俗剪花的当代活化与设计,势必需要与当代都市生活紧密相关的 “时尚指向”、“设计驱动”等为关联词,寄望于 “设计”这层在观念上区别于 “美术”而显得中立与局外的定位,传递出有别于 “民间艺术”之外的当代都市意义,强调的是设计师作为当代民间艺术的非当事人性 (并非是一个传统的、来自民间的艺人)对剪花艺术进行基于当代中国都市化语境下的、落地的视觉活化[4]。以此将经过设计后的中国传统剪花,平行放置于全球跨文化时尚,体现其在当代的社会性。
民俗剪花在当代的社会性更多的指向剪花作为中国典型民间艺术中的个体,在如今全球化、都市化语境下进行设计活动时所表现出的个性,其特征更多的是由剪花背后的文化基因所塑造。剪花承载的民俗乡土文化是由历代中国人在漫长时期内逐渐形成的观念、行为、风俗和习惯,表现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知和反馈。剪花经过了从原始社会初生到明清时期鼎盛上千年的实践探索和审美经验积累后,形成了稳定、独特的内涵与审美情趣。因此民俗与乡土的文化基因是贯穿并承载剪花当代社会性的重要支点,无论是学院派造型艺术家或是当代中国设计师均在以其文化基因为支点、剪影镂空为形式路径的指引下,探索剪花的当代视觉活化设计建构方式。
时尚为指引即指向与时代同步、以民俗剪花为入口则为当代中国都市时尚的更新、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积淀与传统审美支撑,同时在当代 “中国设计”指引中、“优雅的文化设计”为诉求目标下,亦为民俗剪花的当代设计活化与再生提供了际遇。
剪花作为典型民间艺术形式隶属于中国传统造物的设计实践活动,是历代中国人主动适应和尝试驾驭客观世界过程中,力求达到 “手脑合一”的高级活动之一,其历经的题材、风格、技法变化体现了剪花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历来对当时当地 “时尚”的积极融合与主动适应[5](表1)。

表1
如今剪花在 “中国设计”的大时代背景下,凭借其独特的剪影镂空形式语言,加以时尚的风格、当代形式达到吸引观众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
首先,鲜明的文化识别性。现代主义设计风靡直至当下全球产品日趋雷同这一现实,使得具有差异性与文化感的设计产品成为了吸引观众的第一要素[6]。就当代艺术或设计作品而言,人们需要首先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随之引起关注才会主动深化认知。剪花因其色彩、镂空、材料等形式语言优势,天生具备鲜明的文化识别性 (图1)。

图1
其次,催生情感认同。情感首先由文化识别感激活,引发记忆和想象得以强化。伴随着不同情感从激活到强化,对设计作品的文化认知也从注意阶段,转向更具价值观取向的喜爱、厌恶等情绪的产生阶段。由于多数中国民间剪花的吉祥题材在当代,具有跨文化的高度认同,因此更容易获取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情感交流,也为当代中国剪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先天的基因优势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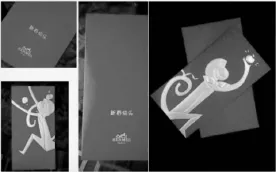

图2
最后,当代方式解读。对剪花的当代解读势必结合时代语境,在此即为当代都市化语境下的时尚、流行与审美。进一步而言,时代的语境不仅包含审美选择,更应涉及当代中国都市生活方式、时代行为模式等,加以创作与设计协同创新合力完成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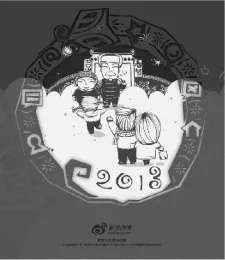

图3
基于上述以民俗剪花为切入点的活化设计而言,强烈的文化感是设计创新的重要源泉、各类时尚语言与媒介是其活化路径,以此形成时尚与传统剪花在似与不似之间彼此依存。
三、基于当代时尚的优雅设计
现代设计中对审美价值的实现可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 “美”的实现,之后是 “雅”的实现。而诸多现实案例证明,并非所有 “美的设计”都能达到 “雅的设计”,却只有将 “美”和 “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另一境界的 “优雅”。“优雅”属于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底蕴深邃的美,也是一种与时代和谐但又卓然而立的 “雅”。民俗剪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表征,糅合当代都市时尚审美选择进行视觉设计,凭借其文化的 “特殊符号”放置于全球设计产品中,是突显其在当代全球化趋势下优雅的 “文化个性”有效路径之一[7]。
在中国民俗生活上千年洗练中,剪花图式语言俨然成为了一种生命体,存活在使用中、发展在创新里。较之那些随着时间洗涤而没有被当代沿用的传统文化语言,剪花这一 “生命体”只有主动的在当下中国都市生活语境中做出适应性的设计调整,因地制宜的融合当代都市时尚,借时尚之名解封继而活化再生,才能依照其文化逻辑生生不息。
同样,为达到当代的 “优雅”从而对民俗剪花进行时尚解读与设计时,尚需从以下四个原则或方面考虑:
首先,新颖原则。创新是民俗剪花时尚设计的首要原则,民俗剪花的当代解读发迹于重构剪花文化元素之中或元素之间的原有关系,经过设计使得剪花元素的外观属性、意义属性或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异化或强化。新颖即可从新感受上产生,也可从传统的感受上传达新情感或产生新理解,但是传统元素和创新元素之间需要合适的平衡比例,控制新旧之间的视觉对比度,掌握适度 “似与不似”之间的分寸 (图4)。


图4
其次,清晰原则。将传统民俗剪花放至中国当下社会语系进行再设计时,如采用多种寓意,则它们之间的协调应有主次、对比、共鸣之分,从而显得特色鲜明且审美价值取向清晰,不至于引发认知与审美的混乱。协调既指向传统与当代形式之间的协调,也指向形式与寓意、情感之间的协调 (图5)。



图5
再次,准确原则。以民俗剪花为设计起点的作品必须饱含准确的情感及寓意指向,准确是深刻的基础,深刻为准确的前沿。同时,“深刻”还可能为寓意准确带来意想之外的创新惊喜。将民俗剪花作为文化元素而进行的时尚设计是一种有目的的再造,设计手法可以是置换、解构重组与隐喻等等,均能为当代中国都市化语境中、文化变迁下的民俗剪花带来新的时尚际遇。
最后,节省原则。基于节省能有效地提高视觉形象的鲜明度,增加关注度和情感的强度,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此,节省特指通过时尚设计后的剪花以多样的视觉形象去激发中国当代都市人群最丰富的情感与提供最丰富的语义。
四、结 语
就广义上而言,对于中国民间装饰艺术形式的当代活化与再生问题,前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主张:民间装饰艺术在当代的再生设计,很大意义上是在设计过程中对 “度”的衡量,即设计之 “度”。确切而言,活化与再生在当代需做适度的设计且不可过度,其学术性的高下也显示在对 “度”的把握上。
作为中国民间装饰艺术形式之一的剪花,自南北朝发展并推演至民国,迄今却没落到亟需抢救的边缘,追本溯源很大程度上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 “文革”,以及随后改革开放下经济外向型发展所引发的连带对 “度”的判断标准缺失,今日我们通过时尚与设计的重塑,理应是再一次对 “度”重新审度与把持的过程。
对于中国民间剪花的当代活化路径与设计研究,其根本是通过研究让原本 “民间创作”、“世代传承”为主体的剪花手工艺,在当代转向于 “都市时尚”为目标、“设计语言”为主要手法的创新实践。研究的基点在于 “文化”二字,通过设计语言将之 “时尚再造”,改变一贯以来民间剪花作为文化遗留物的风俗,使本土知识体系下的 “乡土”在中国当代社会都市化语境中传承并遵循原有的逻辑生长、发展。换言之,剪花以设计的名义 “再生”,是将源于西方 “创造物化美”的设计方法嫁接于 “创造心理感悟”的东方审美之中。在本源上,以设计的名义将中国民俗剪花艺术于都市 “再生”,使得民俗剪花落地于 “民”,并且遵循当下的逻辑生长。
[1]薛晓芳.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递嬗:基于文化构成角度的解读 [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60-63.
[2]乔晓光.空花·剪纸研究与创作 [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3]王雪.制度化背景中的剪纸传承与生活实践 [D].中央民族大学,2011.
[4]李松.作为文化多样性符号的中国民间剪纸:兼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和国家意识 [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5]陈竟.中国民俗剪纸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金晖.剪纸艺术:从传统到当代语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4).
[7]潘云鹤.文化构成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黄向苗)
Rejuvenation of Paper Cutting Trend Based on Contemporary Design
WANY Yi,CHEN Qing
The loss of contents of paper cutting patterns is an unavoidable real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The rejuvenation of paper cutting trend based on contemporary design thinking should be one of a positive pathway.The study constructs on the above pathway with direction of“Utilization of West in Chinese Form”,in order to create a fresh image of contemporary paper cutting which is fitting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market nowadays.
folk custom;paper cutting pattern;rejuvenate;design;pathway
J528.1
A
2016-02-02
王怡 (1981— )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视觉传达设计研究 (杭州310015);陈青 (1963— )女,陕西西安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间手工技艺发展研究 (上海 200444)。
∗本文系2016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项目 《大运河 (杭州段)剪纸时尚有机更新策略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Z16YD035);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民间手工技艺发展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6BSH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