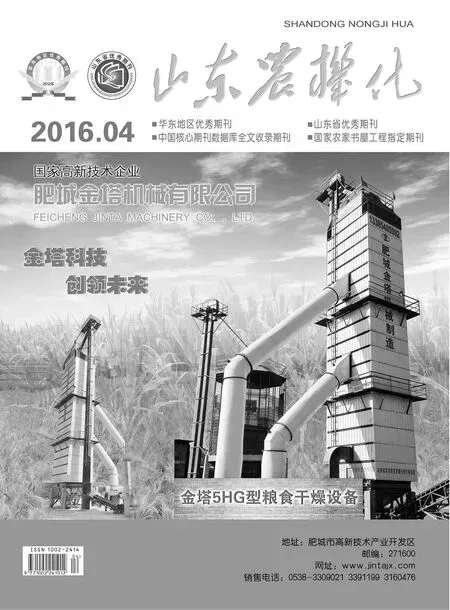牡丹寻芳:国运昌时花运昌
牡丹寻芳:国运昌时花运昌

“绝代只西子,众芳唯牡丹”。自唐朝“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景,到宋朝文人连篇累牍的牡丹谱录,牡丹以王者气象,成为盛世图景的绝佳点缀。兰州大学历史学者杨林坤,专门点评宋人牡丹谱录,重新编著《牡丹谱》,花景伴随时景移,一条牡丹寻芳之路清晰呈现。
唐代繁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在中国历史上,牡丹最初在荒野寂寞开放。
唐朝舒元舆作《牡丹赋》,发出惊疑感慨:“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伟乎,何前代寂寞而不问,今则昌然而大来?”这么瑰丽的花卉,为什么唐代之前却默默无闻?上古时期,并无牡丹之名,牡丹与芍药通称为芍药。秦汉时期,牡丹才以木芍药之名,称闻于世,根皮纳入药材类目。
舒元舆《牡丹赋》行文工整,是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咏颂牡丹辞赋。他写道,武则天时期,“天后之乡西河(今山西汾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此后牡丹从皇宫,经由士族门第,向寻常百姓家传播。武则天大兴佛寺,而牡丹与佛教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唐初佛教的经典和仪式上,都曾出现牡丹的身影。
到开元盛世,牡丹名品迭出,盛于长安和东都洛阳。《西阳杂俎》记载:“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可见唐代的牡丹不仅花色绚丽,花型大气繁复,而且出现了复瓣重台牡丹。
电影《聂隐娘》中,晚唐时期公主下嫁藩镇,带白牡丹花遍植府邸。白牡丹花颜色高洁,花品名贵,更能衬托其皇室身份。这一象征意味浓厚的细节,在史书中有据可查。
开元末,裴士淹奉使幽冀,途径汾州众香寺,偶得一株白牡丹,甚为惊异,遂植于长安私邸,自此方有关于白牡丹的记录。当时牡丹之盛,从舒元舆的描写中可见:“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牡丹的栽培技艺随之日益精进。当时洛阳有一位宋单父,擅长种花,因此被玄宗召至长安,在骊山栽植了一万余株牡丹,红白斗艳,幻化多姿,被世人尊称为花师。
宋代谱录——观国之兴衰于园圃兴废
据1916年版《临沂县志》记载,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原有阳明寺。阳明寺中有北齐武平七年(公元567年)的石碑。寺庙殿前有一株牡丹,花盛开时,紫色花瓣,黄色花须,形状像荷花。花株下环绕着石栏杆,栏杆上刻字,有“大观庚寅(公元1110年),彭彬敬志”字样。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这株花仍然存在,花开花落七百多年,竟是一株宋朝牡丹。
宋人审美情趣普遍秉持清韵绝俗,相比唐朝的激情浪漫,更趋理性冷静。即便如此,宋人仍然没有摒弃对牡丹的喜爱。恰恰在两宋时期,涌现了大量记载牡丹的植物写作,有据可查的牡丹谱录超过20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爱牡丹,他曾经遍访民间,将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一一记录,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
那时,北宋西京洛阳栽培和欣赏牡丹成为一大社会风尚,“大抵洛人家家有花”。牡丹真正走进了百姓之家,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以繁育牡丹为生的花户。
北宋末年,洛阳因战乱而致使牡丹衰败,牡丹繁育中心转移到了陈州(今河南淮阳)。北宋灭亡以后牡丹繁育中心又南移到天彭地区(今四川彭州)。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兴衰;洛阳之兴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辽金时期,随着北京成为政治中心,牡丹开始在北京地区引种。元朝时期,牡丹名品寥寥可数,重瓣花朵几无可见。两宋时期的许多名贵牡丹品种正是在这一时期失传的,致使牡丹谱录在两宋与明清之间出现了明显断档。
明代广植——亳州牡丹数年百变
进入明代,亳州成为北方新的牡丹繁育中心。正德、嘉靖年间,亳州薛凤翔的先辈西原、东郊二公非常喜欢牡丹,走遍四周郡县,搜访上好牡丹名品,移植入亳州。从此亳州牡丹开始名扬天下,出现了“亳州牡丹更甲洛阳”的盛况。
亳州牡丹的最大特征是种类繁多,育植迅速。薛凤翔曾自豪地写下:“永叔(欧阳修)谓四十年间花百变,今不数年百变矣,其化速若此。”导致亳州牡丹育种神速的原因,是当地人掌握了牡丹种子繁育的奥秘和技巧对于牡丹常用的嫁接繁育是一次较大突破。
据《亳州牡丹史》记载,亳人“计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者”。每到牡丹花开之时,“虽负担之夫,村野之氓,辄务来观。入暮携花以归,无论醒醉。歌管填咽,几匝一月,何其盛也”。至隆庆、万历时期,亳州牡丹达到极盛。“亳中相尚成风,有称大家者,有称名家者,有称赏鉴家者,有称作家者,有称羽翼家者,日新月盛,不知将来变作何状。”
有明一代,不仅亳州牡丹盛极一时,安徽宁国、铜陵,江南太湖周围,西北兰州、临夏、临洮,广西灵川、灌阳等地的牡丹也有较大发展。
清代奇闻——曹州牡丹甲于海内
清代的牡丹繁育中心在曹州(今山东菏泽)。早在明代中后期,曹州牡丹就已经有了一定栽植基础,有“曹州牡丹甲于海内”之称。据《五杂俎》记载曹州一士人家,牡丹种至四十亩。
入清以后,曹州牡丹“新花异种,竞秀争芳……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至乾隆年间,曹州牡丹盛过亳州。《曹县志》云:“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
曹州牡丹名品,还成为了蒲松龄《聊斋志异·葛巾》中的女主人公:癖好牡丹的洛阳书生常大用在花园中巧遇一宫妆绝艳女郎,两人互生好感,眉目传情,喜结良缘。后葛巾又牵线将自己的妹妹玉版嫁给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其实葛巾和玉版,都是曹州牡丹的化身。
葛巾紫,花开紫色,楼子台阁型。此品花瓣非常繁碎,排列紧密,雌雄蕊全部瓣化。花冠硕大,状若紫云,是牡丹名贵品种之一。玉版白牡丹,单瓣,白色花朵。叶瓣纤细直长,像拍板一样,颜色温润洁白如玉,有深檀色花心。
而清代曹州牡丹之盛,不仅品种繁多,种植规模也蔚为壮观。当时曹州东北各村普遍种植牡丹,尤以赵楼、洪庙两地为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为了办理外交事务的便利,慈禧太后曾下懿旨,将牡丹定为大清国的国花。
(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