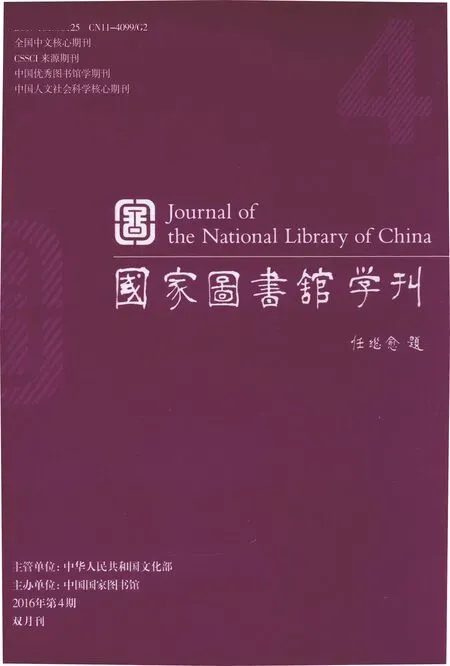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实践逻辑
刘爱华
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实践逻辑
刘爱华
图书馆转型发展具有自主性,更具有显著的受动性,脱离不了图书馆生存环境的变化。探讨图书馆转型发展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发展自身,图书馆服务供求间的矛盾和数字环境带来的机遇,构成了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经理性辨识,其功能定位就在于:知识协同创造服务平台。这种功能定位既构成了图书馆转型发展的方向性规定,又预设了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跨界合作为突破口。图2。表1。参考文献44。
研究图书馆 转型发展 数字环境 知识协同创造 跨界合作
1 引言
OCLC 2010年的报告《研究图书馆:危机与系统化变革》指出,研究图书馆面临着价值受质疑、技术落后、馆员服务能力欠缺等重大灾难性危险[1]。2011年,Rick Anderson在《研究图书馆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以馆藏为基础、以解决“信息稀缺”为目标的研究图书馆的传统组织结构、业务实践以及观点,将走向一个死胡同[2]。近年来,图书馆转型问题在国内也引起广泛关注,如张晓林[3]、初景利[4]、吴建中[5]、朱强[6]等在充分肯定研究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基础上,均对图书馆转型进行了宏观层面的论证,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支撑和理论基础。图书馆转型既是图书馆行业实现自身整体进步的必经过程,也是回应环境变化、理解用户需求、完善自身构造的必然选择。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图书馆不仅遭遇了因生存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倒逼”问题,而且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背景下,面临着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双重焦虑”。因此,在转型研究中,最缺乏的并非是宏观指导,而是具体思路的建构,尤其是逻辑关系的梳理。当前,探讨图书馆转型发展,需要明确三个具有逻辑关系的基础性问题,即逻辑起点、功能定位和战略突破口。逻辑起点是基础,功能定位是方向,恰当的战略突破口是保障转型道路不受阻的切入点。
2 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
研究图书馆(以下简称图书馆)作为学术环境中重要的服务机构,自然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系,相应地,必然有其逻辑起点。其转型的逻辑起点可以理解为建构和开展图书馆转型实践的初始环节,孕育于转型过程中的服务供求矛盾建构功能的发挥和数字环境中机遇的把握。具体而言,数字资源和移动图书馆的应用淡化了图书馆物理空间的价值,从而推动了图书馆空间再造;科研服务嵌入协作的牵强和低层次,用户在新科研信息环境下对弱信息、战略性阅读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呼吁与之相配套的动态能力的提升;以职能为线索的组织机构部门化设置,无法支撑服务创新新常态下的驱动力转换,从而催生以任务为线索的组织机构团队化设计。此外,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为图书馆服务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1 充分发挥服务供求矛盾的建构功能
2.1.1 移动获取盛行下的空间再造
数字化转型加速了纸本资源的边缘化,强化了用户对电子资源的依赖。尤其是随着移动图书馆实践日趋成熟,图书馆已掌握在用户“手”中,用户的资源与服务诉求只需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持终端便可满足[7]。再加之各种信息服务机构、数据库商和搜索引擎在信息服务市场中的强势进入,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地位日渐衰落,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之一是图书馆原有空间功能的逐渐消退。也正是这种消极影响造就了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可能,为图书馆特色空间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余地。传统图书馆空间定位于储藏文献资源的物理实体,总体上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以藏为主”到“以藏促用”两个重要阶段。图书馆的这种空间功能忽略了“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成长性,限制了空间转向的广度,从而压制了空间这一图书馆特有资源的显示度和影响力。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预言:现代社会,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8]。空间再造是最大化发挥图书馆空间的场所价值和服务价值的根本出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图书馆对空间再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美国费耶特维尔免费图书馆“神话般的实验室”的创客空间[9],查塔努加公共图书馆的“测试厨房”[10],以及玛丽华盛顿大学辛普森图书馆的数字彩绘、T恤制作和迷你可乐瓶打印等创客项目空间[11];我国上海图书馆以“激活创意、知识交流”为核心理念的“创新空间”[12],长沙市图书馆为实现科技、文化、创意等元素交汇而打造的“新三角创客空间”[13]等。
图书馆空间再造,首先应在理念上将图书馆空间上升到资源的高度,从资源化的角度来理解、管理空间。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指出,空间资源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14]。笔者认为,图书馆的空间资源主要包括三部分,(1)空间物质资源;(2)对物质资源进行优化设计的空间布局资源;(3)在前两者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和功能定位而形成的有助于空间范围拓展和重复利用的空间广度资源。空间物质资源突出的是空间的物质性,空间布局资源强调的是空间中物质的分布状态和位置关系,而空间广度资源注重的则是为使空间资源可持续利用而进行的开发管理。其次,在定位上需明确空间再造并非是对图书馆物理空间的“推倒重来”,而是在既有空间格局基础上,通过功能设计和布局调整以及对空间功能的重塑,实现图书馆物理空间从馆藏存储地向协同创新、信息交互与共享、创意思考的“第三空间”转向。这里强调的是空间在功能上的再造和空间再造的资源节约性。最后,在思路上应着力于空间的功能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空间功能的融合设计,如传统藏借阅功能空间与休闲、交流空间的融合。空间功能的融合应具有灵活性,在不同时期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组合。二是空间功能的开发。在用户需求调研基础上超越传统空间功能,沿着综合化、开放型的功能方向,探索空间的新功能,如创客空间、展示空间、创意与协同创造空间、体验空间等,以此充分体现出空间的场所价值和服务价值,提高空间生产的效率。此外,为保证空间价值发挥的最大化,不仅应持续对空间资源质量进行科学评估,还要注重对空间资源的宣传与营销,从而不断提升图书馆空间资源的影响力。
2.1.2协作化嵌入服务模式下的动态能力提升
当前,信息和科研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科研范式向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转变,创新模式向自主型、交叉融汇型、转移转换型和具有战略性转变。同时,创新的实现更需由合作交互,向多向的、多样化知识相互激励并创造新知识的方向转变[15]。面对科研创新的这种挑战,用户的信息需求变得混沌化、复杂关联化和动态化,用户对“弱信息”[16]的需求愿望日益强烈。不仅如此,用户更倾向于获取面向科学发展结构、科学前沿与趋势以及科学问题解决路径等方面的信息,对“战略性阅读”[17,18]需求十分迫切。在这种科研创新环境和用户信息需求变化的挑战下,协作化嵌入的服务支撑无疑是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要着眼点。正因如此,馆藏阅读空间转向合作学习、合作研究和交互式传播空间的趋势已经出现,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Research Commons[19]。
自学科化服务和知识服务研究开展以来,嵌入式、协作化服务模式就一直被众多学者和实践者所重视,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服务能力有所欠缺。这种能力不能仅局限地定位于可通过规范化学习或者培养、引进等方式形成的学科专业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对瞬息万变环境的识别、适应与利用能力,对动态变化数据的整合与关联挖掘能力,对用户实时所需知识的辨别、理解甚至预测、引导,以及持续供给能力,这实质上就是企业界提出的“动态能力”。1997年,Teece以战略资源观为基础,针对企业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认为动态能力是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并脱颖而出的关键[20]。面对转型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图书馆应建立一种在主动预测外部环境和科研需求变化规律基础上,自觉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机制,并将这种机制以规范化的程序、完善的制度等形式,内化为图书馆应对转型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长效的、持续的、以动态性为特征的能力开发与培育机制。国外管理学界学者对动态能力的内涵给予了丰富的研究(如表1所示),可为图书馆动态能力的构建提供参考。

表1 动态能力的构成[21]
根据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研究图书馆动态能力是指图书馆识别、适应、预测和利用内外部环境变化,并通过服务模式的改进、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跨界、跨领域的组织、协调和融合,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动态化、持续性满足服务需求的能力。图书馆动态能力的提升可概括为“一个面向,三个驱动”的指导方针和“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具体路径。“一个面向,三个驱动”是指面向开放,需求驱动、矛盾驱动和创新驱动。开放是指开放性创新,即以图书馆为主导,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整合外部资源的一种创新活动,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网络性、协调性和共享性等特征[22,23]。显然,开放式创新强调的是寻求资源管理与用户服务整个上下游链条中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盟与合作,如领先用户、资源供应商、技术提供商等。这种开放创新需要用户需求、矛盾建构功能和服务模式创新及管理的驱动。“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资源的识取、配用为中心,以学习能力、跨界合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建设为基本点。图书馆动态能力提升的关键是对包括馆藏文献资源、网络资源、用户资源、空间资源和图书馆人力资源在内的多样化资源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识别、获取,以及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学习和知识管理机制来提升学习能力,以提高工具使用能力、技术敏感和利用能力,以及管理协调能力;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提高跨界动态交互合作能力、支撑跨领域战略创新服务能力;建立有利于能力提升的管理制度,即以能力本位、能本管理和能力组织建设为核心的管理制度。
2.1.3 服务创新新常态驱动下的组织机构团队化设计
图书馆服务创新新常态并非图书馆服务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新常态强调的是图书馆服务进入了有利于创新加速的科研范式转变、技术泛在化和用户需求复杂性时期。这标志着图书馆服务创新进入新阶段,是图书馆服务创新驱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这种新常态是不可逆转和无从选择的,这就意味着图书馆服务创新发展必须回应图书馆生存环境的新变化,并充分利用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这种新常态是从“非常态”[24]向“常态”转变,即图书馆服务创新由封闭式、被动化和自主性向基于用户需求分析的开放式、主动化和协作性转变。从图书馆服务状态来看,这种新常态是从以往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即服务创新进入一个需求深度驱动、模式颠覆性变革和技术泛在化支撑的新正常状态。驱动力转换是服务创新新常态的本质原因和显著特征,而驱动力的源泉来自于以全媒体、全域网资源的管理以及数据关联挖掘和聚类分析为核心的资源发现,以集成化、标准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资源发现服务方法的创新和以弱信息、战略性阅读为核心的科研服务需求的满足。
资源、技术和人才是驱动力创造的关键主导因素,而充分发挥它们主导性作用的重点在于图书馆组织机构的柔性设计,其核心是摒弃部门化运作模式,向团队化管理转变;将传统以职能为线索的机构划分,变革为以任务为核心的团队设计。使组织结构由以职能为中心的、具有标准和稳定结构的部门式的单一模式,转向以任务为中心的、根据用户需求可实时调动和任意组合、具有多任务和多功能的动态服务团队模式。这种团队模式显著不同于以往结构化部门的等级式、线性关联,而是具有网状[25]、“超链接式”、联动的行动运作方式,从而形成面向任务完成的弹性、灵活可变的管理模式。团队化设计的前提是保持图书馆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图书馆组织机构的多模式运作,也即是宏观上起组织、协调作用的职能部门与面向一线服务的团队同时并存。团队组织的线索是面向用户需求的任务解决,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用户群体的服务需求对团队成员进行动态组合。各团队既要有自身明确的责任和边界划分,也需要通过知识交流、知识共享机制的调节,实现各团队的高效协作。团队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有效的学习与知识管理机制的保障,同时还需要图书馆领导层注重人才资源管理,由此发挥人才配置的最优化、人才效用发挥的最大化。此外,团队应是一种开放性的组织,既允许图书馆内部团队成员的交叉参与,也需积极争取馆外的跨界、跨领域成员,尤其是用户的加入。
2.2 把握数字环境中的机遇:大数据思维下的众源信息深度聚合
2.2.1 树立资源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大数据观
大数据与图书馆资源、服务的融合研究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Huwe曾撰文提出,大数据为图书馆用户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26]。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 Renaud、麻省理工学院的Britton等人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大学数字图书馆用户的行为进行深度挖掘,并帮助学校对学生阅读行为及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分析[27]。大数据对图书馆资源管理和知识服务的影响已达成共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数据这一媒介的联系下,这两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比以往更为显著:大数据思维下的资源管理助推深化、全面、精准知识服务的实现,而以大数据分析为手段的服务质量评估又为资源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面对复杂性、动态化的科研知识需求,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仅局限于关系断裂化的网络资源和文献资源已远远不够,包括图书馆OPAC系统在内的各种媒介留下的用户足迹及其之间复杂关系构成的众源信息,均应被囊括在图书馆资源管理范畴内。总体而言,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对象应包括网络资源、文献资源、用户资源和空间资源及其之间的关系(如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利用与满足关系、用户与用户间的关系等)。
大数据环境下,资源管理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资源采集、组织与价值发现的过程中。(1)树立资源采集的大数据观。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资源采集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图书、期刊、专利等文献型资源层面,而应拓展到与整个互联网的融通上。不仅包括以信息为对象的资源,如政务信息、社会聚焦信息、网络热点信息等,还需包括以人为对象的用户资源,如用户图书馆利用信息、用户行为信息、用户关系信息等;不仅要对上述资源的独立存在进行搜集,还需根据服务功能开发的需求对这些资源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揭示,并通过关联分析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再生产,从而产生综合类的数据资源。(2)树立资源组织的大数据观。以大数据思维深化资源组织的深度,使资源组织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源整序,更在乎的是对不同类型、异质型资源之间语义关联的建立。传统的资源整序仅仅是将采集到的各项资源,按一定编码形式进行整体性组织。而大数据环境下,应将资源以元数据为单位进行分解,也即首先进行知识单元的解构,然后根据分析的目的,重新进行语义层次的关联,完成面向需求的知识建构过程,从而实现根据资源使用目的,面向多类型、多层次的异质型资源的组织架构。(3)树立价值发现的大数据观。以往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如传统文献计量法)已无法实现对复杂结构的信息资源的分析,也不能深层次、全方位挖掘资源价值。大数据环境下,资源价值的发现更依赖于各种信息技术的使用,由此实现资源的关联与语义检索、资源内容的语义揭示、资源之间关系的聚类发现,最终为科学前沿跟踪、用户行为分析与预测提供高价值的资源支撑。大数据思维对知识服务的变革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产品的生产和知识服务模式的创新。信息产品一方面是指以数据库形式存在的知识服务产品,如知识库、方法库、推理库、战略库等智库产品[28];另一方面是指面向复杂问题解决的、经处理后的分析类产品,这其中不仅包括用户科研所需的信息产品,还包括用户行为分析产品。以此二者来评估资源价值、推动资源管理的高效性,并最终提供用户科研所需的信息和行为类资源产品。同时,这些产品的内容不仅应是一种实然的满足,更应是一种应然的预测,其服务模式应是一种自助式的、主动化的,并需在产品的经营上多下功夫。
2.2.2 众源信息的聚合思路
众源信息聚合是利用语义技术、关联技术、信息分析技术、信息检索技术等多种技术,将离散分布的各类型、各层次的同、异质资源按照语义关联予以聚集和整合,从而实现资源的深度揭示和价值实现。其目标是通过信息类、用户类和物质类资源的全方位聚合,建立起大数据资源与用户知识需求之间的最优匹配和最短路径,提高服务的精准度和智能化。肖希明、马张华等人提出了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的三个层次,依次为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整合[29,30]。笔者认为,众源信息聚合应是横向多维度、纵向层递式的立体化聚合框架(如图1所示)。
横向上,众源信息聚合应是一个时空相关的多维差异信息处理模型,将用户、图书馆以及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数据建立在由时间维度T、信息维度I和应用维度U形成的三维空间中。在对数据预处理基础上,通过一、二、三维聚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聚合,为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解决方案。纵向上,众源信息聚合应由具有递进关系的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数据层聚合。即针对图书馆内外部各类信息源(从图书馆官方网站、微博、微信、OPAC、进出门管理系统、科研部门等处获取到的信息,可视为图1中的数据源1、2、3……),以用户体验和需求分析为根本,进行数据聚合。第二部分为特征层聚合。将各基础数据源的首次聚合通过关联分析、特征融合、特征差异分析等方法进一步聚合分析,从而对用户科研行为特征和大规模需求以及重点用户进行分析与预测。第三部分为决策层聚合。以特征层聚合为基础,结合历史信息、专家系统、人工经验等,做出分类、推理、识别、判断等决策。根据图书馆发展战略目标和用户特征及需求分析,对图书馆职能战略、竞争战略、用户发展战略等各级子战略进行决策,以“用户需求”与“用户预期”为根本,生成决策模式。以上述三层纵向众源信息聚合为图书馆面向用户服务的功能转型提供决策支撑。

图1 众源信息聚合框架
3 知识协同创造服务平台:研究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功能定位
如果说对逻辑起点的认知与理解是思考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基础,那么伴随逻辑起点联动的功能定位,则是指明图书馆转型发展方向的关键。对功能定位的分析,是任何一个时期图书馆发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会随着图书馆生存环境的变化被反复提出并给予重新审视和回答。对新时期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功能定位是对之前历史的延续,过去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图书馆的功能定位经历了“文献资源收藏中心—文献资源利用中心—文献资源服务中心”,与此相对应,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沿着“文献检索与传递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不断升级换代。今天,伴随生存环境中的机遇来袭和挑战冲击,图书馆进入了转型发展期,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应是覆盖科研全过程的知识协同创造平台。
3.1 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造中的角色定位
3.1.1 科研活动中的知识协同创造模型
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将知识划分为主题知识(thematic knowledge)和非主题知识(unthematic knowledge)两大类[31]。主题知识是指“在言语行为中被主题化了的知识”,通俗地讲,就是与科研任务完成直接相关的知识;而非主题知识则是来自于生活世界的知识,能让主题知识的价值性感知更为直观,从而促进主题知识的理解与信服。现代科研活动中,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日趋普遍,为完成共同的综合性科研任务,研究人员借助自身不同专业背景,提出主题知识。但由于学科跨越性导致的话语体系差异,具有显著专业性的主题知识很难在科研团队中达成充分理解,此时只有通过来自于生活世界的非主题知识才能促进团队成员对主题知识的理解和共识。显然,相比隐性知识而言,非主题知识在描述知识协同创造机制中更具解释力。因为隐性知识关注的是表达维度,而非主题知识关注的是理解维度,它能够使科研人员在不同专业知识碰撞中达成共同的理解,从而推动知识的协同创造[32]。据此,可将科研活动中知识协同创造过程描述为四个阶段,即知识表述、知识解释、知识涌现和知识建构。在参考王馨一文的知识协同创造模型基础上[33],为揭示主题知识和非主题知识之间的关系、知识协同创造流程(process)及其中两类知识的作用关系,笔者将该模型的一维转换为三维,形成图2所示知识协同创造模型。

图2 知识协同创造模型
在第一阶段知识表述中,协同创造主体以主题知识表述为主,非主题知识表述为辅。此阶段的目标是尽量充分地将主题知识表述完整、透彻,而非主题知识可能是抽象思维的表达,也可能是具象思维的描述;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甚至可能是正确想法,也可能是错误认知。无论如何,此阶段最关注的是沟通氛围。第二阶段的知识解释中,为使不同专业知识能够在协同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理解,需尽量发挥非主题知识的解释力功能,因此,此阶段以非主题知识为主,主题知识为辅;在对主题知识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知后,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碰撞、冲突,进而激发各主体之间循环反复对话和反馈,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即进入了以知识涌现为特征的第三阶段。此阶段两类知识同等重要地参与其中,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在上述三阶段基础上,各主体在主题和非主题知识之间建立了有序联系,并达成更大范围的一致共识,从而使不同内容的知识在协同中实现知识建构这一最后阶段。
3.1.2 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造中的角色
知识发现技术不仅可以对主题知识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对选题方向的确定、课题路径的制定提供支持,对知识演进、突变、异变等进行监测,对知识资产的管理、知识使用的标准化和合理化提供决策咨询;也可以通过科学化的实证数据,为非主题知识的体验提供更为具体和客观的感知。通过科学数据分析开发的知识发展态势等特征表现类知识既是一种主题知识,也具有体验性知识的特征,甚至超越了这两类知识的功能,在整个知识协同创造流程的四个阶段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图2所示)。因此,应该说,图书馆通过图书情报方法的知识发现和构建物理与虚拟相结合的知识交流平台,在知识协同创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角色存在于整个知识创造流程的各个阶段。同时,这种媒介角色不仅体现在“软”的知识层面,也体现在“硬”的物理实体层面。图书馆可通过物理空间再造,在多层面、多角度为知识协同创造主体提供优质的空间资源,如针对科研形势、趋势等分析的研究室或沙龙,支持群体化知识检索与分析的实验室,有助于交互学习、合作研讨和成果展示的报告厅等[15]。
3.2 从门户服务到平台服务:灌输性推送向兴趣性吸引的转化
2010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Fulton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的调研发现,研究型图书馆己经倾向于利用系统或平台来为用户提供科研服务[34]。2011年的ALA年会上提出,在数字资源日益丰富、移动服务日趋主流的背景下,学科服务实践成功的关键有赖于综合学科服务平台的应用。最早系统地将“平台化”理念引入图书馆界的是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哈佛大学图书馆联合实验室的Weinberger,其在Library Journal上发文提出“作为平台的图书馆”[35]。图书馆平台化服务即是通过对服务和内容资源的广泛开放和科研交互、协作的平台化支持,不仅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和资源聚合,还为用户内容的再创造、为用户知识的自主贡献提供支持。正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Sherratt所言:门户是用来访问的,而平台是用来建设新服务的[36]。我国首先进行图书馆服务平台化研究的是夏翠娟、吴建中关于图书馆目录服务的平台化转型[37],虽着眼点局限于目录服务,但为图书馆平台化服务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作为资源和服务提供的门户,这是一种灌输性推送的信息服务模式。在此过程中信息以单向流动的方式流向用户,未能充分考虑用户的喜好和需求,从而导致服务效率低下,更不能有效嵌入到用户科研全过程中。而平台化服务模式,将用户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信息流动的方式是多向的。平台使用户的交互协作成为可能,同时还能在平台上建立社区,把具有共同兴趣和关注点的用户聚集到一起,实现其知识的协同创造。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社区建立无缝链接,将图书馆内外部资源与服务、资源与技术提供商以及用户进行深度整合,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完整产业链[38]。这将使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变革为兴趣性吸引,极大地提高知识创造的质量和效率,进而突显图书馆在知识协同创造中无可代替的功能地位,提升用户对图书馆的认可度、忠诚度。并以此形成良性循环,为图书馆在科研全过程中的嵌入树立威信。
3.3 图书馆平台化服务实现的挑战
图书馆平台化服务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开放数据、开放服务无疑是平台化服务内容的核心支撑。数据一旦是开放式的,就意味着数据的来源和内容是广泛的,不仅包括文献资源,也包括用户的使用数据,如用户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数据、用户在图书馆空间中时空维度的活动数据等;不仅包括结构化的资源,也包括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资源,如各种网络平台资源等;不仅包括图书馆内部资源,也包括资源产业链中所有相关者的资源,如资源提供商、技术提供商和终端使用者资源等;不仅包括可检索的资源,也包括需要深度挖掘的关系资源,如用户与文献利用之间的关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等;不仅包括平台自有资源,也包括用户创建的资源。这种大范围的资源获取与组织显然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如此,平台数据的开放性,还会受到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的困扰。尤其是用户资源,以及用户在平台中创建的数据,更为敏感。上述种种问题,均需我们在平台化服务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合理解决方案。第二,平台系统的架构无疑是平台化服务实现的基础,这需要科学的规划与顶层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对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如何利用感知技术理解科研需求,从而将相应的资源持续推送给用户;如何利用互联技术,将信息孤岛链接、整合[39],从而拓宽信息覆盖广度;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类资源进行组织、处理和深度聚合,从而提供知识发现服务等。
4 余论:发挥跨界合作的战略突破口功能
研究图书馆转型起步于逻辑起点,运行在功能定位的过程中,此二者构成了研究图书馆转型的基础和方向。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困难和阻碍。因此,从战略上探索一个破除万难的突破口显得尤为重要。跨界合作无疑能够发挥战略突破口的作用。百度百科中如此定义跨界合作:跨界合作(Crossover)指跨越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等范畴而产生的一个新行业、新领域、新模式、新风格等[40]。在图书馆界,跨界合作是图书馆为提升服务水平,弥补自身不足,与其他行业开展合作的行为。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需明晰。首先,合作对象应是图书馆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以往谈及图书馆合作时,通常着眼于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如联合编目、资源共享、图书馆联盟等。诚然,这种合作对于图书馆建设,尤其是图书馆资源建设大有裨益。但由于多为同质性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因此,更多的是在资源范围与内容的广度与丰富度上的拓展,而对于科研创新复杂性服务需求的满足作用并不明显。其次,合作对象的优势应是与图书馆发生作用后,对面向用户的服务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这其中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合作对象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是否是图书馆自身短期内、甚至长期内无法实现的;合作对象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是否适合于图书馆现有条件,或者对图书馆小范围改造可以适应,而不是大规模改造图书馆现有条件才能适应。二是必须对用户进行调研和实验分析。合作对象与合作内容的选择必须是以用户为主导,因此,用户应全程参与合作的组织与管理。最后,为保障合作质量,合作各方应是平等互利的,唯有此才能不断增强合作各方的兴趣,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如OCLC与各搜索引擎公司的跨界合作中,搜索引擎公司为自己的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内容,OCLC则通过搜索引擎提高了自身的资源利用率,这是一种双赢的行为[41]。
吴建中先生认为,合作是激活社会资源的关键[42]。2005—2007年,国际图联主席Alex Byrne倡导图书馆的合作理念,希望通过合作使图书馆更为开放。2008年,在我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年会上,“跨界合作”成为会议的焦点问题之一[43]。2014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在《大学与研究图书馆新闻》上发布了第三份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报告[44],将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概括为“更深度的合作”,其中提出了图书馆应与研究管理部门、资助机构、研究人员、数据保存者、期刊出版商等开展合作。可见,跨界合作已引起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现如今,科研服务需求的满足不仅需要更加广泛的资源,同时还需要更多智能化技术,就图书馆现有和较长时期的发展以及资源节约性要求来看,跨界合作无疑是图书馆未来发展中的关键战略突破口。后续研究中,笔者将对此进行深入调研与论证。
1James Michalko,et al.Research Libraries,Risks,and Systemic Change[EB/OL].[2015-10-08]. 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0/2010-03.pdf.
2Rick Anderson.The Crisis in Research Librarianship[J].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11,37(4):289-290.
3张晓林.研究图书馆2020:嵌入式协作化知识实验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1).
4初景利,等.在变革的环境中寻求图书馆的创新变革——美国七大图书情报机构考察调研报告[J].图书情报工作,2011(1).
5吴建中.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3.
6朱强,等.感受变革探访未来——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考察报告[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2).
7ACRL.2008 Academic Library Trends&Statistics [EB/OL].[2016-11-06].http://www.ala.org/acrl/publications/trens.
8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9Reeder J.Are Maker Spaces the Future ofPublic Libraries?[EB/OL].[2015-12-16]. http://www.shareable.net/blog/are-makerspaces-the-future-of-public-libraries.
10Goldenson J,Hill N.Making Room for Innovation[EB/OL].[2015-12-16].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3/05/future-of-libraries/making-room-for-innovation/.
11ThinkLab[EB/OL].[2015-12-17].http://umwthinklab.com/2012/09/06/umw-rocksthe-box/.
12曲蕴.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探索:以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4(10).
13黄思宇,等.公共图书馆成为“创客之家[N].中国文化报,2015-12-20(1).
14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J].图书馆杂志,2013(3).
15张晓林.研究图书馆2020:嵌入式协作化知识实验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1).
16Carole L.Palmer.Research Practice and Research Libraries:Working toward High-Impact Information Services[EB/OL].[2016-01-08]. https://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9742/researchpracticieslibraries. ppt.pdf?sequence=3.
17A H Renear,C L Palmer.Strategic Reading,Ontologies,and the Future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J].Science,2009,325(5942):828-832.
18张晓林.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5).
19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s Research Commons[EB/OL].[2016-01-08].http://commons.lib.washington.edu/about/description-of -research-commons.
20Vergne,J.P.,Durand,R.The Path of Most Persistence: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Path Dependence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J].Organization Studies,2011(32):365-82.
21罗仲伟,等.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基于腾讯微信“整合”与“迭代”微创新的纵向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2014 (8).
22刘勇.开放式创新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机制构建及实施策略[J].图书情报工作,2014 (21).
23Pénin J.Open Knowledge Disclosure:An Over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Economic Motiv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7,21(2):326-347.
24齐建国,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
25党跃武,等.开发支持知识服务的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组织管理机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
26Huwe T K.Building Digital Libraries:Big Data and the Library:a Natural Fit[J].Computers in Libraries,2014,34(2):17-18.
27Renaud J,et al.Mining Library and University Data to Understand Library Use Patterns[J]. The Electronic Library,2015,33(3):355 -372.
28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6).
29肖希明,唐义.国外数字资源整合在多领域的研究进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7).
30马张华.信息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7.
31Lafont C.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M].Cambridge:Massachusetts lnstitute,1999:81.
32王馨.隐性知识研究的困境和深化——兼论基于理解维度引入新的研究路径[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4).
33王馨.跨学科团队协同知识创造中的知识类型和互动过程研究——来自重大科技工程创新团队的案例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4(3).
34Fulton C.Library Perspectives on Web ContentManagement System[EB/OL].[2015-12-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631/2579.
35Weinberger D.Library as Platform[J/OL]. [2015-12-10].http://lj.libraryjournal.com/2012/09/future-of-libraries/by-david-weinberger/.
36Sherratt T.From Portals to Platforms:Building New Frameworks for User Engagement[EB/OL].[2015-12-30].https://www.nla.gov. au/our-publications/staff-papers/from-portal -to-platform.
37夏翠娟,吴建中.从门户到平台——图书馆目录的转型[J].图书馆论坛,2015(7).
38Andy Havens.From Community to Technology …and Back Again[EB/OL].[2015-12-28]. http://www.oclc.org/en-US/publications/nexts pace/articles/issue20/fromcommunitytotechnologyandbackagain.html.
39康晓丹.构建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思考——以上海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1).
40百度百科.跨界合作[EB/OL].[2016-01-16].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eXmI _glApqAfMerJ0dG-AOoJCuBarD27sU0U mhof-FyZ83L5pSk43nDaQN9kUxZlA0Vg7YQ_5OxM SozOb8jhsa.
41WorldCat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EB/OL]. [2015-12-25].http://www.docin.com/p-51292791.html.
42吴建中.开放交流合作——国际图书馆发展大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
43让跨界合作成为可能:2008年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年会召开[EB/OL].[2015-10-07].http://www.bengu.cn/homepage/nlc/olcc2008_xhsmb.htm.
44王春生.更深度的合作:美国ACRL《高校图书馆发展大趋势》解读[J].情报资料工作,2015(1).
(刘爱华 馆员 南京工程学院图书馆)
On Practical Logic for the Transi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Liu Aihua
Transition of libraries demonstrates not only autonomy but also strong passivity;i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mmediate basis of its living environment.The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library transition cannot be limited to library development itself: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digital environment form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ransition development.With a rational discernment we can find that,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lies in the platform of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reation.Thi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constitute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ransition development,and at the same time inherently presupposes that its strategic choice should start with crossover cooperation as breakthrough of transition development.2 figs.1 tab.44 refs.
Research Libraries;Transition Development;Digital Environment;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reation;Crossover Cooperation
2016-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