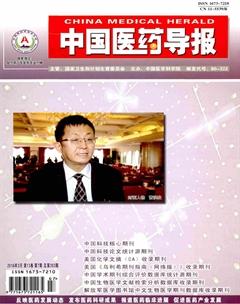腰椎内固定术后深部感染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雍坤 张贤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腰椎内固定手术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但术后不可避免地存在深部感染的潜在风险。虽然感染的发生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发生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且其诊断和治疗困难,预后也存在不确定性,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感染成为临床面临的严峻挑战。感染的防治要点包括避免诱因、诊断及时、用药合理以及常用的保留内固定疗法:清创冲洗负压引流、椎间隙抗生素灌洗、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臭氧水创腔灌注等,同时对内固定的保留和取出做出客观评价,尽量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率。
[关键词] 腰椎内固定术;深部感染;软组织感染;负压封闭引流技术
[中图分类号] R68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3(a)-0039-04
1.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3, China; 2.Wux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Wuxi 214071, China
[Abstract] Spinal internal fix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clinical pract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this operation, it has potential risk of deep wound infection inevitability. It is infrequently which may bring about a series of serious results. Because of hardly diagnosis and treating, uncertainty prognosis, 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of infection effectively has been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clinical practice. Key points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n including avoid causes, diagnose in time, rational use of drug, usual methods of reservation internal fixation: debridement, washing and negative pressure drainage, irrigation antibiotics in intervertebral space,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 ozone water perfusion in wound cavity. Appraising of reservation or move internal fixation objectivity. Reducing probability of infection and improving cure rate try our best.
[Key words] Spinal internal fixation; Deep infection; Soft tissue infection;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腰椎內固定手术已广泛开展,其涉及的解剖部位较深,存在术后切口深部感染的风险,感染一般发生于手术区域附近的肌肉、椎间隙、硬膜外等深部软组织,其导致软组织的炎性反应,甚至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猝死[1],成为广大学者面临的严峻挑战。本文阐述感染的诱因、诊断、治疗、预后及预防等,为临床降低感染率,提高治愈率提供参考,也为减轻患者痛苦,降低治疗成本,缓和医患矛盾提供借鉴。
1 易感因素
内因方面,相关研究指出高龄、营养不良、糖尿病、肥胖等[2]人群容易发生腰椎内固定术后伤口感染。高龄和营养不良是对患者的抵抗力下降角度而言,糖尿病、肥胖则是因局部皮肤血供较差而失养,进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3]。手术时间长、术中出血多、术中输血及引流管放置时间较长、内固定的放置不当、抗生素的使用失当等[4]为感染的外因。而手术时间长、术中出血多[5]、围术期的管理不良[2]与感染的相关性较大。为此在面对高龄、肥胖及糖尿病患者时应当提供更好的临床关注和护理[6],严格控制血糖,提供有效健康教育,精确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以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以尽量避免输血,选择合适抗生素有效控制感染的发生,可获得较高的临床效益和降低治疗成本。
2 分类、诊断
2.1 分类及发生率
可分为早期感染和迟发感染,然而目前对于其时间分界节点仍存在争议,通常以术后3个月、20周及1年等[7-9]作为标准。目前多以术后3个月暂为时间分界节点。早期深部感染的发生率为0.74%[10],迟发深部感染的发生率略高于早期深部感染,约为2.44%[11]。
2.2 早期深部感染的诊断
感染可出现在术后3 d以后,因围术期使用抗菌药物,即使感染也没有明显的体征,仅表现为体温不同程度的上升、伤口局部的红肿、渗出等炎性表现,血常规白细胞(WBC)、C-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指标的上升也可能不太明显[12],因此较难被察觉并重视。血清降钙素原(PCT)是近年来被用来监测和鉴别感染的新指标,研究发现腰椎内固定术后发热合并深部感染的患者PCT指标上升幅度较发热合并浅表感染的患者上升幅度高[13],但临床缺乏可靠对比,因此只能在鉴别感染类型方面提供部分指导意义,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当患者持续上述症状,并出现明显的疼痛、切口脓肿或窦道的产生,甚至内固定的外露[12],才会高度怀疑早期深部感染的可能。同时,血常规可见WBC升高并伴有中性粒细胞的增加,查血沉(ESR)、CRP均可有明显升高[14]。CRP的特异性最好,结合其他指标可以比较准确的评估及监测感染及感染的治疗效果[15]。早期X线检查可能无觉察相关异常,建议通过磁共振(MRI)检查以明确局部深部组织情况异常[14]。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技术灵敏度比MRI更好[15],但昂贵的价格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此外,对感染患者行伤口分泌物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大部分可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14]。因切口细菌培养为诊断感染的金标准,但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培养结果可能为假阴性[16],需要行多次细菌培养并寻找病原菌。早期深部感染患者通过B超检查可发现深部伤口有积液存在[17],此检查的优点在于能够明确积液所处的位置、体积大小,帮助引导穿刺抽液行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提高细菌培养率,还可以判定拔管时机。因此,早期深部感染需通过上述诊断要点及时明确。
2.3 迟发深部感染的诊断
感染表现为术后间隔数月出现低热或无发热,伴有切口处疼痛、腰痛,部分患者有伤口脓肿或窦道[18]。当出现上述症状,通常需要查血液炎性指标,而血常规WBC、CRP等指标变化却不明显[18]。X线检查可有内固定不同程度的松动[18],MRI检查则可发现病变部位的异常信号[11]。当出现感染迹象后,一般会给予行切口脓液细菌培养,但是往往培养不出强致病菌[18],甚至为阴性[11],这就为及时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增加了难度。迟发深部感染的发生率虽不高,但是在术后经过一段康复期后出现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即使血液炎性指标没有明显异常,也不能排除感染的可能性。
因此对可疑感染的患者需高度警惕并及时做相关检查,如果难以明确诊断,应积极分析原因,尽可能寻找相对可靠的诊断指标,以免延误诊断进而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3 治疗
3.1 抗生素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有统计表明深部感染的致病菌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又有17.8%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19-20]。2011年的MRSA相关感染疾病治疗指南[21]指出万古霉素等抗革兰阳性菌药物对于早期感染的治疗是十分重要的,结合利福平可达到较高的治愈率。早期可先经验性使用万古霉素,再细菌培养和药敏结果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使用利奈唑胺可以针对万古霉素耐药菌,使用替考拉宁则对革兰阳性球菌的抗菌效果较好[22]。也可先使用万古霉素或去甲万古霉素联合左氧氟沙星或头孢哌酮舒巴坦[23],等药敏试验结果更换药物,均可获得满意疗效。因此治疗上应针对性应用抗菌药物,但可疑感染者应及时用药,不可因等待培养结果而延误治疗时机。
给药方式采用抗生素先静滴后口服,但给药方式变更的时间点多有不同,目前国内[24]为发现感染到细菌培养结果未报告之前选择广谱抗菌药物,之后根据细菌培养结果选择敏感抗生素静脉注射至切口细菌培养阴性,当伤口创面80%以上被新鲜肉芽组织覆盖,体温、血常规等正常后3d才改口服抗菌藥物。而国外[25]则先使用抗生素静滴4~6周,在接下来的4~12周内换成口服的抗生素。还有先给予抗生素静滴后,当CRP和ESR指标下降50%且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考虑把静脉给药改成口服[26]。给药方式应通过积极观察患者全身及局部情况,结合辅助检查,用以指导治疗方案。
3.2 清创冲洗、负压引流
早期深部感染明确后,应第一时间彻底清创冲洗、负压引流,使创面保持清洁和干燥有利于伤口的愈合。俞兴等[10]采用此法治疗早期深部感染,治愈率可达66.7%。林旭[27]等也认为此方法的治愈率高达92.3%,其中对少数患者行清创引流后,发现引流液浑浊,培养仍有细菌,再次使用上述方法得以治愈。及时清除病灶,持续冲洗为此方法的关键。
3.3 椎间隙抗生素灌洗
因抗菌药物难以深达椎间隙等软组织病变的部位,深部椎间隙及其周围软组织的感染可选用此法。俞雷钧等[28]先对所有患者进行病灶清除,抗菌药物持续灌洗,根据患者症状在CRP和血沉指标改善后改为间断冲洗,经过治疗后所有患者均获得满意疗效。刘昱彰等[29]也用此法获得了较高的治愈率。及时清除病灶、在感染尚未控制前持续的灌洗量为彻底治疗感染的重点。
3.4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
VSD的作用机制在于负压使伤口和外界隔绝进而避免感染,同时持续的吸引可以不断吸收伤口分泌物,从而促进伤口的愈合[30]。国内学者[24,31]认为此技术能显著促进伤口的愈合,降低感染率,而且操作简单,疗程缩短,能减轻患者痛苦,降低治疗难度,治愈率极高。因此,VSD技术应该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3.5 臭氧水创腔灌注
臭氧能够促进伤口愈合,缩短愈合时间,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32]。有研究指出水溶性臭氧有着更为强力的杀菌作用,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种微生物[33-34]。目前治疗感染性创面以10 mg/L与20 mg/L的臭氧水效果满意[35]。国内已有用臭氧水有效治疗早期感染的报道[36],避免了取出内固定,治疗时间短,治愈率高,并发症少。此方法优点在于减少抗生素的使用进而减轻药物的副作用,降低治疗成本,缺点是对创腔内臭氧水注入的时间、注入量及引流管拔出的时间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3.6 内固定的保留与取出
目前大多数观点倾向早期尽可能保留内固定,原因是过早取出内固定可能导致腰椎稳定性下降或丢失。Kim等[19]发现,较早取出内固定后,2/3的患者腰椎前凸角角度减少和椎间隙高度下降,随访时发现多数患者出现因腰椎稳定性下降而造成的腰背痛症状。目前还是有学者在保留内固定的基础上治疗术后早期深部感染,并取得较高有效率[10,27]。保留内固定适用于可控制的感染及尚未完全建立稳定性的腰椎内固定节段。
另一种观点为取出内固定,原因是不取出内固定器械就不能清创彻底,残留病灶容易导致感染复发[37]。俞兴等[10]对术后早期深部感染难以控制的患者行二次清创取出内固定后继续冲洗引流,感染控制率达到66.7%。此外,MRSA相关感染疾病治疗指南[21]也建议迟发深部感染的患者在适当的时机取出内固定较好。迟发深部感染因出现较晚,通常腰椎内固定节段已经骨性融合,其恢复了稳定性,因此合适的时机取出内固定也是明智的。
4 预后及预防
深部感染的诊断和治疗较为复杂,预后存在着不确定性。轻者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完全治愈,重者则可能需要多次手术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应该理性的面对病情,尽可能的帮助患者减轻痛苦。同时,预防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尽量避免易感因素,比如及时做好患者术前评估,控制术前血糖,确保手术过程中的无菌性,缩短手术时间及减少术中出血量等等,其次是应加强围术期的管理,密切观察患者术后的症状及相关检查,如发现可疑情况需要高度警惕,如明确诊断需即刻治疗,最后对术后伤口的处理也要谨慎,保持创面的清洁和干燥有利于降低感染的风险。此外,对患者术后定期随访也很重要,可以方便经治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这对于迟发深部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是十分有必要的。
5 小结与展望
一旦发生深部感染对医生或者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敏锐、及时、果断、预防与治疗并重则是成功控制感染的关键。对需要行腰椎内固定手术的患者,在术前要做好术前评估和抗感染策略,感染一旦确诊,应尽早予以有效治疗,术后使用敏感抗菌药物,在控制感染的基础上对患者的内固定尽量保留。对于有些不取内固定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患者,应该理性、果断的取出内固定。同时需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告知患者术后有感染可能,使之有所准备并引起重视。对患者来说,一旦发生感染,取出内固定一来治疗费用高,二来再次承受痛苦,大多不能接受,因此保留内固定的有限抗感染治疗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方法,也有助于降低治疗费用、缓和医患矛盾。
由于深部感染的发生率不是很高,尚缺乏大样本的临床治疗病例,这也就意味着疗效的相对不确定性。最后,鉴于目前诊治的理念和方向,期望在本方面的研究能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未来能有更先进、有效的防治方法用于临床,为患者造福。
[参考文献]
[1] 王兆红,吴德慧,马超,等.腰椎管狭窄症椎体间植骨融合术后急性切口深部感染的处理[J].中国骨伤,2012,25(11):928-930.
[2] 陈映娟,原超.腰椎内固定术后伤口感染的原因分析及治疗策略[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5,30(1):104-105.
[3] Olsen MA,Nepple,JJ,Riew KD,et al. Risk factors for surgical site infectionfollowing orthopaedic spinal operations [J]. J Bone Joint Surg Am,2008,90(1):62-69.
[4] Schwarzkopf R,Chung C,Park JJ,et al. Effects of perioperative blood product use on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following thoracic and lumbar spinal surgery [J]. Spine (Phila Pa 1976),2010,35(3):340-346.
[5] 陈鹏,陈刚,朱国兴.腰椎术后感染的原因分析与治疗策略[J].临床骨科杂志,2013,16(5):506-509.
[6] 纪慧茹,张倩,刘春梅,等.老年腰椎管狭窄症患者伴糖尿病围手术期的护理[J].护士进修杂志,2012,27(12):1099-1101.
[7] Petilon JM,Glassman SD,Jr Dimar N,et al.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lumbar fusion complicated by deep wound infection:a case-control study [J]. Spine (Phila Pa 1976),2012,37(16):1370-1374.
[8] Wimmer C,Gluch H.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wound infection in posteriorspinalfusion with instrumentation [J]. Spinal Disord,1996,9(6):505-508.
[9] Di Silvestre M,Bakaloudis G,Lolli F,et al. Late-developing infection following posterior fusion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J]. Eur Spine J,2011,20(Suppl 1):S121-127.
[10] 俞兴,徐林,毕连涌,等.腰椎后路融合内固定术后早期深部感染的因素分析及治疗[J].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2013,13(6):433-437.
[11] 王清和,李士学.腰椎内固定术后迟发性感染3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8,8(1):127-128.
[12] 欧阳振,杨斌辉,刘丰虎,等.腰椎术后伤口早期感染的治疗体会[J].实用骨科杂志,2014,20(3):249-252.
[13] 王簕,杨波,尹飚,等.在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早期发热患者中监测4种血清感染指标水平的临床意义[J].中国骨伤,2015,28(1):66-70.
[14] 孟宪志,刘殿鹏,丁勇.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早期感染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2,19(24):187-189.
[15] Gemmel F,Rijk PC,Collins JM,et al. Expanding role of 18F-fluoro-D-deoxyglucose PET and PET/CT in spinal infections [J]. Eur Spine J,2010,19(4):540-551.
[16] Radcliff KE,Neusner AD,Millhouse PW,et al. What is new in the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of spine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J]. Spine J,2015,15(2):336-347.
[17] 黄开,廖永发,李振宏,等.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深部感染的诊治分析[J].中国临床新医学,2010,3(3):266-268.
[18] 張永平.手术治疗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迟发感染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12,16(32):4230-4231.
[19] Kim JI,Suh KT,Kim SJ,et al. Implant removal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fection after instrumented spinal fusion [J]. Spinal Disord Tech,2010,23(4):258-265.
[20] Mok JM,Guillaume TJ,Talu U,et al. Clinical outcome of deep wound infection after instrumented posterior spinal fusion:a matched cohort analysis [J]. Spine,2009, 34(6):578-583.
[21] Liu C,Bayer A,Cosgrove SE,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by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for the treatment of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J]. Clin Infect Dis,2011,52(3):e18-e55.
[22] 张志平,郭昭庆,孙垂国,等.胸、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深部手术切口感染的微生物学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47(2):358-360.
[23] 孟宪志,刘殿鹏,丁勇.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早期感染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2,19(24):187-189.
[24] 孙明举,高赛明,王艳辉,等.闭合式负压吸引技术治疗脊柱内固定术后深部创口感染[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2,22(7):665-666.
[25] Sierra-Hoffman M,Jinadatha C,Carpenter JL,et al. Postoperative instrumented spine infection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J]. South Med J,2010,103(1):25-30.
[26] Stoffel M,Stüer C,Ringel F,et al. Treatment of infection of the spine [J]. Adv Tech Stand Neurosurg, 2011,37:213-243.
[27] 林旭,譚伦,曾俊,等.保留内固定植入物治疗胸腰椎术后感染[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5,19(4):537-542.
[28] 俞雷钧,张春,刘宏,等.腰椎间盘术后椎间隙感染9例临床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1):2614-2616.
[29] 刘昱彰,张世民,董福慧,等.椎间隙灌洗法治疗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切口早期深部感染的疗效分析[J].中国骨伤,2012,25(10):866-869.
[30] 苗振林.VSD治疗骨科创伤感染的临床观察与分析[J].河北医药,2014,36(17):2645-2646.
[31] 郑亚东,白宇,陆生林,等.负压封闭引流在胸腰椎后路内固定术后早期伤口深部感染治疗中的应用[J].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2013,10(1):35-36.
[32] 谢鼎良,黎飞猛,姚传龙,等.医用臭氧治疗Ⅱ类伤口90例临床疗效观察[J].现代医药卫生,2014,30(4):553-554.
[33] 吴杭庆,王良喜,孙勇,等.臭氧水在深Ⅱ度烧伤创面治疗及抗感染中的作用[J].江苏医药,2010,36(2):148-150.
[34] 张桂祥,林修光.臭氧水稳定性与杀菌性的试验观察[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9):1772-1773.
[35] 余斌,黄华军,林庆荣,等.臭氧水对感染性创面内源性细胞因子含量的影响[J].实用医学杂志,2010,26(10):1719-1722.
[36] 刘永光,旷甫国,颜屈伦,等.臭氧在腰椎后路内固定手术后早期感染的治疗体会[J].四川医学,2014,35(8):1020-1021.
[37] Hedequist D,Haugen A,Hresko T,et al. Failure of attempted implant retention in spinal deformity delayed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J]. Spine(Phila Pa 1976),2009, 34(1):60-64.
(收稿日期:2015-12-28 本文编辑:苏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