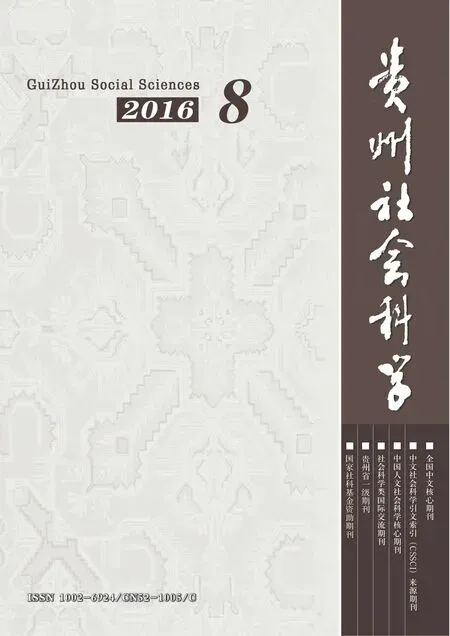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李亚娟
(1.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2.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李亚娟1,2
(1.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2.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湖北武汉430079)
我国民族社区具有遗产性、民族性和乡村性三重特点,伴随着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民族社区的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总结我国台湾地区自上而下的社区营造模式、泰国自下而上的第三方管理模式、新西兰政府主导的原住民经营模式和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体制下的合作管理模式,四种民族社区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通过旅游发展理念、旅游管理结构、旅游产业联动和旅游空间拓展等角度为我国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该类区域生态本底脆弱,生存环境恶劣,人地关系矛盾突出,致使劳动力大量流失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新世纪开放环境下,旅游业逐步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在提高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盲目跟风或“复制”式的乡村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以及日渐增长的游客量,致使许多特色民族村寨遭受着人为的破坏,加速了特色民族村寨的变异与消失。民族社区是少数民族群体与所处生态系统长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在研究如何维持生态系统、传承文化特色和保持地域价值时不仅仅是“选择”、“更新”,更是“挖掘”、“恢复”和“保持”。国外对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在旅游开发理念、旅游管理结构、旅游空间拓展和文化保护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文通过梳理不同少数民族发展现状,归纳总结了我国台湾地区、泰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模式,旨在为我国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提供经验借鉴。
一,台湾原住民社区:自上而下的社区营造模式
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多称“原住民”,人口为53.3601万人(截止2013年底),集中分布在台湾本岛山区高山密林和东部沿海纵谷平原以及兰屿岛上(见图1),约占据台湾总面积的45%[2]。清同治13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排湾族)致使日军侵台,清政府“开山抚番”政策打破了原住民与外界的隔离状态,推动了原住民与外界的联系。台湾光复以来,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3];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原住民为争取民族区域自治而斗争的活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关注“土著人”问题。国际大环境激发了台湾原住民的维权意识,在“正名运动”*正名运动: 1984年12月,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对族群的名称提出正名为“原住民”而示威游行,组成“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正名运动便为其中知名的一个,要求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以“原住民”代替“山地同胞”、“山胞”、“山地人”、“番仔”、“番人”等称呼。的基础上,原住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诉求,成为台湾当代最具民族性的“泛族群运动”或“泛原住民族主义”运动[2][4]。

图1台湾原住民聚集区
(一)“自上而下(top-down)”政府主导模式
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泡沫,大量年轻原住民失业返乡滋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行走台湾:文化就在社区里. 2013年07月11日,来源:人民日报.http://www.hellotw.com/twxw/shwx/201307/t20130711_853691.htm。如何发展原住民社区成为政府的重要发展问题。1994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首次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理念[5],企图建立社区参与的特色社区共同体。自1994年至2000年间,“行政院”斥资执行“社区总体营造”计划[6],其他部门也推出相关社区营造计划[7](见表1)。

表1 社区营造战略实施
(资料来源:总结自刘立伟[7],2008)
1998年台湾当局实施了《促进原住民地区观光事业之研究》,对原住民部落旅游资源进行盘点和摸底,改善内外部交通,对本地旅游从业人员进行职业训练。然而这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旅游开发模式,过分关注游客数量和经济效益的增加两个方面,忽视了原住民的需求,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破坏性的开发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8]。
(二) “社区营造”指导下的旅游发展模式
2002年,台湾“原住民委员会”对原住民部落进行重建和社区总体营造[9][10]。通过开发“原住民地方文化馆”和“主题公园”模式,开展台湾原住民部落营造,通过对保存性记录、记录性记录等民族形式进行开发[11](见表2),将民族节庆、民族景观、民族实体物件等融合在旅游活动中。

表2 原住民旅游资源形式和项目
(资料来源:巫铭昌[11],1999)
原住民地方文化馆是为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在“社区营造”活动基础上提出的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以“推展原住民族文化”为前提,将原住民馆建成社区文化中心,并规划临近配套旅游路线,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截至2014年底,已建成28个地方文化馆。在管理维护方面,“原民会”制定了“援助民族地方文化馆评鉴制度”,每年对28个地方文化馆进行评鉴,提出强化与调整的经营方案,并根据地方文化馆的定位、特色等方面进行评估与诊断,以落实地方文化馆政策的推动与整合(见图2)。根据《2013年度全国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馆活化辅导计划总成果报告书》,目前原住民地方文化馆已推出了“文化观光”策略,以原住民地方文化馆为核心,串联所在的社区,并结合地理范围内多个人文景点,强调“文化价值观光”、“在地自主受益”、“生活分享互动”、“文化认同与尊重”的旅游发展理念。原住民地方文化馆的打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3年底游客人数达到了120多万。

图2 2013年度办理“全国”援助民族地方文化馆活化辅导计划
二、泰国民族社区:自下而上的第三方管理模式
泰国旅游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60年,泰国政府已成立了专门的旅游促进机构(即现在的泰国旅游局)。70年代末,泰国旅游机构就开办了旅游训练所。80年代,在总理府之下设立旅游委员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旅游业已成为泰国创汇最多的行业,居首位。泰国北部山地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背景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一直是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泰国政府便寻求北部山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控制森林和人力资源等措施以建立稳定的农业经济体系[12]。当前泰国山地民族旅游方式可分为民族村寨游(Tribal Village Tour)、国家公园游(National Park Tour)和地方博物馆(Local Museum)。民族村寨旅游最早始于北部清迈地区,如今可接待游客的山地民族村寨已广布于山地民族地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多由森林覆盖区转化而来,多开展丛林游(Jungle Tour),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各府均建造了不同民族的博物馆。
(一)第三方(NGO)参与的旅游管理模式
泰国清莱府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依托于非政府组织Mirror Cultural Arts Centre(以下简称MCAC)。MCAC是当地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其最初的发展目标,旨在探索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使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将旅游业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该组织的经费来源多样,包括国内外捐赠者、网络募捐,以及艺术中心纪念品所得的收入。MCAC脱离政府和企业,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及公益性特点决定了组织对民族社区发展“以居民利益”为主的特点,为“自下而上”的基于社区的旅游开发模式奠定了基础。
(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旅游开发模式
清莱府Jalae民族旅游社区距清莱市区仅20公里,外部交通便利。该区域唯一的旅游吸引物是位于森林保护区的Huey Mae Sai瀑布,Jalae社区在通往瀑布的路上。背包客将Jalae社区视为服务中心。为留住游客,在社区居民的提议和MCAC的支持下,2005年Baan Jalae山地部落生活与文化中心和虚拟山地部落博物馆在社区内建立,作为配套旅游吸引物。
2002年,MCAC和山地部落领袖建立了以“基于社区的旅游发展项目”为主题的合作关系,Jalae社区被选为试点区域。根据居民意见,MCAC协助居民开办了在线旅游网络平台,涵盖了Jalae社区的历史文化、社区活动、旅游路线,还包括电子快讯和留言板讨论平台。通过民意调查,多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积极性较高。

表3 旅游收入居民所得比例
(资料来源:Theerapappisit[13],2008)
根据表3所示,参与MCAC组织旅游活动的社区居民可直接获得将近80%的旅游总收入(1040泰铢/1300泰铢)。MCAC组织帮助社区的行政和财务管理官员将所得旅游收益用于交通、通讯和其他运营支出。墨尔本大学博士PolladachTheerapappisit的旅游影响研究发现,Jalae社区这种第三方参与下“自下而上”的旅游发展模式以社区居民参与和获益为主要目的,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和游客的普遍好评[13]。
三、新西兰毛利社区:政府主导的原住民经营模式
新西兰的毛利人是土著居民中重要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北岛各地区。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毛利人受到冲击,人口锐减。新西兰自治后,毛利人民族权力获得了尊重,1987年毛利语成为官方语言。目前,已有超过80%的毛利人移居城镇,接受了西方文明,半数以上通用英语,欧化程度远远高于澳洲土著人[14]。
20世纪初,旅游业已成为新西兰最大的创汇产业,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亚热带海滩风光、阿尔卑斯火山地貌、独特的毛利文化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打造出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的旅游主题。作为土著民族的毛利文化成为贯穿新西兰旅游业发展的文化纽带,在塑造新西兰旅游系统的同时也强化了其文化地位。
(一) 政府主导下毛利语言的振兴
自1840至1974年,毛利人一直处于英国当局的民族同化合并政策下,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但该强制性政策引起了大部分毛利人的反抗,经过上百年的斗争[15](见表4),自1987年起,毛利语争取为除了英语之外的官方语言。截止2013年底,占全国人口3.7%的新西兰人讲毛利语,且以10岁-20岁的居民为主,趋于年轻化(见图3)。毛利语言的普及,特别是毛利语标语和广告的视觉效果,以及毛利语言符号的地标建筑等文化符号为整个国家创造了直观的民族文化氛围。

图3 新西兰毛利语使用者的人口比例

年份政策与活动措施1984-1974民族同化政策不允许毛利人居住在白人居住范围以外的地方1881土著人学校立法英语为教学语言,所有校内活动按照西方教学模式进行1955新西兰教育部与毛利领导人会谈毛利人首次参与制定全国的毛利语言教育政策1961新西兰政府放弃民族同化政策新西兰政府采取一体化政策,通过结合多民族文化策略代替原有的民族文化融合策略1963新西兰议会旨在保护古代毛利文化遗产和毛利人技艺的议案通过1987威坦哲法院调查国民普遍要求在法庭、教育系统、广播电视及公众服务行业使用毛利语,并成立了毛利语委员会1995毛利庆祝活动鼓励国民学习毛利语,正视毛利民族在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地位1997.10新西兰教育部多数学校将毛利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授2004电台政策国家拨款运营的毛利语电视台
(资料来源:Tourism New Zealand[16],2014)
(二)自然人文相结合的毛利旅游套餐
新西兰在发展毛利旅游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将毛利文化打造成旅游营销噱头,而是切实以文化推广的目的将文化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并依托周边自然旅游资源和农牧业资源,重视其配套开发,以达到自然人文相结合的目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毛利旅游景点是位于罗托鲁瓦(Rotorua)的毛利文化村(Maori Village),于1966年由毛利艺术和工艺研究所改造而成。从资源上讲,罗托鲁瓦不仅拥有南半球有名的泥火山和温泉区,还是新西兰重要的农牧区,同时该市丰富的湖泊资源为游客提供了大量的滨水游憩机会;从文化上讲,罗托鲁瓦是毛利文化的中心,也是原始毛利社会文明的诞生地。稳固的毛利家族、毛利社区、毛利部落和毛利环境构成了完整的自然文化生态系统。毛利文化村与法卡雷瓦雷瓦地热保护区紧邻,形成了完整的游览区,而且保护区收入可用以支持各类毛利艺术的塑造和传播,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毛利文化旅游区。同时,除了地热保护区外,毛利文化村周边还有多样的旅游景点和项目,以此弥补文化旅游产品的单一性缺点(见表5)。

表5 自然人文相结合的毛利旅游套餐
根据新西兰政府的调查,国际游客对毛利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基本保持一致[16],对于活动的质量、价格和安全性持满意态度,成为原住民旅游发展成功的典范。
(三) 以毛利会堂(MaraeAtea)为中心的旅游扩张
毛利会堂是部落居民聚会、接待外宾、举办大型节庆、宗教仪式的中心,每个部落至少要建造一个会堂,作为庆典活动及接待外宾的场所。毛利会堂以其独特的设计和民族符号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被称为毛利民族的博物馆。新西兰目前有毛利会堂1050座,作为典型地标建筑,也作为旅游业开发的首站,以毛利会堂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表演和宗教节庆仪式来复活原始毛利文化和文明。同时,多家旅游企业已与毛利会堂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毛利会堂住宿服务,让游客体验传统的迎宾仪式,体验原汁原味的毛利文化。该旅游项目受到国际游客的普遍欢迎[17]。
(四) 毛利民族旅游公司的发展
作为毛利文化的传承人,越来越多毛利族人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毛利族人参与旅游活动最早始于Ngāti Whare(毛利族部落名称)和Tūhoe iwi(毛利族部落名称)族人提供的“导游远足团”,毛利族人熟知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地理资源背景,使其在旅游业发展中树立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随着毛利民族地位的提升以及毛利文化传播的需要,由毛利族人开办的旅游机构逐渐兴起。随着旅游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毛利旅游机构招聘本族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活动,同时毛利族的权威机构毛利基金会(Ngai Tahu Maori Trust Board)也为毛利族人提供营运资金。毛利旅游公司由本民族居民运营管理,从毛利历史和文化符号的提炼到旅游产品的策划和推广均由毛利族居民全权管理,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毛利文化深度体验之旅,而毛利居民也直接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四、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国家公园体制下的合作管理模式
澳大利亚原住民主要指拥有传统土地的澳洲大陆、塔斯马尼亚、离岸岛屿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的岛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s)。自1787年欧洲人大批移民澳洲,导致冲突不断。1910至1970年间,澳大利亚当局采取了同化政策,导致了“被偷窃的一代”的惨剧*白澳政策:1910年至1970年间,澳大利亚政府推行了“白澳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近10万个土著儿童被政府强行从家人身边带走,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导致土著家庭骨肉离散。年长的孩子会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肤色较浅的土著孩子和混血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在长达11个月的土著受害者调查中发现,收养营中生活环境和条件恶劣,经常受到性骚扰。该项政策于1970年废止。,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当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加深,2008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开向原住民道歉,提高原住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作为澳大利亚文盲率、失业率和犯罪率最高的贫穷阶层,土著人问题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推出了多条经典的土著旅游路线(见图5),将旅游业作为保护土著文化、提高土著居民经济水平的手段。澳大利亚旅游研究中心(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 TRA)在调查的基础上,将文化遗产旅游的内容分为剧院、音乐会和其他艺术表演活动、博物馆或艺术馆、艺术或手工艺研讨会或工作室七类,其中历史或遗产建筑/遗迹或纪念、建筑博物馆或艺术馆类静态文化吸引物成为游客的首选,而土著遗址或社区遗迹的参观游客比例较少(见图6)。一方面源于澳大利亚当局政府对偏远地区和边缘岛屿的土著居民社区多采取保护政策。而针对澳大利亚大陆内部的土著部落,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内部的土著部落则采取保护性开发的措施。本研究以澳大利亚原住民集中分布的卡卡杜国家公园为例,探索景区内土著部落与旅游发展之间和谐发展的政策措施。

图5 澳大利亚土著旅游点示意

图6 澳大利亚土著旅游内容构成
(资料来源:澳洲旅游研究中心,2014)
(一)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
1979年卡卡杜地区被列入国家公园列表。公园的第一个管理计划于1980年颁布,计划承认原住民拥有参与管理的权利,但在公园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未能体现;1986年第二个国家公园计划中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Karadu Natioanl Park),15个成员中有10个为原住民,逐步落实原住民的参与管理权力;1991年,原住民参与并制定了第三个国家公园管理计划,正式成为计划的制定者,参与到决策层;1999年,第四个国家公园管理计划中以及对外旅游宣传中,将卡卡杜国家公园称为是“原住民的国家公园”,肯定了原住民的在土地占有方面的权利和地位;2006年,第五个国家公园管理计划中,原住民自身权利已完全认可,并确立了“合作管理”公园的理念,将原住民与白人统治者平等地归入管理层(见表6)。

表6 国家公园管理计划的演变
(资料来源:Eagles,P.F.J等[18], 2002)
(二)“合作管理”模式的深入
“合作管理模式”是土著居民和澳大利亚管理局一起参与并指定国家公园的管理策略和计划。作为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和土著文化的持有者,土著居民在管理国家公园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同时,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文化体验,确保原始土著文化的维持和延续[19][20]。
20世纪末,卡卡杜国家公园每年可带来上千万旅游收入,但1997年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其并未为卡卡杜区域的原住民带来巨大经济效益[21]。为此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社区参与的政策措施,加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活动的程度。在合作管理模式下,国家公园管理局从土地利益、资源使用以及原住民居住地建设等多方面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如土地利益方面,为原住民提供一系列雇佣和学习机会,鼓励外来商人雇佣原住民,以确保原住民从其拥有的土地中获取经济利益;资源利用方面,管理计划确保原住民可继续使用公园的自然资源。此外,通过对原住民进行就业培训,发展社区护林员加护等措施,使越来越多的原住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
五、结论与讨论
与台湾地区原住民地方文化馆和新西兰毛利文化村异地复建的民族社区不同,我国民族社区多是少数民族与其居住自然背景长期作用、相互影响下的产物,具有原住民生活场所和旅游资源的双重功能。我国目前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多采取政府主导和外来公司投资的管理模式,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的社区居民往往面临着民族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自身地位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22]。在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经验的借鉴下,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为理念发展模式:台湾地区、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民族社区开发过程中均由政府主导进行,以“土著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其开发理念,土著居民拥有政策制定权及较高的旅游收入分配比例,故而土著居民对旅游发展持积极参与与支持态度,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间矛盾也未凸显。因此,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不仅是旅游扶贫的目标,也是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开发理念。
(2)从政府主导到共同合作的旅游管理模式:借鉴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土著旅游的发展模式,提出“合作管理”的概念,即宏观政策制定者、中观管理者和微观操作者等旅游利益相关者打破原有的逐级管理模式,社区要素、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参与决策制定和产品开发的全过程。
(3)旅游生计方式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旅游生计多样化产业发展模式寻求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间的融合,以留下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社区居民)为目标,强调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传统农业生产作为旅游业发展的资源基础在旅游开发活动中的重要性,减少旅游业发展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消极制约作用,从而达到各产业间可持续发展。
(4)全域景观化背景下多核心型社区梯度-网状空间开发模式:当前民族社区“景区化”开发模式忽视了与周边社区地缘性关联以及与本底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特殊性,割断了子单元与区域复合系统和其他子单元小型复合系统的空间关联、生存关联和社会性关联,造成了旅游核心社区与外围社区之间邻里关系的恶化。因此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应从“景区化”向“景观化”方向过渡,打破区域限制。借鉴新西兰毛利会堂的空间拓展模式,打造一级核心民族旅游社区或民族资源点,通过点-面发展,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利用交通优势,强化与次一级民族旅游社区间的空间练习;通过点线面之间的连接促进民族社区区域发展。
[1]Nunez,T.A. Tourism, Tradition and Acculturation:Weekendismo in a Mexican Village[J].Ethnology,1963,12(3):347-352.
[2]余光弘,李莉文. 台湾少数民族[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1-8.
[3]郝时远,陈建樾. 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5-62.
[4]张崇根.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组织[J]. 民族研究,1994(2):41-49.
[5]陈亮全. 近年台湾社区总体营造之展开[J]. 住宅学报,2000,9(1):61-77.
[6]方琼瑶. 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D].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论文,2005.
[7]刘立伟. 社区营造的反思:城乡差异的考量、都市发展的观点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讨[J]. 都市与计划,2008,35(4):313-338.
[8]郭建芳.台湾原住民部落旅游之概况[J]. 统一论坛, 2006(1):41-42.
[9]洪泉湖. 全球化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C]//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休闲旅游论文集,2003.
[10]王亚欣.对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营造的思考[J]. 旅游学刊,2006,21(4):27-31.
[11]巫铭昌. 原住民部落总体营造经验谈(文化产业篇):以屏东太五乡万安部落为例[J]. 原住民教育季刊,1999,15(3):16-46.
[12]贺圣达. 访缅甸、泰国、老挝三国:印象与观感[J]. 东南亚, 1995(4):53-59.
[13]PolladachTheerapappisit. The Bottom-Up Approach of Community-Based Ethnic Tourism: A Case Study in Chiang Rai [J]. In K Murat, A Handan (Eds), Strategies for Tourism Industry-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M]. InTech:Hampshire. 2012:267-294.
[14]李晶.新西兰土著毛利人问题及其走向[J].中国民族,2006(11):27-30.
[15]李桂南. 新西兰语言政策研究[J].外国语,2001,5(135):39-42.
[16]Tourism New Zealand,2014. http://www.tourismnewzealand.com/
[17]唐文跃,张捷,罗浩. 新西兰旅游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3):87-91.
[18]Eagles,P.FJ.,S.EMcCool,andC.D.Haynes. Sustainable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 2002.
[19]Hockings, M., Stolton, S., Leverington, F., Dudley, N. and Courrau, J.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2nd edition) [R]. IUCN,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2006.
[20]Taylor J. Aboriginal people in the Kakadu region:social indicators for impact assessment [R]. CAEPR Working Paper No.4. 1999. pp:50-52.
[21]贾鸿雁. 澳大利亚文化旅游发展及其启示[J]. 商业研究,2013,429(1):195-199.
[22]LI Y J, Turner S, CUI H Y. Confrontations and concessions: An everyday politics of tourism in thre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Guizhou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6,14(1):45-61.Doi: 10.1080/14766825.2015.1011162.
[责任编辑:李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演变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41361033);国家旅游局面上项目“旅游扶贫背景下西南民族社区时空演变机理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16TAAG024);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CCNU16A03016)。
李亚娟,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地理。
F592.7
A
1002-6924(2016)08-036-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