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注
●杨训波
赌注
●杨训波
一
离开花村20年后,司徒杰重新回到了花村。
和他出走时所不同的是,他的左手臂不见了,一截空袖管随着身体的摆动而摇晃着。他个儿长高了,却瘦得像一根老玉米秆。他脸色苍白,一双眼深深陷在老眉下,头发很长,黑得像墨汁。一条牛仔裤,裤管上破了几个洞,两个膝盖从破洞中露了出来,一件白色衬衫也是脏兮兮的。
这一切都让村民们唏嘘不已,尤其是那只没了手臂的空袖管,让村民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唯一让村民们欣慰的是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那女子身穿一件红色上衣,一条牛仔裤将她修长的大腿展现无遗,头发长且黑,脸色白皙,一双黑眼睛生动含情。
看到村民们都盯着女人看,司徒杰得意地说,这女人叫喜悦,我失去了一只手臂,赢回了这个女人和数也数不清的钱。他说这话时,用右手重重地拍击着自己没了左臂的空袖管。
女人看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只用右手将她乌黑的长发理朝头后,然后抬头望着天空。
看到村民们不解的眼神,他笑着说,乡亲们,我离家在外打拼20年,就学会了一样本事!
听了他的话,村民们又是一阵唏嘘,离家20年了,他的话里早已没有一点花村的口音了!
“学到了什么本事,快给我们说说嘛!”有人叫嚷道。大伙都仰着头、张着嘴巴看着他。

看到村民们的那副日脓样,他再次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说道:“赚钱的本事!”
听到此,村民们都开心地笑了,这种本事多好呀,谁还不想有这种本事!
看着长高了个儿,一扭头长发就潇洒地朝头后甩去的司徒杰,陈大顺不禁想起了曾经和自己一起光着屁股比谁尿得更高的那个发小司徒杰来,他们一起在花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他依然爱吹牛!”陈大顺嘀咕道。看着眼前的司徒杰,陈大顺的眼里漫出了泪水,一种熟稔之感顿生。让他激动不已的是,曾经一度认为死了的司徒杰会突然出现在村里。
“小杰,那就把你的本事教给我们吧!”他高兴地喊道。
透过人群,司徒杰寻声望去,他一眼就认出了陈大顺,但他不领旧情,只大声问道:“你是谁呀,你是村里人吗?”
“他是大顺呀!就是陈大顺呀!”一个名叫阿九的年轻人解释道,“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小时候,你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呀。”
“贵人个球,连发小都会忘记的人,还谈得上是贵人!”陈大顺小声骂道,“他娘的,二十年不见,个儿倒是长高了,可脑子却缩水了!”
“怕是脑子进水,变日脓了!”阿九凑合道。
“你才脑子进水呢!”陈大顺白了阿九一眼,骂道。
此时,村长陈富达走到他面前,慢声细语地说道:“小杰呀!你爹娘死前,托付我将这所老房子管理好,现在你回来了,我就把房子还给你了,你打扫一下,住进去吧!”
“在村背后的那座山上,你有空就去看看吧!”陈富达说。
“那是当然,不用你教我。”他淡淡地说。
陈富达无奈地摇了摇头,走开了。杳无音讯20年的浪子终于回到村里,陈富达自然喜出望外。他本想着把司徒杰请到家里,好酒好肉招待一次,然后发动村里人帮着他收拾一下那间破旧的老屋,可司徒杰却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这让他感到心寒。想起司徒杰那对残疾父母,为了找到他,每个花镇街都要去赶街。在街上,他们见人就问,只要有客车停下,他们都要艰难地爬到车上看看。在村里,两口子整天坐在村口,翘首望着远方的路,期待儿子从那条路上回来。最终在一个冬天、一个下雪的冬天,他们在出去寻找儿子的途中被冻死了。是陈富达带着村民将他们的尸首用马车运回来,安葬在村后头的一个山头上的,其坟向就面向着进村的那条路。
回忆起这些旧事,陈富达感伤地落下了眼泪。真是天不遂人愿呀!想不到这对残疾夫妻居然生养出了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儿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经常有同学笑话他有一对残疾父母,他就挥拳打人家,到了初二的时候,他终于无法忍受同学们的讥讽而离开学校,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花村!
“真是不孝之子呀!”走在回家的路上,陈富达咬牙切齿地骂道,“简直是连毛驴都不如!”
村长走了,村民们也纷纷离开了。季节已到秋季,正是收粮食的季节。此时的花村,谁家都堆放着一些刚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棒子,夜色里,一家人都围在一起,在黯淡的灯光下将玉米棒去皮,然后扎成捆,挂在自家的楼房上晾晒,整个村都处在忙碌中。蛐蛐们在墙角哼唱着小曲,空气里弥漫着有人烧玉米棒所发出的香味来。
其中, λ为初始扰动波长, 无量纲Atwood数A=(ρh-ρl)/(ρh+ρl), ρh和ρl分别为重流体和轻流体密度. 当重流体密度远远大于轻流体密度时, 即A=1时, 非线性饱和阈值大约是扰动波长的0.1倍. 也就是说, 在Atwood数为1的情况下, 当基模的幅值达到扰动波长的1/10时, RT不稳定性就已经进入非线性阶段. 在进入非线性阶段之前, 高次谐波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 当基模的幅值接近扰动波长的1/10时, RT不稳定性正在经历弱非线性阶段, 高次谐波迅速增长, 和基模共同作用决定着界面的演化发展.
“小杰,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喊我!”临走时,陈大顺喊道。听到声音,司徒杰头也不抬地回道:“用不着,老表!”
“唉,他的心都被狗吃了,居然把我当成他的老表了。”陈大顺叹息着离开了那间破屋。一路上,他的脑海中多次涌现出司徒杰和他玩耍时的场景来。
“也许他有钱了,忘记了我这个穷朋友了!”陈大顺想到。回到家里,他让老婆做了饭菜,然后又跑着给司徒杰送去。司徒杰看了一眼热腾腾的饭菜,说了句:“我们今晚吃压缩饼干!谁让你给我们送饭了!”一句话,让陈大顺呆在那里。片刻后,他一甩手将饭菜扔在地上,气呼呼地跑回家里。一路上,他的泪珠不断地往下落,他的心里堵得慌。
“你可真不是人!”喜悦看着地上的饭菜,骂了一句。
二
司徒杰的父母是一对残疾人。
母亲因年幼时一场大病,成了聋子。父亲则在一次伐木中压断了一条腿。后来,这对残疾人生活在了一起,并生下了司徒杰。他们省吃俭用,一心想供儿子上学。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在儿子上初二的那年开学的时候,他拿着那笔学费失踪了。父母四处寻找,都没有踪影。村里人都一致认为,司徒杰肯定是死了。
事实上,初二那学期,当司徒杰怀揣着父母给的学费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曾在心里暗暗发过誓,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混出点名堂后再回来。然而,生活并非小说,它不会按着你的意愿来展开,开始的那几年,司徒杰混迹于社会中,他做过小偷,专偷女人的项链,他做过骗子,专门骗取老人的钱财,也做过搬运工,在建筑工地上给人挑沙子抬砖头,最终却阴差阳错地混进了一个赌场而无法自拔。
在他离开花村十年后,父母在一场大雪中离开了人世,留下一所老房子,等着他的归来。
当时的花村仅仅是一个有着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这是一个生长粮食的所在,整个村被绿色的森林包围着,人们靠种庄稼和养牲畜生活,小日子在平静安稳中甚为舒适,显然,这是一个幸福的村庄。
回到村里后,司徒杰在破败不堪的房子里设下牌局,村里的人们在那间已十多年没人住的房间里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活法。许多年轻的、年老的男人和女人都到那个破屋里玩牌赌钱。但是,赌场并非庄稼地,不可能让你日夜都有丰收,那些习惯摸镰刀、捏锄头把的双手,并不习惯摸牌,村里人逢赌必输,几个月下来,全村人只要进了司徒杰家的人都输了。看着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空着手走出门去的乡邻们,司徒杰总是哈哈大笑,他喜欢看输了钱的人那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也只有在此刻,他的心里才有一种拥有金钱的满足感和打败他人的成就感,只是这种感觉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就在那种感觉涌上心头的时候,陈富达的那张脸就在他眼前摇晃起来,这让他那颗得意的心瞬间如泄气的皮球,一种失落感瞬间涌遍了全身。
“他娘的,我就不信,你陈富达就不喜欢赌!”他在心里暗骂道,“总有一天,我要你像其他人一样天天往我这里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司徒杰这个恶毒的计划并没有如愿。
陈富达是一村之长,他的家族是一个耕作之家,本分做人,靠劳动吃饭是祖辈传下来的家训。这些日子里,他一直留意着走进司徒杰家门的村民们,许多个夜晚,他到东家坐一会,然后又到西家,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不要玩牌。有一次,他还召集村民大会,告诫村民们离开牌局,然而村里的人并没有听他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运气。
三
“兄弟呀,我们家从祖上下来就是本分人家,你现在却成了个赌徒,你也想成为司徒杰一样的人吗?”一天晚上,陈富达坐在陈大顺家里,语重心长地劝说弟弟。
“你不赌也就算了,还希望别人和你一样!”五大三粗的兄弟听了兄长的话后,反驳道,“村民们又不去杀人放火,他们是用自己的钱去赌,那是他们的自由嘛!”
“对于村民,我能劝的都劝了,但他们不听,那是他们自找死路,而你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呀!”他喝了一口白酒,耐心地说道。
陈大顺不再说话,只顾喝着老白干。这么多天来,一直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年幼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到外面闯荡了20年后,居然不认识他了。事实上,开始的时候,陈大顺到司徒杰家,只想找他叙叙旧情,但司徒杰始终没有理他。他想,只要他在那里,司徒杰总会和他说话的,于是就玩起了牌,期待着在玩牌中和司徒杰叙叙旧,但几天下来,他把准备给老娘买过冬衣服的一千多块钱都输了,但司徒杰依然没有和他说话。
“你倒是说话呀!”看到兄弟没有言语,陈富达大声说道。可陈大顺只顾喝着老白干。他的脑海里,全是他和司徒杰年幼时一起玩耍的情景。看着兄弟那副嘴脸,陈富达甩手就给了兄弟一记耳光。
“你居然打我,你再打一次试试!”他吼道,吼完就把酒碗重重地摔在地上。
大哥又给了他一巴掌。此时,大顺早已握紧的拳头,重重地打向大哥,却被陈富达伸手握住了。
“你这个畜生!”他将兄弟的拳头松开后,盯着兄弟的双眼,轻声说道,“你居然动手打你的哥哥,你这个畜生!”说完,他走出了兄弟家的大门。
陈富达走后,大顺的婆娘丑妹说道,听到了吧,老杂毛,老娘的话你不听,你哥的话你也不听!你要是再进司徒家的门,老娘就不和你过了。
“他娘的,你再吼,小心老子把你废了!”大顺骂道。听到大顺喊叫,那婆娘顿时歇了声,自个儿忙去了。大顺一口将碗中的老白干喝了,走出门,朝司徒杰家走去。五大三粗的陈大顺前脚刚走,一脸麻子的丑妹也走出了家门,她回娘家去了。
“小杰,你出来,我们一起吃碗酒!”他进门就喊道。
司徒杰老远就看到大顺的影子了,但他装作不看见,只顾忙着给别人发牌。
“小杰,来,我们一起吃碗酒!”大顺又喊道,见他没反应,大顺走过去,拍了拍司徒杰的肩膀。“来,我们喝碗酒,小杰!”
“哦,你是叫我,我还以为你在叫小姐呢!”司徒杰阴阳怪气地说,“来来来,你也玩几把牌,这里是玩牌的地方!”
“我不玩了,我已输了很多钱了,我只想和你喝酒!”大顺说道。
“来这里就要玩牌,喝酒,那是多大点事呀,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还是小杰吗?”大顺的心里终于升起一股愤怒之火,“我来这里玩牌,输了一千多块钱,就是为了和你说说小时候的事,可你总是这样冷漠地对待我!”
对于大顺的责问和辱骂,司徒杰装作没有听见,他笑着道:“来我这里,没有钱也可以玩。只要你开口,要多少我都敢借给你!”
“你那是放水钱。”大顺说道,“你那是在害人呀!”
“你知道,所谓水钱就是会生钱的钱嘛!我借给你100块钱,可以让你赢回好几个一百块,而你只要每天给我10块钱就行了!”
听司徒杰这么一说,陈大顺不想再和他讲话,他坐了下来,向喜悦借了500块钱玩了起来。这一夜下来,陈大顺的手气太坏,在赌桌上输得一塌糊涂,当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时已是中午了。
见到儿子回来了,老娘踮着她的小脚,站在大门口,她骂道:“小背时鬼,你又去赌了!”
看到老娘守在门口,陈大顺索性坐在门前,点燃了一根烟。
“你给我站起来,小偷生鬼!”老娘喊道,“你这个小畜生!”老娘歇斯底里地喊叫对他的儿子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大顺没有说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又慢慢地将烟吐了出去。老娘看到这里,上前踢了他一脚,骂道:“你这个小畜生,你还有脸在这抽烟!你这个畜生,你媳妇都回娘家了,你还有脸在这抽烟!你这个小畜生!”这个牙齿即将掉光的老太太骂完,哭了起来。
“你再喊,小心我把你作赌注!”大顺本来心情烦躁,看到老娘又打又骂的,心情更加烦躁,随口喊道。
听到儿子要把自己当作赌注,老太太一跺脚,大喊一声:“天啊,这个挨千刀的小畜生!”她呜呜地哭着骂着,踉跄着奔出大门,朝着大儿子陈富达家走去。
看着老娘伤心离去的样子,大顺一摔手,将烟蒂重重地砸在地上,吼道:“他娘的,这是什么世道!”然后他迈步走进家门,喝了碗白酒,找来一领蓑衣,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再说那老太太一进大儿子的家里,就一屁股坐在堂屋里,哭声更加响亮起来。听到老娘的哭声,大儿子陈富达立刻给她倒了碗红糖水。
老娘没有喝,大声地哭喊着。陈富达走到老娘面前,安慰道:“娘,别哭了,大顺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回头我再说说他啊!你先在我这里住下,别难过!”
“他媳妇也回娘家了,你看她还抬着个大肚子的呀!”老太婆哭喊着,那眼泪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打着转悠,老是落不下来!
看到老娘伤心的样子,陈富达喊道,媳妇你来照看我娘,我去把那个王八蛋找回来!说完跑出了家门。这时,陈富达媳妇九妹正在厨房里做饭,她大声喊道:“娘,你别哭了,我在做饭呢!你再哭,我就没心情做饭了!”
老娘听到此,顿时止住了哭声,已经一天没吃东西的她,空空的胃让她止住了泪水。
陈富达走在通往司徒杰家的路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的脑海中不时闪现出司徒杰年幼时和陈大顺玩耍的场景来。那些年,司徒杰经常和大顺吃住在一起,俨然一对亲兄弟。可外出20年后,司徒杰完全变了,也许在外的生活,给了他严重的打击,那些严重的打击冲淡了他年幼时的幸福时光。陈富达迈着大步,一路小跑着前进,最后冲进了司徒杰的家里。此时,司徒杰正在院子中遛鸟。陈富达飞起一脚,将司徒杰手中的鸟笼踢飞出去。刚刚还叫得欢的画眉鸟被这惊吓,扑腾在笼子里,惊慌失措地叫嚷着,似乎在怪这个老头打断了自己的歌声。
司徒杰弯下腰,从地上提起鸟笼。对着画眉说道:“别怕,小兄弟!”说完,他把鸟笼挂在树上,转身道:“是谁惹我们的村长发火啦?”
“把大顺喊来!”陈富达瞪着鸟笼,大喊道。
“你对着画眉说话,它可听不懂,它只听得懂我的话!”司徒杰慢吞吞地说!
“你这个鸟人,把我兄弟喊来,我要他回家!”陈富达转身盯着司徒杰吼道!
“你吼也没用,你兄弟早就回家了嘛,他在这里玩了一夜,刚回家了嘛!”
“他出事了,你知道吧。”陈富达喊道。
“他一个穷光蛋还能出什么事!”司徒杰眉毛一挑,轻描淡写地说。
陈富达听到司徒杰的话,挥动着巴掌就朝他打去,却被司徒杰用右手轻轻地抓住了:“有话就说,可不要动手打人!”说话间,司徒杰的右手发出力气捏住陈富达的手,让陈富达疼得差点喊出娘来。
“大顺可是和你从小一起玩大的,你何苦要害他呢!”陈富达声音小了下来,“这全村老少,哪家不是你的父老,你在外面干尽了坏事,现在又回到村里来害人了!”
司徒杰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放开了陈富达的手,不再搭理他。
陈富达看着司徒杰那副模样,气呼呼地走出了大门,朝大顺家走去。此时,大顺在葡萄架下的一张八仙桌旁睡得正香呢!
他本想叫醒他,但看着兄弟那熟睡的样子,又不忍心惊扰,只好坐在一边,等着兄弟醒来。
“小杰,来和我喝碗酒!”陈大顺突然叫了起来。陈富达看过去,是大顺在说梦话,他的脸上还挂着笑脸。
“这个畜生,连做梦都想着司徒杰!”他嘀咕着蹲下身摇晃着大顺。
“在梦里一定是赢了不少钱吧!”陈富达冷冷地说道。
大顺看了眼哥哥,坐了起来,没有言语。
“你老婆跑了,老娘也走了,你还在这里呼呼大睡!”他大声骂道。
大顺站起来,走进堂屋,倒了两碗白酒,他喝一碗,把另一碗递给大哥。看到大顺没有言语,只顾喝着酒,陈富达的胸中燃起了一团火,他举起手掌朝兄弟的酒碗打去。大顺一转身,躲过了兄长的那一掌,忙说道:“大哥,你说归说,可不要砸我的酒碗!”
“你这个畜生,白养你了!”哥哥喊完,坐在地上,他端起自己的酒碗,一口干了,伤心地哭了起来。
看到哥哥哭了,陈大顺坐到哥哥身边,安慰说:“大哥,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打牌只想让小杰重新记起我来,你知道我俩小时候是多好的朋友呀!”说到这,陈大顺的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都那样了,你值得吗!”陈富达问道,“再说,你现在输了那么多钱了,如今老婆也跑了,你还去赌,你拿什么做赌注呀!”
“命,拿我的命当赌注!”陈大顺狠狠地说道,“如果小杰还那样冷漠地对我,我可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凡是赌博,都是用命作赌注的!”陈富达说,“你看看那些赌棍赌徒,哪个不是在玩命!兄弟,你可不能像他们一样啊!”陈富达说完,再次哭了起来。
陈大顺是陈富达的小兄弟。父母一生共生下了五个孩子,陈富达是老大,中间还有三个姐妹。只有这个小兄弟,出生几个月,父亲就在一次伐木中被倒下的大树压断了腿,失血过多而死。可以说,这个兄弟是他一手带大的,如今,姐妹们都相继出嫁了,只有这个兄弟,虽然也讨了老婆,但一直不让他省心。他从小喜欢舞枪弄棒的,喜欢到处结交朋友,东游西荡四处玩耍。后来老娘和他合计给他娶了个媳妇,让媳妇来管教他,刚结婚那段时间,陈大顺变得温顺了些,也和自己的婆娘下地干活了,但是司徒杰回来,又让陈大顺变得疯狂而不可理喻起来。
四
花村的四周都是高山,花村坐落在高山的怀抱里,一条名叫广渠河的小溪从高山上下来,从村脚流淌开去。司徒杰没有回村之前,村里三十多户人家,家家养牛羊,户户种庄稼,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地上劳作,大地也慷慨地给人们丰厚的回报。谁也想不到,村中这种幸福恬静的生活,全因司徒杰的归来而彻底打乱了。
那些年,因为交通不便,村里人很少外出,司徒杰回到村里后,花钱修通了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马路,可直接开车到花镇。这花镇就是村民经常赶集的地方,也是当地乡政府所在地。路通了,司徒杰也买了辆红色的皮卡车,人们惊奇地看着他单手开着车奔驰在路上,一条空袖管在车窗外飘荡着。陈富达看到此,心里暗暗吃惊,原来这小子虽然少了只手臂,却也练得了一身功夫,想到此,他那只被司徒杰捏过的手掌似乎疼了一下,吓得他立刻收回目光,不再看那辆红色皮卡车。
据说,司徒杰到花村开设起牌局后,自己却不再参与赌博,而把心思都花在寻花问柳和吸毒那些事情上去了。几个月后,全村人才知道,司徒杰的牌局是一个无底洞,尤其是向他借了水钱的人,更是无法还清。那水钱,是随时日不停上涨而没有止境的深渊,你向他借了一百元,每天还他十元,只要没有还完这笔钱的一天,那十元的利息就像水一样积攒了起来,最终会积攒成大江,将你淹死掉。当然,也有一些年轻的男人盲目地自信着自己的手气,相信自己能从那里成倍地捞回自己输出去了的钱。为此,他们三番五次地前去,每次都空手而回。直到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村长来,于是在一个夜晚,村里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村长家,请他出面制止这种类似抢劫的行为。
“他抢了吗?”身着长裳,留着八字胡的村长陈富达听完了来者的抱怨后,冷静地问道。
“本人虽然不会赌博,但也知愿赌服输这个道理的,你们自己去赌,输了又来我这里说人家的不是,这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呀!”村长说道。
“村长,你可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好的,那老朽就教你们一招吧!”村长说道,“你们都不要去赌了,还是像过去一样,该种庄稼就种庄稼,该放牛就去放牛!”
“你这不是废话吗?”听到村长的建议后,有人说道。
“难道是司徒杰给了你好处!”有人猜疑道。听到这话后,村长的目光落到了说话的人脸上,不语。
此时,恰好村长老婆九妹给大伙端来一锅炒熟的瓜子。
“阿九啊,饭可以随意吃,话可不能乱说啊!”九妹气呼呼地喊道。
阿九顿时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阿九,你输了多少。”村长问。
“三千多块!”阿九小声答道。
“不多嘛,你家有八个姐妹,如果没有钱了,你可以用她们作赌注再去赌!”村长说道,“至于你怀疑我得了司徒杰的好处,那我告诉你,赌棍手里的钱,我连看都不愿看!”
当晚,村长并没有意识到,当晚他虽然没有给年轻的人们一个有用的建议,却给阿九创造了一个机会。
“有人说你就是一条赌棍、一个浪人。说你有再多的钱,他也不会看上一眼。”第二天,阿九在司徒杰的耳边嘀咕道。
“说这话的人应该是村长吧!”对于阿九的告密,司徒杰并没有愤怒,他告诉阿九,做人可不能这样,才听到一点风,就告诉别人要有雨了,这对你没有好处!
“村长对你那么好,你却来我这里说他的坏话!”看到阿九脸色泛红,司徒杰转移了话题,问道:“你在我这里输了多少?”
“五千多块了!”阿九撒谎道。
“好啦,你到喜悦那里去,让她给你六千块!”司徒杰说道,“取了钱给我立刻滚蛋,别让我再看到你!”
阿九的笑容僵持在脸上,急忙跪倒在地上,装作很伤心的样子。
“我虽然没钱,但愿赌服输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又怎能要回那点钱呢!”阿九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那你就继续来玩吧,没钱了就向喜悦借,你想借多少都可以!”说到这,司徒杰给阿九发了一支烟,并给他点上火,他自己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继续道:“在我这里借钱,有个规矩,你借一百,每天都得给我十块的好处费,换句话说,如果你借了一百元,十天后,你就得还我两百元。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阿九满面欢喜地说。
得到了司徒杰的原谅,阿九连声道谢后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阿九本来也是村中一个人物。他是近十年来村中唯一读过高中的人。高考失败后,他到北京一家餐厅打工,后来认识了一个外省妹子。父母闻此消息高兴不已。这几年来,随着附近村庄的年轻女孩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在家中盘庄稼种地的一些大龄男人已很难找到老婆,村子里的老光棍剧增。老两口看到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有了个外省的女朋友,高兴得几夜没有睡意。那年的冬天,当阿九带着那个外省女郎回到家里时,因为走路的时间太长的缘故,那女孩的脚肿了起来。一个月后,她的脚伤痊愈,骗了阿九的钱财,跑了。女朋友跑了,阿九就开始四处寻找,花费了父母给他准备结婚用的钱,最终也没有找到,从此,阿九陷入到郁郁寡欢中。
司徒杰的归来,给了他一个好去处,于是他便天天去,去的次数多了,玩牌的时间却少了,因为他看上了喜悦,喜悦也看上了他。只要司徒杰外出的日子,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走在一起。
五
作为一个在赌场上厮杀多年的老油条,司徒杰信奉的是人活一世,潇洒一生的哲学。当初,他由于水钱越借越多,而手气却一日不如一日,最终还不起钱,只好让庄家砍了他的一支手臂作为还债。就在有人将他的左手砍去的最初,他感到非常的不习惯,上个厕所不利索吃饭喝水不利索,甚至连走路也感到身体歪向了右边,这时候才怀念起拥有左手的日子来。想到砍掉他左手的那些人,他就咬紧牙齿,发誓要把那些人的左手也砍下来,但想归想,最终因为懒惰因为怯懦因为没有本事而让他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和砍掉他左手的老板混在一起,他成了那个老板的手下,专门给赌场里需要借钱的人放款和收钱,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因为没有了左手,他在心里不断暗示着自己的左手还在,并不断地练习单手的生活。十年来,他能单手玩麻将、单手穿衣吃饭,尤其还练就了单手驾车的本领。十年来,他慢慢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人,他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赚了钱就去喝酒和吸食毒品,等花光了钱,又回到老板身边,如此反复地让时间在不断地吞噬着他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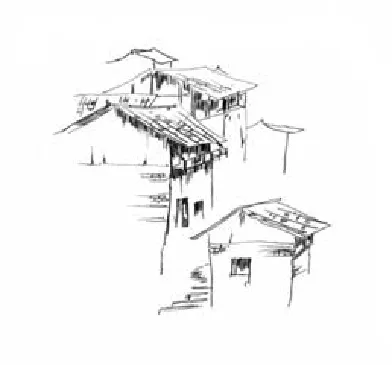
十年后,庄家也成了个老头了,这个一生流连在女人、赌徒中的人总担心着司徒杰会向他报一臂之仇,像他当年派人砍掉他的左手一样对待他,于是心生一计,给了他大笔的钱财和一个名叫喜悦的女人,让他回到老家去,希望司徒杰到老家开设赌场,放水钱过活。
“我可不愿再回到那里去,那里车路不通,人们也不喜欢赌!”他迟疑道。
“你傻呀,赌徒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嘛!”庄家开导他,“你放水钱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天天来赌,没有钱,你可以让他们用田地啦、牲畜甚至是用老婆来抵押嘛!”
“放手去干吧!我让喜悦姑娘和你去,做你的帮手,如果你喜欢,就把她当作你的老婆吧,我没有意见的!”庄家心里清楚,就司徒杰那样一个赌徒,再不让他离开,最终只会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像司徒杰那样五毒俱全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听庄家这么一说,司徒杰眼前一亮,仿佛嗅到了村里隐藏的那些金钱的味道。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和喜悦出现在了村里。
再说这个名叫喜悦的女人,也是个赌博成性的女子,她在当时司徒杰的庄家处借了大量的钱财豪赌,最终无法偿还,并以自己的人生做赌注,将自己的身体全都贡献给那个庄家。
两人回到花村时便商定好在村里开赌场,喜悦专门收钱和放水,等赚够了钱后,两人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阳光道。因此,两人虽然在一起生活,但并无感情可言。特别是开通马路后,司徒杰买了一辆皮卡车,他经常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开着车到花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喜悦也借机和阿九在那间破屋里幽会。
阿九虽然生得矮小,相貌却生得可爱,一张没有胡子的嘴也像是在蜂蜜里泡出来的,专会哄女人开心。喜悦虽说是见了大世面的人,过的却是风尘女子的生活,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对待过她,因此遇到阿九,听着他的甜言蜜语,她那颗冰冻多年的心,终于融化了下来,她爱上了他。
六
自从那次下了决心要给司徒杰一点教训后,陈大顺便开始留意司徒杰的行踪了。只要看到司徒杰开着车离开村子,他便掩入山林,远远地追踪着司徒杰的行踪。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守在司徒杰回家的路上,手里拿着一个烟花炮竹,准备吓唬吓唬他。就在司徒杰急速开车从陡崖上的马路上驶过、陈大顺准备点燃烟花的瞬间,那辆红色皮卡车突然就冲出了山崖,在坡上翻滚了又翻滚后,砸在一棵大树上。
忘记了自己是来教训司徒杰的,陈大顺大声呼喊着司徒杰的名字,从石头背后冲出来,朝着红色皮卡车冲出去的方向冲了下去。
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浑身是血的司徒杰从车里弄出的时候,司徒杰有气无力地说:“大顺,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你,但我没脸认你,我是一个赌棍,一个吸毒鬼。刚才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了我的爹娘了,我要走了!”
听到这,陈大顺放声大哭起来,他奋力地把司徒杰背在身上,艰难地往上爬,可才走出几步,司徒杰就在他身上断气了。后来警方来了,鉴定结果是因长期吸毒产生了幻觉而落崖死亡。
司徒杰坠崖身亡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那些输了钱财的人拍手称快,说那是报应啊!他们没有到司徒杰家前来探视,只有一些老人在哀叹,作孽呀,人在做天在看,小杰那个畜生终于把自己作死了呀!
一天黄昏,陈富达走进了司徒杰的破屋。面对村长的突然造访,喜悦有点不知所措,她一再向他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但对于她的热情,这个已近60岁的老头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激动。
他说道:恭喜你呀,司徒杰死了,你的愿望也达成了!
喜悦没有言语。
我希望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陈富达说道。
喜悦点了点头。几天后,阿九和喜悦都不见了。
村里人说,阿九肯定是学到了司徒杰赚钱的法子,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编辑手记:
一篇小说具有引人阅读的魅力之一往往是其蕴含多种解读的可能,《赌注》便是这样一篇小说。作者有意淡化时间背景,却营造了一个封闭的小村庄,写了一个离开村庄20多年的人回到这个村庄后带给村庄和村民的变化。小说里塑造的陈大顺一心渴望着和回归后的司徒杰叙叙旧,甚至不惜以赌博来博得一点能叙旧的时间。而司徒杰的冷漠和变化是陈大顺最在意的,也是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一方面。而从另一个叙述者陈富达的叙述和花村的变化来看,却可读出这是一个封闭与接纳相互碰撞而产生变化的故事。花村本是一个平静、封闭的小山村,人们勤劳从而有所收获,但是司徒杰回来后开设赌场便打破了这个村庄的宁静,能不劳而获的赌博改变了村里年轻人的生活。象征封闭的花村在接纳了司徒杰后就改变了(包括人的改变和思想的改变),这种巨大变化正是整个故事所隐喻的,借此作者带我们感受了淳朴农村遭遇开放和吸纳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与思想变化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