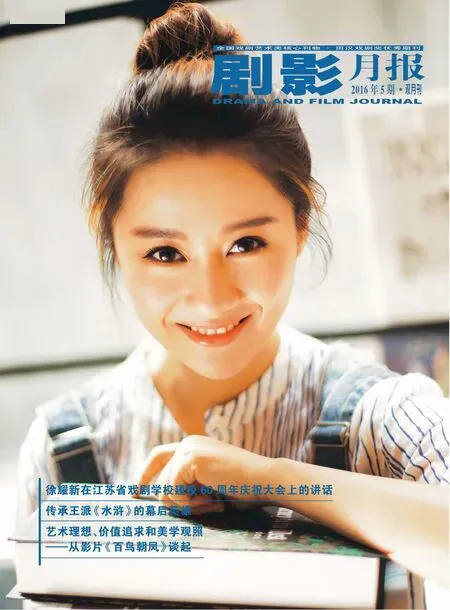新论话剧的“思想性”
■王美娟
新论话剧的“思想性”
■王美娟
一向以思辩性和哲理性探秘人生奥秘、褒贬人性善恶、净化社会灵魂的话剧艺术,在当下,其“观赏性”被解释为“娱乐”且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首要位置,致使一些专业人士也认为“娱乐性”已经成为当前话剧走出困境的唯一法宝,甚至被戏剧界和评论界当作评判一部话剧优劣长短的最高标准。在这样的戏剧氛围中,话剧的“思想性”作为本体特征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标识,正在被消解、被吞噬。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是一个可怕的现实。究竟是什么诱人的东西在动摇我们话剧创作者一贯坚持的理想信念与艺术追求?我们的话剧究竟是纯商业的“消闲娱乐”,还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人类高雅的舞台表演艺术?话剧的“思想性”正在接受挑战,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能不能战胜这个挑战,关系到话剧艺术的定位和发展走向,因此,应该引起我们对于当前话剧“思想性”的关注和思考。
“思想性”是话剧观演关系的心灵通道
今天,提出话剧的“思想性”,很不时尚,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话剧传统的“战斗性、革命性、宣传教育性”,会产生一种“不可言传”的排斥心理。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话剧的固有认识,似乎非“战斗性、革命性、宣传教育性”不能成为话剧。但是,只要我们稍有一些世界范围内的话剧常识或者看过一些优秀的经典话剧,比如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再到奥尼尔或者迪伦马特,那些久演不衰的经典名剧,哪一个不是充满了深邃的撼人心魄的“思想性”而脍炙人口,从而成为人类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瑰宝。于是我们就会正确认识和理解话剧真正的“思想性”而不至于如此排斥了。
中国话剧的“思想性”为什么给人以战斗的、革命的、宣传教育的印象,致使今天的观众仍然会产生排斥心理?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一百年前,当话剧舶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话剧先驱者出于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和符合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主动放弃了欧美诸如未来派、表现派等众多演剧流派,独尊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进步的批判现实主义写实派的社会问题剧,这不能不说是客观上的一种“历史巧合”。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危亡之际,中国话剧的先驱者们以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将中国社会维系民族危亡的重大问题作为主要思想内容写进了以思辩性和哲理性见长的话剧,搬上了舞台,启迪了民众,获得了成功。应该说,这是历史选择了话剧。因为,当时昏暗的中国需要有人呐喊,饥饿的民众呼唤社会的变革,话剧写出了现实的残酷,写出了民众的呐喊,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和教育,而是话剧艺术思辩性的本质所在,生命所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不仅成功地引进了话剧,而且充分体现了话剧艺术“关注现实、关注生命”的本体特征。因此,中国话剧走过一百年的历程,牢牢地扎根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然而,今天的中国话剧,虽然不再以“革命的、战斗的、宣传教育的”作为“思想性”的内涵,但是,话剧关注现实、关注生命,写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美丑善恶的“思想性”,应该仍然是话剧的本体特征之一。因为,今天的人们不仅希望了解大千世界的奥秘,更希望了解人类自身的心灵奥秘和生命奥秘。今天的话剧,其“思想性”以崭新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思辩,在话剧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条现场交流的心灵通道,让我们在剧场这个大屋子里一起探索人类自身的灵与肉的奥秘。
因此,无论是过去的话剧,还是今天的话剧,没有“思想性”,就没有话剧。
“思想性”是话剧观众的一种精神娱乐
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茶楼或咖啡屋之类的休闲场所看到一个新的广告词:发呆。这个词和品茶、聊天、打牌等连在一起,似乎“发呆”也是一种休闲。其实,这里的发呆就是“思考”,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类会“思考”,人类需要思考。思考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娱乐。娱乐不仅仅是唱唱跳跳之类的休闲自得,也不仅仅是凶杀打斗之类的感官刺激。娱乐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不仅仅取决于娱乐的客体形式,更多的是取决于娱乐主体的精神需求。一部话剧的“娱乐性”因观众而异,取决于观众的审美习惯、审美能力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不由话剧创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当今有文化有品位有思想的话剧观众,除了看故事、看人生,更多的是把“思考”作为看话剧的主要兴趣之一。有调查称:一些“追星”的年轻人同时也喜欢看话剧,他们说,要玩,去看演唱会;要思考,去看话剧。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压力太大,他们特别需要思考。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坎坷、失败太多太多,生活的不理解、情感的不确定、人性的大奥秘等等都是他们需要思考的。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论悲剧时说:“我认为悲剧的意义就是像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悲剧赋予他们对事物深刻的精神感受,摆脱日常生活琐碎的贪欲。当他们看到舞台上的悲剧时,他们感到仿佛是把他们自己毫无希望的希望体现在艺术中。”可见,我们所说的“思想性”,既是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之一,也是观众因为需要思考而走进剧场去看话剧的理由。
今天,话剧“思想性”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社会矛盾到生活矛盾,从阶级矛盾到人类自身的心理矛盾,话剧的“思想性”已经以“人性思考”话题进入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今天生活富足与精神痛苦相对矛盾的时代,话剧最能够解答人生的复杂课题,最能够启迪心智、发人深省、净化人的思想和灵魂。从这一点来说,话剧比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具有这方面的优越性。
人类需要思考,话剧的“思想性”是一种思考着的精神娱乐。
“思想性”是当代话剧观众的审美需要
话剧是艺术,是美的。一切美的事物都是客观存在,需要人们去认识,去解读;只有认识了,解读了,才能感受美的存在,才能享受到这个“美”的事物。若论单纯的感官娱乐,话剧既不唱,也不跳,几乎与生活状态一模一样,似乎在看邻家的生活,没有什么娱乐可言。那么,为什么话剧是“美”的,美在何处?观众看到了话剧的什么?
首先,作为综合艺术的话剧,其文学的诗意,导演的艺术智慧,演员的表演魅力和舞美的赏心悦目,有说不尽的艺术和美学的价值,这些都是话剧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否认,话剧艺术的“思想性”也是一种美,是一种大美,美在人类的心灵,美在人类的精神。这个“美”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观众在审美过程中自觉获得的一个心理存在。莎士比亚的惩恶扬善、易卜生的自由解放、斯特林堡的心灵游历、迪伦马特的哲人风范、奥尼尔的人性探秘等等,无不充满了审美的意义、审美的趣味和审美的满足。与其它任何艺术一样,在话剧的审美过程中,人类提高了自我认识、自我解剖、自我欣赏、自我启迪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质量,这应该是所有看过话剧的人都会产生的心灵感受。当下的观众依然处在各种社会压力和生活矛盾当中,他们需要自我认识、自我解剖、自我欣赏、自我启迪,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参与到话剧艺术的审美活动中来,最终满足他们精神的需求和艺术的享受。
有人说,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读图时代、物质时代,人们把艺术完全当成了娱乐、消闲和装饰,人们不再思考社会和人生,他们拒绝艺术的深刻。但是,只要我们冷静地看一看周围,看一看世界,社会依然纷繁,世界依然精彩,听歌的听歌,读书的读书,看戏的看戏……我们不能只看到社会的一个层面,一种浅表。一部能够让人们“思考”的话剧,一部能够表现或解答人生困惑的话剧,一部能够使人精神上得到满足的话剧,是一部好的话剧,今天的观众需要这样的话剧,今天的时代更需要这样的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