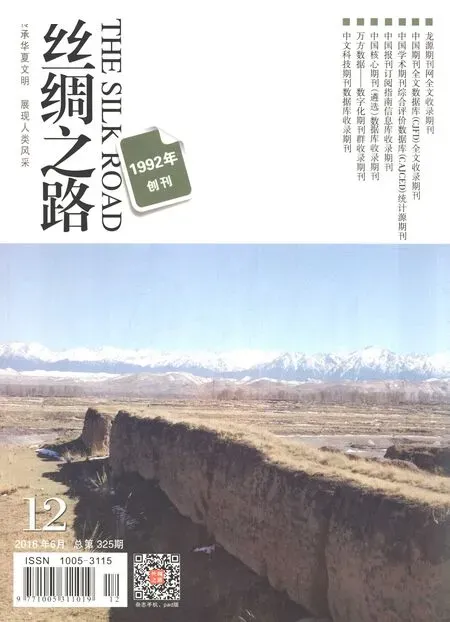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僧人女性随侍问题研究
——以敦煌壁画和绢画为中心*
白琳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僧人女性随侍问题研究
——以敦煌壁画和绢画为中心*
白琳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从敦煌地区的古籍文献及图像资料中均能找到晚唐五代时期僧人随侍现象的端倪。本文通过史料与图像二者之间的比对、联系,对出现的女性随侍的身份、地位等问题进行考证探究。
[关键词]晚唐五代;佛教僧人;敦煌图像;女性随侍
晚唐五代时期,在佛教世俗化的影响下,僧人随侍现象已经不再拘泥于寺院僧职的狭隘范围内,而是逐渐转向僧人世俗家庭的生活中。敦煌文书中有多处记载关于僧人与世俗家族共同生活的事例以及僧人收养养女、蓄养奴婢的现象。如P.341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提到僧崇恩收养有养女娲柴。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净人”、“白徒”就是指寺奴性质的随侍。那么,敦煌文书中所记载的养女、女婢等身份之人与敦煌图像中出现的女性随侍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女性随侍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研究佛教世俗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敦煌图像中的女性随侍
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图像中存在多处僧俗共存于高僧日常修习佛法的场景。莫高窟第17窟为洪辩影窟,北壁建有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坛上塑洪辩泥像,北壁上画有菩提树,树枝上挂净水瓶、挎袋,以示洪辩在菩提树下坐禅,菩提树左侧画比丘尼一,双手捧持对凤团扇。菩提树右侧画近事女一,一手持杖。①这身俗装女像,身着圆领缺胯长衫男装,头绾双髻,腰束带,左手执巾,右手持杖。这一女作男装在此出现,后文会作简要探究,此处不赘述。但把菩提树右侧女像称为近事女似有不妥之处,推断当是寺婢性质的俗家女子。
另,莫高窟第139窟,是河西都僧统阴海晏的影窟,位于第138窟前室北壁,坐北朝南。窟内塑禅定佛一身(清修),壁画上画七佛趺坐像,窟内北壁背景东侧绘比丘尼,双手持杖;西侧绘近事女(面部毁),梳两个小抓髻,用红丝带扎起,身穿男式衣服,一手持巾,一手持净瓶。②这里同17窟一样,仍然出现一俗一尼的形象,这里俗装身份的女子从发髻上看应为侍婢身份,“近事女”一词并不十分准确。
又如,莫高窟第137窟,五代时修建,宋时重修,洞窟为覆斗形顶,北壁塑禅定比丘一身(残),壁画屏风二扇,一扇画沙门经行山间,一扇画沙门对石灯宴坐。西壁屏风一扇,画一沙门,一近事女经行山间。东壁画屏风一扇(残),存芭蕉、瓶、盆等物。此窟坐北朝南,原为五代一影窟,后重修第136窟时被毁大半。③这一洞窟形象地表现出了这位比丘日常修习佛法的场景,有随侍服侍左右,其中女尼应为等级较低的沙弥尼或者僧官一类。
再,位于第444窟前室北壁的莫高窟第443窟,为公元976年敦煌三界寺等僧众对444窟进行重修,并在前室北壁修建某位高僧的影窟(第443窟)。窟内只有一方形佛床,塑像现已不存在。北壁画有菩提树,树上挂有净瓶和挂包,左右两侧壁画有侍童、供养比丘和供养人像。④从这里所画的侍童中可以得到两个认识:一已经存在僧人将幼童收养为子女或者私蓄为奴婢的现象;二这里的侍童虽辨别不出性别,但也可以知道已经是作为随侍身份出现了,应该等同于文献中的“侍人”、“净人”的性质。
同时,从供养人像也能看出僧人蓄养奴婢的现象。蓄奴现象较多出现在生活比较富足和安逸的僧尼家中。如MG. 1778绢画十一面观音菩萨图,下部供养人画像,右侧画一比丘像,身后立一小比丘尼像。⑤Ch.lv.0015绢画《水月观音像》,供养人画像右侧为一尼像,其身后亦立一小尼像。据沙武田先生考证,小尼像很有可能是两名尼僧生前的奴婢侍从。⑥可见,生活相对富足的僧人已经有蓄奴行为。
另外,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绢画淳化二年《报父母恩重经变》,供养人为一比丘尼,榜题“故大乘寺阿师子戒行□一心供养”,坐床榻、胡跪、持香炉,身后三身完全是世俗装女性侍从供养像,为典型的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中女供养像的装束打扮,大袖襦裙,两身花冠,一身双丫髻,分别持扇、瓶、包袱。⑦这里出现的三身分别持有比丘尼修习所用之物的世俗装女子代表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所供养比丘尼的俗家随侍。
二、敦煌古籍文献中的女性随侍
多处有关佛教的文献资料记载了高僧身边出现了侍从、侍者,身份均为出家僧尼。如关于玄奘法师身边存在随侍的记载:“显庆三年下敕为皇太子造西明寺成。命给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⑧可以看出当时给玄奘剃度,十人作为随侍照顾其生活起居。同时,“侍者”一词应为僧人身份,为身份较低的沙弥或者沙弥尼一类。这也印证了敦煌图像中高僧身边出现女尼的合理性。
文献资料中不但记载了高僧身边有僧官或沙弥尼性质的侍从,而且还有养女身份性质的侍从。
据P.341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记载内容如下:
僧文信经数年间,与崇恩内外知家事,劬劳至甚,与耕
牛壹头,冬粮麦叁硕。
娲柴小女,在乳哺来作养育,不曾违逆远心。今出嫡(适)事人已经
数载。老僧买得小女子一口,待老师终毕,一任与娲柴驱使,莫令为贱。
崇。
从这段文书能够看出,娲柴是崇恩领养的义女,已嫁人,而婢女是其个人私买的,所以决定将其留给娲柴。⑨可见,僧人在俗家修行,可收养养女,蓄养奴婢,并有权决定其去向,这种已现象并不少见。僧人收养养女虽有悖传统的佛教教义教规,但确实是为了平日能有人照料侍奉自己,为自己养老送终。这种养女身份的侍从显然不同于出家为尼的随侍。
较养女身份地位低一些的就是奴婢身份的侍从。如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51号《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请户口牒》,是一份僧俗混合编辑的材料,现据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⑩转录该文如下:
前略
弟僧恒璨婢要娘
弟僧福集婢来娘
后略
这里写在两位僧人名字后面的均是服侍自己的女子,显然就是女婢的侍从身份。这种奴婢身份的侍从地位是十分低微的。
从以上文书的内容及其性质看,僧人收养养女,蓄养奴婢已然得到僧俗两界的认可,而且僧人随侍的身份及地位划分是有明显的界限的。
三、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女性随侍
僧人身边女性随侍的出现受到社会环境及社会思想的影响。究其缘由来看,是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催生的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其一,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私有制影响下的等级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世俗社会的等级观念深入佛教思想内部,使得佛教思想戒律松弛,传统的教义教规已经完全不同于初始状态。如传统佛教教义规定男僧应不近女色,但是女性身份随侍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一常规,而敦煌图像中又看到僧人身边又出现了女作男装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能够看到唐代思想开放环境下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看到佛教在当时社会思想环境影响下的适应力与包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僧人身边会出现女性随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随着寺院阶级分化的出现,出家僧人往往将世俗欲望和利益思想带入寺院日常生活中。佛教戒律本身对僧人蓄养奴婢的限制也在逐渐放宽。寺院僧人蓄养奴、婢,“有净人数千”⑪的情况甚为普遍。僧人出家而不离家,收养养女,与世俗生活联系十分密切,基于这种佛教世俗化的发展状况及文献记载,敦煌图像中出现的俗家女子形象就很有可能为僧人的养女或女婢身份。
女性身份随侍的出现是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渐世俗化的生动诠释。
四、结语
基于对敦煌古籍文献和图像的初步整理,针对僧人女性随侍这一问题的简单探讨,不仅从僧人蓄养奴婢、收养养女作为随侍的现象,说明了佛教在打破传统教义教规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包容性,而且女性随侍的出现也表明了佛教世俗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和饱满了。
[注释]
①贺世哲撰:《藏经洞》,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②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第111页。
③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⑤沙武田:《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页。
⑥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⑦参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编:《敦煌——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另见甘肃省博物馆编:《妙相庄严——甘肃佛教艺术展》,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⑧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四·译经篇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9页。
⑨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⑩〔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79年,第566页。
⑪《法苑珠林》卷52《感应记》。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23-02
*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项目-中央专项(Yxm201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