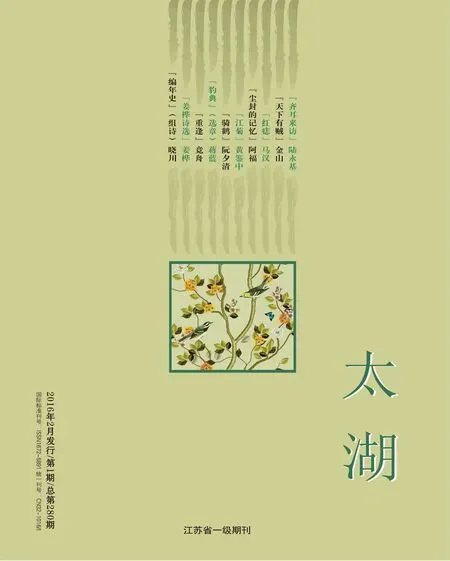冯小拧的艺术行为
缪文宗
冯小拧的艺术行为
缪文宗
冯小拧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和笔墨打交道。他的这个兴趣是小时候被颇为痴迷书法艺术的祖父培养出来的。那时候,祖父经常对他们姐弟几个说,字是出面宝,一个人有无学问,你不开口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字就不一样,一出手别人就看出来了。为此,姐弟几个小时候常常都被祖父拉着练字,也都练出了一手好字,其中冯小拧的字写得最好,因此祖父挺喜欢他。祖父是个老教师,脾气有些古怪。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做任何事都要有股子拧劲,不能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要有主见。当然也不能太拧,拧过了就容易认死理,就容易一条道跑到黑,所以他给他取个名字就叫冯小拧。
或许是长期练字的缘故,冯小拧的性格一直比较平和,遇事不大计较,也比较想得开。刚开始的时候,年轻气盛的他心里还揣着一个颇为蓬勃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将来能在市里乃至省里搞个个人书展。为此他下功夫临了不少帖,也多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市里找那些有名的书家指教,但是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永远是功底不错,但缺乏灵气。至于灵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时间一长他就想开了,就算是自娱自乐吧,毕竟还有单位这块平台供自己施展呢。冯小拧是在进厂的第五年被调到工会搞宣传的,这一干就干了近十年。两年前,单位换了新领导,在调整科室的时候把他精简了下来,说现在写字都用电脑了,没必要再特意设置这个宣传岗位了。于是被精简的他被安排去了仓库。就一般人来说,对此心理上可能会有些接受不了,但他二话没说就去了。毕竟库房的工作不算太忙,闲时还可以练练笔——只要不剥夺他的这份乐趣,换个岗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接受的——只是现在他的字拿出来展示的机会少了,只有等仓库里偶尔更换一些标识牌的时候,他那手漂亮的字才正儿八经派上点用场。
当然,如果就这样说冯小拧没一点脾气,那就错了。毕竟他不是圣人,吃的也是五谷杂粮,所以难得他也会拧一下。比如,这次为了妻子吴秀云的身份问题,他就犯拧了。
妻子吴秀云的身份是农民,这在她娘家户口簿的户别一栏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冯小拧和妻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的婚,已经十来年了。当初因为户口制度还比较紧,加上又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所以她的户口就一直留在娘家没有迁出来。按理讲是农民自然就有地,但是就在前两年,村里借土地调整就把以前在她名下的半亩多地给收了。理由是她人已经嫁出去,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况且你在城里也找到了工作,村里自然不会再留地给你了。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吴秀云就和村里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毕竟户口还在,所以遇到像选举这样的大事,村里还是尊重她的政治权利,把写有她名字的选票给她,包括同选票一起发的两条毛巾。而且因为她户口还在村里,所以当村里有像修桥筑路这等事,按人头摊派劳力的时候,吴秀云自然也会摊到一份,你不来可以,一个劳力折合多少钱,你就出点钱。他们夫妻俩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毕竟有几次村里分红,吴秀云还是能享受人均的百分之五十,进进出出似乎也差不了多少。
十多年来,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反正女儿出生后户口是跟他走的,上学什么的都不受到影响,再说像妻子这样的情况村里也有好几个,所以也就都没放在心上。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一直没有引起他们重视的户口问题,现如今会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尴尬。
年前的时候,冯小拧和妻子合议了一下,准备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他们现在住的还是单位七十年代初造的三层的红砖房,这房子以前是给职工做集体宿舍用的,所以结构简单,都是方方正正三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后来,单位新建了宿舍,就将这些房子陆续安排给了住房困难的职工。他和妻子结婚的时候,申请到了其中位于二层的一间,当时两人还为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爱的小巢而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但随着女儿的出生长大,那三十来平米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显得局促起来。去年年底,单位里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原来分配的房子一律要现金过户,否则退房。他去打听了一下行情,现在他住的地方要花一万多块钱。这就很让他有些心疼了。本来蜗居在这座破旧的楼房里已经够让他在不断改善住房条件的弟兄亲友面前抬不起头了,就连女儿都在嫌弃这儿像个贫民窟,宁愿申请了寄宿学校也不肯每天回来。现在单位居然还要逼他出万把块钱把这破房子买下来,这就让他很有些窝心。妻子也不愿意,说我们有钱不会去买新房子,还买这老房子做啥?于是俩人一横心,就商量着去买经济适用房。
然而就在他们拿着户口簿去登记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按规定每个人可以享受二十五个平方的优惠价,可是因为妻子的户口在农村,所以他们的户头上就只能享受两个人的优惠,扣除两个人五十平方的优惠外,其余面积只能算市场价。优惠价和市场价之间相差约一千七一个平方;也就是说,就因为妻子是农村户口,他们为此就要多出四万二千五,这可是他们夫妻俩一年多的收入啊。
两个人当下就傻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想到事情会因为户口问题而卡上一根骨头。怎么会这样呢?他对妻子啧着嘴说。妻子以为他是在怪她,本来就不痛快的心里,就更加不爽了,当即一跺脚赌气说不买了,说着掉头就走。
回到家里,冯小拧看了看坐在一边生闷气的妻子,叹了口气,就铺开了纸笔。每当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总是用练字的方式来平息心中的郁闷。但是,今天这个方法好像不灵了,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就像有一个火车轮子,那四万二千五就圈在那轮子上一直在卡嚓卡嚓地转动:都说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没啥差别,像现在无论是工作还是买东西谁还看你什么户口。可你说它没用,眼前就现刷刷地要多掏四万二千五,这后面的单位是元不是分呐,也不是日元而是人民币!百元大钞摞在一起将近四公分呢。虽说多年来,夫妻俩也从嘴里省下了一点薄薄的积蓄,但这多出来的四公分,他们一家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好几年呐。想到这里,他把笔一扔,这户口真他妈的可恶!
那天妻子情绪很低落,晚上扒了两口饭就早早上了床。等冯小拧收拾完上床的时候,就感觉到背对着他的妻子肩膀正在不时地抖动,他伸过手去朝妻子脸上一摸,就摸到了一手的泪水。他的心颤了一下,心疼地扳过妻子的肩膀,对着灯光用手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妻子的眼角已有了细细的鱼尾纹,脸也没有过去那样光滑细腻了,过去黑缎般的头发也夹杂了几丝白色。十多年了,妻子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默默守护着生活中的这份清苦,从没抱怨过什么。作为一个男人,他没有给妻子过上富裕的生活,反而让妻子陪着他住在这破旧的老房子里,让她也在亲友间抬不起头来。作为丈夫,他有愧啊……
想到这里,他轻轻摸了摸妻子的脸说:别难过,明天我们就去填申购登记表。
要多花四万多块钱呢,你不觉得这钱花得冤枉?
嗨,买套房子三十来万,这大钱都决定出了,还在乎这些小钱做啥。
你口气倒不小,四万多块还是小钱,等什么时候你赚个大钱给我看看?
哎,你还真别说,小时候我妈请人替我算过命,说我命里有财运。俗话说,命里有财跑不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真赚大钱了,让你整天坐在钱堆里数钱。
你就会贫嘴。妻子点了一下他的额头。尽管妻子知道,就他一个在单位看看仓库每月领领死工资的小保管员说什么发大财,简直就是瞎子拉胡琴不靠谱的事儿。但被他这么一哄,心情还是明显好了起来。
冯小拧见妻子笑了,突然就有些按捺不住,说:那我就来些实际的。说完就翻身跨了上去。妻子虽说也有近四十了,但身材还是有模有样,加上皮肤本来就白,和人们印象中黝黑敦实的农村女人完全不同。冯小拧一直很迷恋妻子的身体,因此每次做起那事也就特别卖力。让那四万二千五见鬼去吧,让那户口什么的都统统见鬼去吧,他边做边想。
冯小拧此时也确实想开了,钱多出就多出点吧,好比别人买商品房,市场价一点优惠都没有,这样一算自己还是合算的。所以他也就把这事丢在脑后了,毕竟买房子是大事,后面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呢。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才仅仅过了半年,妻子的身份问题再一次让他陷入了困惑。
那天,他们一家子去乡下探望岳父母,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说是为加快城乡一体化,乡下的地都要被收去了,为此市里专门划出一笔钱来要对当地的农民统一按标准进行补偿,而且听说这补偿款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
这个消息对正因买房闹亏空的冯小拧一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说买房的时候多花了四万多,但现在不是补回来了吗?冯小拧想着就感到很兴奋。
但是兴奋了没多久,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所谓的失地补偿,是对有土地的农民说的,妻子的地两年前就被村里收去了,她还会有吗?这一想,原先兴奋的心情马上就像浸了凉水一样冷了下来。
一连几天,他为此搞得整个人心神不宁。这件事必须弄清楚!
但是又到哪里去打听呢?他在心里琢磨了好几天,终于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于,原是和他一起进厂的。进厂没多久,恰逢单位为了档案管理达标,特意组织人员对原有的档案重新进行编订整理。冯小拧因为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就被借调去了,和他一起被借去的还有这个姓于的同事。两人在一起相处了有大半年,关系还不错。借去的时候,两人还是同一个起点,待档案整理结束后,彼此就有了差距。他依旧回了原来的车间,于同事却借这个机会进了单位的人事科,没多久,又通过关系借到了机关,两年后关系转了过去,现在已是市社保局的一个科长。
于科长还算是个念旧的人,见了他很是热情。还没等他摸出特意花了四十多元钱去买的那包苏烟,对方就把一支软中华递到了他手上:抽我的抽我的。闲扯了几句后,他就和于科长讲到了正题。于科长听后说,这事我知道,这笔补偿费市里先拨到我们社保局,前两天刚转下去,我来帮你查查文件。
查过文件后,于科长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这事你不用担心,文件上规定是按户头人口结算的,应该没事。再说了,是农民就应该有田,至于村里收回土地,那是村里搞的小动作,这本身就不符合相关的规定。于科长还告诉他说,市里拨下的那笔补偿款分为两块,其中百分之七十直接进入农保基金,用作失地农民在到达退休年龄后的生活保障,其余的再以现金的形式分发到每一个人。
听他这么一说,冯小拧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下来。
眼睁睁地等了一个多月以后,乡下就传来消息,说村里将加入农保的名单张贴出来了。得到消息后,冯小拧夫妻俩特意去了趟乡下,还特意去村头看了张贴在那儿的名单,在众多的名字里他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吴秀云”,这使盘绕在他们心头的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看过名单的夫妻俩很有些兴奋,一起去附近的船厂买了几样小菜,还带了两瓶酒。平时很少喝酒的冯小拧那天情绪很高,和岳父、小舅子有说有笑,居然也喝下了半瓶酒。
回家的路上,酒意微醺的他觉得心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他一路上盘算着这笔补偿款到手后派些什么用场,虽说到手的也就一万多块,但也足够他们添上几样东西的了——首先要换的是家里那台结婚时买的21吋电视机。那台电视机已修了两回了,动不动就要闹罢工,等搬新房的时候一定要淘汰了换一台大点的液晶电视。然后再给女儿买一台电脑,女儿想电脑都想疯了,一到星期天就去同学家玩电脑,等家里买了电脑以后,女儿就不必上别人家去玩了。还有,妻子骑的那辆自行车也该换成电动的了,都十来年了,那辆车除了三角架几乎所有的零件都换过好几茬了。再说每天上下班光花在路上要一个小时,来来去去也挺吃力的。当然,还得给妻子添置两件像样点的衣服,她的衣服都是小百货市场去淘的一些便宜货,出门常常连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他这么想的时候,心情就像天边的云朵一样悠闲和舒畅。
晚上,夫妻俩坐在床头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冯小拧就把自己路上的这些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却摇摇头表示不赞同,说女儿今年已上高一,两眼一眨就要考大学,现在买房子又贷了款,估计这几年手里根本攥不了几个钱,所以这笔钱得留给女儿上学用。
还是妻子想得周全。听她这么一说,冯小拧只好乖乖把自己的那些打算卷巴卷巴扔一边去了。是啊,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能比女儿的将来还重要呢,要怪就只能怪家里太缺钱。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不远处那条通江的马路上,不时传来汽车驶过潮湿路面发出的沙沙声。
过了一会,妻子把头躺进他怀里轻声问道,你说这补偿款多久才能够发下来?冯小拧捏着她的耳垂笑道,你那么着急干啥,还怕少了你的啊。
钱只有到手了心里才会踏实,诶,你说这总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吧。
你这不是多操的心吗,你当煮熟的鸭子真能飞啊。
夫妻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都陶醉在即将到来的希望里。
然而,就像上了年纪的人常念叨的那样,这世上的事体没人能说得准。就在冯小拧对妻子说这番话的时候,或许他压根就没想到这煮熟的鸭子真的会飞,而且飞得毫无道理。
冯小拧夫妻俩才刚刚兴奋了半个来月,岳父的一个电话就像一盆兜头的冷水顿时就把他们心头那份摇曳的期盼浇得一片冰凉。岳父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最近在村上听到消息,说像秀云这样嫁出去的人可能没有现金补偿。
怎么会这样呢?冯小拧举着电话愣愣地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明明农保名单上还有的,怎么到现金这块就没有了呢?他怎么想都想不通,就决定明天一早和妻子到乡下去一趟,把事情弄个清楚。
第二天刚到村口,他们就遇到了正准备开车出去的村长,冯小拧一个快步就上前拦住了他。村长一愣,看了看随后跟来的吴秀云,马上就明白了。他脸上堆起笑,掏出一根苏烟递给了冯小拧说,大侄婿,是不是找我有事?
冯小拧没接,说是有事想问一下。于是就说了岳父那里听来的消息,问他是不是真的。
村长没有马上回答,自顾自点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再长长地吐出一条烟雾。然后才慢慢地说,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来说很意外,其实我也很意外,上次农保名单上还有,怎么这次说没就没了。因为村里这种情况也不止秀云一个,所以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大队部。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我也做不了主。
冯小拧说,之前我已经问过,这补偿费是按户头和人口下拨的,这又是哪里的政策?有没有红头文件?或许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的情绪就有些激动。
村长听了脸上就有些紧张,说:秀云家的,你这么问就有问题了,我们做事都不可能胡来的。说着他脸色又缓和下来: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这事搁谁心里都不好受。可这也是没办法啊,你想,我和秀云她家论起来还是亲戚呢,虽然远了些,可我祖父和她太祖父毕竟还是亲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自家人能不帮自家人吗?可是……村长无奈地摊了摊手,继续说道,大侄婿啊,这哪里的政策我也不知道,反正上面怎么说我怎么做,你如果有疑问的话,不妨去大队里问问,或许他们解释得比我清楚。我现在还有点事,得先走了,有空去我家里坐坐。说完,他就钻进了自家的桑塔纳,冲他俩摆了摆手,兀自扬长而去。
看着小车一溜烟地远去,妻子问道,现在怎么办?冯小拧说,那我们就去大队部找个说法。说着去岳父那儿打了声招呼,门也没进就直接奔大队部去了。
大队部临近镇上。进去后他们根据楼口的指示牌上了二楼,二楼并排有好几个办公室,虽说正是上班时间,但办公室里却都没人。他们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听到旁边洗手间的门响了一下,接着走出一个拿着报纸的年轻人来。那年轻人瞟了他们一眼问道,有事么?
冯小拧就跟着进了办公室把来意说了一遍。年轻人看了看吴秀云,然后点着头问道,现在你的名下还有地吗?
5)指导同学根据临床诊断结果将表达谱数据在EXCEL里进行分组,然后进行t检验,并且按照P值进行升序排序。
两年前被村里收去了。
收去了?为什么?
说是人嫁出去以后,村里就不留田了。
这是你们村里搞的土政策!年轻人看着他们摇了摇头说,当初这田就不应该让村里收去,现在的补偿就是根据你名下的土地的面积来计算的。你没了田当然就没有补偿了,这也只能怪你们当初怎么肯轻易把田让出去啊。
夫妻俩一听当时就懵了,怎么事情绕了一圈绕到自己身上了?
没办法了?
没办法,我们大队十八个自然村都是这样定的,田是村里收的,这事你还得找村里。冯小拧突然就想起了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农保的名单上还有她的名字。
那是大队里是出于体恤和照顾,像你妻子这样,人不住在这里但户口还在的,统统把名字都放在了里面。但她毕竟没田了,所以现金补偿的一块就不能享受。
谁告诉你的你就找谁要去。对方轻轻一句话就把冯小拧给噎了回来。
这么说这事就没戏了?冯小拧的喉结艰难地滑动了一下,干干地问道。
基本没戏。对方回答得很干脆。
夫妻俩呆呆地站了一会,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从大队部走了出来。还没走到停车的地方,吴秀云就在后面忍不住抽泣起来。
看到妻子流泪,冯小拧的心里一阵窝火,他不明白事情原本打听得好好的,怎么到了这里就变了样?这不明摆着欺负人么?想到这里,他忿忿地把路边的一颗小石子一脚踢出了好远。
不行,这事要弄个清楚!
下午,冯小拧又去了趟社保局,于科长听他把事情一说,就显得很诧异,说怎么会这样呢?文件上并没有这样规定,这肯定是下面哪里出了问题。
我也是搞不明白,明明农保还有的,怎么到了现金补偿这块就没了呢。
这个倒好理解,因为农保是市里直接办理的,至于现金嘛,就只能层层转拨,这里面有些事就说不准了。说着,于科长颇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能帮忙想个办法?冯小拧搓了搓手,求援似的看着他问道。
啊,这个忙恐怕帮不了。于科长马上就摇了摇头,见冯小拧正看着他,便解释说,因为这具体工作毕竟下面在搞,不在我的范围内,所以手也不能伸太长。再说了,这是下面的土政策,我人微言轻就是想帮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要不你把这事情去信访办反映一下?
听于科长这么说,冯小拧就知道这事还真难办了。他知道,找信访办不大可能解决问题,以前他们单位里就有人因为企业改制中的一些问题去信访办交过材料,结果没几天这些材料就转到厂里来了。弄得那个交材料的人后来没法再呆下去,只得走人。他可不想做这些无用功。可难道就这样放弃不成?想来想去没有放弃的理由啊。虽说前面的买房子多出了四万多,而这笔补偿款现金部分也就一万多,两者相差了一大截,但毕竟前者有正式的文件规定,且理由也站得住脚——农民可享受一定的宅基地自己建房——而这笔补偿款却是扣得根本没道理啊。不,不能就这么算了。
冯小拧考虑了一个晚上,决定再去找一次村长,毕竟田是村里收去的,这个说法还必须到村里去找。当然,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从正面讲道理摆理由已是不可能顺利解决这件事了,那么就只能放低自己的姿态,用商量的口气去求村长能否照顾一下。而眼下求人帮忙是不能空着手去的。于是吃个痛装了个一千元的红包,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去了趟村长家里。
村长显然已经知道他们去过大队部了,因此他刚提起补偿款的事,就摆手打断他的话说,大侄婿,今天你来我家坐坐我欢迎,但如果是讲补偿款你就别多说了。你们大队部也已经去问过了,想来事情也应该很清楚了,你来找我也没用,我早说过我做不了主的。
冯小拧没想到村长这么快就把门关上了,这使他原先在家里想好的一些话一上来就失去了用场。他张了张嘴,很吃力地挤出一句话来:可是,队里说这次补偿款是根据各人名下的土地的面积计算的,而秀云的田是村里收去,所以……话还没说完,村长的脸就沉了下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没、没什么意思,我只不过想和叔你商量是不是可以帮忙想想办法通融一下。说着冯小拧就从口袋里拿出那只准备好的红包。你这是干啥,快收起来。村长怕烫似地朝后闪了闪说。叔,还请你多帮忙啊。冯小拧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烫,觉得自己此刻很有些摇尾乞怜的味道。
哎,哎,我说你别来这个呀,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你这样也太小看你叔了,你叔是这样的人吗,快收起来。村长边说边皱着眉忙不迭地挥手,仿佛那红包是一坨令人恶心的脏物。
这个情形让冯小拧一下子变得进退两难,当时他恨不得给自己扇上个嘴巴,你这不是自个儿犯贱自找难堪吗?
村长的油盐不进让冯小拧没了辙,他呆在那里想了想,干脆把红包又揣回了口袋。然而,即便这样他还不想就这么放弃。那……叔,冯小拧解嘲似的干咳了一下:秀云的事你看还能不能想想办法?
嗨,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如果这是秀云一个人的事,我或许可以帮你想想法子,可是这村里像秀云这样的不止一个,你说我帮了秀云其他人到时顶起来怎么办?
话虽然还是比较婉转,但冯小拧还是听出来这事没戏。心里不由得一急,便把那句在心头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叔,怎么说秀云户口还在村里,户口簿上明明白白写着她是农民,你说农民怎么就没有田呢?
村长睇了他一眼,给自个儿点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你说秀云和你结婚后,已跟你在城里过日子,村里怎么还会给她留地呢,当初收地的时候我不就对你们讲过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我们农村里的规矩。
你说是规矩,怎么这前后其他村里没这样的规矩?冯小拧说这话并不是没根据,在他单位里就有附近村子的人,昨晚回去后他就去打听了。
嚯,看来你还真打听了不少。我告诉你,农村里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十里八村每个村情况都不一样,规矩自然也不一样。村长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就挂着一丝少见多怪的嘲笑。
话说到这份上,就是傻子也能听明白了。冯小拧就有些气愤,说道,这算什么规矩,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
如果你们觉得真咽不下这口气,办法倒是也有,不过……村长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没有说下去。什么办法?冯小拧急急地问道。我不能说,这话不中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中听不中听的,你说吧。真要说?说。这是你让我说的,那就不能怪我说瞎话。村长清了清嗓子说道:秀云要拿这补偿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你离婚,离婚后她只要是回娘家来,村里自然就会把田还给她……
什么?冯小拧听了不觉一愣,他没想到这所谓的办法竟然是让他回去和妻子离婚!
我说这话不中听你还偏让我说,我说了你又没法接受,这个……村长摊开手装出一脸的无奈。
话说到这份上,冯小拧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只得悻悻地从村长家里出来。刚出门,就听到村长在后面嗤儿嗤儿地笑。这笑声让他在蓦然间产生出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回到家,妻子看他一脸沮丧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顺利。因此也就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去厨房把准备好的饭菜端出来。看着妻子进进出出的身影,冯小拧就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妻子上夜班,所以吃完晚饭就早早上床了。冯小拧铺开纸笔,想让心头窝着的那股气顺顺,但写了好几张纸心里还是乱糟糟的。他就想不通,怎么一个小小的村委居然可以无视上头的文件为所欲为。什么规矩,明明就是想着法子黑老百姓的钱。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掷了手中的笔。
难道就这样算了?不算你还想怎么样,就是黑了你,你冯小拧又能怎么样?这么忍气吞声不太窝囊么?不然你想怎样,你无权无势能翻得了天?不行,我不能让这口气白白窝在心里。那你有什么办法?冯小拧闷着头坐在那里,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激烈地争论着。
直到妻子起来上夜班,他还没想出一点头绪。妻子走后,他上床无聊地打开了电视,无意中看到某生活频道的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坐在路边的老人,老人手里拿着一个硬纸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还我公道!”大字的下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好几行字。听了一会他才清楚了事情的大概:老人的儿子前不久去医院挂水,谁知挂着挂着就死在了医院里,家属去医院讨说法,医院说死者本身有心脏有问题,就诊时没和医生说明,挂水时发生心肌梗塞,错不在医院,所以拒绝赔偿。老人说自己儿子身体一直很好,前一阵单位还安排过体检,没说有啥病,怎么会挂挂水就死了呢?为此老人多处申诉,但一直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出此下策。老人说,虽然对于赔偿她已不抱多大希望,但她至少要把事情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
冯小拧看着老人手里的纸牌,突然就灵光一闪,对啊,就算事情不抱希望,但也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把这口气憋着啊。想到这里,他一翻身就下了床……
大约二十分钟后,冯小拧就拎着笔墨站在了村委门口的那块水泥场上。这时已是午夜时分,明月当空,月光如雨,整个村子都已枕着泥土的芳香睡着了。周围的田野里,秋虫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冯小拧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水泥场,他知道这块水泥场是村里最好的水泥场。此刻平整细腻的水泥场在月光的映照下微微泛着一层白光,就像一张偌大的宣纸。
本来他来时就想照电视里老人的做法来一番控诉的,当他看到这净白如纸的水泥场却改变了想法,觉得还是写首诗好。由于平时练字熟读不少诗,所以依样画葫芦诌上一首也不是什么难事。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便俯身取出笔墨蹲在那里刷刷写了起来:
农民有田本天理,岂因出嫁把田还。
文件本按人头补,村里偏照规矩办。
所谓规矩自己定,糊弄村里老百姓。
日月昭昭天犹在,怎敢就把良心卖。
写完后,他站起身看看,发现那一个个散发着墨香的黑色大字,在泛着月光的水泥场上竟是显得那么灵动还隐隐带着立体感,好似摩崖石刻。他写了这么多年的字,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这样奇妙的感觉。呆呆地看了一会,刹那间便产生出一种创作的冲动来。再写些什么呢?他低着头想了一会,就想起以前祖父经常背诵的那首毛泽东的七律: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不错,就是这首!不仅诗作本身很有气势,而且也符合他此刻的心情。拿定主意后,他便俯身挥洒起来,那一刻他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意念都在这笔下奔涌流淌。他写的是行草,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提笔站起身来看着地上的整幅作品,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整首诗气韵流畅墨意盎然,特别是其中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笔墨淋漓气势嶙峋,是整幅作品中写得最出彩的。
冯小拧站在如水的月光下静静地看着,那一刻他有些陶醉,觉得眼前的这个作品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幅……
作者简介:
缪文宗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多篇作品在《广西文学》、《飞天》、《散文》、《雨花》、《山花》、《阳光》等刊物发表,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江阴市作协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