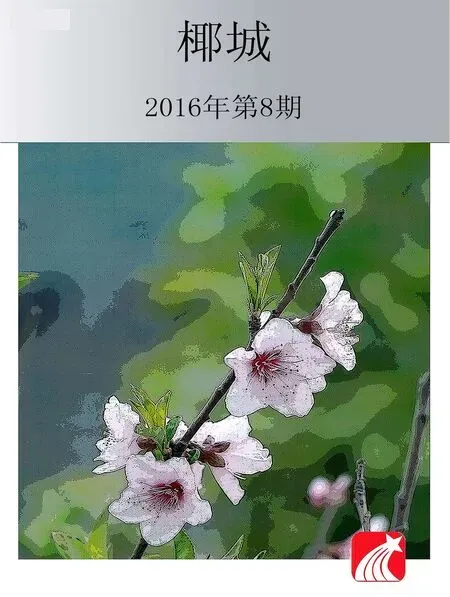习俗顽固
习俗顽固
一
习俗是带有地域性的人文景观,一项习俗不会是也不应该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但肯定是被处在某种观念框架下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甘心传承。
文人骚客笔下的习俗,常常链接着某地某群体的某项特征,常常蕴含着特定人群未必高尚但却相当感人的热情……其实这都是经过遴选后的命笔。某地的某些习俗,直说了还是相当野蛮的——比如国内某地的新婚闹洞房习俗,居然牵涉到对新娘的侮辱或占便宜,以致今天仍然不时传出因此而酿的血案悲剧……
我的出生地广西崇左,习俗也不少,大多数习俗也都表现地域文化的深厚积聚,但嵌在其中的某项习俗,说它野蛮吧也许有点过,但缺乏起码的人情味却是明显的——比如建造新宅3年内,如果遭遇不期而至的亲朋葬丧,就有一种习俗相当值得探讨。
新宅建造从动土到落成入住,各个环节遵循一系列既定的习俗,这都可以理解,比如动土时挑选集合多种吉象如福寿、聚财、命理等的所谓好时辰;比如在上梁大吉中,张挂着“上梁大吉万事如意”的条幅,燃起鞭炮,唱着“上梁歌”,把香烟、糖果、粽子、糍粑、米花等跨过梁上撒到地面上,让围观的大人或稚童们争抢;比如择日入宅“安香”“归火”,需以家中主事者的生辰八字为主要参照系,再拼出其他家庭成员的种种资料以免犯所谓的“冲煞”;比如入住摆酒的同时,接受亲朋馈赠的镜屏、画幅、题字、家具和礼金等……
总之新宅落成后所获得的馈赠是多样的,收到的祝福更是慷慨的,一时间整个世界好像都在为你展现笑脸。但终于还是会遇上了令人不快的事儿——岂止是不快?简直是悲哀——因为传来的是有关葬丧的消息。
人生自古谁无死?在我们偌大的国度里,有关葬丧消息的发布可谓每天不断,只不过消息发布的方式与发布的范围大小不一样,显赫者逝世能登传媒显要版面,而平头百姓呜呼则仅在局限的范围内传告。当然,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最关键的是某个具体的葬丧消息是否与自己有关。如果葬丧消息发自官方,某级领导人逝世,出于遵守规定或发自内心,你我他都参与吊唁与告别仪式;倘若葬丧消息发自特定的某人,而你又处在特定的新宅落成时段中,这就给你出一道难题:去参与还是不去参与?不去吧,逝者的确是至亲好友或平素和睦相处的邻居街坊,去吧,此间又有一个陈陈相因的习俗:盖新房子未满3年者,绝对不能去参与任何白事!在两难抉择带来的冲突中,基本上都以前者向后者妥协作结,哪怕逝者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等跨代至尊,或者是伯叔姑舅姨等上辈旁系血亲,以及堂姐妹表兄弟等平辈牵系一族……
这条无形的“规定”不知诞生于何时并已经维系了多少年多少代?反正我所在的小镇上,基本上就没人敢去触碰——即使在几十年前文革期间最不按世俗“牌理”处事的年代,这里的人们也仍然牢牢遵守这道顽固习俗——哪怕那时候所盖的新屋有时候甚至仅仅是茅草棚而已。现实记录中,由于新屋落成的原因,已经有舅舅过世外甥不近,叔叔西归侄儿不沾的多起成例,比较极端的居然还有:老父亲逝世,而已经出嫁的女儿竟因夫家建造新宅而不能去尽孝道……
二
近年我回老家祖宅建造新楼,新楼落成不久便遭遇了上述情况:我的堂姐夫未及古稀便遽逝。我堂姐是我堂叔的独苗女,没有兄弟姐妹。而我兄弟仨,没有姐和妹,所以我很早就把这位同族堂姐当成亲姐。
我家祖上是镇上的非农户居民,60年代初我母亲便是镇供销社职工,那时候,长我10多岁的大哥已经大学毕业,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大哥把长我4岁半的二哥接到他工作的城市去读书。家里仅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八岁多时,母亲被派到县里学习三个月,于是母亲便把时读小学一年级的我托付给一位同族婶婶——也就是我这位堂姐的母亲照料。在我的儿时往事存储箱里,清晰地保留着长我六七岁的堂姐帮我打热水洗脚,并哄我入睡的深深记忆……
我长大后恋爱结婚,堂姐竟然又以未婚之身帮我把媳妇接进家门……
堂姐晚婚,她的俩儿子都在外打工。姐夫辞世,此时尤其需要亲近、劝慰守护和帮忙,我尽管疼痛在心,却在顽固习俗力压下困守新楼中,始终未敢露面,只能在书房里独自默默垂泪。
乡人都深谙习俗的强大压迫力,堂姐当然也会理解我此时此刻的无言痛楚。堂姐的极好人缘此刻得到最大的体现:看望的、伴随的、守夜的、张罗的、帮忙的……都不乏人手,但不管怎么说,此时偏偏少我这个弟弟出现,实在有点儿不是滋味。
奈于习俗,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终于有人向我出谋献策:“你暂时不能参与白事是铁定的,但也不是没有变通办法,你可以暗中委托某人先代替你送出奠仪,但必须过40天后,才能把这笔奠仪数额还给此人。”像在黒厚的云层中窥见一抹玫瑰色,我带着一丝欣慰接受了这一建议。
接下来又有人指点:堂姐夫出殡后第3天就可以去看望姐姐了,无需再守什么七七四十九天……于是在第三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携妻出现在堂姐身边,挽其臂膀,陪她垂泪,劝之节哀……
乡中智者劝我所做的所谓“变通”,其实也是此间人们久被习俗束缚后的一种反弹,这种反弹的力度虽然有限,但至少说明,人们对习俗中蛮不讲理的一面已经不太愿意继续百分之百地忍受下去了。
三
这到底是何人做出的规定,何时订出的规矩,并以“习俗”的名义压迫着人们必须去执行?既然它具有这么明显的违背人伦的不合理性,但长往以来人们何以都去遵从它,恪守它?我曾尝试与三五友辈以及多位乡间智者对之进行探讨,标准答案当然是没有的,但稍微想一想便会意识到:这一定是从新宅落成的“安全”角度去考量,说到底不外就是担心新宅之喜提前被骤然而至的葬丧氛围浸染或冲刷,所以极力延缓新宅主人与葬丧白事搭边。
倘若进一步设问:果真有人出于我行我素的态度违反这一习俗,那导致的后果又将是什么呢?难道就一定驾车出车祸,游泳沉江底?难道土地爷专门去划定你家新宅这一小块地来设计发生地震?或者你家虽然地处平坦地带,而遥远的山体滑坡却专门为你家堆叠而来?反过来说,现在层出不穷的自然灾祸与人为事故,其因果链条难道都是不幸遇难者不遵守上述习俗所至?
回答当然是确凿否定的,既然如此还怕什么呢?国家政策中,原先某些照顾不到人性的部分条文,在“以人为本”的旗号下都会被调整。根据这一精神,再试从更加贴近世情事理的视角去做剖析:一项习俗,它总该围绕着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一般都应该充满善意,崇尚理性,张扬人情。从传统的忠孝节义标准看,百善孝为先,既然这一严重缺乏人情味的习俗绝对违背了“孝”的核心圭臬,难道还不应该对之进行甄别并予以调整?
不能说乡镇中所有习俗都一直没做过改革,比如原先新宅入住之日,亲朋送贺礼,品种再多也不能送挂钟——因“送钟”与“送终”谐音,当为禁忌,但近年来也开始有人兴起送挂钟了,而接受者也在“福大不忌”的解释下欣然接受。至于上述这一偏离人性人情的习俗,乡中智者终于想出了“变通”的招数来应对,也属可圈可点,但是未免太被动、太窝囊,太不理直气壮。习俗的潜在力量纵然再强大,但它也经不起众人去反拨,去抬杠,去据理力争……或者根本就没必要去“争”,而需作悄悄改动或者不予理睬,你没顾忌我没顾忌,大家不都爽心惬意了吗?
——哦,应该抨击的也许不仅仅是习俗本身,该反思的也许不仅仅是缺乏思考盲目从众的人们。这一刻我顿然反思:最应拷问的是我自己呀:曾被人冠以“杠爷”的阿廖,你不管在网上或者在现实论辩中不知就多少个话题与人抬过多少次杠,但今在这一顽固习俗面前,你何以表现得如此窝囊?如此憋气?你为何不敢与这个顽固的习俗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