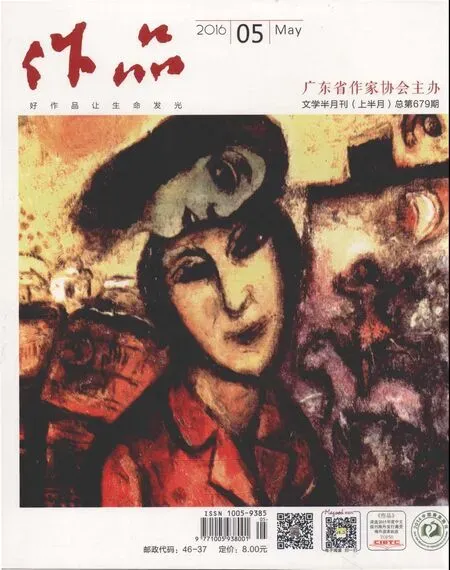会飞的父亲
文/李 浩
会飞的父亲
文/李 浩
李 浩男。1971年生于河北海兴。发表作品260余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小说、诗歌入选30余种各类选集和大学、中学读本。作品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 《侧面的镜子》、 《蓝试纸》、 《告密者》。长篇小说《如归旅店》、 《镜子里的父亲》。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第十一届河北文艺振兴奖,首届都市小说双年奖等。
1
我准备写作第三篇《会飞的父亲》。我想,这一次,我将加入一点寓意在里面。这本是米沃什的句子。原句是:“现在我想讲米德尔的故事:我且放进一点寓意。”
好吧,我且放入一点寓意。这也是我的习惯,我习惯如此,一向,我总是概念先行——我觉得这是一个被误读、被用坏的好词儿。没有这一点寓意,父亲是无法飞起来的,我以为。游戏性是文学的另一条翅膀,反复地写《会飞的父亲》,是我留给自己的游戏。
这时问题来了:父亲不能仅靠寓意飞翔。他还需要其它的辅助,譬如飞机,滑索,火箭,飞毯,床单,或者鸟的翅膀。或者热气球。热气球不能用,在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哥哥柯西莫就是拉着热气球垂下的绳索“升入了天空”——我当然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这篇小说我不准备再使用所谓的“互文”。飞毯,是阿拉伯人的专属,父亲借不来它,它不合适。至于床单……当然更不可以了,俏姑娘,蕾梅苔丝,她乘坐床单和尘世的责任、鬼火告别,这个出现于《百年孤独》的美妙段落我已经在《镜子里的父亲》中借用过一次,第三次,等于是第三次把爱情说成是玫瑰,书上说这样就是平庸的愚蠢。是的,飞毯,床单,热气球,不是父亲此时能得到的,它们属于红笔划掉的禁用词。
想想前面:第一篇《会飞的父亲》,里面的父亲是凭借想象飞走,他不存在,没有出现过,是一个模糊的虚词,对他的种种飞翔完全是儿子的幻想,他被赋予神迹和能力,当然,这和父亲“离去”的真实距离遥远。第二篇,父亲依然没有借到翅膀,我有意让他始终沉在日常里,他的飞只是象征——我在这里面就加入了一点儿寓意。
暂时把寓意放在一边,现在,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能让父亲从地面上飞起来。这是个问题。有难度的问题。这时我还不想制造神话,神话,是下一篇的。是的,我曾试图把翅膀塞给父亲,在他的肩胛处涂上粘接的蜡——但随后,它又一次遭到否决。我将即将飞起的父亲按住,拔光了所有的羽毛。
那,我的父亲,他还可以建造一个庞大的器械,凭借它从一个山坡处向下滑翔……似乎可以。这是一个解决之道。和这个身份相称——我的父亲,李老师,是一个乡村诗人。我计划,让父亲重回乡村诗人的身份,他希望飞翔,这样会让他赢得更多的尊重,而尊重一向那么稀薄……
最后一刻,我再次放弃了它。
当然可以塞入寓意,这没问题,乡村诗人的身份本身就有寓意感,何况还有尊严,飞翔……我放弃它是因为它留下的空隙太小。这是一个小口径的气球,里面放不进太多的气体,那一小点儿的寓意如果仅像樱桃的大小,也是我不想的。再说,在我的《乡村诗人札记》里边,这样的寓意已经放置过一次,将它重新拿出来,就会看到浮在上面的种种锈斑。父亲的飞翔需要另外的路径。
他,或许,需要一双飞行鞋?
我把“飞行鞋”写在一张购物小票的纸上。背面。
2
我如何,才能让父亲再次飞起?这不仅是个问题,还是个难题。
他没有飞起来的渠道。没有路径。没有飞行的鞋子。没有腿——好吧,这属于灵感:会飞的父亲,在他飞起来之前我干脆让他更低,让他更没有可能——我决定,在这篇小说里,父亲将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不止飞不起来,就连普通的生活,跑和跳都已不再能够。不止如此,我还要,让他完成自我囚禁——出于羞愧、虚荣、对尊严感的呵护以及对观看的拒绝,他,要把自己囚禁在一个房间里面,足不出户。那间房子将成为他的壳,他是一只软壳的蜗牛——我说过我要在里面塞入点寓意,这个壳将成为寓意的部分:车祸使父亲更深地缩进了壳里,他的怯懦本性更强烈地呈现出来,当然,在我们这个家庭中间他还是一个坚固而强大的存在,他要时不时地向我们施压,施威,让我们不能忽视他,并把他的不快乐加到我和我们的身上。
可此时,他依然没有飞翔起来的渠道。《会飞的父亲》不能不提到飞翔,这个飞翔必须给予父亲,否则,它就……我的踟蹰依然在这里,而且在“降低”之后,飞翔的可能性又一次遭受限制,我如何说服自己和阅读者,这个被按在轮椅上同时又将自己囚禁于房间中的父亲能够学会飞翔,并且可以飞离他不习惯也不喜欢的生活。
它,实在费思量。一天,一天。我想,我也许应当暂时地放弃它,我还有别的什么需要写作,譬如一个大水将至的故事,譬如一个杀人犯的故事,他杀了自己的女友和她的妹妹,选择了逃亡,而追逐他的警察则是邻居,她告诉女儿的是另一个故事:楼上的死亡不是真的,忙碌的担架抬走的不过是一碗鸡汤。再譬如,一个德国故事:一个德国人,在二战时作为少年的兵员来到苏联,这时他完全是懵懂的根本没受过多少训练。第二天,他站岗,苏军的士兵摸了上来。出于怯懦,他没有发出呼喊也没有摸到自己的枪——这一日,是德军败退的开始,之后的结果当然就像历史中写的那样。这个德国士兵一路躲躲闪闪返回到故乡,此时的故乡已经满目疮痍,它被苏军占领,而他的妹妹也已经死去。接下来许多年,他过着平静的生活而内心里却时时波涛汹涌,自责近乎压垮了他——他以为,是自己的怯懦导致了帝国的溃败,并导致了妹妹的死亡,因此上,他在无法洗刷掉自己的耻辱之前不配得到任何的快乐。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试图秘密潜入苏联刺杀某个人或某些人,计划还算周详,但新闻里,他名单上的人却一个个减少直到斯大林也已去世,这个计划还没有进行。在日常里他是平静的,但容不得别人嘲笑,更容不得别人说他怯懦,在那时他则完全是一只有怪癖的刺猬。时间在走,一年一年,他慢慢地老了,而柏林的墙已被推掉,苏联不复存在……沧海桑田,邻居们越来越与他格格不入,而他时不时会在记忆里沉浸,不能自拔。这一日,来了两个白俄罗斯的人,一男一女,他们来德国旅行……老人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谈及二战,两个人对此毫无兴趣,只是女孩偶尔谈及,她的爷爷曾参与过战斗不过很快在战争中受伤没有随部队进入到波兰。恰是这句话引起了这个已经老年的德国人的热情,他邀请他们在他的家里住下来。晚上,老人拿出自己藏了很久的军刀,反复的擦拭着——也许,这是一次机会,他终于有机会向人们证明,他战胜了怯懦,哪怕为此搭上性命。或许,有机会,我会在文字中让这个老人说出:他并不爱那个帝国。但他也不接受帝国毁灭的疼痛,何况,它的毁灭似乎与他的怯懦失职有关。“我大约能理解你们所说的正确。只是,我的不一样。”
这是一篇构思许久的小说,早在三年前我就写下了提纲,或许,开始写作它更为合适。我坐在电脑前,删除了“会飞的父亲”,换上“怯懦者”——它等于撕掉了一页。即使使用电脑,我也听到了纸片被撕碎时的那种声响。
新故事将要开始。不过,对于《会飞的父亲》牵挂还在。它是一粒未曾发芽的种子,只要它在,只要有了适合,芽还是会发出来的,我相信。
3
是什么阻挡了我对德国故事的书写?可能还是这粒种子,它构成了堵塞。它挡在曲径瓶的瓶口,使可能的水流总是不畅。这时它还是硬的。
如鲠在喉。它让我想起布罗茨基的诗句,他说,有关鱼的诗,就像是一根梗于喉咙里的鱼刺——真是恰当的比喻——在这里,似乎已经删除的标题也如鱼刺,我看不见它,但它在着,并时时用刺痛感对我完成提醒。放下它的努力是无效的,我做得不够,面对电脑上的白纸之白,面对《怯懦者》,轮椅上的父亲总是不经意地出现,在那边,不住地咳。
劣质的烟呛到了他。
妻子向我谈及玻璃,先是“自杀”的镜子:它突然地从高处摔下来粉身碎骨,没有征兆也没有人动它。后来是窗户,刚刚擦过的玻璃又被小雪弄脏,而那个高度却让她晕眩……好,好啊,父亲的故事来了,它冒出了继续下去的芽:我让父亲的轮椅爬行到一个高处,无论是楼顶,工地,桥头还是别的什么,有个高度就足够,至于这个高度在哪可以在写作中慢慢思量,他试图飞身下去,不,我不会让他真的飞下去,而是会将他安排在那个位置上——那是个支点,但在文章结束,他只会固定于这个支点上,“飞而不翔”——我设想,面对找见他的我,父亲作出这样的解释:我想向下面看看。就是这样。而我站在他的位置上向下,飞翔的快感、晕眩感和恐惧感同时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在那一时刻,我是否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可以开始了,就如此开始:我将“怯懦者”删除,然后将“会飞的父亲”换回来:当然,这是个新的,和之前的那些字没有联系,电脑不会记忆,即使我使用的是五笔。
4
我且放入一点寓意。
一场车祸,将父亲固定于轮椅上:原本,我试图在这里就放入寓意,譬如车祸之祸,要在这个“祸”上赋予……接下来的一刻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方式。需要的寓意将在后面出现,它只是枝杈,过多的枝杈会夺走核心感,影响到树木的生长。原本,我还想为父亲的车祸找一个缘由,不可告人,但车祸使它获得了呈现——接下来的一刻我再次否定,它会将小说引向另外的方向,而那个方向,并不是我想要的。
在构思中,我将安排父亲哭泣,而在囚禁的时间里,我将安排父亲面对火炉发呆,像一段不思考的木头……这样的安排让我兴奋。因为它可以使用引文。我喜欢使用引文,这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嗜好,或者怪癖,或者“掉书袋”,或者其它的什么——它时常显得不可遏制。是的,我不太准备修正我的这一嗜好,在之后的写作中它还会获得延续,我的理想也是写一部“全部用引文完成的伟大的书”——
我的父亲将这样哭泣:“这个坐在床中间哭泣的人看上去很像我父亲。他在哭泣。眼泪顺着脸颊流淌。能看出来,他正为什么事痛苦不堪。看他这样,我就明白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了。他喷涌得像消防水龙头被敲掉了栓,他的哀号在所有这些房间里冲出冲进。我将手置于胸前,以一种安慰的口气说,‘父亲’,这并没有使他从悲伤中走出来。它忽尔高声尖叫,忽尔低声呜咽。他的幅度变化极大,他的雄心也不相上下。我又说了一遍:‘父亲’,但是他不理睬我……”而在囚禁中,关于父亲的文字将会是这样:“父亲开始足不出户。他封起那些炉子,研究起永远捉摸不定的火焰的本质,体验着舔舐烟囱出口处闪亮的煤烟的冬季火蛇的咸咸的金属味和烟气味。那段时间,他总是在不同房间的某个高空地带痴迷地干着形形色色的修理的小活儿……他开始与各种实际事务渐行渐远。”我准备,将这样的文字塞入到我的小说中去,让它们镶钳于……我承认在我想到让“父亲”降低将他困在轮椅上的最初便想到要使用这两段引文,它们几乎同时,只有细究起来“父亲坐在轮椅上”才会略略靠前那么一点儿。唐纳德·巴塞尔姆,《我看见父亲哭泣时的情景》,另一段文字则来自于布鲁诺·舒尔茨,《鸟》。我愿意在我的写作中加入它们,我愿意,和那些对我影响深刻的文字构成互文。
我几乎要塞进去了,这完全是举手之劳。我也确实将《我看见父亲哭泣时的情景》的句子塞入到了小说里面,但随后,又删除了它。出于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考虑,大约是不够合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我的手边没有《白雪公主》,而书橱里也没能找到。那么多的书,有时翻捡起来真是费劲。
克制使用引文的嗜好,对我来说颇有难度。这时,我依然还在犹豫:是否,要重新加入它和它们?它,和这则故事的血型是匹配的。
5
整个故事将如此设计:父亲受伤,车祸,被迫坐进了轮椅,让善于奔跑的他骤然地低于了生活。他无法接受,当然无法接受,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因此变得无能,进入到一种可能的“丑陋”的生活,这会让他感觉羞愧,无助,甚至竖起刺猬的刺。在一段时间的囚禁之后,“与世隔绝”之后,父亲忽然变得——我要让他变化,开始他的“积极生活”:与老人们下棋,打牌,在经历了一些不快之后他有了一个新去处:篮球场,成为备战的县篮球队的“编外教练”(书写这样的生活于我不太具备难度,生活中,我的父亲确是体育迷,也曾任学校篮球队的教练和裁判。平时,因为妻子的关系我也偶尔观看NBA比赛,熟悉一些技术术语)。然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话多的父亲并不能让那些陌生的面孔信服,他们听从的是教练的呼喊而不是我父亲的,这让我的父亲很是气愤。每次回到家里,他依然处在气愤之中,痛斥几号球员完全没有球感,痛斥教练的指挥和换人总是失当,如何如何……在家里,只有母亲会对他表达不满:你看就看,别给人家乱指挥,你就看不见人家的脸色!都烦你啦!你当你是谁?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你行?你腿好着的时候就行?我们当然要制止他们的争吵,劝告母亲让着父亲点,毕竟,他不痛快,毕竟,现在有这样一个去处(我要让父亲变成一个话多的指挥者,他愿意“插手”一切事物,包括之前他从来不感兴趣的。他仿佛是一个百事通达的行家,从而有了一贯固执的“正确”,更不容忍辩驳——轮椅上的生活让他更加脆弱有了更多的刺,同时也让他更不宽容。弱的,向更弱的进行施加,向自己的家人施加,我要让故事里的父亲变得这样,这则故事需要这样的“寓意”,它是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的)。但受挫会有。当父亲越过边界,对家庭之外的人员发号施令和训斥的时候他的受挫感就来了——还是篮球场,父亲自己把轮椅摇到教练身边,他根本看不到教练的脸色。教练没说什么,但一个高大的球员却急了,他把手里的球递到我父亲的手上:你不让我上,你上。你上我的位置!父亲当然不能。但父亲的嘴还是硬的——你打不了这个位置,看你刚才的表现,这些天来的表现,我发现你太僵硬,不灵活,也飞不起来,技术不扎实。当年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位置,当年……我弟弟想劝阻住那个冲动起来的小伙,他不过去也许还好。
球场,父亲不能去了,他也不愿意去了。在经历一系列的挫败之后,父亲再一次“隔绝”起来,他重新成为个人的孤岛,变回到弱者,更弱者,软壳的蜗牛,在那些日常的、琐细的、不具有伤害可能的事物中也不肯探出头来。偶尔,他会在房间里偷偷地哭,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自然看不到这些。结尾是:某个夜晚,父亲从他的房间里消失,我们睡着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夜起的母亲发现了身侧的空荡。她呼喊我们,我们出去分头寻找,最终我在一个高处(这个高处,是楼层?高地?或者其它的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个可以暂时不思量,留给写作的渠,我想水会自然而然地流至那里)寻见了父亲。当然,我得小心翼翼,只是靠近他,和他的轮椅坐在一起。这时天边已有微光,借着光,我可能看到他手上磨出的血:为了这个高处,他一定极为艰难。他朝着远处张望,仿佛我是陪他到来的那个人,一直在。“爸,你在看什么?”我问。“鸟。它们飞到那边去了。”然而,我并没有看到一只鸟的存在,我,只看到了高处的晕眩(结尾,和之前的设想有了一些小的变化。变化还会发生,它将伴随写作的全部过程,这也是贮含的魅力和趣味之一,我觉得)。
似乎还不错。已经可以向下进行。我要把波澜预留出来,这属于小说技艺的常规,不具备太多的难度。当然,我也已经想好,父亲需要停留在那个高处而不是让他真的“飞翔起来”,否则,它就会落入到某种俗套,我要让他被冲动和恐惧反复纠缠——我知道这样的心理,恐惧时常会有所战胜。在写作开始之前,我设计最多的恰是最后一段,尽管我一时看不清父亲脚下是楼顶还是桥头,或者别的……我设计了那天的晨曦,设计了向下的昏和暗,设计了……它是一个有爆发感的点,不,它不能爆发,我要做出涡流更要做出表层的平静,它要在平静中止住,但回声在,回声悠长——是的,我要的效果是这样。
写作,从明天开始。它已经不可能再有消失。我给自己放一天假:暗黑破坏神,我使用法师,使用冰系、电系、火系的魔法和游戏中的恶魔作战,这一战斗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
6
梦见改变了我的方向,它给予了另一个结局,不期而至:那天晚上,我梦到了父亲,梦到了一个集市和拥挤的众人。它是梦,所以我们都比此时年轻。梦里的父亲没有轮椅,他当然不需要这个,他需要的是气球——他把买到的气球递给了我的儿子。
意外的是,梦里的父亲真正有了飞翔。
梦中的父亲背景高大,他拉着我儿子向前,挤开众人:众人的中间,有一架黑色的滑翔机,不是电视里出现的那种,它更像是一台由旧铁组成的机器,没有机翼——机翼,是在我父亲飞翔起来之后突然出现的,他带着巨大的轰鸣绝尘而去,消失于远方(直到写下这段文字,我才意识到我的儿子在他爷爷坐进滑翔机内的时候就没有了踪影,在那么多人之间,我没有半点儿为他的担忧。在梦里,他还是个孩子,没有一米八的身高)。
“出事了,”有人喊,接着众人朝远方涌过去……我愣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惊醒,这时天已经大亮,妻子已在客厅:那日的NBA七点开始,她喜欢的詹姆斯迎战马刺。“我刚才做了个梦,”我对她说,“它,可能会改变小说的方向。”“什么?”
是的,方向,我决定放弃父亲到操场指挥篮球训练的描述,有了这个结局,那个故事和其中的寓意已不重要——我将把我的这个梦作为结尾,而它,或多或少会分解结尾的力量,而且会使小说变得过于绵长,我以为。我需要为小说建立平衡,哪怕是种“危险的平衡”,而父亲到操场指挥的篇幅不会太少,当我加给它的力量过大时,那结尾的,父亲乘坐滑翔的机械飞走的力量势必遭受影响——我无法将二者变成合力,让它们产生“共通感”——有一个有关雕塑的故事,罗丹为巴尔扎克雕像。像雕成了,它几乎是完美的,尤其完美的是巴尔扎克的那双手,所有的观众都对它的存在发出惊叹……结果是,暴力的罗丹使用了斧子。他砍掉了“巴尔扎克”的手——因为,它夺走了对巴尔扎克神情的注视,而那,则是罗丹更为重视的。对于这篇小说而言,我也只得使用斧子,无论有着怎样的惋惜。同样让我惋惜的还有之前想好的结尾,相对而言,梦中提供的这种似乎更有意味。在确定使用梦境提示的结尾之后,它依然有小小的分叉:一是,按照梦中的提供,父亲坐上滑翔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飞走,越来越小,直到我们再也找不到它,天空中只剩下灰蒙蒙的空;另一则是,这是一次有故障的飞行,笨拙的父亲手忙脚乱,他的操作出现了错误——当我们,赶到出事的地点,他正从泥泞之中湿漉漉地爬出来,而旧铁组成的滑翔机已经摔得不像样子。
这两个结局有着各自的……我将它们放置在天秤的两端,然而我的这架天秤始终摆荡不已——好吧,暂时放下,反正它只会在后面出现,我可有思考的时间,在这个细节上可以暂时不做纠缠:现在,开始。
7
我说,“把我的父亲囚禁起来的是……一次车祸。据说他本可躲过那劫,然而一向善于奔跑的父亲却突然在路中停了下来,直到失控的桑塔纳2000将他撞飞出去——那么高,超越了他所能的想象,他感觉自己在天上飞了一天或者更久……”我让它成为叙述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故事就有了泉眼。我想,这篇小说的叙述,嗯,中速略慢,我让它带出一点松木的、树脂的气息,同时带出的还有——日常生活的粘稠度,是的,是这个词,粘稠度,这篇文字应当较上一篇《会飞的父亲》更粘稠些,我要更多地加入生活和计较的杂质,我要让妻子、弟弟、弟媳、母亲一同参与到这则故事的涡流并成为其中的部分,至于儿子……他不出现。在有了各自的分担之后,作为“人物”他没有特别之处,没有特别需要的承担。
我承认所有原型都来自我的家人,我只会杂揉一些很小的“杂质”进去:小说里的母亲既是我的母亲,不过我把我大姨的一些性格、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会添加在她的身上。弟媳,她的存在是重要的,我想象她是——是的,“一切都对我有用——我听到的事情,我看见、读到的东西;总之,任何东西都以某种方式给我正在做的工作提供帮助。我变成了一个贪食现实的人。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我必须经历那种苦修、苦练的工作。”
第一节,车祸。父亲陷入了轮椅。语调平缓,短促,介绍性的小节。
第二节,父亲将自己囚禁起来。他会把自己囚禁在卧室的房间里。在囚禁之后他是沉默者,他不说话或者只有最简单的表达,喧哗的是我们,我们试图对他“理解”也试图以另外的力量拉拽他——这是起点,点到为止。
第三节,喧哗需要继续。不止一件乐器。母亲的,她是言说的核心,需要在叙述中建立固定机位:她的不满,怨怼,愤恨,恼怒。对她的劝慰当然要用其它的乐器演奏,它们停在一个低频,时断时续……之后,场景转移,母亲退场。这一章节父亲并不出现,但他,一直占居于话题的核心。
记得有次讲座,李敬泽谈及《红楼梦》,他说大观园里的姑娘媳妇们遇人说的都是颇让人顺耳的客套话、恭维话,但里面却总有不经意包裹着的小刀片。好吧,某些刀片可以借来使用。
第四节。弟弟和弟媳试图说服我们,让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个提议遭到拒绝,这个拒绝来自父亲。父亲坚持着自我的囚禁,它会得到再次的强化。他是一座孤岛。其实母亲也是,我和我们也是。不过,车祸和车祸所带来的,让父亲的孤岛性质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这是我在写作这篇《会飞的父亲》之前就预留的寓意,它会进入到显微镜下——当然,作为策略,我不让父亲言说,不让父亲过多地参与到言说,他和他的,要尽可能通过我们的喧哗勾勒出来。故事里的其他人尽可能地呈前,行动着言说着,而父亲则像一团影子。这团影子慢慢地,成为固体的性质。
叙述依然缓慢,粘稠,杂质纷多,有一股缓缓下坠着的倾向。
它成为一件和耐心比赛的事情。我站到阅读者的角度,思量:它就一直这样下沉?我的耐心即将耗尽,是否还要再坚持一下,再一下下?我承认我在猜度,博弈,既要尽力地拉伸阅读者的耐心又同时不至让它耗尽。它会有个临界的点,我尝试着找到它,在尽可能靠近之处将它拉升起来。我是一个匠人,我懂得……这是阿赫玛托娃的一句话,掉书袋的嗜好又一次回到我的身上。
我且加入一点寓意在里面……飞翔成为渴望,越是不可能,它则越强烈一些。从日常中飞走,或许是父亲积蓄很久的愿望,而当这种可能被完全地截除之后……但父亲,事实上,父亲不会谈到它,绝对不会。我懂得这个父亲,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大抵是我,不会。是的,所有的寓意都不会自动呈前,在此时的故事和结尾的飞翔之间,需要一个铺垫,它既是一层的波澜同时也是通道:我怎样,能让父亲在集市上的飞翔成为他坚持的可能?要知道,他坐在轮椅上,不肯见人。要知道,让他不顾我们和管理者的反对而以残疾人的身份坚持坐上滑翔机,需要力量也需要合理性……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结局有某种的突兀感,风筝的样子,而我之前的所做都是沉的实的,而沉下、落实也是这篇小说的主体基调,不能伤害它。我,应当设置一个怎样的情境,细节,波折,让父亲不言说的这个“渴望”以一种生活态的样式呈现出来?
这是个问题。它需要得到解决。还以水流比喻:水流下来,经过沟,壑,受石头和坡地阻挡,树枝和树叶的阻挡,它变得曲折,也会冲开某些并不坚固的,携带它们顺流而下。现在,水流遇到的是一个高大的坡,它被囤积,旋转,积累……堰塞感。我要为这条水流寻找恰应的去处。去处在那儿,它已经早早地被固定下来,这没什么好丢脸的,问题是,我得采取手段让它越过,冲刷,最终汇入。真得费思量。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不要,为父亲的车祸建立“秘密的理由”,给它延接毛细血管?我承认早有预谋,在第一节的叙述中,我让父亲停在路中的原因成迷,不做解释——父亲,在我们所见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秘密的却是属于他更渴望的?父亲,在那个秘密生活中,他的孤岛性质会不会得以缓解或者稀释,还是基本等同于我们所见的日常,释放和遮掩同样在着?
为什么你要旅行?
因为房子太寒冷。
为什么你要旅行?
因为旅行是我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常做的事。
你穿着什么?
我穿着蓝西服,白衬衫,黄领带和黄袜子。
你穿着什么?我什么也没穿,痛苦的围巾使我温暖。
你和谁睡觉?
每夜我和不同的女人睡觉。
你和谁睡觉?
我一个人睡觉,我总是一个人睡觉。
你为什么向我撒谎?
因为实话像别的不存在的事物一样撒谎,
而我热爱实话。
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更多意义。
你为什么要走?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马克·斯特兰德,《献给父亲的挽歌》。又一次想到了它。它曾在我的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中镶入,我喜欢这首无以伦比的诗,充满着深意和悖论和悠长意味的诗——我准备再一次将它给予这个父亲,它的血液将融入于小说叙事的血管里——或许,我应当为父亲安排另一个女人。或许,那个女人其实一直拒绝。他去找那个女人,她不在,或者她有别的客人,反正我父亲只得悻悻地返回,结果遭遇了车祸。或许,我可以安排弟媳打听到这些,她在其中添油加醋之后尽数倒给母亲,而母亲则……如此延此方向,留给母亲的戏份会得到骤然地加强,它会成为另一股水流,不是汇入而是向另外的方向流出——我当然可以给它设计终点,让它不至于夺走太多,何况这一细节的加入会使小说生出更多的繁复和厚重来……
这是又一个费着思量的问题,需要仔细权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电脑前发呆,随手抄起些什么:《鳄鱼街》,《希尼诗文集》,《特朗斯特罗姆诗选》……它们沉默着,用自己的声音沉默,不肯为我决定。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她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人?又一个小时,天暗下来,外出的妻子回来做饭。七点半,CBA比赛,妻子讨厌马布里的北京而喜欢易建联的广州,这一毫无理性的偏见让她的观看有着太强的倾向性。我也跟着观看比赛,有意遗忘刚才的思量,反正暂时没有结果,不如……比赛结束。受挫的妻子很是忿忿,而我重新坐到了电脑前。半个小时。我用游戏来打发,玩着蜘蛛纸牌——
之后的决定有着偶然的成分:我决定不做衔接,让它只是空出的线头,父亲在车祸之前的前史我不做任何的交待,我也不准备为他再找那个一直面容模糊的女人了。我要和马克告别,他不在这里,不出现,实在抱歉。
分掉的力量我可以补回,但,另一个女人的出现,会让小说进一步变“俗”。它会滑向平庸,让我成为第三十个把女性比喻成鲜花的诗人,我以为。当然,如果加入前史,我也必须在前面重新设置埋伏着的支点:它不能凭空出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样的小说中不能。小说当然是弄虚作假,但它在它开始建立的逻辑中或伸或展,它也必须有让人“信以为真”的力量——我也没有太多的兴趣掘开路面重新铺设一条新管线。
8
“首先,有个想法,一种围绕某个人、某个处境的推想、某种只是发生在心里的念头。然后,我就动手记下来,做卡片,写出故事脉络——人物从这里开始,到那里结束;另一个人物从这里开始,在那里结束——总之,拉出一条条小小的线索来。等我一旦动手创作时,首先把故事的总框架搭起来——可是从来也没有按框架写过,因为一写起来我把框架就完全改变了;但这个总框架对于我开始动笔还是很有用的……”巴尔加斯·略萨曾这样说过。他如此,于我心有戚戚地谈到小说的生成,从一个想法、一个围绕某个人、某个处境的推想开始,然后搭起框架——可当我一开始写作,这个框架就开始改变,我添加,抽掉,解除,又重新找回……略萨说,在动笔之后他就不去操心,“而且写得很快”——在我这里,情况却往往不是如此。我的时间会停滞,为一个场景,细节,一句对话,一个词,一个词的移动……
我写得很是缓慢。但一直试图,让它呈现出仿佛是信手拈来的样子。
9
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叙述再一次放慢,集中于一日,让这一日长于……这一日,被安排在除夕,在新和旧的支点上,我和父亲,和所有的家人当然希望这一日后旧壳蜕去而新生开始,尽管那样要求时间有些牵强。放在这一日,还因为它总是被过多地赋予,譬如欢乐,譬如团圆,譬如亲密与和气,譬如相互的恭维——这是复杂的一日也是具有表演性的一日。在小说之外,在我的日常中,它也是如此:复杂的一日和具有表演性的一日。在虚构中,父亲折断了腿,被安排的复杂和表演中必须注意到它:“一家人,都付出着小心,仿佛在房间的某处埋藏着小小的炸药,它,很可能因为某句话的火花而发生爆炸,而每个人,在这样的爆炸当中都会受损。”
它本不在预想之内。它是偶然想到的,在我处理堰塞、挖掘新水渠的时候。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一缕微弱的光,它来自于电视:我安排,父亲在这个复杂和表演的日子里做出了妥协。他要打开自我虚拟的、栅栏上的锁,进入到客厅里:让他合理地进入客厅也颇费脑筋,我当然不能使用强力,它不会有效。于是,我安排了客人,我安排客人和父亲的热络关系,那些由他将父亲“推到外面”则完全可能,何况是这样一个日子。好吧。这个活,交给招唤出来的客人做。
这,不能本质性地解决问题,父亲还要退回,是的,我需要设计他的退回,否则故事就失去了它的曲蜒,父亲性格里的固执也就无从得以体现——要知道,他是那种我所习见的“家长们”,那些父亲们的行事中都有不可违背的乖张,这一点应当得到体现。好吧,他还要退回,我设计在午饭之后——怎样把父亲重新拉回客厅里,让他坐在电视旁观看?经过一番的挑捡,掂量,我安排家人们在下午离开,只有我在——终于,父亲不再拒绝。电视。体育台。这是生活里我父亲的习惯,我把他的习惯同样拿来,塞给轮椅上的父亲,让他目不转睛滑翔,电视里的滑翔。那时,我还将它看成是铺垫,是一个过渡性的波澜,它要冲出缺口,在已经想到的结尾处形成高潮。这时,我让父亲反复地提到自己的腿。他注意着,也试图让我注意到——一向孤岛着的父亲,在这个复杂着的节日里开始言说,当然,这也是被积蓄起的。
我写下众人们的忙碌。我要让父亲依然处在“孤岛”的位置上,尽管他已经来到客厅,就在我们进进出出、说说笑笑的范围之中。这时,塞入一点寓意的想法又一次沉渣泛起,他可以有个杯子,他可以“不小心地”制造玻璃破碎的声响引起注意,或者,“我看见父亲哭泣时的情景”,他故意捶着自己的腿,把轮椅摇得吱吱响……过去在家里一向强势的父亲已经变成“软壳的蜗牛”,可他,还有力气将怨愤、恶毒和不甘向我们释放出来,他不允许我们忽略他的存在尤其是他的痛苦,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弱者,往往施虐于更弱者”——在前面,母亲的言语中已经有所携带,它不需要太多补救性的铺垫工作……不过我没有那样书写。
我需要把所有的羽毛都扎入鸟的肉里去,并连接血管和神经。新想出的细节当然是漂亮羽毛,但连接工作让我却步——这时,故事的汇聚已经基本完成,它有了喧响,枝外的枝能舍就舍——至少在这篇文字中应当如此。我承认我越来越喜欢在我的作品中有更多的繁复的容纳,但,但是,就短篇而言,我必须克制让它无限制繁衍的可能。它需要一个相对的、具有围绕感的核心。在这里,这个核心应当是,飞翔。
10
父亲盯着电视。而电视里,山坡上的滑翔依然在继续。“此时,它采用的是装在滑翔伞上的‘主观镜头’,它在飞,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景色的倒退,起伏和抖动。父亲没有注意我们的来来往往,而是,再一次把自己沉进了电视里,他的身体随着镜头的变幻而调整着,或者左侧,或者右侧,或者抬头……父亲在飞翔,一个健全的父亲在飞翔,这时他完全忽略了“在这边”的生活,忽略了自己头上渐多的白发和有着复杂气味的身体,忽略了折断的腿和里面的钉子,忽略了胃痛、绝望和不安——他和电视里的那个飞翔者融成了一个。他听得见风声的呼啸,他感觉得到身体的起伏,感觉得到在气流中攀升时的艰难,感觉得到来自山谷的巨大吸力,感觉得到风吹打在脸上时的抖动,他……在经过他身侧的时候我偷偷看到,父亲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段文字出现之后,我才恍然,它应当是结局,这是最后一波的高潮,梦里出现的那个飞翔已经不再需要。它提示了我,而我故事的构架也一直尽力地伸向它,但到此,它大约会是蛇足——不,在这篇题为《会飞的父亲》的小说中,我要,始终将父亲按在低处,我不给他飞起的机会,一次也不给,一点儿也不给,我给的,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愿望。而已。
我要囚禁住他。其实,源自于生活的力量更大,我以为。
(责编:王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