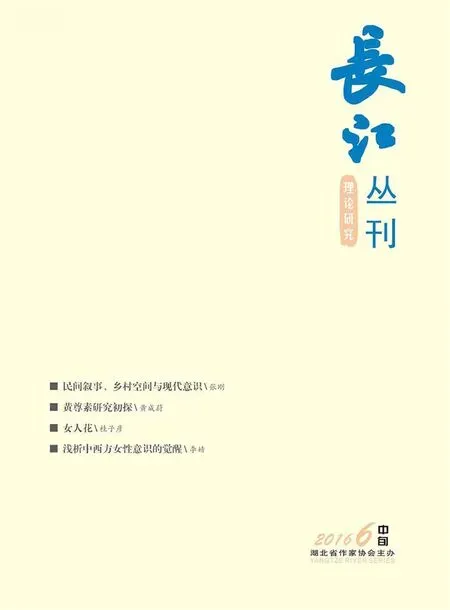浅析《光明天使》中父亲形象的在场与缺席
刘诗源
浅析《光明天使》中父亲形象的在场与缺席
刘诗源
【摘 要】欧茨作品中的父亲从来都不是主角,但作品中的父亲形象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难以作为青少年的成长榜样,甚至还会对子女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光明天使》(Angel of Light)就是一部子女因父亲之死而迷失自我、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解读《光明天使》中的父亲形象,通过分析父亲的“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感知父亲性格缺陷与其子女悲剧结局的关联,从而领悟文本背后,欧茨对家庭环境深远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关注和担忧。
【关键词】《光明天使》 父亲形象 在场 缺席 欧茨
一、欧茨与其长篇小说《光明天使》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是蜚声当今世界文坛的美国女作家,她对美国社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提供给读者一个洞察美国社会现实的独特视角。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曾对欧茨女士作出如下评价:“对许多小说家来说,多产影响作品的质量,但对于欧茨来说,多产成就了她的实力。她的才华是无止境的。”她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者融会贯通,可谓是前无古人,因而评论家们用一个新名词——“心理现实主义”来定义她的写作风格。
《光明天使》是一部悲剧,是一种对病态的演绎。担任美国联邦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莫里斯·J·哈勒克是个外貌不堪、渴望被爱的名门独子,其妻是华盛顿社交界名媛伊莎贝尔· 德·贝纳文特,不仅爱慕虚荣、纵情声色,更是水性杨花、招蜂引蝶,钟情于参加各种宴会,与莫里斯婚后丝毫不加收敛,背地里一直与十几名情夫共度风花雪月,她的主要情夫还是丈夫多年的好友、子女的教父尼古拉斯(尼克)·马顿斯,这对奸夫淫妇相互苟且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可似乎有所察觉的莫里斯选择了麻木的容忍,这种可鄙的软弱最终令此二人肆无忌惮,为使收受贿赂的尼克安然无恙,他们串通一气半诱半逼让莫里斯替尼克承担了受贿罪并且辞去了万众敬仰的职务,尼克还顺理成章地谋求到本属于莫里斯的职位。后来,伊莎贝尔因无法承受人们纷纷避嫌致使的门庭冷落,变相地将可怜的倒霉蛋莫里斯赶出家门,心如死灰的莫里斯最后选择以死亡来结束自己惨淡的一生,临终时还留下许多字迹潦草的书信和笔记,还在为他曾宣布过的“在世界上最爱”的两个凶手脱罪。莫里斯与伊莎贝尔的一双子女——儿子欧文·杰伊·哈勒克与女儿柯尔斯顿·安妮·哈勒克,多方查证,断定父亲死于谋杀,决心对始作俑者伊莎贝尔和尼克展开美其名曰“伸张正义”的复仇计划。父亲的死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兄妹俩的脑海中无法磨灭父亲生前高尚正义同时又懦弱麻木的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后痛下杀心,一定要寡廉鲜耻的母亲和身兼母亲情夫、父亲好友、他们教父三重身份的尼克血债血偿。
二、父亲形象在场的缺席
莫里斯一味逆来顺受世态炎凉,根本没有奋起反抗的意识,而且平日莫里斯与女儿相处的机会太少,交谈的机会也太少,在欧文和柯尔丝顿兄妹俩最需要引导的青春期,没有做好父亲的榜样,是二人误入歧途的根源所在。可以说,他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是一种在场的缺席。他自始至终的怯懦,不仅直接导致了自身的悲剧,也间接致使缺失成长榜样的一双儿女步入歧途。在柯尔丝顿和哥哥欧文这对悲愤兄妹复仇之路上,柯尔丝顿虽然是妹妹,但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她一步步诱导并紧逼哥哥和她一同走上复仇之路,小说对她的着墨更多。
柯尔丝顿就读的海斯中学接连好几个年轻的姑娘自杀,矛头直指学校里潜在的秘密组织——自杀俱乐部,哈勒克夫妇十分担心女儿的人身安危,单方面决定将其转学。莫里斯单独约见女儿一同吃饭时,语气和蔼地问她是否知道学校里的“俱乐部”,由于天性的软弱,莫里斯根本无法说出“自杀”二字,柯尔丝顿毫无所谓地说不知道,随后无论父亲如何严肃地追问、可怜地哀求,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奈父亲向她伸来手并且紧握住她,是一种又冷又湿的感觉。柯尔丝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甚至无法将“自杀”一词说出口的莫里斯,最后竟会是自杀身亡的结局。其实那次见面时莫里斯的状态就已逐渐变得不好,对莫里斯来说,努力去爱别人却无法得到爱的回应,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燃烧,当爱用尽的那一刻,他那没有能量补给的生命只能凋零。后来,柯尔丝顿在父亲搬出家独住后,只身前去探望了六次,不过这只是为了勉强尽一些做子女的责任,而非出于对父亲的爱,每次的探望也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而且毋庸置疑父亲的状况一次比一次更令她感到失望,脸色蜡黄、双眼通红、毛发稀疏、骨瘦嶙峋,生活邋遢又消沉,浑身散发出孤独的气味,她看得出父亲正在走近死神,这让她愤怒,这让她鄙视父亲的软弱,这让她更加痛恨母亲的无情。莫里斯人生最后时光的那段消沉完全不是为人父该有的状态,这极大地扭曲了柯尔丝顿对人生的认知。
其实从柯尔丝顿儿时开始,家庭环境就是不同寻常甚至有些诡异的,哈勒克全家竟然都十分喜爱尼克,而且还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无以复加的爱,脾气平和、天性善良的父亲更是对尼克更是充满感激和信任,虽然通常人们会觉得尼克是“跟在莫里斯屁股后面”的人。父亲莫里斯在为人处世上是有些麻木的,而这种麻木通常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兄妹俩作出了为人友善的正面表率,因而柯尔丝顿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父亲莫里斯是个好人,然而正是这种“好”最后招致了恶毒的尼克攫取了本属于父亲的一切,父亲的“好”就演变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这最终令柯尔丝顿价值观崩塌,所以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蔑视“好”人。其实父亲莫里斯种种“宽宏大量”的表现,是源自内心渴望被爱的孤独感,他从心底里去爱别人、相信别人,就是为了换得自己可以被爱的权利,这种性格缺陷最后致使他屈辱的自杀身亡,给儿女留下无尽的疑惑与愤恨,直至最后拍案而起。
三、父亲形象缺席的在场
小说以父亲莫里斯可耻地死了九个月后,兄妹俩商谈如何为父报仇为开端,可见父亲之死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父亲之死带来的阴影时时刻刻笼罩着兄妹俩,因而此时的父亲形象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接着通过欧文与母亲伊莎贝尔的一通电话,引出家庭成员关系面临破裂、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多次勾搭情人的事实,从而更进一步激化母子关系。天真幼稚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发现某些罪恶,但一个人成长的标志不是发现罪恶,而是如何面对他发现的现实。[1]柯尔丝顿无法接受父亲惨死布林唐沼泽的事实,从一开始剑指母亲和尼克,决定采取暴力手段讨回公道。
柯尔斯顿鄙视父亲的麻木不仁,所以父亲死后,她渐渐变得敏感、多疑近乎病态,反复思考着人死是否还能复生,努力发掘着死亡的前因、真相以及后果。可以说父亲之死彻底震垮了她的精神,她消极地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吻呼喊“父辈们全死了”,生活中俨然成了一个邋里邋遢、半疯半傻的问题少女。悲痛交加之余,她完全无法接受父亲那些认罪的书信和笔记,认定那些东西不是父亲写的,是别人伪造的,或者父亲也可能是在一伙人威逼利诱下写的,那伙人不仅合谋陷害了父亲,隐瞒了事情真相,而且还谋杀了父亲。于是她心心念念着要为父亲“安排一个更好的归宿”,内心笃定父亲是唯一爱她的人,父亲是她的骄傲,她也永远不会忘却父亲的爱,可爱的父亲永远不会被她忘却。相比父亲生前的种种令她愤怒的行为,可以看出父亲之死对她的打击影响之深,这时的父亲是一种缺席的在场,父亲的冤屈形象在她身边萦绕不散,一直折磨着她的神经。
父亲去世后,悲痛的阴霾一直笼罩着柯尔丝顿,如何为父亲洗刷冤屈的念头一直压抑着她。后来柯尔丝顿想方设法约见了母亲的情夫之一安东尼(托尼)·迪·皮埃罗,试图打探事件的原委并询问他的一些看法,托尼作出了“你父亲是个好人”、“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这样的听起来似乎不错实则无比刺耳的评价,托尼继续说“他绝望了”、“他失去了希望”,这些话就像一根根利刺扎进了柯尔丝顿的心里,作为母亲情夫之一的托尼也认为是母亲逼迫父亲搬出家门,而且母亲还可能告诉了父亲自己已经有了希望能结婚的对象,柯尔丝顿听后激动地说道“他们谋杀了他”、“他们雇人杀了他”。最后柯尔丝顿约见了无耻到极点的尼克,在他熟睡之际,朝他喉部、肩部、胸部狠扎十二刀,可她的怯懦让她发现自己无法结果尼克,最终放弃了手刃仇人的致命一击,她意识到是狂热的复仇迷失了她的心智,她自己也不过还是个孩子,最后她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儿子欧文起初对父亲的逝世没有产生过疑虑,甚至还对原本只是家中独子与长兄的自己,成为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而感到一丝窃喜,他也同意帮助母亲设法劝导已近乎疯狂的妹妹。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欧文一直以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的父亲为榜样,对待学习勤奋认真,希望能考进哈佛大学法学院,可父亲的自杀令他颜面扫地,不再愿意谈论有关父亲的话题。但其实他内心深处已意识到妹妹柯尔丝顿是对的,甚至在接到妹妹那封信——装满伊莎贝尔和尼古拉斯的照片的信以前,他就已经隐约知道了事情真相。想到母亲在父亲死后,依旧轻浮放荡,最终欧文不得不直面残酷现实,不得不肩负起复仇的重担,因为他名叫“哈勒克”,他要对父亲的屈辱抱不平,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重复,如果这世上还有正义的话,应该死的就不是父亲莫里斯,而是不可饶恕的母亲伊莎贝尔,可他又会质疑,谁能执行对凶手的惩罚呢?万分痛苦的欧文最终决心与妹妹一道努力谋划如何替父报仇。
最终欧文选择加入恐怖组织“美国银鸽解放军”,神经兮兮地欢呼着“永远离开美国”。复仇之日他是以组织中“人民法庭”的身份回到自己家中审判母亲,此外他还会以“革命的正义行动”为名,引爆四颗炸弹炸毁他们家族的府邸,造成一场轰动的毁灭性爆炸。欧文与母亲进行了一场无比漫长的搏斗,三分钟内刺伤母亲三十七刀……在清理身上的血迹时,欧文看着家里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已被他遗忘的儿时与家人相处的往事,身体突然无比疲乏,再也没有力气离开。一直以“为父亲伸张正义”为生活动力的他,在事情了结后,像是突然被抽空了,无法想象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昏昏睡去最后和母亲一同灰飞烟灭。
四、结语
不得不感叹欧茨女士辛辣的文风,《光明天使》极其深刻地反映出家庭环境对子女成长的影响,作为美国联邦司法委员会主席莫里斯的子女,欧文和柯尔丝顿本该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面对现实中不公的事情,首先应该想到如何积极寻求司法帮助,但由于心地善良、性格怯懦的父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作为正确处事的榜样,反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负面的榜样——人善被人欺,这种父亲在场的缺席导致他们对生活和法律不再抱有希望。可以说父亲的性格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兄妹俩的认知,最终兄妹二人选择加入以推翻法西斯资本主义为名的恐怖组织,用手刃凶手这样十分极端的方式来为父亲“伸张正义”。可二人在达到复仇目的后,也走向了精神崩溃。本文通过分析父亲形象的在场与缺席,解读父亲在青少年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中的重要影响,对家庭教育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苗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7.
[2]Hans Bertens.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 London:Routledge, 2002.
[3]Joyce Carol Oates. Angel of Light. New York: Dutton, 1981.
作者简介:刘诗源(1992-),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研究生在读,文学硕士,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