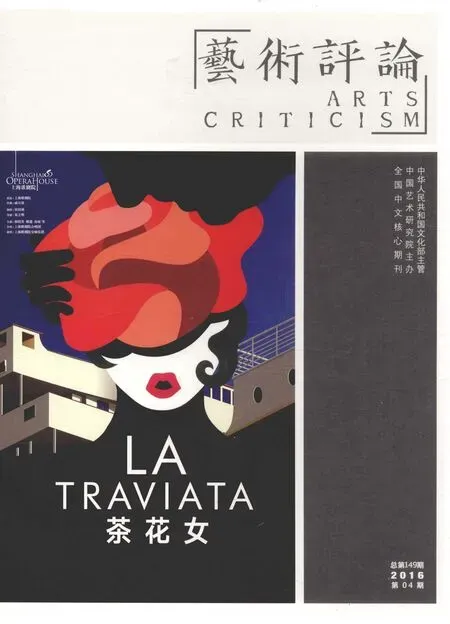至情所系 不在“义民”
——从蒲剧《枣儿谣》说到戏曲的时代文学属性
陈泳超
至情所系 不在“义民”
——从蒲剧《枣儿谣》说到戏曲的时代文学属性
陈泳超
我曾有一个顽固的执念,认为当代戏曲已经基本丧失了时代文学的属性,蜕化为单纯的观赏艺术了。我所谓“时代文学的属性”,主要并不指情节、人物、修辞等各类艺术技巧,而是直指其对于所属时代而言的思想性和社会功能。在我看来,文学必须负载作者独特深切的生命体验,对人生、社会乃至世界都有锐利的观察和别致的表述,发人心声、启人心智、饫人心府,努力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和见证。古典戏曲之所以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曾经担当过时代的先锋:关汉卿的《窦娥冤》,在抨击元代社会不公平现状的同时,发出了底层民众痛苦而不屈的悲壮之音;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借一个并不新鲜的还魂故事,痛切传达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汤显祖《牡丹亭题词》)的爱情观,其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在那样一个理学禁锢的时代,显得如此卓尔不群,难怪它甫一面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它如《桃花扇》的家国兴亡、《白蛇传》的从妖到人……无不在某一方面显示其特立的价值。
当代戏曲的新编剧目不是没有过这样的追求,比如《巴山秀才》《曹操与杨修》以及王安祈改编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就曾经达到过相当的高度。但以我这样戏曲外行有限的观剧体验来看,像上述成功的案例实在是吉光片羽、凤毛麟角,大多数要么陈词滥调、似新实旧,要么就是对社会流行观念的肤浅套用,以达到简单的宣传功用。我并不否定文艺具有宣传教育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品只要面世,都带有一定的教育性,关键是必须遵守文艺的特殊规律,创造出有深度有生命的作品,才能到达这个目标。当下的戏曲新编剧目,似乎很少有真正的社会反响,甚至我怀疑它是否还存有成为时代文学的追求,它比诸戏剧领域的其他形式比如话剧,相差很远,更不用说小说这样的非表演性文学形式了。照我看来,戏曲已经跟绘画、书法、古琴一样,成为了单纯的古典艺术,齐白石的鱼虾、李叔同的题字、管平湖的《秋鸿》,当然美到极致,但我们不会从那里面去寻找社会担当,戏曲亦然。既然如此,我更愿意看传统剧目,因为它通常经过了千锤百炼,具有更浓郁典范的艺术魅力,事实上,昆曲假借“非物质遗产”的思潮重新焕发青春后,搬演最多的仍然是《牡丹亭》,人们又何必要看新编剧目呢?
2015年12月23日,我因缘际会,看了一场山西运城蒲剧团进京演出的新编剧目《枣儿谣》,再次强化了我的这一顽固执念。
其实,我在观剧过程中还是很受感染的,因为这个剧目的本事就很感人。稷山县农民吴伯宗(又名吴绍先),因两个弟弟在幼年时被人贩子拐卖出去,他发誓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于是抛妻别子,离家十数年,行走千万里,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将他们找到并团聚,却因劳顿过度而英年早逝。这是一个朴素而富含人性的真实故事。几年前,我曾经有个机缘到稷山县进行文化考察,在青龙寺后院空地上,亲眼看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所题之“稷山吴绍先义行碑”,并听当地文化人介绍了吴绍先的事迹,当时我就很受震撼。这次观剧,这样的震撼又被该剧的艺术表现力给激活了。我这里说的艺术表现力,主要指以王艺华、贾菊兰为代表的全体演员深厚的功力和饱满的情绪,他们入戏深、出戏切,充分表演出蒲剧那种声震屋瓦、响如裂帛的魅力。当然,舞蹈、舞台、灯光等等也都不错,不必细说,但最体现文学性的剧本编导,我却颇为腹诽。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容易编,虽然是真人真事,但从历史记载到当地传说,都只有“春秋十七道里三千,神明见视骨肉团圆”(前引“稷山吴绍先义行碑”碑侧题榜)这样的概述,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离奇的细节,这正是当初让我难以释怀的地方:吴绍先寻弟的行为是如此不可思议,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编剧者以历史记载为骨架(比如二弟在宁古塔、三弟在京师之类),以民间传说为血肉(比如妻子可能虐待弟弟之类),合理展开想象,编制出遇盗挨打之类细节,还用稷山县特产板枣为“戏眼”,编出一首“枣儿谣”贯穿全戏,在在见其匠心巧思。
但是,整台戏如何立意?它的灵魂在哪里?
该剧宣传手册上重点标出了一串反问句:“问大地,何为同胞?问苍天,何为弟兄?问风雪,何为骨肉?问荒原,何为亲情?”这样天问式的呼号虽然略显肤廓,倒还基本切题。我要追问的是,这样兄弟之情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更深刻的精神呢?剧本本来也设计得不错,开始就让母亲病逝,临终前叮嘱作为长兄的吴伯宗一定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吴伯宗既有一诺千金的信义、又有骨肉情深的情意,才演了这一出惊天动地的万里追踪,以此作为全剧的灵魂,其实已足动人了。但编剧大概希望追求更高广的意义,一上来就让吴伯宗兄弟于母亲病危的床前,正儿八经地对读着“兄道友、弟道恭”之类的《弟子规》词句;更在全剧的结尾,在吴伯宗及其两个弟弟已经像丰碑一样矗立在舞台中央之后,又附加上象征性的一幕:主人公吴伯宗单独站到了舞台中间半高的斜坡上,在其上方高悬着康熙的赐匾“兄弟孔怀”,在其下方则是一群小孩在雾气昭昭中来回踱着方步继续诵读《弟子规》中更长篇的训词。我是否可以这样解读其寓意:吴伯宗艰苦卓绝的事迹,上无愧于天子倡导,下有功于后代教育?
然而,这样的场面构思,从时代文学的层面上评估,是对吴伯宗事迹的提升还是贬低呢?
在我看来,吴伯宗事迹原本就是家庭亲情的自然流露,它生动体现了人类最深沉最光辉的血缘天性,并非封建文人浅俗文字的教化结果。这一点,晚明的文人和思想家早就说得很透彻了。冯梦龙在《情史》里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去做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我们现在塑造的吴伯宗,应该是“从道理上去做”呢?还是“从至情上出者”呢?李贽在《童心说》里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本剧让吴伯宗从小到大到死,都规规于《弟子规》里面几条肤浅的教义,其“最初一念之本心”反因之而淡化消减,在我看来,不啻是舍近求远、本末倒置了。
吴伯宗的事迹当年曾经打动过李光地、陈廷敬、方苞等一批康熙年间的著名文人官员,留下了一些传记和诗文。他们在歌颂吴伯宗事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他在艰难困苦中,是如何时时不忘儒家经典之教诲的。比如曾奉敕编纂过《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在其《书吴伯宗寻弟事》(《榕村集》卷三十三)中这样写道:
伯宗颇识字,尝于旅店读《论语》,至“父母之年”,则歔唏哭失声。呜呼!《小宛》之哀,兴于“明发”。能友者,未有不厚于孝者也。伯宗虽农民,在京师,国相泽州陈公髙其义,既与为礼,又为诗七十六韵以歌之,缙绅士友多就见之者。夫农之秀者则升为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侧耕夫,以内行之敦,为有道者别识,卒于贤臣名士,青史烂焉。余诚未知伯宗志质何如,然愿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无使异日乡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后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类。”则虽未泽于诗书,文以礼乐,而使乡党嘉尚,以终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诸?
看来理学名臣笔下的吴伯宗,跟本剧中的吴伯宗很有些相像。不过,我认为这些记载除了说明吴伯宗真的识字之外,其它很可能只是理学家们眼中的吴伯宗,甚至是他们理想中的吴伯宗。如果吴伯宗果真如此作为,在日暮图穷的旅店里还因读《论语》而痛哭失声,往好里说,是“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往坏里说,或许很有些故意表演的意味了。无论如何,比诸至情至性而言,读不读书并不重要。但理学名臣们特别愿意表彰他这一点,所以许多京师名彦都屈尊纡贵地接见他、讴歌他,称之为“义民”,甚至暗示他“夫农之秀者则升为士,古之制也”,仿佛农民一定巴望着因此“义民”事迹而升入士人行列似的。
本剧的编者当然没有这些封建士大夫的迂腐理念,但又何必要前前后后加入那些《弟子规》呢?又何必要将封建帝王的题匾高悬于天呢?何况,康熙题匾之事,其实并无实据。我在观剧之后,专门查过《稷山县志》的乾隆版、嘉庆版和同治版,在各版吴伯宗事迹的相关文字中,从未出现过康熙题匾“兄弟孔怀”的记载。按理说这么荣耀的重大事件是不可能不被载入小小的稷山县方志中的,我很纳闷这个题匾之说究竟从何而来,放在剧中是何用意?
再说,《弟子规》真的那么值得宣扬吗?像“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样的行为规范,现代人做得到吗?成人都做不到,却要孩子们去做,这恰恰违背了孔子所代表的经典儒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是也,它只是宋明理学的产物,相比于经典儒学,其对人性的过度压抑,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不客气地说,它真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吁了!
当然,这不能苛责于《枣儿谣》的编导。如今社会上风行的所谓“国学热”,带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对传统文化不加辨析,不分精华糟粕,似乎只要是传统的就值得宣扬,于是变得鱼龙混杂、面目不清了。像《弟子规》重点宣传的是下对上要顺从的观念,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观念完全对接不上。我们要造就的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公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民”“义民”。
也许《枣儿谣》的编导们要叫屈了,因为剧中只朗诵了《弟子规》中的开首以及讲兄弟友爱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这么几句,或许并没有要全盘接受《弟子规》的意思。问题是这些文句既然出自《弟子规》,就自然带上了与它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色彩,那么,全剧到底应该宣传普通民众自然生发的至情至性,还是其受理学教诲后的“义民”身份?正是在此层面上,我认为编导们未能独立思考、深入发掘吴伯宗事迹对现代社会的真正意义,只是简单搬用流行“国学热”的表面文章,正代表了我所批评的新编剧目的一种通病。事实上,此类新编剧目,通常主要是为了各级汇演、评奖而排演的,很少进入作为市场的剧场,更几乎不可能成为从业者存身立命之本,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群众反馈。
所以,我认为,戏曲如果不能成为活着的时代文学,其生命力或许就只能存在于一些乡村庙会上了。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