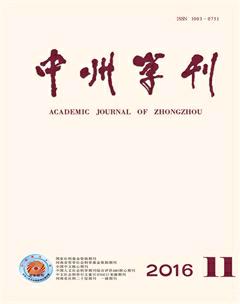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北朝后妃出家现象探析
白春霞
摘要:北朝时期数量众多的后妃出家为尼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观。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女性几乎没有独立的人格,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细究北朝后妃出家为尼现象,虽有“守贞”之意,但多为“失势”“受罚”所致,当然也有“明哲保身”“委曲求全”之计掺杂其中。这种比丘尼身份全新功能的出现与北朝的政教关系、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规制的加强、女性在宗教信仰中的边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男性述说为主的史载中,对女性活动的认知显然缺少了女性的主体声音。
关键词:北朝;后妃出家;比丘尼
中图分类号:K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24-05
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鼓励扶持下获得了迅速发展,一时间寺院林立,浮屠栉比。相比于南朝,佛教在民众生活中的实用性、功利性特征体现得更加强烈,“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①。北朝时期佛教影响民众世俗生活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佛教信徒群体。在北朝女性佛教信徒中,后妃出家为尼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对其出家原因更为重视。如夏毅辉认为北朝皇后出家是“帝崩或帝废”“为太后不容或蒙受株连被废,宫闱之争”②等所致。与夏毅辉的观点类似,陈怀宇认为,后妃为尼是“或者皇帝过世或者国家政权倾灭或者失宠于国君或者家世不幸受政治牵连”所致,“没有一个是为了学道为尼的”。③许智银也认为,当时“统治者崇信佛教”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某些女性不得不以出家为尼”④自保。这些研究多是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加以论述。与以上研究略有不同,石少欣的研究则涉及到了女性的角色问题,认为“比丘尼作为新的女性身份出现在社会,为皇室政治斗争提供了处理失败者的新思路,比丘尼的这种社会功用,堪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研究北朝佛教尤其应该注意”⑤。受石少欣研究的启发,本文试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北朝后妃出家为尼现象及其原因,以期说明佛教对以后妃群体为代表的上层女性的影响和意义。
一、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之现象
从正史资料看,北朝自拓跋魏入主中原至隋亡北周,共有17位皇后出家,如果加上其他妃嫔,数量会更多。皇后出家为尼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为北魏孝文帝废后冯氏,也即佛教深入北魏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时期。《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北魏共有五位皇后出家,分别是孝文帝的两位皇后、同父异母的冯氏二姐妹——废后和幽后,宣武皇后高氏,宣武灵皇后胡氏,孝明皇后胡氏。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均出家为尼。北齐出家为尼的皇后有文宣皇后李氏祖娥,孝庄皇后尔朱氏,后主皇后斛律氏和胡氏。北周出家的皇后最多,12位皇后中有6人出家,包括孝闵皇后元胡摩,武帝皇后李娥姿,宣帝同时立的五位皇后有四位出家,分别是皇后陈氏,皇后元氏,皇后尉迟氏,皇后朱氏。
性终其一生的场所。北魏时期出家为尼的孝文皇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均居于瑶光寺。宣武皇后高氏出寺觐见母亲时暴毙,丧还瑶光寺,孝文皇后冯氏最后终于瑶光寺。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瑶光寺为北魏时期以皇家为代表的上层女性修习佛法的场所,皇后为尼居于瑶光寺,使之具有了皇家内道场的性质。后妃出家使得比丘尼身份成为服务北朝政治的一种工具,当权者对比丘尼身份的灵活弃取也致使后妃在宗教信仰中丧失主动权。为尼的宣武高皇后在瑶光寺外暴毙,丧还瑶光寺,以尼礼入葬,这是高氏在宫廷内斗中彻底失败的表现;在尔朱荣兵压城下之时匆匆落发的宣武灵皇后胡氏死后以太后之礼入葬,表明皇室仍认可其原来的身份;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死后也以尼礼入葬,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号为“寂陵”,此举是为了彻底打消蠕蠕公主对文帝的猜忌。后妃为尼现象是北朝政权对佛教采取实用政策的结果,也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共同作用于女性生活的结果。
二、北朝后妃为尼之类型
北朝后妃为尼者很多,其具体情况多有不同,有的是自愿为之,因而潜心志道;有的为暂时委曲求全的举措,因而等待时机还俗;有的是触怒当权者而遭受的惩罚,因而只能苦熬岁月。为更加深入地认识此问题,以下分类详细论述之。
1.顾全大局的委曲求全之举
有时候,后妃出家为尼是皇帝和后妃都无奈的选择。皇帝和皇后感情甚笃,皇帝使皇后为尼,只是困境之时一种暂时安置的办法,危机过后就会安排其还俗。文帝时“蠕蠕寇边,未遑北伐,故帝结婚以抚之。于是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西魏文皇帝为安抚蠕蠕,娶蠕蠕公主并立为皇后。现实形势迫使原来的文皇后乙弗氏出家为尼。对已经出家为尼的文皇后,“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后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⑥与此类似的还有北齐“彭城太妃尔朱氏,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当时神武帝面临的边境形势是“蠕蠕强盛,与西魏通合,欲联兵东伐”。神武本为世子求婚,以缓解两国紧张的关系,蠕蠕主阿那瓌要求高王自娶。神武无奈迎娶蠕蠕公主,太妃“后为尼,神武为起佛寺”。⑦文皇后和太妃尔朱氏出家为尼是为了顾全大局,打消新立皇后的顾忌;皇帝也并未真正待之以比丘尼之礼,在他们看来皇后只是暂时改变身份而已。文皇后虽然自杀,但文帝要求自己万岁之后文皇后配飨,彭城尔朱氏在天保初年被尊为太妃。
2.国亡、帝崩、帝废之时的安置方式
在国亡、帝崩、帝废之时,安置前帝后妃为尼成为一种选择,在北周北齐之时,这种情况渐趋普遍。北魏李彪的女儿“幼而聪令,”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⑧北周“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谨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长安,周文以后赐武帝。后得亲幸,生宣帝”。“隋开皇元年三月,出俗为尼,改名常悲。”⑨北周“孝闵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晋安公主。帝之为略阳公也,尚焉。及践祚,立为王后。帝被废,后出俗为尼”⑩。北周宣帝同时立五位皇后,除了隋文帝长女杨氏外,其余四位皇后在宣帝崩后先后出家为尼。这在北朝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她们分别为皇后陈氏,为尼后改名华光;皇后元氏;皇后尉迟氏,为尼后改名华道;皇后朱氏,在北周灭亡后,亦出家为尼,改名法静。
3.触怒皇帝皇后之后领受的一种惩罚
北魏世宗元愉“纳顺皇后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顺皇后借助自己皇后的身份强令李氏为尼,又夺其子交给自己的妹妹抚养,总算是替不见皇帝礼答的妹妹出了气。北齐后主皇后胡氏因为遭到陆媪在太后面前的诋毁,“太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发,送令还家”。胡皇后被人诬陷毁谤太后而被剃发送还本家,这无疑是一种惩罚,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时代,被剃发的胡皇后应该就是被迫为尼。北齐后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为皇太子妃,后主受禅,立为皇后”。后“光诛,后废在别宫,后令为尼”。因为父亲被诛杀,皇后斛律氏受牵连而遭废黜,令之为尼也应该是对丞相斛律光的女儿的惩罚。
事实上“青灯古佛旁,任何时候都不是妇女的世外桃源,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用新的压抑形式(戒律)去代替旧的压抑形式(礼法),并未缔造过什么自由的生存空间”。强迫后妃告别繁华的世俗生活,过一种孤独寂寞古卷青灯的日子,对于习惯了养尊处优奢华舒适的她们来说是一种极为严厉的惩罚。
4.宫斗中的一种明哲保身之计
北魏宣武高皇后“性妒忌,宫人稀得进御。及肃宗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魏书·皇后列传》中未明确交代皇后高氏为尼的原因,但结合当时宫内的形式可以判断高氏在与灵太后的宫廷角逐中败北,为避免更大的灾难而选择出家为尼。最后却仍未逃脱“暴崩”的结局。“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宣武灵太后虽然自幼与信奉佛法的姑姑相依托,也略得佛经大义,但召六宫皆入道,亦自落发的目的并不是要修学佛法,拱手交出北魏政权,而是想借助比丘尼身份避免尔朱荣的迫害屠杀、保全皇族血胤。临时仓促落发为尼的灵太后并未改变局势,仍被尔朱荣沉入河底身亡,“太后妹冯翊君收瘗于双灵佛寺。出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灵太后死后仍以皇后之礼入葬,说明皇族也认为她落发为尼仅是情急之时的权宜之计。
5.无奈时斩断尘缘的一种解脱
北魏孝文帝废皇后冯氏得恩遇甚厚。但后来高祖“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寻废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受孝文帝恩义甚重的皇后冯氏遭到同父异母姐姐的无情排挤、百般诽谤,被废为庶人。虽然史家认为她最后出家为尼是因为“贞谨有德操”,但也应与对亲情的极度失望有关。北齐文宣皇后李氏“赵郡李希宗女也”,“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閤,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李皇后遭受了巨大的身心创伤,经历了人间苦难之后,因为性爱佛法,所以彻底斩断尘缘,遁入空门。
对于处在生活顺境中的人来说,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信仰,可能都只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寄托;而对于遭受巨大人生变故的人来说,某种信仰可能就会实质性地改变她们的生活。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成为一剂医治遭受人生变故女性精神痛苦的良药,通过在尼寺的蔬食斋戒、参禅打坐、诵经悟道等活动,使人忘掉尘世的苦难,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进而增强生存下去的勇气。
无论是以上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是女性不得已而为之的“被选择”,即使是皇帝宠爱的后妃在出家、还俗上也难见女性角色的主体意识。孝文幽皇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念焉。岁馀而太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后立为皇后”。冯氏因病出家和病愈还俗的命运是自己无法主宰的。
三、北朝后妃出家为尼的原因
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毁法灭佛时期,北朝佛教一直处于兴盛发展态势,但北朝上下“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北魏政权为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给予僧尼免除赋役等特权,于是大量普通百姓剃发出家,因而僧尼人数激增,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天下僧尼数达二百万。倘若说普通百姓是为个人私利而剃发出家的话,那么身居高位的北朝后妃为什么也要选择出家?细究起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北朝时期佛教政策的影响
佛教在北朝时期传播广泛,影响巨大。北魏时法果主张“现在的皇帝就是现在的如来”的思想被北朝佛教界长期继承下来,佛教表现出对政权的强烈依附,僧人对帝王尊崇有加,依靠政权的力量扩张势力;北魏政权也把佛教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北魏文成帝时发布诏书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文成帝认识到佛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因而遵照前例仍使僧尼行使教化百姓的任务,“北魏以后北朝佛教的国家色彩变得浓厚起来,咒术的、实践的、大众化的倾向也增强了”。为使佛教真正教化百姓又不威胁自己的统治,北朝政权对佛教采取了强势控制措施。要求僧尼皈依,远离繁华都市,潜心禅修,少问世事。社会上各种传闻逸事也为此造势,北朝时期崇真寺比丘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述说阎罗王对众僧的处置:坐禅苦行诵经者得升天堂,聚徒讲经教化檀越造作经像者被关到暗室。阎罗王认为“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胡太后时,下诏:“不听持经像沿路乞索。”“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阎罗王要求的实为北魏统治者的主张。统治者害怕僧尼讲经时借题发挥,鼓动百姓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亲自出面干预佛教的修行方式。北朝佛教几乎完全丧失了超脱、独立的精神,成为政权的婢女。
为更好地实施为我所用的佛教政策,北朝统治者也赋予佛教徒以特殊的权利,世宗即位,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或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佛教徒不但与俗民适用不同的法律,还可以避免繁重的国家赋税,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劳动力为躲避租税而出家为僧尼的现象。北朝佛教深度世俗化和工具化使得比丘僧尼身份有时候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这个群体是方外之宾而非顺化之民,可以不受世俗之礼法的约束,甚至在战乱之时可以免遭杀身之祸,这也是一些后妃在危难之时匆匆剃发为尼的原因。
2.强化的贞节观念与佛教清规戒律的结合
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与儒家思想的逐步深化,父权制的发展和对女性贞节观念的强化密不可分。北魏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极为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开始于北魏时期的礼教复兴建设使得女教工作被强化,与之相伴的是社会对女性的贞顺节义要求加强,且贞节的标准有了变化,从要求妾为夫殉死到要求妻为夫殉死。这种观念在社会舆论上有时候以一种极致的方式出现。北魏洛阳“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梁氏惶懼,舍宅为寺”。韦英妻梁氏因夫死不治丧而嫁,使得死去的丈夫白日来归,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梁氏因恐惧而舍宅为寺表明北朝时期佛教已经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共同规制女性的生活。
逐渐强化的女性贞节要求与佛教对比丘尼的戒律要求完全吻合。如比丘尼戒律《四分律》规定“若比丘尼与男子同室宿者,波逸提”。“若比丘尼与男子说法过五六语,除有智女人,波逸提”。“若比丘尼独与男子露地一处共坐者,波逸提”。避免与男子接触是比丘尼必须遵守的基本戒律,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女性之贞。尼寺的封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神秘和圣洁,于是出家为尼就成为孀妇为夫守贞的最好代名词。皇帝使后妃出家为尼就能保证她们在不适合这种身份时不被染指。不但皇帝,权臣高官也纷纷采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死后姬妾不落入别人之手。北魏名位显著的权臣高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北魏丞相元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生活豪奢淫逸,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元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北朝后妃在夫死或国亡之时出家为尼,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似都含有为夫守贞之义。北朝时期,出家为尼开始成为女性保持贞节的委婉表达,同时宗教也成为父权制社会压制女性、服务男性的工具。
3.后妃佛教信仰的边缘化
北朝佛教发展迅速,出家僧尼人数众多,但真正因为宗教热情而出世修法者却少见记载。很多人因为统治者个人祈福目的而被度为僧尼,成为服务政权的牺牲品。“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西魏文皇后在文皇帝敕令其自绝之时“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为落发”。被落发的数十侍婢很难说全是情愿出家为尼。后妃虽然身份特殊,但与普通百姓一样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更遑论宗教信仰了。北魏政权建立初期,道武帝为巩固父权制,防止母后势力干预皇权,仿效汉武帝之制,设立子贵母死制度,“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这一残忍且矫枉过正的防后妃参与政权的制度至宣武帝时期才被革除。虽然子贵母死制度未真正绝断后宫女性临朝称制的机会,但影响深远,同时也足以说明北魏政权对后妃是设防严守的。在政治权力方面处于被严厉压制防范的后妃,附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体系内,根本无权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黄怀秋在论述女性与基督教信仰关系时指出:“基督徒女性们在经典、在传统教义、在礼仪、在教会政治上”“都受到边缘化的推挤,只能附属于整个父权体制下的男性家主,而成为无声的边缘人。长久以来,女性们生活在这种边缘化的世界中,后者已经成了她们中最真实(却未加反省)的一部分。”不唯基督教中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在其他宗教信仰中被边缘化的状态是相同的。北朝后妃虽然处于女性群体的上层,但在整个男性主导的政权体系中仍处于无权的依附状态,北朝政权对佛教的工具性政策使得后妃出家为尼成为服务政治需要的手段,她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宗教选择和宗教命运。
当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面纱去认识北朝后妃出家为尼的真实动机时,发现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总体来说,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与佛教信仰关系不大,出家为尼一般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制度下,皇后贵妃虽身居高位,身份特殊,但在政治生活中也大多无权,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就是跟随在皇帝身后亦步亦趋,皇帝崇佛,她们就焚香诵经,施地立寺;皇帝废佛,后妃们就得放弃自己的信仰追求,这直接导致了女性在宗教信仰中被边缘化的结果。
北朝后妃出家为尼与佛教追求精神超脱的主旨相去甚远,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把宗教当成为自己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正如常金仓先生在论述中国上古三代是人治而不是神治时指出:“中国人把现世看作是人类的一切,统治者唯一重视的是治乱安危,是权力之勿失;人民所重视的便是长寿、富贵、多子孙,立德、立功、立言。至于宗教信仰、祀神礼仪,无论其多寡,都不过是圣人们用来教导世人(包括统治者)的工具罢了。”
北朝皇后出家为尼现象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孀居妇女的宗教选择并开启了唐代的内道场制度和唐代皇帝去世安置后妃出家为尼的惯例,用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加深对这些承前启后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注释
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2、368页。②夏毅辉:《北朝皇后与佛教》,《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③陈怀宇:《中古时代后妃为尼史事考》,《华林》2002年第2卷。④许智银:《论北魏女性出家为尼现象》,《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⑤石少欣,陈洪:《北魏世宗高皇后出俗为尼考—兼谈北朝后妃出家与宫廷政争》,《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2期。⑥⑦⑨⑩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506、517—518、529、527—528、524、523—524、507页。⑧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9、589—590、336、340、332、333、3035—3036、3040—3041、1523、214、3039、49页。蔡鸿生:《学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125—126页。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94页。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60—62、146页。焦杰:《〈烈女传〉与周秦汉唐妇德标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新修大正大藏经》《四分律》卷二四《尼戒法三十拾堕法》,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734—735页。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黄怀秋:《女性灵修的特质——以基督宗教和后基督宗教为研究方向》辅仁宗教研究,2002年第6期,转引自李玉珍:《中国妇女与佛教》,李贞德主编:《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477页。常金仓:《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