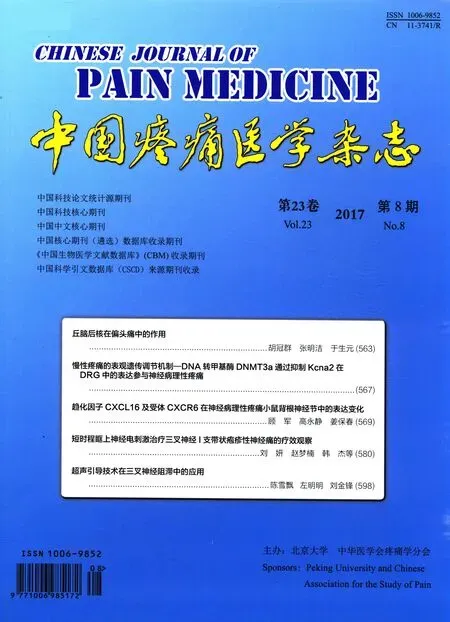中国有了一个疼痛科—庆祝疼痛科成立十周年大会讲话
韩济生
•疼痛科十周年•
中国有了一个疼痛科—庆祝疼痛科成立十周年大会讲话
韩济生
中国有了一个疼痛科,这个标题有点口语化,意思是中国的医学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事物:“疼痛科”。这个新事物不是突然出现的,是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酝酿、筹备、奠基,再加上十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局面。在今天这个大好日子,回顾既往,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前景。也符合中国文化中所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曾子大学篇)” 。
针刺研究培养了疼痛医学人才
大规模的针刺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全国的很多大院校和科研院所都开展了针麻原理研究,这为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也为中国的针刺疗法推向国际作出了贡献; 1970年以前,国际上有关针刺的科研论文凤毛麟角;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举办的针刺疗法听证会,这个为期两天半的大会参会者一千余人,多数为医务人员,也包括律师和医务政策制定者,我有幸被邀请作为学术活动的第一个报告人,把我们中国针刺镇痛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大家,让世界了解了针刺镇痛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不只是“心理作用”,而是有其物质基础;从此以后,NIH增加了一个机构“辅助疗法研究中心”,发放大量科研基金,从而有关针刺的科研论文直线增长,至今未衰。我的科研团队也连续13年得到NIH科研资助。我们对针灸国际化的另一个贡献是制定电针仪的国际标准,2012年国际标准组织(ISO)在韩国召开会议,授权中国为主,联合韩国、日本和加拿大制订电针仪的国际标准,不久即将定稿。从1979年以来,我应邀访问了27个国家和地区,作209场学术报告,介绍中国针灸的最新科研成果。2010年加拿大蒙特里尔举办的第13届世界疼痛大会上,我应邀做了针刺镇痛原理报告,在会后一年内该报告的点击率在21个大会发言中位列第三,说明国际疼痛学界对针灸的兴趣。 2012年在意大利米兰的第14届世界疼痛大会上我获授IASP荣誉会员的资格(全球总共35位),也是对中国疼痛医学的一个肯定。
疼痛研究从基础走向临床
针灸发源于临床,导致大量研究开展于基础。1995年,在时任卫生部陈敏章部长的帮助下,法国UPPSA疼痛研究所和北京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中法疼痛治疗中心”。当时设在北京医科大学校医院二楼的“中法疼痛诊疗中心”不仅有疼痛门诊,而且有18张病床,既有临床工作,也有科研和干部培养,成为医、教、研三结合的新型机构。该中心前后共开展了十三届全国性的疼痛医学培训班,对于训练培养我们的临床疼痛医师起了很大作用。
国内外学术交流
1979年,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去参加国际麻醉药疼痛研究学会(INRC)和其后的国际疼痛会议(IASP);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学到他们如何深入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交流。1989年在北京举办自己的东西方疼痛会议,奠基会员164人。在今天的大会上,当年164位奠基会员中尚有赵志奇、高崇荣、王福根、宋文阁等6人参会。特别感谢当时IASP总干事John Loeser专程前来参会,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疼痛学会,次年即成为IASP的中国分会。1989~2010年前后共举办了七届东西方疼痛会议,参会人数达2 314人次,对于了解国际疼痛学发展趋势大有裨益。2015~2016年我们发展了IASP会员300余人,目前总数达到400余人,2016年在日本举办的第16届世界疼痛大会上也有了中国专场报告。值得提及的是,在日本参加会议期间,樊碧发教授被邀请到日本的国会去做报告,介绍中国疼痛医学的发展现状及进一步发展趋势,引起日本疼痛学界及政界的重视,明确表达了借鉴中国经验的愿望。
创办《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和编写疼痛教科书
为了提高专业医师水平, 1995年创建了《中国疼痛医学杂志》,由于疼痛医学是新兴学科,办刊初期收到的稿件需要花费大力加以修改,经过20年努力,科研水平与稿件质量同步提高,表现在《中国疼痛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逐步升高;有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也进入快速增长期;这两项参数仍然是我们有待努力的目标。
2000年,应中华医学会要求,我们组织编写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疼痛学分册》(2004)和《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2007)。这两本书和2012年编写的《疼痛学》集中了十年来疼痛临床医学界的智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产物。对促进疼痛医学发展、规范疼痛医学的诊疗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卫生部227号文件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关于申请成立疼痛科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在2007年新闻发布会上深情地回顾了这个过程。他说:五年前我在医政司担任副司长,韩济生院士作为中华医学会主任委员带领有关专家拜访医政司,希望能在编制系列中设立疼痛科。我调到医学会三年了,韩院士又到医学会找我,反映医疗卫生界专家的意见。当时在医学会征求各方意见,关于是否成立疼痛科看法是不一致的。韩院士说:“我已经70多岁了,我做了一辈子疼痛医学,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以我现有的精力反映同行的意见,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下设立疼痛科”。我必须说,我们疼痛专业领域里这些专家孜孜以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今天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医师协会张雁灵会长说,卫生部每天对外签发很多文件,但没想到这227号文件的签发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并不是每个文件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代表着227号文件反映了医学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人民的实际需求。
记得正当我们申请成立疼痛科处于十分困难期间:吴阶平院士伸出援手,建议我们向医学界院士说明情况,请求支持。包括吴老在内的18位院士(韩启德、裘法祖、王忠诚、吴孟超、汤钊猷、顾玉东、郭应禄、孙燕、王世真、胡亚美、樊代明、陈可冀、沈自尹、秦伯益、杨雄里、陈宜张及韩济生)亲笔签字的支持信对于建立疼痛科起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十年来我们通过具体行动给了18位院士们一个结结实实的回答,没有辜负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对我们殷切期望!
卫生部,特别是医政司有关领导深入研究,倾听了我们的意见,认真分析利弊,审时度势,协调了各方认识,终于签署了227号文件,于2007年7月16日向全国发布。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进行科研合作,心情真的是无比激动!赶紧回国。2007年10月14日世界镇痛日前夕,在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2007年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吴阶平副委员长、韩启德副委员长,卫生部陈啸宏副部长、尹大奎副部长,医政司领导,美国疼痛医学会候任主席Dubois教授等分别致辞,国际疼痛学会主席Jansen博士特为此发来贺电。
再回想一下,在我们成立疼痛学会的第一个十年里面,真的是工作量极大,时间非常紧迫。涉及的问题既多,需要解决的时限又短:合法行医的医师需要资格证,年轻医师要有晋升通道,疼痛业务范围有待确定,物价部门需要核定治疗费用标准,疼痛科质量监控体系需要建立,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有待确认……最后走到专科医联体的建立。回想这一步一步,每步都非常艰难。可以非常明确的说:如果没有一个无私奉献、团结奋进的团队,靠任何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也绝对完成不了这些任务!所以说,团队的力量,合作的力量是无穷的!今后一定要牢记这个要诀,决不能加以违背!有人说,创业难,守业并加以发展更难。到此我才更好的理解习主席关于“不忘初心”的叮嘱,是何等铿锵有力!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评审工作。我们疼痛科是2007年刚刚建立的科室,如果不加以特殊的努力,基本上不可能进入第一批次重点学科评定。但实际上2012年我们就有了第一批六家医院通过了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的评审工作:卫计委中日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深圳南山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有了六个重点学科作为骨架,使得我们学科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将来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的机会。在此我要向有关同仁致以特殊的感谢之情。
疼痛科创业十年的业绩
2007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启德院士给我们的题词是:“免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和医师的神圣职责”。2009年韩启德院士的题词是:“廿载奋斗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建科创业消除顽痛惠及众生”。马晓伟副部长的题词是:“为民除痛,造福社会”。这些题词,永远有效!
据初步统计,十年来我们疼痛科就诊病人总数由80万增长到794万;住院病人数由6.1万增长到48.2万人次;这都是大家齐心努力干出来的!特别是有的地区,经济条件不是十分发达,但在上列指标上位居前列,令人油然产生发自内心的感佩!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孙燕、匡培根、赵志奇、崔健君、严相默、王全美、李仲廉、高崇荣、谭冠先、宋文阁、俞永林等老一辈同志的指导,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王福根、樊碧发、于生元、刘延青等历届主委的努力,以及许多年轻同事的团结奋斗精神。
今后我们的队伍将成倍扩大,组织和管理的任务势必更加艰巨。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忘初心,在政府支持、疼痛医学界团结努力下,未来10年,中国疼痛医学必将迎来更大辉煌!
(根据韩济生院士讲话录音整理)
10.3969/j.issn.1006-9852.2017.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