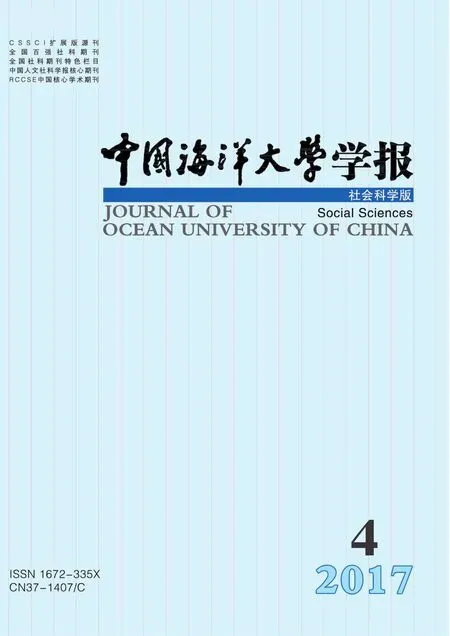童稚性及其在当代汉语童诗中的艺术表现*
何卫青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童稚性及其在当代汉语童诗中的艺术表现*
何卫青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童稚性是童诗区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标志性美学特征,它首先是一种诗歌创作的理想审美图式,是一种以儿童似的、新鲜的、陌生的、第一次的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能力。写作童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去捕捉儿童看待世界及其万物的方式。其次,童稚性也是童诗写作的一种艺术构思方式(具象化、泛灵化、游戏化),有着具体的文本体现。
童稚性;三个“声音”;实词意象;虚词意象;游戏;三种语言活动
一
电影艺术理论家爱森斯坦在其名作《并非冷漠的大自然》中,怀着对汉字绘画性的惊异感,表达了对汉语诗歌(古典诗歌)的欣赏。他认为,中国诗歌“更接近造型描绘的规律”是一种“未经分化的诗作法”。这种诗作法无疑保留着诗歌的“童稚阶段”的印迹——一定程度的童稚性。他认为:“如果从我们的诗歌的‘童稚’领域去寻找类似的例子,那么会找到无数这样的范例。……当然,这首先是在儿童书和儿童诗方面。”[1](P295)
在以习以为常的或消失、或隐退、或淡化为构成原则的诗歌创作中,童稚性的确是童诗区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标志性美学特征。
童稚性首先是一种诗歌创作的理想审美图式。
它既与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中的“童心”有相通之处,又跟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和“健康的孩提性”相关。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对儒家天性善论的继承,“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2](P67)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童心”作为初心,是未被外界环境所污染的“童子”之心,“绝假纯真”,这种对“童子”-儿童本性的认识,也正是当代中国童心主义或者说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理论基础。当代童诗的创作,是把“童心说”当作一种创造美学来把握的。
然而,作为成人的童诗诗人,“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2]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这就需要马斯洛所说的“第二次天真”和“健康的孩提性”,将已经成人化了的诗人后天习得的逻辑、科学、常识、文明习气、原则、规则、责任心、理性等等,用非逻辑、非理性、不合规则、反常识的“陌生化”手段崭新地呈现出来。
“第二次天真”和“健康的孩提性”是对童子初心的“回忆”“溯源”和“重建”。
所谓“童稚性”,就创作心理而言,是一种以儿童似的、新鲜的、陌生的、第一次的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能力。写作童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去捕捉儿童看待世界及其万物的方式。不是从某双偶然的、淡漠的眼睛去观察,而是以从前从未见过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万物的眼睛(就像以一双初次来到地球的外星人的眼睛)去观察。这是一种无偏见、清澈化的观察。尽管可以说,“童稚性”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理想化心理图式或前提,童诗的写作,却潜藏着实现其的最大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以童子之初心写诗的人,是在莺雀掷柳迁乔织就的锦绣里,做一个清浅明亮的梦;是用孩童燃烧的激情插上翅膀,做一次美幻的飞翔。
二
如果说“接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的话,日常生活语言再现了我们的现实世界、日常生活,诗歌语言则虚构了一个不属于这种生活的世界。这种虚构,似乎依赖于超乎规范、反常、陌生化的词语组合。诗歌创作,首先是一种从直接表意到迂回表意,从熟悉到不熟悉的过程。这种特殊的话语与接受者(诗歌读者)之间的交流,不是日常生活语言在“再现”意义上的精确,而是暗示、体验、启发。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创作,是消除幻想和现实之间区别的一条途径。诗人以其创造性的幻想造出“并不存在之物,并将其置于存在物之上”。[3](P8)
一句话,诗歌是“文字游戏、语言链、模糊的意义链以及像梦幻一样的记忆链的混乱堆积。”[4](P351)诗歌的原创性从其反常性中获得辩护,而这种“反常性”,不妨看成是符号学所说的“标出性”。“标出性”本是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其建立在相对可统计的基础之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给他的朋友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小的一项,是标出项;而对立使用较多的那一项,是非标出项。”[5](P281)因此,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关于标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对立项不对称的规律。将“标出性”这个概念运用于诗歌研究,主要在于考察一首诗歌标出项与非标出项的“比例”。标出项越多,该诗的标出性越高,其诗性也就越强。当然,并不是标出性越高的诗歌,就一定是好诗,同样,标出性不高的诗歌,也不一定就不是好诗。
“童稚性”是考量童诗“标出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童诗写作的一种艺术构思方式,有着具体的文本体现。童稚性的诗歌构思有这样几个特点:
具象化:具象化的思维是一种非类化的思维,它专注于个体激起的感知、情绪、态度等反应,而非抽象的类属性质和特征。在当代汉语童诗中,具象化的构思在文本中的体现,则是在其幻象的世界中,诗人用来描述事物、抒发情感、吟唱故事所用的词语,很少动物、植物、人等等这类抽象的专属名词,而是包含着无数具有抒情意味的幻象和意念的“专有名词”。比如,不是“雨”,而是“味道很心慌的雨”(童子《要下大雨啦》);不是“河流、湖泊”,而是“雄性的河流,雌性的湖泊”(薛为民《天籁》);不是“声音”,而是“被淋湿的声音”(童子《要下大雨啦》);不是“橹”,而是“一柄飞行的橹”(高洪波《小老鼠学飞》);不是任何一只“蚂蚁”,而是“蚂蚁恰恰”(萧萍《蚂蚁恰恰》);不是任何一个“花园”,而是“巨人的花园”(徐鲁《巨人的花园》);不是“阳光”,而是“柔软的阳光”(金波《柔软的阳光》)……
这些幻象和意念越少具有实在性,越富有诗意,诗歌的标出性也越高。
泛灵化:万事万物皆有灵,内在与外在、心灵与非心灵没有区分。这是一种人类童年期的思维,也是儿童思维的重要特征。“任何是在都是神秘的,因而任何知觉也是神秘的。”[6](P61)这种构思在当代汉语童诗中,首先表现在诗中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意象和意境:
比如:“神秘的心”:我的心和水井相同/一直通到青草池塘”(童子《素描小院》)
“神秘的眼睛”:一只眼睛闪烁五月的蓝/一只眼睛沉淀十二月的灰(宁拉《谣曲37》)
“神秘的妈妈”:我妈妈穿着小姑娘最爱穿的衣裳/我妈妈穿过树林就长大(童子《我妈妈哪儿都想去》)
……
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意境,比如“悬鱼镇”:
在悬鱼镇,你可以/看见云端的神仙/听见风中的灵语。
……
在悬鱼镇,/即使霜冻也披着鲜花的长袍/即使鹰巢周围,也有野羊在跳跃。
……(宁拉《悬鱼镇》)
泛灵化思维在童诗创作中,通常选用拟人化的修辞格来体现。拟人化,意味着赋予非人动物、植物、非生命物、甚至时间、空间等无实在性的概念以人的思维语言。比如“不在家的时间先生”(童子《时间先生不在家》)、“唱歌的绿叶”(王宜振《绿叶之歌》)……
泛灵化意味着人与非人动物、植物、非生命物等等之间的屏障被打破,彼此是可以交流、沟通的。这在童诗文本中,体现为歌者吟唱“声音”的特殊。当代汉语童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泛灵化吟唱“声音”大致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自语”:即抒情主人公向非人之物发声,而对方是不能回答的。跟蜜蜂说话、跟门前的合欢树说话、跟春天、天空、海洋、太阳、星星……说话,仿佛它们都能听懂。在《摇木马》中,抒情主人公问木马道:
木马,木马/你摇晃得太厉害/那个小孩/还没有坐稳/就被摇大了……(童子《摇木马》)
第二种是“他语”。抒情主人公以他者而非自己的声音吟唱。这个他者,可以是小动物、可以是草木,也可以是天空、河流、海洋,可以是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比如:
梨树说:当我的枝头/挂满果/人来一伙又一伙
当我的枝头/没了果/只有小鸟来看我(薛为民《梨树的话》)
太阳说:悲伤的人啊!/只要你们在我的海洋居住/风和鱼饵,就毫无意义(宁拉《阳光》)
在童子《小浣熊,我要给你最热烈的拥抱》中,孤单寂寞的鱼向小浣熊发出了友谊的邀请:小浣熊,我是水底吱吱笑的鱼/我想借你美丽的尾巴一次……
第三种是“对语”,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音”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动物与动物、植物与植物、动物与植物等等之间展开。
比如:刺猬和乌龟的对话:“唉!胆小怕事的乌龟先生,/你懦弱的灵魂可怜又可悲/整天囚禁在硬邦邦的壳里,/生活对于你有什么趣味?”……
“对,硬壳暴露出我的怯懦,/但长刺也显示不出你的无畏。/既然我们的实质相同,/最好是马上闭住你的嘴!”……(高洪波《乌龟和刺猬》)
这三种“声音”,都是对儿童独白与对白的思维方式[7](P145)的模拟。
三
童稚性的第三种艺术构思方式是游戏化。
游戏是一种主体性活动,其基本要素是:自愿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划与限制;虽非重要的活动,但非常吸引参与者;有着规则的约束。[8](P18)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部分,“儿童不仅是玩,他们就生活在游戏中。作为生活,他们的游戏有着极大的灵活性,是随时随地,超越时空的,儿童就是游戏。通过游戏,他们建立起通往未知的道路,通往此时此地以外的领域。”[9](P39)游戏化,是以童子初心创作童诗的诗人们通往童稚的道路,通往童年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写作童诗,是一种幻想式的语言游戏,是“戏耍语言”。[10](P181)
任何一首诗歌,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三种基本的语言活动: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11](P4)一般来说,这三种语言方式在同一首诗歌中并非均衡存在,而是因诗而异,各有侧重,当然,也不存在纯粹的抒情、纯粹的叙事、纯粹的戏剧。
抒情式语言活动,在形式上体现为语言的音节、韵律等。中国古典诗歌,多用双声字、叠韵、叠音字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诗歌音节的变化奥妙无常,音韵节奏的变化规律使音声低昂有序,形成有节奏的韵律之美。比如“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屈原《楚辞·离骚》);“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陶渊明《和郭主薄》)“缤纷”“菲菲”“蔼蔼”充分调动了人们的语感,用音律来刺激读者的听觉,感受诗句的音乐美。因此,李善在《文选〉中也说:“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
不过,随着古典诗歌逐渐式微,汉语新诗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表意系统。诗歌文体的主导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散文因素渐增,音乐因素渐减,剥离了外在标识的诗歌语言,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因语言的标出性降低,导致诗体确立困难重重。从早期白话诗人的格律尝试,到闻一多、何其芳、林庚等诗人的探索,都没能使格律诗在格律/自由格局中占据上风。新诗的主导性因素,不再是音乐因素。[12](P165)
作为新诗一分子的当代童诗,同样面临这个难题。除了重形式且形式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音乐性上的童谣(儿歌),音乐性也不再是当代童诗抒情式的主导因素。不过,当代汉语童诗中,有一部分语言材料不是起着叙述情节和描绘场景的作用,而是作为由一个短语和字词组成的音乐伴奏,在整首童诗的进程中,起着类似于随游戏进行的伴声作用。这是一些与其作为意象,不如说作为音乐才可以理解的字眼,它们的存在,烘托某种气氛,而非呈现什么。与其深思其含义,不如去倾听它们的声音和节奏。
这种抒情式的语言游戏在当代童诗中有两种突出的方式:一是拟声词的使用;一是重复的“呼唤”。
拟声词,拟的是动物、植物、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的声音。比如诗人童子的诗中就有许多拟声词:
“吱!”(《包粽子》)
“房子太潮湿了……/蛐蛐,蛐蛐,蛐蛐(《听见蟋蟀弹琴》)
“又听见鸟声喳喳”(《麻雀》)
“嗡嗡叫着苹果妈妈妈妈”(《苹果的储钱罐》)
……
总之,在童诗中,“总有一种声音,一定可以模仿松果掷中月亮”(童子《上弦月》),总有一种声音,作为游戏词语被感知。
重复的呼唤则有增强(游戏)节奏、营造氛围的作用。仍以童子的诗为例:
荠菜花,荠菜花,小手高高举(《春天的花束》)
艾蒿艾蒿艾蒿艾蒿/豆苗豆苗豆苗豆苗/猪秧秧猪秧秧猪秧秧/(你们答应一声啊!)……(《一阵春风吹过来》)
这整首诗都以重复的呼唤在模拟春风吹拂的节奏。
另外,抒情式的语言游戏有时也体现在对音乐性风景的倾听,比如:
“我倾听小溪在山谷里流淌/倾听小鸟在黎明时歌唱/倾听黑夜星星的絮语/倾听古塔上的风铃的哀伤。……”(金波《倾听》)
“小溪的流淌”“小鸟的歌唱”“星星的絮语”“风铃的哀伤”全都是音乐性的“风景”,以“我”自称的孩童歌者以“倾听—/倾听—/倾听—/倾听—”这种重复的节奏吟唱并倾听。
如果说抒情式的语言活动在于对自然音的模仿的话,那么叙事式的语言活动则“在呈现,它指向某物”,[11](P78)即词语所表明的物象(或存在之物,或不存在之物))。这类似于爱森斯坦所赞赏的语言的“图像”,不过象形的汉字“自带”造型感,而对于以汉字为母语文字来说,因熟悉,这种造型性、绘画性很难引起爱森斯坦的那种惊异感。汉语诗歌的“叙事式”语言活动,更在于词语所指意象的选择、组合、搭配,一种文字游戏。
叙事式的语言要素在于词。词有实词和虚词。实词以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为主,虚词以形容词(词组)为主,相应的,有实词意象和虚词意象。在汉语同时中,名词(词组)所指的意象,不妨称为“静态意象”;动词(词组)所指的意象,不妨称为“动态意象”;而虚词(主要是形容词及形容词词组)所指的意象,不妨称为“情绪性意象”和“音乐性意象”,比如前文提到的拟声词就是一种音乐性意象。情绪性意象和音乐性意象属于上文所说的抒情式语言元素。童诗中,静态意象的基本元素,大都来自大自然:草木、飞禽、走兽、山川、河流、天空、海洋等等;动态意象的基本元素,也大都指向人以及万事万物的日常活动:喜怒哀乐、走跑飞游等等。不过,这些熟悉的、现实的事物与动态意象的组合、搭配越是具有超逻辑性,非现实性,游戏化程度就越高,童稚性也就越突出。
静态意象和动态意象的组合搭配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其一,通过悖理、错位或语义的破解、重组制造幽默、搞笑的审美情趣,引发一种反常、奇特、荒诞的感觉:大清早,太阳睡醒了,/伸个懒腰,/打个哈欠,/使劲憋红了脸,/一跳出东山。…… (薛为民《太阳看鸟蛋》)
这首诗的诗句,都是合乎语法规范的,但从语义的角度看,却荒唐、怪诞。太阳是一种静态的视觉意象,它如何能“伸懒腰”“打哈欠”(这是动态意象)?从心理的角度看,这来自于“无生命的事物与有生命的事物的同一”,[13](P261)这种荒诞感,则出自名词所指的静态意象(太阳)与动词所指的动态意象(伸懒腰、打呵欠)的不“般配”组合,两者性质不相符。诗歌传达的是诗人所感受到的太阳这两个意象与某种动作之间的“质”的等同。这种感受“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分类标准,不仅把不同种类的东西统一在自己的感受之下,而且把世间绝然不同的运动和静止现象统一于自己的感情之下。”[13](P264)
其二,通过联感,打通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觉印象的界限,将看起来不相干的静态意象组合起来,并用一个静态意象的性态描述另一个静态意象的性态。如前文已经例举过的“粉红色的羞涩”“心慌味道的雨”等,这种意组合无疑有一种神秘的幻觉感。
再比如:“天空中融化的海洋冰激凌/落下一滴甜蜜的水在蜜蜂的额头”。(宁拉《即景》)
天蓝与海蓝同构,因此天蓝是“海洋冰激凌”,无边无际的天蓝,是融化的冰激凌。这里,有视觉、味觉的相通,造成一种奇特的想象。
其实,很难将童诗中静态意象和动态意象的选择组合方式归在某几类之下,无论什么样的组合,都以丰富、不合常规的想象力为前提的,上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只是在汉语童诗中比较常见的。
诗歌中的戏剧式语言活动,则诉诸于逻辑,即场景、情节、事件等。诗歌中的场景、情节、事件越难以用日常生活的逻辑解释,诗歌的标出性就越高。在童诗中,戏剧式场景、情节、事件都带有游戏性,它们不以日常生活场景、事件的“再现”为被构建的前提,而是一些幻想性的角色游戏。如果说叙事式,包含着语言的奇迹的话,那么,戏剧式,包含着想象力的奇迹。
在当代汉语童诗中,戏剧式的语言活动,有两种游戏性突出的模式:
一是“进入奇境”。
写诗,是一个重新发现世界的过程,不是记录世界,不是写下已有的、已知的观念、信仰、意义,而是在写的过程中去发现意义、信仰、观念和现实。如同掉进兔子洞的小姑娘爱丽丝,要在一个超越现实逻辑的世界探索前进。首先相遇的是奇境世界里的居民:“用松果抛掷月亮的松鼠”“走进房间的大象”“建造地下铁的鼹鼠”“忙着作揖又磕头的叩甲(注:即俗称的磕头虫)先生”“爱上月亮的长颈鹿”“在水底吱吱笑的鱼““线头国的国王”“不在家的时间先生”“蹑足走过的月亮”、凤姑娘、雪娃娃、薄荷、大丽花、蚂蚁、哭精、名叫“困难”的怪物……,这些居民所做的事情是超越现实逻辑,“无意义”的:运送云朵、拥抱小浣熊的尾巴、带着小米去拜访笼中的麻雀、写清凉的故事、玩篮子里挤土豆的游戏、舀月亮……
这个“奇境”,是一种典型的幻想式游戏情景。
二是“猜谜”。
这个谜,可以是具有实在性的事物,也可以是虚化的道理、观念。“猜”意味着诗人描述的是事物产生的效果,而不是事物本身。“猜谜”这个行为本身就带有非实用价值的游戏性。
全世界有多少人?/嘻嘻,/哈哈!
全世界有多少人?/猜吧,/查吧。
全世界有多少人?/猜的——/直拍脑瓜。/查的——/比比划划。
全世界有多少人?/嘻嘻,/哈哈!
全世界有多少人?/我不用猜,/我不用查。
全世界有多少人?/就仨:/你、我、他!(薛为民《全世界有多少人》)
用脑经急转弯式的出乎意料,在幽默的重复中揭示谜底,恍然大悟之后的沉思,都是猜谜游戏过程中典型的情感和心理反应。
有时,这个“谜”也可能始终不揭,创造一种模糊、含混的迷宫。探索迷宫本身是目的,是乐趣的来源,谜底如何,迷宫能否走出,并不重要。
正如前文所说,任何一首童诗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抒情式、叙事式、戏剧式三种语言活动,只是侧重不同。不同诗人也各有擅长,比如金波的童诗以抒情式的童稚表现为重,薛为民的童诗以叙事式的童稚表现为重,而童子的童诗多以戏剧式体现童稚性的想象奇迹。
至此,笔者考察了童稚性在当代童诗中的若干表现方式。然而,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寻找当代汉语童诗的“共同之处”,因为没有一首诗跟另一首诗是一样的,所谓“共同之处”并不存在。这种考察也不是要为“童诗”做诗体自足性的确立或辩护,因为并不是具有童稚性的诗歌就一定是童诗,某些非以儿童为隐含读者的诗歌也可能包含很强的童稚性。以童稚性考察当代汉语童诗的创作,不过是试图从诸多诗歌文本中缓缓抽丝,浮一缕光掠一段影而已。
[1] (苏)C.爱森斯坦著,富澜译.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2] 李贽.传世名著百部之焚书·童心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
[3]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李双志译.现代诗歌的抒情结构[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剖析[M].天津:百合花文艺出版社,1998.
[5]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 詹栋梁.儿童哲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8] (美)杰弗瑞·戈比著,康筝译.你生命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9] (挪威)让-罗尔·布纳克沃尔德著,王毅等译.本能的缪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0] H.加登纳著,兰金仁译.艺术与人的发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11] (瑞士)埃米尔·施塔格尔著,胡其鼎译.诗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 乔琦,邓艮.从标出性看中国新诗的走向[J].江苏社会科学,2012,(3).
[13]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高 雪
Innocence and Its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Poetry
He Wei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s one defining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innocence distinguishes children's poetry from other genres of poetry. It is firstly the ideal aesthetic schema of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poet's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to grasp the world in a childlike, fresh, strange and initial way. In a certain sense, writing children's poetry is to capture the way that children look at the world. Then, innocence is an artistic way to conceive children's poetry (concretization, animism and gamification) which has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in the texts.
innocence; three "voices"; content word image; function word image; game; three language activities
2017-04-10
何卫青(1971- ),女,四川大竹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I206.7
A
1672-335X(2017)04-0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