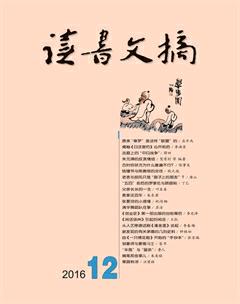父亲长长的一生
共产主义,好像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好像只要大家站成一排,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共产主义似的。我就接到过一张表格,叫我把到了共产主义需要些什么,全都填上。这怎么填呢?我只好跟父亲商量。父亲没接到这样的表格,只叫我别填,到了共产主义不就按需分配了么?着的什么急呢?我想倒也是,记得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活资料的极端丰富,一是思想品德的极度提高。父亲写过一首赞扬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的新诗,开头却引用了《礼运》中的两句古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喝酒闲聊的时候还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恐怕就是这样了。想来制作表格的那一位是不会把思想品德忘了的,正是“大跃进”,使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再存在,待表格上的数目字统计上来,大家就可以按计划比着“放卫星”了。
“大跃进”中,连作诗也“放卫星”。心里想到什么,说出口来又顺溜,那就是诗。男女老幼都作诗,屋里墙外都是诗,村村都开赛诗会。我父亲也忍不住,写了不少“大跃进式”的诗。5月下旬,父亲由文联组织,去张家口外“走马观花”,带队的是自谦“诗多好的少”的郭沫若先生。
在劈山大渠工地的油印小报上,郭老发现了一首好诗:
扁担不长三尺三,
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
昨天担走两座山。
大家看了都说好,都说是真正的诗。这“大家”,姓名见于我父亲的日记的,还有萧三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父亲认为这首诗歌颂了集体劳动,特地写了篇赏析文章。“大跃进”渐渐没人提起了,何况是一首佚名作者的小诗呢?即使真个是好诗,也只能当作诗读,万万不可当作计划来执行,当作成果来统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管怎么说,“大跃进”使更多的人接触了,或者贴近了深入了劳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像雨后春笋。我父亲注意到了小说,他一连写了十来篇评论,都是新人新作。最先介绍的是浩然的 《喜鹊登枝》 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后一篇是以十三陵水库工地作背景的。这篇小说被选进了某出版社的语文补充读物,把我父亲写的评论附在后头。这样编辑是不错的,至少可以让教师省下一半的备课工夫。过了几个年头相安无事,1964年3月接到北大附中一位同学来信,说他们班的同学认定:吃晚饭的时候将军在沙堆背后听人讲的,不是长征故事,而正是九年前,将军带领部队,在十三陵一带作战的故事。我父亲当夜给这位同学写了回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又说“当时我怎么会想错的,现在也弄不明白,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还说立刻给出版社去信,请他们在再版时改正,连如何改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问同学们是否妥当。
三年困难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
过了“大跃进”,紧跟着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两者的界限不十分分明,一共六七个年头吧。城里人,1958年年底就会发觉,菜场上起了细微的变化,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渐渐紧张起来,第二年春节,瓜子花生上市比往年迟,箩筐里一抢就空了。负责采购的满子曾抱怨过,父亲也许觉得新鲜,无意中在日记上挂了一笔;后来可能因为读到了陈叔老新作的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就什么也不记了。那个时候家喻户晓:叫你扳着指头数一数,无论怎么说,成绩肯定比缺点多,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三年困难”从哪年哪月算起呢?从降低个人每月的口粮标准算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在父亲的日记上就没找到这个年月。父亲和我总是书生之见:六亿人口都在挨饿,我们没有特殊化,一同挨饿,这才是正道。没有特殊化,其实并不彻底,父亲和我都有“特供”,跟司局级干部一个样,每月另加糖和豆;父亲有两斤肉,我也有一斤;香烟都是一条,父亲是“红牡丹”,我是“大前门”。特供的价钱跟市价一个样,可是在困难时期,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这点儿特供,已经叫我们特殊化得羞于启齿了,困难时期票证虽多,可是物价未涨,薪水未减,人们手上的钞票就越积越多。经济学家说这可不是好现象。得把那过剩的钞票收回来。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一部分非必需消费品的价钱。对我们家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酒了:售价转眼间翻了几番,尽管这样,名牌白酒在市场上竟一抢而空,剩下的只有浅黄色的金奖白兰地,喝惯国产烈性酒的人嫌它不过瘾,又不习惯陈年橡木桶的那种怪味。人舍我取,我父亲就专喝白兰地。一瓶十五元,兑上四分之一的凉开水,等于十二元。我还嫌贵,找到了一种调制的白玫瑰,味道太甜又异香冲鼻,难喝极了,好处是才五元一瓶,哪儿都有卖的,兑上凉开水,酒价还能下浮。父子俩对饮,各喝各的,都自己骗自己。
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西北角,有个小小的小吃部,记得在困难时期,每月发给每位在京委员两张用餐券。委员凭券可以带着家眷去小吃部,人数不限。小吃部摆着十来张小桌子,两人对酌正合适,四个人就觉着挤了,两张桌子拼起来勉强可以坐六个人,你总不能把一大家子都带去吧。荤素小菜七八种由你挑;还有白酒供应,五粮液、剑南春,每人限购一两;服务员挺有人情味,连小孩也算。点心主要两种:担担面和冬菜包子,多少随意。最后一起算账,吃不完的全部带走。父亲不大肯去,我和满子可不肯放弃这点儿既得利益,有时还带着孩子去。满子忘不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个铝饭盒,把冬菜包子带回去孝敬老太太和姑母,还有个带盖的日本塑料杯,把多买的和喝剩的白酒,一滴不剩都带回家,让父亲独自开怀畅饮。1960年下半年,城市中因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有些单位做了普遍检查,人教社近三百人,患浮肿的超过了百分之十二,我父亲属于比较严重的一拨。医生送来一大包特效药,看外表像红砂糖拌的麦麸,用沸滚的开水冲服,如炒面,疗效想来是开胃通便。
祖母,终于老熟了
好久没提到我的祖母了,她老人家已96岁了,终于老熟了。过世前十来天,她还念叨说:“我就想吃咸鸭蛋,亦勿肯搭我买一个。”她不知道为了一个没找到的咸鸭蛋,我们已经跑遍了半个北京城,还没法跟她说清楚,眼下是困难时期。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糊涂了,家里少了个天天见面的人,她从未问过一声。她老是斜靠在床上,生活全由我姑母照料。一日三餐,连放在床头盘子里的西式蛋糕,各种蜜饯,香蕉苹果橘子,都要我姑母喂进嘴里。我父亲有个特殊任务,老太太是缠脚的,脚指甲长得很慢,可是奇形怪状,又厚又硬,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对付。父亲像修脚师傅一个样坐在矮凳子上,开亮的台灯放在一边,让老太太把脚搁在他膝盖上。他戴上老花镜,左手握住老太太一只脚,右手三个指头捏住刻字刀,就像刻牛角印章一个样,看准了才下刀,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三个指尖上。如此聚精会神,真该摄下个特写镜头来。
老太太对死的态度值得研究。早在还能下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她把一件单衣叠好,用一块大手帕包好。问她干什么,她叹息说:“终归要去噶,捺哼去法亦勿晓得,亦无人陪。”问她去哪儿,她想了一会儿说:“只有到来格路上去。”我想这是往事的再现,我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搬动太多,每回搬动,都没先跟她说清楚缘由,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嘴里不说,脑子里却老在转,如今翻出来了。后来,老太太的精神更加错乱,常说谁谁接她来了。说的大约是她娘家的人,大多连我父亲也从未见过。她看到的自然是幻觉。跟她说没有人,她却说就坐在那里。我父亲和姑母都是直性子,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时候竟会跟老太太吵起来,弄得我们小辈不知如何才好。亏得依正弦曲线发展,有峰有谷,闹几天又好几天。
2月3日晚,老太太心脏停止跳动。在嘉兴寺入殓。灵柩在寺里停放了八天,12日上午在福田公墓下葬。刻在碑面上的字由父亲自己写,一律用正楷。正中一行八个大字:“我母朱太夫人之墓”。铭语119字:“我母朱太夫人生于1865年6月17日,殁于1961年2月3日。我生66岁,违离膝下非恒事,有之往往旬月耳,较久者一度,亦仅一载有馀。今则永不复亲颜色。归熙甫云,世乃有无母之人,其言至衷,我深味之矣。子叶圣陶敬书。”铭语字小,没用标点;每行30字,分为两个两行,列在八个大字两旁。归熙甫就是归有光,明末清初的散文家。“世乃有无母之人”,是他作的 《先妣事略》 的结束语。我父亲很称赞他悼念母亲的这篇散文:说的都是家庭琐事,最后用这七个字点出了他对母亲的无尽依恋。
父亲的浮肿依旧如故,小腿上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部内社内有好些人劝他去外地休息旅行。他在日记上几乎天天提到自己如何疲累,有时还说,感到自己思路迟钝,恐怕不能再写什么了。可是同事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怎么能独自放手就走呢?
十年浩劫,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总算说到1961年10月了,三年困难还没结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到哪一天才算完呢?读者诸君请别着急,各位不放心的,无非是那十年浩劫。
1966年8月2日,新上任的何伟部长召见林砺儒和我父亲,说教育部要改组,两位老先生不复参加行政工作,问有无意见。两位不约而同,都说没有意见。父亲又在日记上说:“余在教育部已十二年,未作甚事,实为尸位。颇思辞去,而恐未便,遂久因循。今闻此言,殊有竟体一松之感矣。”回家的路上,真个去浴室洗了个澡。后来听晓风兄说,中央做此决定,可能是保护性措施。父亲问他:“人教社还去不去呢?”他笑着说:“人教社是兼职,本职已经免了,自然不必去了。何况大家都忙着写大字报,叶老去了也尴尬。”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九月中旬,教育部有个什么战斗组,贴出了一张四千来字的大字报,《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我的儿子三午听说赶去抄了一份回来。结尾的判语,称我父亲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清除叶的反动影响,涤荡叶遗留的污泥浊水,把语文教学的阵地夺回来,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文教阵地上高高地飘扬!”例证如铁,文气似镰,跟报刊上的长篇大论不差多少。看来还放了一马,没跟哪个黑线人物联系在一起。
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自《论 〈海瑞罢官〉》起,我父亲一篇也没放过。读过之后常跟我们说,莫非自己真个老了,语感已经迟钝。每篇文章都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既尖锐又现实,自己怎么一个也看不出来呢?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甚至不敢怀疑。如今大字报写到他自己头上来了,虽然批的不过是片言只语,却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要是明后天被拉去开会批斗呢?看来得准备个检讨提纲,辩白是不行的,能表个态。父亲独自坐在屋里好几天不作声。至美听说赶来了,大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慰父亲,闷了个把星期,父亲的提纲好像还没写得,他叫永和陪着出去走走:先到中央美术学院,专门去看大字报。父亲这才开了眼界,大字报满院满墙,哪位教授不摊上十张八张的,还附有漫画像。拐到文化部,连楼道走廊里也贴满了,大院子里还搭起了芦席棚。父亲终于不再那么紧张了,偶尔有说有笑了。谁知道开不开批斗会呢?部里,社里,属于他名下的大字报还是有,零零星星大多挑他修改课文的失误,也有光打雷不下雨的。每个人至少得写几张大字报是有定额的,说不定只是凑数而已。
(选自《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 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