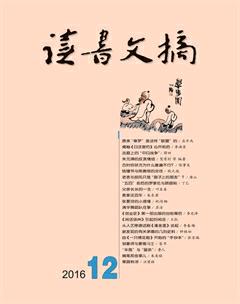张爱玲的小报缘
祝淳翔
青年张爱玲的海外求学路两度被战争打断。“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大读了三年,只差几个月就能毕业,又遇上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二年夏,时局稍定,张爱玲搭船返沪。她先考入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想谋取一纸毕业证书。但“圣校”的教学法让习惯自学的张爱玲不太适应,同时,她利用课余时间替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分散了精力。张爱玲渴望早点经济独立。她既不想毕业后当公司文员,又有了英文写作的成功经验,于是才读了两个多月便主动退学,转而拓展中文卖稿生涯。
尽管张爱玲生于上海,却因镇日读书,涉世未深,与现实社会难免睽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场的新环境,她需要走出书斋,与外界多打交道。而为了尽快熟悉都市风尚,免不了多翻报纸,尤其是小报。
喜读小报
张爱玲爱读小报。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这看法略嫌夸张,也未必准确,却反映了她对小报抱以极高的认同感。
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 社在咸阳路二号召开“纳凉会”茶宴。席间,《海报》 社长金雄白问及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答复说:“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
张爱玲对小报的认同感,也体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私语》 写她小时候与父亲同住,“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并且“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与胡说》又说,自从路易士发表怪诗 《散步的鱼》,遭小报逐日嘲讽,张爱玲竟也“全无心肝”地“跟着笑,笑了许多天”。
《公寓生活记趣》 述及一位“开电梯”的人,“我们的 《新闻报》 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在那次纳凉茶会上,张爱玲进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沪后的张爱玲与姑姑同住,除了 《新闻报》,她们也订小报,所以每日闲读,成了忠实读者。
若问张爱玲订了哪两份小报呢?目前至少可知其中之一,即 《社会日报》。
话得从张爱玲返沪后发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 (《杂志》 十一卷五期,1943年8月出版) 说起。此文先是兴致盎然地抒发对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与胖,内心则遇事通达。遂举例细数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时,听店里的学徒口齿伶俐地对其同伴解释“勋”、“熏”二字的分别;二是 《新闻报》上的广告,文字“切实动人”。当谈及上海到处是性灵文字时,则抄引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并给予佳评: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打油诗的作者,经张爱玲的同龄“粉丝”李君维披露,说是唐大郎:
四十年代,我是上海小报的忠实读者,排日拜读唐大郎 (云旌) 的诗文。据此推断,此诗是唐大郎所作。“张女云姑”系指京剧名伶张文涓和云燕铭。张爱玲文中也说明此诗写作背景:“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张文涓余派女须生,唐大郎极赏其艺,时有诗文称颂;云燕铭其时在上海唱戏,后来去了东北。
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大郎即享誉沪上。他常年为多家小报执笔,作品既多,又富情趣,人称“江南第一枝笔”。笔者运气不错,花费数月之功,终觅得张爱玲所引“唐诗”的原文和出处:
难求一首
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求任使踏穿鞋。
张文娟与云燕铭,为更新之两块头牌,一夜邀饭于新雅,故作此诗,必有人从旁骂曰:“文人无耻,一至于此。”(《社会日报》 1943年1月22日,署名:云哥)
首先,由于纯凭记忆,张爱玲记错一字。其次,“去年”不能算错,因为那年2月5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依国人所见,1月22日可算作前一年。其三,诗注里的更新,指位于牛庄路的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新雅则是南京路上的新雅酒楼。两地相距约三百米,步行仅需五分钟。至于唐大郎自称的“文人无耻”与张爱玲所谓“放任”,是否不谋而合了呢?笔者心存疑虑,却也不便说透,惟愿读者对“踏穿鞋”一语多费思量。
《社会日报》 堪称小报里的翘楚。在主编陈灵犀的刻意标举下,力求正派,不涉狎亵。还引入曹聚仁,成功打通新、旧文学的樊篱,吸引了众多新文学作家。鲁迅就曾以笔名替该报供稿,而徐懋庸、郑伯奇、周木斋、金性尧等名家,也都为其撰文。话虽如此,如论其中最知名且稿件最丰者,依旧非小报界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属。《高唐散记》自1936年一直写至1945年,总数多达千余篇,笔名还有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郎虎等等。
初识唐大郎
按照通常的看法,张爱玲的首篇散文既对唐大郎赞叹有加,两人以后也有长期合作,那他们初识时理应关系融洽。然而事实却在意料之外。
1944年底,唐大郎以“刘郎”笔名发表 《见一见张爱玲》 (《海报》1944.12.2)。文中说自从读过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 《浣锦集》 和 《传奇》,便对她们景仰备至。他听说苏青“比较随便”,然而“张爱玲则有逾分的‘矜饰,她深藏着她的金面,老不肯让人家?一?的。”(?:北方土话,指用眼睛迅速地看。——笔者注) 两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张爱玲的表兄李先生,唐同他说“曾经想请她吃饭,结果碰了个钉子”。李先生拍胸脯为其牵线,竟也“消息杳沉”。后来李答复说,“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开身”。短文最后竟称:
《倾城之恋》 在兰心排戏了,据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我就不想再见一见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任是李先生来邀我,我也不要叨扰了。
明显能辨出唐大郎的心情有多激愤。
不久,《倾城之恋》 公演于新光大戏院,唐大郎观剧后撰文,不仅对舞台上两处表演细节提出商榷,还指摘张爱玲的剧本:“剧中对白,文艺气息太浓,如‘这一炸,炸去了多少故事的尾巴。在小说中,此为名句,用为舞台台词,则显然为晦涩得使人费解。”(《〈倾城之恋〉杂话》,《社会日报》1944.12.22) 这也透出当时唐张关系并不热络。
让我们将时针倒拨四个月,那年的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亚 (署名秋翁) 在 《海报》 刊文《记某女作家:一千元的灰钿》 (按:灰钿意为冤枉钱),向张爱玲突施冷箭。很快,小报文人纷纷参与,多替秋翁摇旗呐喊。好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也有少数人訾议平氏“容量太窄,浪费楮墨”的,其中就有唐大郎。因此,很难想象张爱玲有什么理由不想与唐氏见面。难道她真的过度谨慎?还是因为太忙顾不上?或许正如 《到底是上海人》里所说,张爱玲只对诗句印象深刻,却忘记了作者。这大概意味着彼时的张,尚未将那两个名字对应起来吧。
关系渐热络
僵持局面很快得以冰释。1945年4月14日,唐大郎与龚之方合作创办小报 《光化日报》,该报第二号,发表张爱玲六百余字的杂感 《天地人》,意味着两人正式合作之始。此后唐大郎再提张爱玲时,便多见推崇之辞,并常为张爱玲抱打不平。在此举一个例子:
1947年2月17日,唐大郎在 《铁报》 发表 《彩色的鸭子》,先说“最近又把她的 《传奇》 增订本,也翻覆看了几遍,她的著作,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继而聚焦于短篇 《留情》,“有许多小地方都是所谓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最后调侃某人认为张爱玲不识鸳鸯,而唤作彩色的鸭子,其欣赏力尤其“别致”。唐文看似无意,实则有感而发,所针对的目标是几天前 《沪报》 的短文《张爱玲不识鸳鸯?》 (1947.2.13)。
这年10月,唐大郎打算把三十岁至四十岁所做的诗,整理一次,到年底印一本 《定依阁近体诗选》。因有人对书名提出异议,便想改题 《唐诗三百首》,碰到张爱玲,她也认为这名字来得浑成,并建议选诗工作,应委之别人。而当唐大郎打算放弃一部分打油诗时,又为张所劝阻,并告诉他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诗,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
唐大郎还打算以张爱玲送他的 《传奇增订本》 封面背后的几句题词,作其诗集的短跋,并请桑弧写序 (《序与跋》,《铁报》1947.12.2)。这设想尽管美好,诗集却终未付印。所幸张爱玲的题词保留至今,字里行间洋溢着张爱玲对唐大郎文才的钦慕之情:
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
一年前,正是唐大郎与龚之方替张爱玲出版了《传奇增订本》。但上述赞辞读来颇见诚意,不该仅仅视为张的投桃报李。此时张、唐的良性互动,意味着他们已从普通的作者、编者关系,升格为朋友,而且友情深挚。
最后的联络
解放后,张爱玲与小报及唐大郎继续保持着密切关系,主要的合作成果是张以梁京笔名,在唐大郎主编的革新小报 《亦报》 上,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 与中篇 《小艾》,其中 《十八春》 在报上连载结束后,经修改出有单行本 (亦报社1951年11月版)。
1952年初,香港大学寄来了复学通知书,于是张爱玲翩然离去,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不过张爱玲与唐大郎之间还有“故事”。
注意到1988年4月24日《文汇报》 有篇采访录 《柯灵谈张爱玲》 里的一段:
听说她当年去港理由是继续赴香港大学完成学业,到了香港后,出于生计,她一面给美国新闻社译书,一面写电影剧本,以后又写过两篇反共小说,即 《秧歌》 和 《赤地之恋》。先是用英文写的,后用中文写。这两部小说没多少读者。当时有朋友写信给她,希望她不要反共。
这位写信劝张爱玲不要反共的朋友是谁呢?读罗孚 《怅望卅秋一洒泪》 一文,中谓:
我1953年从北京经过上海,带了小报奇才唐云旌 (即唐大郎) 给她的一封信,要我亲自给她,替我打听她住址的人后来告诉我,她已经到美国去了。这使我为之怅然。那封信,正是唐大郎奉夏衍之命写的,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四十二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受了骗,骗我的不知道是张本人,还是我托他打听的人。
两相对照可知,柯灵谈话里的朋友,应该就是唐大郎。然而此后,唐、张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联系。
(选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