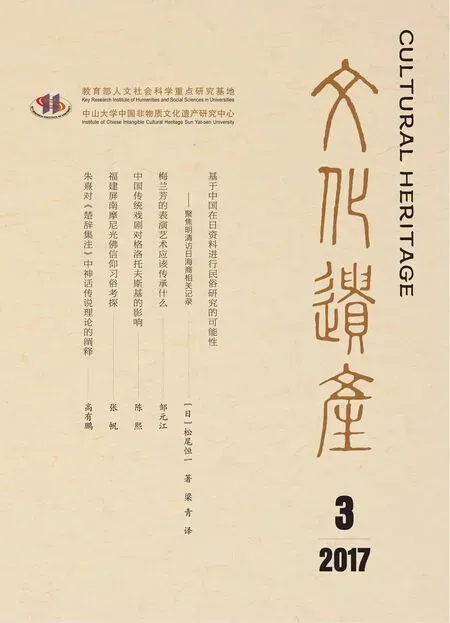十六国乐官制度钩沉*
黎国韬 李 敏
十六国乐官制度钩沉*
黎国韬 李 敏
十六国政权或“全用汉制”,或实施“胡汉分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汉人的制度,所以往往有乐官机构的建置。对此展开稽考可知,后赵、前秦、前凉、慕容诸燕、后凉等国留下的乐官史料相对较多;从中又可看出,这些国家的乐官制度或较有规模,或较为完善;在乐官制度统辖下的一大批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探讨,可以为音乐史、戏剧史、官制史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十六国 乐官制度 伶官乐器 贡献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乱华,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国”政权(304-439),这批政权的建立以“淝水之战”(383)为界,可分为前后二期:前期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等六国,另有代国和冉魏不入十六国之列;后期政权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十国,另有西燕不入十六国之列。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十六国”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3页。由于十六国政权绝大多数为胡人所建立,所以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这些史有定论,毋庸多赘。
但从另一方面看,十六国的政治体制分为“全用汉制”和“胡汉分治”两种,前者如前凉、前燕、后燕(前期)等国,后者如前赵、后赵、北燕等国。无论全用汉制抑或胡汉分治,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汉人的制度,所以在维护中原传统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若干成绩。比方说,仔细稽钩史料即可以发现,十六国政权大多数都有“乐官制度”的建置,在乐官制度统辖下的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都作出了不少贡献。可惜的是,前人对此尚缺乏专文的探讨,兹不揣浅陋,试为考述如次。
一
论十六国政权的乐官制度,也可以分前后两期来谈;前期诸国之中,以后赵和前秦两国的相关资料较多,故不妨用为主要的例子。先看后赵,这是由羯人石氏建立的政权,国内采用了胡汉分治的政策;②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7页。具体到礼乐制度方面,则有很多模仿西晋之处,比如《晋书·载记·石勒》记载:
勒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③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36页。
石勒既然使用中原“天子”的“礼乐”,则必有乐官制度的建置,而且仿用西晋制度的地方肯定不少。④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时期主要实施太乐、鼓吹、清商、总章等四署分立的乐官制度,详拙文《太乐职能演变考》(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所述,兹不赘。石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其灭前赵时得到的乐器有直接关系,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二·石勒》记载:
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诨仪、乐器于襄国。*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3页。
由此可见,石氏从前赵刘氏手中抢到的礼乐之器数量不少,而这批乐器则是刘汉灭西晋时抢得,并传于前赵刘氏的,所以后赵乐官制度应是辗转沿袭西晋之制。以下再看后赵乐官、乐人的一些相关记载,以窥其乐制的大略:
《邺中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着锦裤珮玉。*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二《服章部九》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88页。
《邺中记》:虎大会,礼乐既陈。……又于阁上作女妓,数百衣皆珠玑,鼓舞连倒,琴瑟细伎毕备。*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八《乐部六》引,第2569页。
《邺中记》(《河溯访古记》引):三台有女监、女伎。*佚名:《邺中记》,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4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8页。
由于《邺中记》是有关后赵石氏都城历史的记述,所以上引三条材料均与后赵的乐官制度有关。其中第一条史料提到“女鼓吹尚书”,这一乐官名称为前朝所无,但《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提到:“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范晔撰、李贤等注,司马彪撰志、刘昭注补:《后汉书》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2页。而《太平御览·乐部六》所引《魏志》又提到:“杨阜为武都太守,会马超来寇,曹洪置酒大会,女倡着罗縠衣蹋鼓,一座皆笑。”*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八,第2569页。因此,后赵的女鼓吹尚书大约是从东汉“鼓吹妓女”和三国“女倡蹋鼓”发展而来。第二条史料提到了“女妓”,其实就是女乐,设置女乐供皇家、贵族享乐之用是中国先秦已有的传统,不必多述。第三条史料提到“女监、女伎”,大约也是女乐官的一种,惜史料有限,详细不得而知。
另据田融《赵书》(案,赵即指后赵)记载:“侍郎邵恭执麾不降。”*田融:《赵书》,收入《中国野史集成》三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17页。所谓“侍郎执麾”,实出于“节乐”之用,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鼓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大予具乐器,……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司马昭撰志、刘昭注补:《后汉书·礼仪志》,第3125-3126页。由此可证,后赵一朝以“侍郎执麾”,实为“节乐”之用;这种做法上承后汉,而下启北朝,如北齐时期就有黄门侍郎“掌麾节乐”的制度,可谓一脉相承。*案,有关问题详拙文《汉唐协律乐官发展考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4期)所述,兹不赘。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军戏”的出现,据《北堂书钞·乐部·倡优》引《赵书》云:“石勒参军周延,每大会,使与俳儿着介帻,黄绢单衣。”*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427页。这是有关古代参军戏的最早记载。稍后于《北堂书钞》,又有《艺文类聚·布帛部》引《赵书》云:“石勒参军周雅,为馆陶令,盗官绢数百匹,下狱。后每设大会,使与俳儿,著介帻,绢单衣。优问曰:‘汝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馆陶令,计二十数单衣。’曰:‘政坐耳,是故入辈中。’以为大笑。”*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9页。这条史料也出于《赵书》,但较《北堂书钞》所录更为具体,可以互相补证。总之,这两条史料都确切证实了中国古代戏剧史上著名的参军戏乃从后赵政权之中产生,创作此戏者即当时的乐官“俳儿”,亦即通常所说的“俳优”。
接下来看前秦的情况。前秦是氐人苻氏建立的政权,虽然和石赵一样采用胡汉联合统治,但史家一般认为该国的汉化程度要高出许多;而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四·苻坚》记载:
七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元子,皆束修释奠焉。高平苏通、长乐刘祥并以硕学耆德,尤精二礼,坚以通为《礼记》祭酒,居于东庠;详为《仪礼》祭酒,居于西序。(原案:据《御览》卷二百三十六)*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四,第265页。
由此可见,苻氏对于汉族的礼乐传统非常重视,其乐官制度的建置也应当较为完备;*案,古代礼乐相须为用、缺一不可,苻坚既对《礼记》、《仪礼》极为重视,则在乐制建设上肯定也具备一定规模。而前秦礼乐传统的延续,与苻氏所获西晋乐工不无关系,据《宋书·乐志》记载:
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箱金石始备焉。*沈约:《宋书》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0页。
由此可见,前秦国内原本拥有一些西晋时期“闲练旧乐”的“乐工”;这些乐工乃前秦灭前燕时所获,有《魏书·乐志》所载为证:“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儁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入于关右。”*魏收:《魏书》卷一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7页。这则史料表明,西晋灭亡后,伶官乐器初归刘汉和石赵,其后石氏为冉闵所灭,冉闵又为前燕所克,前燕再被苻氏大臣王猛所平,于是西晋的“伶官乐器”就曲折地落入前秦国的手中了。
除上述伶官乐器外,有关前秦乐官制度的史料尚有数则,如《晋书·载记·苻坚》记载:“坚尝如邺,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第2894页。这条引文提到了“伶人”,可惜只是泛称,具体官职不详。《晋书·载记·苻坚》又记载:“(王猛)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疏固辞不受。”*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四,第2931页。这条引文提到“女妓”,当属内廷女乐;但苻氏将内廷女乐分为上、中、下三等,在以往中原各朝均未见载,可以算是一项比较新奇的制度。*案,汉代的内廷女乐也分等级,但分级很细,且没有上、中、下这样的分法。
此外,《隋书·音乐志》还记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魏徵等:《隋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7页。这条史料表明,苻坚平定凉州张氏以后,曾经得到了前凉的清商乐。这批清商乐是汉魏晋以来的“旧曲”,由于前凉张氏原为西晋藩属,所以拥有比较完整的清商旧乐,它们在其他地区早已零落殆尽,因而十分珍贵。复因此,前秦专门设立管理清商乐的乐官也不足为奇。约而言之,前秦的乐官制度是相对完善的。
十六国前期政权中,还有前凉张氏的乐制值得一提,这是十六国中唯一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在当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年4期。具体到礼乐制度方面,则基本上沿用晋制,《十六国春秋辑补》中的《前凉录四·张骏》及《前凉录六·张祚》所载可以为证:
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第501页。
和平元年,祚纳尉缉、赵长等议,僭王位于谦光殿,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二,第513页。
两条史料所述的“舞六佾”、“舞八佾”,均为汉族传统的宫廷礼乐制度,据此大致可以肯定,前凉应有太常太乐官的设置,因为自秦汉以来,汉族政权的宫廷雅乐都是由太乐官掌管的。*案,有关太乐乐官的情况,详拙文《太乐职能演变考》(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所述,兹不赘。而据前引《隋书·音乐志》可知,西晋灭亡后,汉魏清商旧乐在前凉政权中得以保存,其后则为苻坚所得;苻坚被东晋打败后,这批旧乐有部分又流入南朝,并对南朝清商新声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案,有关魏晋清商旧乐和南朝清商新声的发展情况,详拙文《作为历史概念的清商乐》(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3期)所述,兹不赘。因此,前凉乐官对于清商乐的保存和发展也起过积极的作用。
二
到了十六国后期,鲜卑慕容氏建立了好几个“燕”国政权,有关它们乐官建置的资料相对要多一些,所以我们拟先从这几个燕国谈起。黎虎先生《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一文曾经指出:
慕容鲜卑的音乐基本上也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即由第一阶段的早期慕容鲜卑民歌向第二阶段的宫廷音乐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来其早期的音乐主要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慕容鲜卑民歌。第二阶段的音乐则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汉族的传统音乐,并逐渐将两者结合起来,上升为汉化了的宫廷音乐。而第三阶段随着慕容国家的消亡,慕容音乐也逐渐完成了与汉族和其它民族音乐融合的进程,融入中华民族的古代音乐之中了。*黎虎:《慕容鲜卑音乐论略》,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黎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了慕容鲜卑音乐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正处于十六国的后期,当时慕容燕国的音乐似乎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据《魏书·乐志》载:
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逮(北魏)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魏收:《魏书》卷一百九,第2827页。
由此可见,自从苻坚在淝水一战被东晋打败后,鲜卑贵族离长安东去,前秦的“礼乐器用”有不少为西燕慕容永政权所得。而这批“礼乐器用”即前秦王猛“平邺”时掠回“关右”者(见前述),所以是名符其实的西晋重器,由此足见鲜卑慕容音乐受汉族音乐的影响之大。及至慕容垂平定慕容永后,这批重器又落入了后燕政权手中——所以前引黎虎先生所言是确有依凭的。另据《晋书·载记·慕容垂》记载,后燕慕容垂破长子后,“(慕容)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舆、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三,第3089页。由此可见,除礼乐器用以外,西晋的“伎乐”人员也曾流入后燕政权之中,这对于慕容鲜卑民族音乐的汉化与提升无疑起到重要作用。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西燕和后燕政权都建置了类似西晋的乐官制度。
如前引《魏书·乐志》所述,后燕夺得的这批伶官乐器随着中山城破,一部分流入了北魏政权;而另一部分“太乐细伎”则为慕容德、慕容超建立的南燕政权所得,有《隋书·音乐志》所载为证: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50页。
不难看出,由于后燕被北魏所破,其钟律令李佛投奔南燕,南燕慕容德政权因而拥有一批数量不少的“太乐细伎”——亦足以证明西燕、后燕、南燕诸政权均有太乐官署的建置。但为了赎回母亲,慕容德的儿子慕容超继位后,不得不把一百二十名太乐细伎送给后秦姚兴——后秦亦因此而有太乐署之建置。姚兴被东晋刘裕击灭后,这批太乐细伎又流入了南朝;这是继前秦魏晋清商旧乐之后,又一批重回南朝汉人政权的伎乐;仅此而言,十六国对于保护和传承音乐文化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另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南燕录五·慕容超》记载:“(太上五年,409)遣其将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陷之。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阳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第454页。假定这“男女二千五百人”中有一半教习成功,南燕太乐署的规模也是相当惊人的。
除上述慕容燕国和后秦外,还有一些政权实施了胡汉分治政策,如后凉、北燕、夏国等;而在汉治制度方面,他们不约而同模照汉族政权,设置了礼乐卿“太常”。这一点有前人的研究可据,如缪荃孙《后凉百官表》考证:“丁亥二年”,有“太常卿宗燮”;*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册,开明书店民国25年,第4065页。“庚子二年”,有“太常杨颖”。*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册,第4067页。《夏百官表》则考证:“庚戌四年”,有“太常姚广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册,第4077页。《北燕百官表》又考证:“辛亥三年”,有“太常丞刘轩”等等。*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册,第4080页。根据缪氏的考证可知,太常在十六国后期政权中是普遍设立的,而自秦汉以至于明清,太常辖下一般都设有乐官机构太乐署,所以不难推断,后凉、北燕、夏国等均有太乐的设置。
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后凉,由氐族人吕光所建立,该国除了设置太常太乐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乐官机构。据《晋书·载记·吕光》记载:
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有余匹。*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二十二,第3056页。
由此可见,吕光平定龟兹之后,拥有了大批的“奇伎异戏”。虽然史料说鸠摩罗什及众臣劝服吕光东还,但实际上,由于苻坚的败亡,吕光及这批“奇伎异戏”最后还是留在了他所建立的后凉。另据《隋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徵等:《隋书》卷十五,第378页。
由此可见,后凉国所获的“奇伎异戏”中有一大部分是龟兹乐伎。这批龟兹乐经改造后,形成了“秦汉伎”;被北魏夺得后,又称为《西凉乐》;到了西魏、北周的时候,更被尊称为《国伎》。后来隋文帝设立《七部乐》,《国伎》就是其中一部;而隋炀帝所置《九部乐》中,《西凉》也是其中一部。由此不难看出后凉音乐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所以笔者推测这批“奇伎异戏”也有专门的乐官机构予以妥善管理,否则很难流传到后世。
最后说一说北凉,这是卢水胡(一说匈奴族)酋长沮渠蒙逊建立的国家,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二·沮渠蒙逊》记载:“玄始十四年(425)七月,西域贡吞刀、吐火、秘幻奇伎。(原案:依《御览》七百三十七)”*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六,第666页。自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西域乐伎便大量流入中原,但十六国时期的相关记载却不多,所以是一条较为重要的音乐戏剧史料。北凉得到这些伎乐之后,理应设立乐官机构予以管理,可惜史料阙如,已无法考知其详情了。
三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十六国政权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实施“全用汉制”或“胡汉分治”政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借鉴了汉人制度,所以往往有“乐官”的建置;而通过稽考钩沉可知,后赵、前秦、前凉、慕容诸燕、后凉等国留下的乐制史料相对较多;从中又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乐官制度或较为完善,或较有规模,在乐制统辖下的一大批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也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黎虎先生曾经指出:“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汉族传统音乐与慕容鲜卑音乐的相互结合和吸收是这个时期民族音乐融合过程中的主旋律之一,在此基础上又先后与氐族、羌族、拓跋族、匈奴族、羯族及域外诸民族、国家的音乐相互结合和吸收,在错综复杂的交叉吸收过程中,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广泛的交流和融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华夏音乐,从而把中华民族古代音乐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黎虎:《慕容鲜卑音乐论略》,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第615页。
以上所言甚为有理,但学界从乐官制度层面切入,考察十六国音乐史及其音乐价值的研究尚属阙如,所以本文专门就此展开探讨。当然,现存关于十六国乐制的史料毕竟有限,多数情况下,只能结合乐器、乐舞、乐人的流动和传播,对当时乐官制度作出大致钩勒,许多重要问题目前尚难作出细致的考证。所以本文不过引玉之砖,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一点关注,并希望能为音乐史、戏剧史、官制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罗曼莉
黎国韬(1973-),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李敏(1986-),女,山东寿光人,文学硕士,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委院长办公室科员(广东 广州,510260)。
I207.3
A
1674-0890(2017)03-069-05
* 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