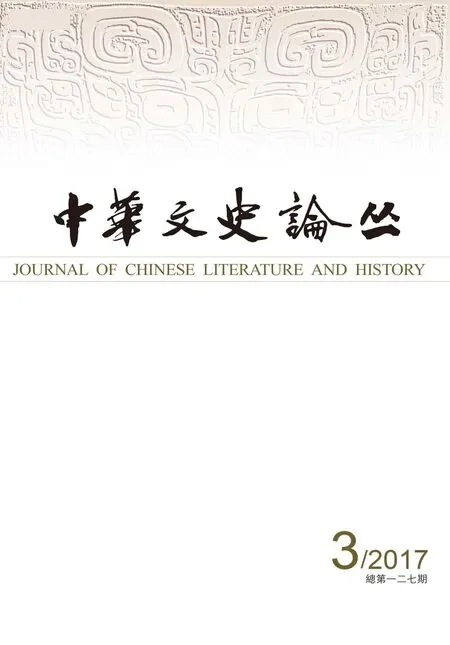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張興武
提要: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關鍵詞:唐宋轉型 慶曆新義 古文創作 邏輯聯繫
趙宋儒學“新義日增舊説幾廢”的深層轉變肇始於慶曆時代,*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毛詩本義》提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21中。而與之相表裏的“古文”創作也從此走向繁榮;前人所謂經學自孫復、石介而後盛,古文自歐陽修、尹洙而後興,*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86册,頁248。即謂此也。也正因爲如此,有不少學者將慶曆時代視爲唐宋轉型的分界點,或稱“近世”文化之開端。*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2。仁宗以後,隨着“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的深層探索,*《宋元學案》卷九《百源學案》黄百家案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67。尤其是經過洛、蜀、新、朔、閩等宋學流派的論辯與紛爭,慶曆“新義”的細化分解與選擇性傳承已成定勢,而所有這些,又深刻影響北宋“古文”盛衰演變的基本格局。如果説范仲淹、歐陽修、蘇舜欽、尹洙等人已經成功擺脱了“執後儒之偏説,事無用之空言”的現實困境,*《歐陽修全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670。確立了“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博於古而宜於今”的創作宗旨,*《歐陽修全集》卷一一二《薦布衣蘇洵狀》,頁1698。取得了“新義”探索與“古文”創作相得益彰的卓越成就,那麽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蘇軾及王安石等儒學名家的“古文”創作則呈現出因學而異、得失互見的風貌與特點。然而,文學史家卻很少注意到慶曆“新義”關涉北宋“古文”盛衰的深層邏輯,以爲學術研究與詩文創作分屬兩途,涇渭分明,不可混同而論。殊不知在“複合型人才”引領文化思潮的趙宋時代,學術探索不僅是相關作家獲取心靈智慧、提升精神内涵的重要途徑,同時也通過潛移默化,深度影響其審美判斷和藝術追求。從這個角度看,深入考察慶曆“新義”制約北宋古文發展的種種隱情,乃是文學史研究者難以回避的重要課題。
一
慶曆儒學“新義”的基本内涵是什麽,它與歐陽修倡導的“古文”變革究竟有着怎樣深層的聯繫?這是本文首先要解答的問題。
由范仲淹及歐陽修等文化精英倡導實施的“慶曆新政”,看似單純的朝政革新,實則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術文化及文學變革思潮。宋初三朝學校不興,“學者莫知所師”,*《歐陽修全集》卷三九《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頁565。儒學名流如聶崇義、邢昺、孫奭、田敏及王昭素等皆承襲漢唐學術傳統,將主要力量集中在字詞訓釋方面;而與之相關聯的科舉考試也“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604,3605。在此情形下,“慶曆新政”的首要任務便是“慎選舉,敦教育”。*《范仲淹全集》卷九《上執政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190。除朝廷以法令形式“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外,*《歐陽修全集》卷二五《胡先生墓表》,頁389。范、歐諸公還積極倡導“明體達用之學”,期望天下學子能“深思治本,漸隆古道”,*《范仲淹全集》卷九《上執政書》,頁190。“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范仲淹全集》卷一《上時相議制舉書》,頁209。爲此,他們設計並實施了“先策論而後詩賦”的科舉改革,明確提出了“不專辭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答手詔條陳十事》,《范仲淹全集》,頁478。“以曉析意義爲通”的取士標準,*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卷一四七,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565。極大地促進了“義理之學”的發展。與此同時,范、歐等人更以“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的主體自覺,*《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頁10268。將“知古明道”與修身、行事、立言合而爲一,爲天下士人樹立榜樣。而在學術層面,歐陽修以《詩本義》和《易童子問》等闡發“新義”的著作垂範學壇,引領思潮。而與之同時,胡瑗、孫復、石介及李覯等人則以草澤身份築室授業,後又執教太學,始終將“經義”解析與“時務”、“治道”相聯繫,爲“宋學”啓蒙導夫先路。要之,自“新政”實施以來,興學之風大盛,廣泛持久的“義理”教育促進了各個儒學門派的形成與發展;全祖望所謂“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黄宗羲《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頁251。即謂此也。由此可知,將慶曆時代看作“宋學”與“漢唐之學”的分野,確有依據。
慶曆儒學“新義”的時代内涵及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以“盡萬物之理”、“究物之深情”的學術創新理念闡釋經典“義理”,*《歐陽修全集》卷六一《易或問》,頁878。尋繹儒道本質,分析其與現實政治文化默然相契的内在本質,此其一也;借“復古”之名批判釋老之説,改革“祖宗家法”中有悖儒道精神的既有成規,*范祖禹《進家人卦解義劄子》,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98),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55。此其二也;發掘儒道實踐精神,涵育士氣,使有道者皆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此其三也。凡此三者,在儒學和文學領域各有不同表現,從而呈現着有體有用、文道相濟的豐滿格局。
先説“義理”闡釋中的“性”、“理”、“自然”和“人情”等。
就儒學本身來看,凡慶曆“新義”之所出,必與王弼、韓康伯、杜預、何休、范寧、毛萇、鄭康成、孔安國等前代鴻儒的傳注箋釋相乖離。慶曆四年(1044),閩學先驅陳襄聲稱:“孔子没,六經之道不明於世。諸儒駁雜之説,綸紛怪錯,周環天下。”*陳襄《送章衡秀才序》,《全宋文》(50),頁173。此説看似突兀,實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爲了超越“諸儒駁雜之説”,歐陽修、胡瑗、孫復、石介、劉敞等人將“性”、“理”、“自然”和“人情”等核心命題與現實困惑相結合,重讀《易》、《詩》、《書》及《春秋》等儒學元典,並對其“義理”内涵作出了富有時代特點的新解釋。劉敞所撰《七經小傳》特具創新自覺,陳振孫云:“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書》、《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直齋書録解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82。應該説,陳襄和劉敞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棄傳從經”的新儒學時代。
將義理闡釋與人倫道德的重建相結合,這是慶曆“新義”的重要特點。歐陽修《易童子問》“專言《繫辭》、《文言》、《説卦》而下皆非聖人所作”的初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易童子問》解題,頁11。即在於超越這些聖賢經傳,聯繫現實社會人生,對《易經》卦爻辭作出新的闡釋。如其解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時即云: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歐陽修全集》卷七六《易童子問》卷一,頁1107。
其《雜説》則進一步闡釋説:
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歐陽修全集》卷一五《雜説三首并序》,頁264。
所謂“君子之學”,既包含着貫通經術、明達政體的學養,更意味着復古革弊、兼善天下的責任,故曰“其任亦重矣”。
面對儒道久衰、天下思治的社會現實,慶曆學者通過“義理”闡述,着意强調士行修養和君臣之道。如胡瑗《周易口義》云:“以人事言之,則君子之人,其德素藴,其行素著,聖賢之事業已習之於始,至此用之朝廷之上,隨時而行之,且非臨事而乃營習,故無所不利。”*胡瑗《周易口義》卷一《坤卦》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册,頁195下—196上。他强調君子之德“素藴”、“素著”,應堅守“聖賢事業”,而不是“臨事營習”。針對君臣上下於“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而已”的消極心態,*張方平《用人體要》,《全宋文》(38),頁64。胡瑗特别强調君臣之德,曰:“以人事言之,則君臣始交而定難,難定而後仁德著。故揚子曰:‘亂不極則德不形。’是其拯天下之大危,解天下之倒懸,出民於塗炭。”*《周易口義》卷二《屯卦》注,頁203下。以爲只有君臣道和,天下纔能保持安泰:“是上下相交,陰陽相會,故謂之泰。以人事言之,君以禮下於臣,臣以忠事於君。君臣道交而相和,同則天下皆獲其安泰也。”*《周易口義》卷三《泰卦》注,頁239上。顯然,胡瑗是以太學主管的身份自覺倡導君臣一體的治國理念,而這正與范仲淹、李覯等同聲相應。如范曰:“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范仲淹《易義》,《全宋文》(18),頁403。李覯自謂“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李覯《删定易圖序論》,《全宋文》(21),頁409。是知,自家而及國、及天下,乃是慶曆“新義”中關乎士大夫德性修養與天下興衰的重要話題。
仁宗時期有關“朋黨”的議論甚囂塵上,而“君子”與“小人”的對立尤爲論題之核心,對此儒學家們也在“義理”闡釋層面給予了回應。胡瑗明確指出:“君子則以君子爲朋偶,小人則以小人爲類黨。……若君子同於君子之人則吉,小人入於君子之黨則凶。”*《周易口義·繫辭上》注,頁451下。范仲淹的説法雖稍顯委婉,但語義非常明確,曰:“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范仲淹全集》卷七《易义》,頁124。換句話説,“以義聚”者必爲“大人”。歐陽修早已認定“君子任重”,至慶曆黨論起,他便進一步提出了“真朋”概念。其《朋黨論》曰: 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其結爲朋黨,盡忠爲民,是謂“真朋”。*《歐陽修全集》卷一七《朋黨論》,頁297。不難看出,從重釋《周易》到觀照現實,歐陽公的思維邏輯一直是非常清晰且周延的。要之,范仲淹、歐陽修和胡瑗等人將“義理”闡釋與現實“人事”相聯繫的作法,實際代表着那個時代普遍的學術取向。
此外,慶曆學者對“天理”、“自然”等概念作出了更爲合理的解釋,從而爲玄妙深邃的儒經“義理”賦予了更多人間化的新内涵。他們强調萬物之“常理”,强調“變化”。歐陽修《易或問》曰:“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於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歐陽修全集》卷六一《易或問》,頁878。所謂“究物之深情”,“盡萬物之理”,實際表達着“天人合一”的儒學思想。在此基礎上,歐陽公還明確意識到,天地之間萬物相感以成變,實有其“自然之理”,故曰:“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歐陽修全集》卷一二七《歸田録》卷下,頁1939。復云:“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歐陽修全集》卷一八《明用》,頁304。慶曆學者普遍認同歐陽修以“變”爲特徵的“自然之理”説,如劉敞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祅異變化,一出一没。此皆理之自然者也。”*劉敞《公是弟子記》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98册,頁467下。換言之,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普遍規律即爲“常理”,必須尊重。
在“天理之自然”中,“人情”的占比似乎更重。范、歐、胡瑗諸公反覆申述“人情”即“天理”,亦即“自然”,它超越朋黨意識,没有善惡之别。范仲淹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范仲淹全集》卷七《易義》,頁120。他將“感人心”視爲“道”之消長的關鍵。同樣,胡瑗釋《易》也把“人情”放在首位,曰:“夫人之深未有其理,未有其形,而又天下之心億兆其心,而聖人以己之深,可以通天下之志”;“夫人情莫不欲飽暖而惡其饑寒,人情莫不欲壽考而惡其短折,人情莫不欲富貴而惡其貧賤,人情莫不欲安平而惡其勞苦。是故聖人以己之心推天下之心,億兆之衆,深情厚貌,皆可以見矣。”*《周易口義·繫辭傳上》注,頁493上。顯然,“聖人之心”的核心便是“人情”,倘不能深通“人情”,則斷難“通天下之志”。與胡、范相比,歐陽修更將“人情”絶對化,其論《出車》詩云:“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歐陽修《詩本義》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0册,頁222上。《詩》既如此,《禮》又如何?歐公曰:“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强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歐陽修全集》卷一二三《濮議·爲後或問下》,頁1873。雖説將“人情”順逆視爲制禮準則的説法還有待商榷,但慶曆學人對“人情”的重視絶無可疑。
次論以“復古”爲名對“祖宗家法”進行的批判。
趙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内涵非常豐富,鄧小南教授對此所作的辨析主要集中在制度史層面,她以《三朝寶訓》和《三朝聖政録》的記述爲依據,認爲慶曆諸臣是“祖宗之法”的極力維護者。*詳參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362—381。但事實上,太宗、真宗有關釋老有禆政治的思想,也在“祖宗家法”的意涵之内。宋初三朝儒教式微,而佛老思想的盛行更削弱了儒學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力。宋太宗“素崇尚釋教”,*《長編》卷二三,頁523。曾對宰相趙普説:
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爲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長編》卷二四,頁554。
爲此,他不惜親撰《蓮華心輪回文偈頌》、《聖敎序》等文以示對佛的虔誠。崇佛的同時,太宗君臣還頗重黄老之學。史載太宗“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内。’”*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1。另據《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丙午載:
上曰:“清淨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長編》卷三四,頁758。
真宗即位以後,完全繼承“祖宗家法”,除著《釋氏論》,將釋氏與周、孔、荀、孟並列外,還特設傳法院以印行佛經。鹽鐵使陳恕曾以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辭“甚懇切”,但“上不許”。*《長編》卷四五,頁961,962。帝王既有倡導,大臣多爲附和,以爲“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時有不檢,安可廢其教耶”。*《長編》卷六三,頁1419。在此情形下,釋、老教義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及天書屢降,祥瑞日生之時,就連精通儒經、以發明孔孟之道爲己任的鴻儒邢昺也只能長噓短嘆於館閣之間。
佛老思想與帝王意志的結合必將損害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於是慶曆學者在“復古”的旗幟下憤而攻之。孫復撰《儒辱》,稱“佛、老之徒横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虚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孫復《孫明復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0册,頁176下。其門生石介著《怪説》與《中國論》,將釋、老和楊億目爲“道”之大患,“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宋史》卷四三二《石介傳》,頁12833。其捍衛儒道的姿態和氣勢,不僅得到了歐陽修的贊譽和肯定,更促進了天下學子對儒道權威的尊重。不過,孫復、石介劍拔弩張的意氣撻伐並不能動摇佛老根基,真正從根底入手徹底遏制佛老泛濫者還是歐陽修。其《本論中》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歐陽修全集》卷一七《本論中》,頁288,290。所謂“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朱子語類》卷一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038。即謂此也。禮儀的核心功能就在於“能使人之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上以作其好,不敢陵下以作其威。遵主之道,以建其極”。*王與之《周禮訂義》卷六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4册,頁314上。從維護皇權的角度講,用禮儀對抗佛老,顯然更具效力。
再看以儒道實踐精神涵育士氣的功效。
儒道實踐精神的覺醒與張揚,是慶曆“新義”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内涵。慶曆之前,有識之士修復儒道的努力雖然不曾間斷,但那僅限於“道”的本體層面,其實踐主體特性並未得到有效發掘。慶曆時期,范、歐諸公胸懷天下,激勵士風,爲張揚儒道實踐精神貢獻良多。朱熹以爲宋朝的忠義之風和淳厚風俗都由范仲淹“作成起來”,相對於韓琦等朝廷重臣,范氏“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朱子語類》卷四七,頁1188;卷一二九,頁3086。富弼亦稱范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全宋文》(29),頁60,61。是自覺的履道者。歐陽修與范仲淹“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實現儒道治世功能爲己任。范鎮《東齋記事·補遺》載:“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東齋記事·補遺》,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7。《宋史·歐陽修傳》亦稱:“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宋史》卷三一九,頁10381。這樣的人生追求及價值取向,無疑具有示範和引領作用。在歐陽修看來,只有把“研窮六經之旨”與“究切當世之務”有機結合起來,*《歐陽修全集》卷一五一《答陸伸》,頁2501。方能有益於當世。因此,他反對“後儒之偏説”、“無用之空言”,*《歐陽修全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頁670。明確指出“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歐陽修全集》卷四四《送徐無黨南歸序》,頁631。從這種信念出發,他積極投身“慶曆新政”,推動科舉改革,充分展示出革弊惠民、富國强兵的赤子之心。
在范、歐周圍,有蘇舜欽、梅堯臣、尹洙等當代名流,他們都以不同方式豐富着儒道實踐内涵。蘇舜欽自稱:“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蘇舜欽《上三司副使段公書》,《全宋文》(41),頁29。在短暫的仕宦生涯中,他不顧位卑言輕,“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歐陽修全集》卷三《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頁455。表現出行道救弊的無畏與慷慨。無獨有偶,尹洙亦堅守道義,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歐陽修全集》卷二八《尹師魯墓誌銘》,頁432。韓琦撰《尹公墓表》,謂其“著《敍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尹公墓表》,《全宋文》(20),頁385。毫無疑問,范、歐時代的名儒大家,已不滿足於“知古明道”,而是要將儒道的精神“履之以身”,“施之於事”。正如蘇軾所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納説爲忠,長育成就。”*《蘇軾文集》卷一《六一居士集敍》,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16。有宋以來,“道”的實踐内涵第一次得到如此廣泛的尊重。
有關慶曆“新義”的基本内涵已如上述,而“新義”關乎“古文”革新的深層思致,還可從以下兩方面稍作補充。
首先,把“知古明道”與修身、行事、立言結合起來,在“古文”創作中體現“道義之樂”,這無疑是“新義”轉化爲實踐的重要環節。早在仁宗即位前的真宗乾興元年(1022),范仲淹就聲稱:“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於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范仲淹全集》卷九《上張右丞書》,頁181。他將履道之志濃縮於天下憂樂之中,謂“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范仲淹全集》(下),頁713。其所爲文則充分體現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時代憂患意識,*《范仲淹全集》卷八,頁168,169。是對“道義之樂”的經典詮釋。歐陽修重點强調“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歐陽修全集》卷六七《與張秀才棐第二書》,頁978。以爲“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歐陽修全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書》,頁664作爲范、歐的同道,蘇舜欽也認爲“士之絜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只蹈道以爲樂”,自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上三司副使段公書》,《全宋文》(21),頁27。而與范、歐形兼“師友”的河南尹洙也稱贊王勝之文“其論經義,頗斥遠傳解衆説,直究聖人指歸,大爲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其策時事則貫穿古今,深切著明,於俗易通,於時易行”。*尹洙《送王勝之贊善一首》,《全宋文》(28),頁3。毫無疑問,慶曆“新義”作用於“古文”創作的關鍵着力點正在於此。
其次,范、歐諸公將人的性情之美與“聖賢之道”等量齊觀,極大地拓展了“古文”反映時代人生的深度和廣度。如范公所撰《答手詔條陳十事》、《近名論》、《尹師魯河南集序》、《清白堂記》、《岳陽樓記》等作“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正集》提要,頁1311下。歐陽修乃文壇宗師,其序、傳及墓表等“古文”作品無不敷腴温潤,以情動人,而《醉翁亭記》、《有美堂記》、《豐樂亭記》、《浮槎山水記》等名篇所藴含的情性之美,久已爲文學史家津津樂道。無獨有偶,歐陽公所重之梅堯臣,“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歐陽修全集》卷二二《書梅聖俞稿後》,頁1049。類似的情形,在尹洙、蔡襄、蘇舜卿等人的“古文”作品中多有體現,文繁不贅。總之,慶曆諸公能夠將文學觸角伸展到當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凡山水田園之樂,政教人情之美,無不歸之於“道義之樂”,所謂“新義”與“古文”互爲表裏者,當如是觀。
慶曆人才之盛遠遠超過了宋初三朝,正如蘇軾所云:“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禄無窮。”*《蘇軾文集》卷一一《仁宗皇帝御飛白記》,頁343。當此之際,范、歐諸公興利除弊,敢爲人先。他們不僅將大興學校的國策列入了“新政”,並舉薦胡瑗、孫復及李覯等在野鴻儒爲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激勵士風。從慶曆到嘉祐的二十餘年間,北宋儒學徹底超越漢、唐,創建了屬於自己的“義理”闡釋體系。而與此同時,在石介、蔡襄、蘇舜欽和梅堯臣等人的合力推動下,以“知古明道”爲指向的“古文”革新也終告成功。不過,自嘉祐以後,隨着張載、蘇軾、司馬光、程顥、程頤以及王安石等一大批“宋學”大家的介入,原本質樸簡易的慶曆“新義”,必然要面臨洛、蜀、新、朔、閩等不同學派的選擇和取捨;其細化與分解的過程不僅意味着“宋學”的繁榮,也爲“古文”發展增添了許多變數。
二
如果將慶曆“新義”視爲活水之源,那麽洛學、蜀學及新學等宋學流派則宛如它的支流。不過,隨着支流的漫延,各種全新的“義理”闡釋也會迅速形成自足而豐滿的學術體系。嘉祐以後,慶曆“新義”的延展與深化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尊重“人情”及“自然”的經義闡釋,二是仰望“賢人”和“聖人”的“性理”思考。從儒學探索關涉詩文創作的角度看,全面掃描慶曆儒學“新義”細化分解的學術脈絡,並以此爲基礎,重新審視各學派在“古文”觀以及創作實踐上的顯著差異,乃是深入闡釋北宋“古文”盛衰邏輯的不二選擇。
程頤將仁宗之後的儒學探索分爲“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和“儒者之學”,聲稱“欲趨道,捨儒者之學不可”。*《二程遺書》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35。在他看來,只有周敦頤、張載、陳襄及家兄程顥等纔是心無旁騖的守道者;而像“三蘇”、曾鞏及王安石那樣在“古文”創作方面引領風騷的儒學家,即便有所著述,也很難與純粹的“儒者之學”相提並論。至於“訓詁之學”乃是指堅守漢唐訓釋傳統的司馬光等,他們在史學研究上“抉擿幽隱,校計毫釐”,*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資治通鑑》卷末,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9607。所爲文章亦“文辭醇深,有西漢風”,*《蘇軾文集》卷一六《司馬温公行狀》,頁475。但那種獨特的價值取向終究與“趨道”與否關係不大。程氏對北宋學術分野的評説或稍有偏頗,但客觀上卻爲後人分析慶曆“新義”的流變軌迹提供了方便。嚴格説來,由“新義”延展而引發的學術紛爭,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學理念分歧,主要涉及“文章之學”和“儒者之學”;兩者之間深層而持久的對話,雖觀點各異,卻始終真誠。
王稱《東都事略》嘗云:“歐陽修以高明博大之學興起斯文,大章短篇,與《詩》、《書》、《春秋》相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爲宗,南豐以曾氏爲重,眉山以蘇氏爲師,而文章之傳於今爲盛,信乎與時而盛衰也。”*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文藝傳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82册,頁751上。其實,類似的説法並不完全準確。嚴格説來,文道相濟乃是慶曆“新義”的重要内涵,其構造者與傳承者均非個體,而是“代羣”。嘉祐以後,王安石、蘇氏父子及曾鞏等“古文”大家,學術各有專擅,觀點也不盡相同,但均能自覺接受范、歐及劉敞等慶曆學人的儒學理念,尊重“自然之理”,堅持“性無善惡”,力排迂闊難行之論,所述皆合乎人情,如此纔能促成“文章之學”盛極一時的嶄新格局。
作爲治世能臣和文章聖手,三蘇、曾鞏及王安石等人將“自然之理”與“王道”得失密切聯繫,極大地拓展了慶曆“新義”的儒道實踐内涵,爲“古文”創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激情與活力。如王安石以爲“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天地生萬物,一草之細,亦皆有理”,*《長編》卷二四,頁5827。而“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箋注》卷三《王霸》,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1061。由此可知,荆公新學“一道德”的理論前提乃是尊重“自然之理”、“萬物之性”。同樣的學術理念和治世邏輯,在“三蘇”身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如蘇洵所謂“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云云,*蘇洵《衡論·養才》,《全宋文》(43),頁92。即與王安石隱然相合。不過,由於蘇氏之學雜糅佛老,其對“自然之理”與“聖人之道”關係的解説也較爲複雜。如蘇轍《老子解》云:“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雖然如此,但人之“道”最終還將受到聖人的制約,“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不過,相對於“挫其銳”、“解其紛”之類的勸解與矯正,蘇轍更强調“無心”之治,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老子解》卷一,叢書集成本,537册,頁4,8。撇開“雜學”特質不論,單就尊重“自然之理”來看,蘇轍此論與荆公所謂“王者之道”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在慶曆“新義”長期持久的潛移默化下,不同學派的學者,部分秉持相同或近似的學術理念亦屬必然。如曾鞏爲學頗能“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經》之藴,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而奏疏表狀亦“皆因事而發”,*曾肇《曾舍人鞏行狀》,《全宋文》(110),頁92。其理念情懷與蘇、王諸公絶無二致。
蘇氏父子與王安石都否定“性之善惡”,這一點與歐陽修“性之善惡不必究”的立場基本一致。*《歐陽修全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頁670。荆公嘗曰:“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王荆公文集箋注》卷三《性情》,頁1062。復云:“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王荆公文集箋注》卷三一《原性》,頁1089。同樣的論述在蘇氏父子的文章中亦非鮮見,如蘇軾曰:“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 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蘇軾文集》卷四《揚雄論》,頁111。另稱:“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蘇軾文集》卷三七《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頁1058。此説同見蘇轍《孟子解》,文繁不贅。其實,否定“性之善惡”與尊重“自然之理”互爲表裏,其核心指向是進一步密切“聖人之道”與現實世界的血肉聯繫,而不是相反。
能否尊重“人情”,是歐陽修、三蘇及王安石等“文章之士”區别於張載、二程等“道學之儒”的重要標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文章正宗》提要,頁1699中。程氏宣稱“性即理”,以人的内在道德本性爲“天理”。其所謂“道”、“理”、“性”、“命”者,其實都是指人倫道德,只不過角度不同,名目有别,“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之謂理”,“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六,一八,《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91,204。但不管“性即理”的命題有多少意涵,“情”作爲“人欲”總是受到排斥的。蘇軾對此非常反感,以爲“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蘇軾文集》卷四九《答劉巨濟書》,頁1433。事實上,“情”與“性”的紛爭,正構成了洛、蜀黨議的核心焦點。
在“人情”議題上,首先須關注的是蘇洵的態度,他幾乎在任何與現實有關的問題上都會考慮“人情”。譬如,他認爲用法者“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謂聖人制禮頗重人情,“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稱《詩經》的教化作用本乎人情,“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更有甚者,他認爲分辨姦邪的惟一標準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衡論·申法》,《全宋文》(43),頁94;《禮論》,同上,頁106;《詩論》,同上,頁110;《辨姦論》,同上,頁158。凡此,皆與歐陽修一脈相承。相比之下,蘇軾對人情的理解更加體貼入微,曰:“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蘇軾《蘇氏易傳》卷三“大過·九二”注,叢書集成本,392册,頁67。“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媮”。*《蘇氏易傳》卷二“蠱”注,頁44。“夫有求於人者,必致怨於其所忌以求説,此人之情也”。*《蘇氏易傳》卷三“頤·六二”注,頁65。他甚至將人之常情與事業成敗聯繫起來,説:“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蘇軾文集》卷四《思治論》,頁115。大抵從人情好惡出發,理解法制、禮樂、治亂諸事,便很容易提挈要領,蘇氏父子重視人情的理由正在於此。
王荆公與東坡在政治上雖成對壘之勢,但兩人在學問人格方面頗多相通之處。例如,荆公嘗讀《江南録》,即能從“人情”角度對徐鉉、潘佑加以評判,曰:“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説。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王荆公文集箋注》卷三四《讀江南録》,頁1185。在他看來,徐鉉因嫉潘佑之才,妒潘佑之忠,恥其身善不及佑,故“汙以它辠”,形諸《江南録》;這看似卑劣的作爲實際出於“人情之常”,體現着“毁生於嫉,嫉生於不勝”的必然邏輯。晚年的蘇軾和王安石,在歷經波折之後更能超越凡俗恩怨,重歸閑淡。蘇軾北歸後探望久别的王安石,説:“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説佛也。”*《蘇軾文集》卷五一《與滕達道三十八》,頁1487。應該説,在他們誦詩説佛的快意中,同樣彰顯着性之善,情之美。
相對於歐、蘇、王、曾“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的學術文章,*曾肇《曾舍人鞏行狀》,《全宋文》(110),頁92。以陳襄、張載及二程等人爲代表的“儒者之學”,超越自然物理,否定人情好惡,拓展和深化了慶曆諸公有關心性修養的討論,並逐步將性理之説絶對化。
純粹形而上的“義理”之學發端於慶曆重建之太學,海陵胡瑗實導其波。黄震嘗云:“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菴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語。”*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708册,頁253上。此説影響廣泛,但細節有待詳察。考程頤就讀太學是在仁宗皇祐、治平間,其時石介早已故去,而孫復自慶曆五年(1045)責監?兌2州税後亦未能回到京城,程頤得以受教者惟有胡瑗一人而已。有關程氏學術的傳承淵源,最具權威者當屬“周程授受,萬理一原”之説。*《朱子全書》(2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050。但據前賢考訂,程氏之學獲益於胡瑗者,遠多於周敦頤。如清人劉紹攽《周易詳説》即云:
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之旨。《觀》卦詞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 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大畜·上九》云:“予聞之胡先生曰: 天之衢亨,誤加何字。”《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 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無咎。”《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考《伊川年譜》,皇祐中遊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意是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第知其從事濓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周易詳説》卷一,《續修四庫全書》,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41下。
其實,程氏遠紹思、孟,近師周、胡,取法多門,實屬必然。即便《伊川易傳》也並未沿襲胡瑗有關“人情”、“自然”的既有論述,而是用“理一分殊”來解釋萬物變化。如曰:“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無不感通焉。”*《伊川易傳》卷四《咸卦》“九四”爻辭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册,頁276下。他反覆强調“理”的絶對性,認爲“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伊川易傳》卷一《同人卦》彖傳注,頁206下。且云:“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暌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伊川易傳》卷三《睽卦》彖傳注,頁299下。所有這些,顯然超越了胡公《周易口義》的固有思致,其“理一分殊”的思維邏輯則完全背離了慶曆諸公的“自然之理”。
張載“關學”重釋儒經“義理”的思路與方法和程氏“洛學”頗爲近似,但張氏在《禮》學上的建樹更爲顯著。《宋史》本傳稱其“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宋史》卷四二七《張載傳》,頁12724。清人朱軾云:“薛思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虚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腳,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朱軾《張子全書序》,《張載集·附録》,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396。所有這些,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范仲淹的《明堂賦》。雖然游酢等程氏後學多次宣稱“横渠之學出於程氏”,*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論·别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42册,頁565下。但《張子語録》中的許多議論與“二程”的性理之説卻不盡相同。如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途,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張載集·正蒙·太和》,頁7。不僅如此,在張載看來,人居天地間,不過是萬“物”之一,人能夠以“心”體“物”的範圍是非常有限的,曰:“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如此觀之方均。”復云:“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盡其心也。”*《張載集·語録》,頁313,333。凡此種種,實與歐陽修“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的觀點極爲相似,*《歐陽修全集》卷一二七《歸田録》卷下,頁1939。而與程氏“天理”之説判然有别。張岱年先生認爲張載屬於唯物論者,其自然觀的主要命題有兩重意思,一是“世界的一切,從空虚無物的太虚到有形有狀的萬物,都是一氣的變化,都統一於氣”,二是“氣之中涵有運動變化的本性,而氣之所以運動變化,就是由於氣本身包含着對立的兩方面,這兩方面相互作用是一切變化的源泉”。*張岱年《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張載集》卷首,頁2。很顯然,這種關於宇宙萬物及人“心”本質的討論,與范、歐諸公所謂“自然之理”息息相通,只不過其思考更加深入,梳理也更爲系統化。
程氏之外,閩人陳襄與胡瑗的關係頗爲密切。此公慶曆二年(1042)登進士第,仕仁宗、英宗及神宗三朝。其與胡瑗的直接交往史無詳載,但根據其妹夫倪天隱爲胡瑗整理《周易口義》,以及大妹夫劉彝、門生孫覺等師事胡瑗等史實不難看出,陳襄與胡瑗絶非泛泛之交。更爲重要的是,陳襄在講述《周易》時,也采用了與胡瑗“每引當世之事明之”一樣的做法。*王得臣《麈史》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5。如其《易講義》在解釋《師卦》時便議論説:
如國朝之制,邊帥將兵,必使中貴人監之,故雖有神明之將,動有所牽,不得專制,所以多無成功。往歲西師屢衂,由此患也。夫軍中之法,雖君命有所不受,其可有所牽制乎?*陳襄《易講義》,《全宋文》(50),頁212。
雖僅此一處,亦足見其深受胡瑗之影響。應該説,陳襄與程頤都是胡瑗學術的傳承者,只不過陳襄久歷宦途,更具踐履之便。孫覺謂襄“仕宦所至,必大葺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横經以講”。*孫覺《陳先生墓誌銘》,《全宋文》(73),頁36。劉彝《陳先生祠堂記》亦云:“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且謂其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四人“以經術政事更相琢磨,而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己過,喜於爲善。而夙夜弗忘者,《詩》與《易》也。故其鈎考皆得姬、孔幾微之藴,傳注所至,弗迨其藩籬矣。”*劉彝《陳先生祠堂記》,《全宋文》(48),頁223。此説雖不免誇飾,但作爲理學家的人格風貌亦不難想象。需要説明的是,陳襄對儒學義理的闡釋已經超越慶曆“新義”,初具道學面目。他特别强調“誠”,以爲至“誠”即可通“聖”。如《送章衡秀才序》曰:
天地之道,難通也;神明,難明也;萬物之理,難齊一也。聖人盡心而誠焉,罔不通,罔不明,罔有不齊一。聖人者,天地之合也。賢人者,求合乎聖人者也。然則聖人不世出,烏乎合?曰: 存則合乎人,亡則合乎經。顔淵氏合乎人,孟、荀、揚、韓合乎經。其事則同: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如是而已。*陳襄《送章衡秀才序》,《全宋文》(50),頁172。
聖人以“誠”而通“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普通人若想達到“聖人”之境,就必須“好學”、“誠心”、“明理”、“盡性”;先做“賢人”,再求“合乎聖人”。相比於范、歐諸公“三不朽”的人格追求,陳襄之説顯然要唯心得多。
作爲“閩學”先驅,陳襄曾借着經筵講論的機會,對“宋學”各派領袖的學術文章遍加評説。他極力贊頌關、洛諸公,謂程顥“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職司之任”,稱張載“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一人而已”。相對而言,其對“文章之學”的態度則令人尋味。既稱蘇軾“豪俊端方,所學雖不長於經術,然子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覽,文詞美麗,擅於一時”,復謂曾鞏“以文學名於時,人皆稱其有才。然其文詞近典雅,與軾之文各爲一體,二人者皆詞人之傑,可備文翰之職”。*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全宋文》(49),頁349,348。由此不難看出,陳襄所堅守的“知天盡性之説”,*《宋史》卷三二一《陳襄傳》,頁10419。與程氏兄弟極爲近似;而對“宋學”各派的價值判斷,也是“欲趨道,捨儒者之學不可”。也正因爲如此,熙寧以後,他纔會以“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爲理由,*陳襄《議學校貢舉劄子》,《全宋文》(50),頁60。極力舉薦鄉貢進士程頤爲國子監助教。
明確了“文章之學”與“儒者之學”同源異流的學術分歧,再來討論兩種南轅北轍的“古文”觀就會全面深入許多。其實,嘉祐以後“宋學”流派的全面成熟,説到底都是慶曆“新義”延展與深發的結果;即便以司馬光爲代表的“訓詁之學”,基本情形也是如此。
慶曆諸公雖以“創通經義”爲學術取向,但也並非完全否定訓釋。如范仲淹嘗曰:“《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睹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范仲淹全集》卷八《説春秋序》,頁164。尹洙嘗撰《敦學》文,以爲當日太學爲求“禄仕”而“發明章句,究極義訓”的教育方式有違傳統“師道”,實際效果不僅不如“郡國所貢士”,且“不若閭里誦習者”,因此他建議“以明經爲上第”,讓“學者益勸”,使“師道”回歸本位。*尹洙《敦學》,《全宋文》(28),頁15。換言之,他並不否定以“帖經、墨義”爲主的明經科取士之法,且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尊重前賢訓詁文字。范、尹的經學理念在司馬光身上得到了傳承與發展,其《論風俗劄子》稱:
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説者,謂之精義。*司馬光《論風俗劄子》,《全宋文》(55),頁190—191。
他希望能改變這種狀況,對“僻經妄説”嚴加懲戒,以免“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對漢唐訓詁傳統的尊重,不僅使《資治通鑑》呈現出“名物訓詁,浩博奧衍”的特點,*《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資治通鑑》提要,頁420下。也令其儒學研究别具風采。譬如司馬光推重揚雄,既作《潛虚》以擬《太玄》,又采諸儒之説以撰《法言集注》,*《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法言集注》提要,頁772下。其書特重箋釋,不究義訓,與張載、程頤等大異其趣。此外,光所撰《書儀》十卷,被譽爲“《禮》家之典型”。四庫館臣嘗舉例云:
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内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祫如矩以應方”句,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説,“似於頸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之義最明,與《方言》“衿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説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精之一證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二《書儀》提要,頁180中。
凡此種種,皆屬“訓詁之學”,雖無“宋學”之蔓衍,但根柢深厚,明白而篤實。
慶曆“新義”的延展路徑雖然複雜,但嘉祐以後“宋學”探索多元格局的逐步形成,卻不能不首先歸功於這樣一個先河後海、自源及流的演進過程。不過,自宋元以降,學者對“洛蜀黨議”、“濂洛正脈”等問題的持續關注,已經遮蔽了洛、蜀、新、朔、閩等宋學流派與慶曆“新義”的學術關聯,從而使北宋思想史探索缺失了極其重要的一環。同時,對文學史,尤其是“古文”研究者而言,忽略了慶曆“新義”的分化與延展,也就意味着放棄了對北宋“古文”源流同異的考察。事實上,在“文與道俱”的創作實踐中,無論是作爲載道之具,還是以鮮活生動的藝術形象展示“物我一體”、“神與物游”的哲人風采,北宋“古文”創作始終都離不開儒學思想的觀照和制約,尤其是像蘇洵、蘇軾、司馬光和王安石那樣博通經史、工於文章的“多元主體”。
三
慶曆時期由范仲淹、歐陽修、石介等主導的文壇變革思潮,以表達“新義”爲價值訴求,使散體“古文”獲得了壓倒駢儷“時文”的絶對優勢。即便像夏竦那樣以“文章取賢科,位宰執,流風遺烈,光華休暢”,不僅“當世偉人”且宜“表的於後”的“四六集大成者”,*宋敏求《文莊集序》,《全宋文》(51),頁286;王銍《四六話》卷上,叢書集成本,2615册,頁2。從此也不再是文壇評論的對象。而號稱“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説,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鑚研而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説,鬼神之情”的古文家們,*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三《上范思遠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51。從此便引領着北宋文壇的發展方向,受到持續追捧。不過,迄今爲止,有關北宋“古文”創作的隊伍構成仍然模糊,至少在文學史敍事中還從未有過整體性的交代;除歐陽修、三蘇、王安石和曾鞏之外,其餘那些自稱“文與道俱”的古文家如胡瑗、李覯、劉敞、二程及陳襄等,似乎並没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歐、蘇、王、曾之後,雖然道學探索日新月異,而“古文”創作卻每況愈下。前人將這種極不對稱的尷尬情形普遍歸咎於道學家重道輕文的理念約束,顯然没有足夠的説服力。較爲審慎的解釋或許是,問題的癥結必然在道學家的“古文”創作本身。事實上,北宋儒學家的“古文”創作,在“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和“儒者之學”等不同學者間確有差異,惟有通過具體細緻的考察,纔能充分理解其盛衰成敗的深層緣由。對此,或可從以下幾方面稍事討論。
文學是語言藝術。就三類“古文”家而言,不同的治學理念和書寫要求必然會在潛移默化中深刻制約其語言表達的風格與習慣,並進而決定其“古文”創作的基本藝術風貌。
蘇洵對此深有感悟,嘗曰:
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蘇洵《上歐陽内翰第一書》,《全宋文》(43),頁27。
潛心閲讀古人文章,不僅會提高思想境界,更能從中受到語言的熏陶。蘇老泉從始覺古人“出言用意,與己大别”的眩暈茫然,到“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的逐步感悟,再到産生“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的創作衝動,最後達到“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的自在境界,其過程本身即體現着從學習模仿到自出珠璣的語言發展邏輯。由此也自然會聯想到,蘇軾文章之所以“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蘇軾文集》卷六六《自評文》,頁2069。達到出神入化的高妙境界,也與其自幼接受家學熏陶、熟讀《孟子》、《莊子》等經典要籍有關。東坡文章在語言上追求“辭達”,自謂“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臓,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蘇軾文集》卷一一《密州通判廳題名記》,頁376。有學者以爲,蘇軾追求的“辭達”,“是一種通達事理,自然成文,不刻意雕飾,卻能隨物賦形,追隨行雲流水之變,進而姿態横生的境界”,*林俊相《蘇軾的“辭達”説》,《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4期,頁l24。此説雖有所悟,然“自然成文”畢竟不太可能。東坡於聖賢典籍必定熟讀神會,對古人語言運用之妙更能爛熟於胸;既有不竭之源,然後纔能成就萬斛泉湧之文采,這種修煉功夫豈是“自然”二字所能形容涵蓋。如俞琰《書齋夜話》卷四載:
先儒作文皆有所本,《六經》是也,試略舉東坡之文言之。如《祭統》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之天子。”東坡《喜雨亭記》乃云:“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虚。”其説蓋本《祭統》。又《樂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東坡《王君寶繪堂記》乃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於物。”其説蓋本《樂記》。*《書齋夜話》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5册,頁628下—629上。
其實,精確化用儒經成語,僅僅是蘇軾文章追求“辭達”的一種表現。就整體而言,師法《孟》、《莊》,充分了解相關事物的核心本質,使書寫過程“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蘇軾文集》卷四九《與謝民師推官書》,頁1418。纔是東坡文章妙絶古今的關鍵所在,其語言魅力更在於此。
大抵像蘇氏父子一樣由所學所悟而直達化境的語言大師,如王安石、曾鞏、司馬光等,最終都爲北宋“古文”之繁盛貢獻良多。司馬光、范祖禹、劉攽、范百禄等人被道學家列入了“訓詁之學”的範疇,而事實上,他們“博識洽聞,留心經術”,在“攬商、周之盛衰,考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的同時,*《蘇魏公文集》卷二二《賜尚書吏部侍郎范百禄……獎諭詔》,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93。也將“史家之文”呈現於北宋文壇。*鄧肅《跋蔡君謨書》,《全宋文》(183),頁157。雖説他們的“古文”創作也存在個性差異,但語言風格整體呈現出醇雅深厚、雄贍簡質的特點,直可與歐、蘇、王、曾等文章大家相較互補。
以獨能“趨道”而沾沾自喜的“儒者之學”,其中堅人物如陳襄、張載、二程等,從根本上否定“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的可能性,這一點與蘇洵、司馬光等正好相反。在他們看來,詩文“不當輕作”;古代聖賢的文章乃是“不得已”而爲之,“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而“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此外,他們還將所有“立言”以求其善者全部歸結爲“世人之私心”。*程頤《答朱長文書》,《二程集》卷九,頁600—601。在此種觀念的制約下,文章語言的琢磨錘煉功夫自然被置之度外。
從慶曆太學開始,“儒者之學”的先驅人物便選擇了一種口語化的義理解説方式,其解經話語被門人弟子記録整理下來,遂有“口義”、“義解”、“講義”、“語類”等系列道學之作。如胡瑗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張載《張子全書》有《語録》,陳襄《古靈集》存《易講義》和《禮記講義》,程顥、程頤則有《二程遺書》及《二程外書》傳世。這種創新體制的優點在於方音口語易於知曉,對那些“古文”修養遠不及歐、蘇、司馬光等博雅之士的國子監直講,以及築室授業於偏僻鄉野的道學家而言,選用這種自在方便、能幫助生徒準確理解其講授内容的語言,似乎也是一種時代的進步。但是,以口語解經的文字一旦通行天下,且成爲某種語言風尚,就很容易與“文章之學”形成對立,海内奉學之士不僅會誤解“隨物賦形”、“輸寫腑臟”的文學表達,同時也將在不知不覺間喪失了效法古聖前賢、錘煉語言、創作生動美文的機會。兹以程顥《遊鄠縣山詩序》之風景描寫爲例略示説明。其文曰:
鞭馬至山,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憇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晩,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遍詣諸境,一霎遂霽。明旦,入太平谷,憇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絶,殆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轉西閣,訪鳳池,觀雲頂、淩霄、羅漢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淩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横橋,復憇於重雲下院。出谷游太平宫故基而歸。*《二程集》卷三,頁473。
通篇文字簡略記述遊覽線路,缺乏對沿途美景的渲染和描述,乾癟枯寂,略無文采。特别像“僕復並山”、“因周視所定田”、“水聲清泠可愛”那樣語義不清的文字,實難掩其拙。類似的情形在陳襄《古靈集》中也有所體現,如《天台山習養瀑記》云:“予遊天台山,始至福聖觀觀瀑,尋而上觀三井,涉潭洞,歷桐柏觀,登瓊臺,下龍湫,顧其飛流壯猛,出高入下,不見所困,竟又不得其源焉。其畜之也不匱,其施之也不困,非善習險而固有本者歟。”*陳襄《天台山習養瀑記》,《全宋文》(50),頁224。似這般流水賬式的文字顯然缺乏姿態横生的靈性與美感。其如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押韻語録”條所云:“劉後村嘗爲吴恕齋作文集序云: 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録、講義之押韻者耳。”*《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07。嚴格説來,“儒者之學”制約文章作者,使其疏於語言積累,昧於形容描述,最終不能不導致“古文”創作的衰弱,這一點絶無可疑。
文學反映時代心聲。北宋時期卓有成就的“古文”家皆爲“文章之學”和“訓詁之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文章皆有爲而作,字裏行間總是透露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道實踐精神,*《周易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4下。充分彰顯着匡救時弊的人格自覺。
前人或以“文章之學即科舉之學”,*《書齋夜話》卷四,頁629上。實屬謬悖。蘇軾嘗曰:“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蘇軾文集》卷八《策總敍》,頁225。其《鳬繹先生詩集敍》亦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鳬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蘇軾文集》卷一《鳬繹先生詩集敍》,頁313。由此可知,“文章之學”與科舉辭章背道而馳,其核心要旨是“適於用”,要“言必中當世之過”。
黄震嘗曰:“歐公之文粹如金石,東坡之文浩如江河。”*《黄氏日抄》卷四二,頁203下。其所以“粹”且“浩”者,以自强故也。譬如,蘇軾文章長於論事,凡有論奏皆及“當世之過”。其熙寧中在密州作《蓋公堂記》,以諷王安石新法,“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四《東坡文章不可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48。東坡如此,蘇洵、蘇轍、王安石與曾鞏諸公又何嘗能外。朱熹嘗云:“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朱子語類》卷一三,頁3111。《御選唐宋文醇》卷五二在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後評論説:“論新法害民,兩蘇文字爲最矣。然軾之文於言國命人心處雖極纏綿沉摯,而剖晰事之利害則不若轍之確實明白也。”*《御選唐宋文醇》卷五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47册,頁867下。實爲確論。而從《新論》、熙寧二年(1069)《上皇帝書》、《上昭文富丞相書》、《東軒記》及《祭歐陽少師文》等文可以看出,蘇轍切於匡救時弊,其心與乃兄一般無二。王安石雖因變法而受到指責,但他公而忘私,以文章節義冠冕海内,就連司馬光都贊許有加。荆公病歿時,光曾以書簡叮囑呂公著説:“介甫文章節義,過人之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廢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毁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與呂晦叔簡二》,《全宋文》(56),頁76。來自敵黨的尊重,最能説明王安石坦蕩忠直的君子品格。客觀説來,在士大夫羣體以矯時救弊爲己任的北宋中期,三蘇、王、曾及司馬光等人通過奏疏表箋及其他各體文章,將憂時濟世的君子心聲表達得淋漓盡致。
比較而言,張載、二程等道學家及其學術傳人如楊時、游酢等,多將心思集中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内在修養,*《朱子語類》卷一四“或問明明德”條,頁264。其於天下家國之事雖亦有言,但終究不像蘇軾、司馬光諸公激昂慷慨,勇於承當。張載稱“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乃是將“虔敬”功夫放在首位;其所謂“爲天地立志,爲民生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張載集·語録上》,頁311;同書《語録中》,頁320。側重點只在立言樹德而已。程顥盛贊邵雍“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邵堯夫先生墓誌銘》,頁503。言語之間實際隱含着自我觀照的濃重意味。另據《二程外書》載:“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説‘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二,頁445。這種以“窮理盡性”爲主的思維定式,即便在疏奏文字中也很難有所改變。如程頤皇祐二年(1050)撰《上仁宗皇帝書》云:
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二程集》卷五《上仁宗皇帝書》,頁510—511。
此種情形,實際傳承着“慶曆之學”中令人厭惡的虚誕成分。正如歐陽修在《議學狀》中所説:“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虚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歐陽修全集》卷一一,頁1673。事實上,程頤的“心性”説教對於時政得失鮮有裨益。
必須承認,北宋中期勃然而興的伊洛關閩之學,雖然在“心性”探索方面卓有建樹,但相關學人不諳當世之務,難以表達時代心聲。在那種相對封閉的思想狀態下,欲使其“古文”創作豐滿酣暢如歐、蘇諸公,絶無可能。
文學因豐富多姿的心靈世界而精彩。北宋“古文”的藝術魅力主要來自“人情”與“自然”,前者是作家“虚明應物”的心靈體驗,*《朱子語類》卷一一六,頁2797。後者則彰顯着“天壤之内,山川草木魚蟲之類,皆是吾作樂事”的超逸與豁達。*《蘇軾文集》卷六《與子由弟》,頁1839。在北宋文壇,能夠通過鮮活生動的藝術形象,盡情展示“物我一體”的學人風采,使古文創作達到“天道與藝俱化”之境界者,*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校本,2008年,頁552。非三歐、蘇、王、曾及司馬光等人不可。
文章之動人者莫先乎情,若東坡之文“尤長於指陳世事,述敍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黄氏日抄》卷六二,頁551下。其文如《灩澦堆賦并敍》、《赤壁賦》、《衆妙堂記》、《醉白堂記》、《超然臺記》等,均能在揭示“自然之理”的同時,生動抒寫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的精神情懷,*《莊子集釋》卷一下《天下》,頁1098,1099。超逸灑脱,充分彰顯着心靈自由的奇妙快感。即便表疏奏章,也往往滿含深情,真切動人。如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薫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饈,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匕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蘇軾文集》卷三七,頁1050—1051。
此疏言辭激越,切中民隱,絶非高談“心性”矯揉造作者所能及。
蘇氏兄弟與王安石、司馬光等在思想上都是以儒爲本,以佛老爲用,故其情感世界總是呈現着“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的複雜情狀。*《蘇軾詩集》卷二五《寄吴德仁兼簡陳季常》,頁1341。他們雖歷盡人生波瀾,卻絶無頹喪萎靡之情。蘇轍撰《御風辭》,借列子行御風之事以抒豪情,謂“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蘇轍集》卷一八《御風辭》,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37,338。作者用得自天外的奇思妙想,渲染着超越萬物、與天地同生的曠達情懷。曾鞏文章“紆餘委曲,説盡事情”,*王構《修辭鑑衡》卷二引《童蒙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82册,頁281上。其《秃秃記》被譽爲“諸記之冠”。*《黄氏日抄》卷六三,頁558上。其文記高密孫齊溺於嬖寵,殺死親子事,末云:“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絶也久矣。如齊何議焉?”*《秃秃記》,《曾鞏集》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76。毫無疑問,該文所述乃世間永恒主題,而作者寄深情於敍述之中,故能感人至深。曾鞏嘗爲歐陽修所築豐樂亭作記曰:
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遊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醉心亭記》,《曾鞏集》卷一七,頁276。
其文雖無《醉翁亭記》之空靈超逸,然思賢之深情,“醒心”之微意,實不待智者而辨。
“道學之儒”的本質追求僅在於自我心靈的錘煉和提升。在他們看來,若能使個體精神與天地之道契合爲一,便可獲得精神愉悦,其如程顥所云:“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頁17。在此情形下“自然”與“人情”便只能悄然隱退。在當日道學家中,周敦頤和陳襄稍具文采,前者撰《愛蓮説》,頗爲世人所稱道,但也僅此而已。至於後者,李綱雖稱其“所爲文章,温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李綱《古靈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3册,頁499下。然遍覽其集,連篇累牘皆係仁義道德之語,昧於人情,疏離自然,幾無人間煙火味道。
北宋中後期“古文”創作盛衰變化的内在動因極爲複雜。除了上述創作理念和價值取向方面的懸殊差異,“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和“儒者之學”的不均衡發展也至關重要。經過多次朋黨之禍的戕害,與時政關係較爲密切、頗富個性魅力的“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已漸告衰殘;不僅蘇氏兄弟、曾鞏及王安石等“古文”聖手漸入佛老幻境,其後學門生也逐漸失去了“輸寫腑臟”、“言必中當世之過”的自信和勇氣;即便偶有所作,也没有了那種“虚明應物”的心靈體驗,再難展示“物我一體”的超逸情懷。相比之下,在各地學舍中潛會精研的“儒者之學”因爲遠離政治漩渦,仍能保持百舸爭流的發展態勢。只可惜,由於濂、洛、關、閩諸學派都從根本上否定文學的價值,因而道學探索越是深入,“古文”創作就越趨衰殘。南渡以後,文壇更趨蕭條。不僅像行雲流水般自然通達、妙趣横生的優美語言無處尋覓,忠直激切、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浩然之氣亦蕩然無存,就連那種徜徉於山水間的愜意,與禽鳥魚蟲往來對話的閑情都已消失殆盡。伴隨着“伊洛之學”尋求正統地位的排他性努力,二程的“講義”和朱熹的“語類”成了那個時代最時髦的文章,無數青年傾聽着道學大師的方音口語,如癡如醉。而那些美妙閑雅的北宋“古文”,似乎都成了遙遠的傳説。
概而言之,如果説慶曆前後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那麽慶曆儒學“新義”的形成與分解,及其關乎“古文”盛衰的學理邏輯,無疑是這個分界點上最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慶曆“新義”的形成,標誌着自中唐延續至宋初百年的儒學變革思潮最終取得了成功。范、歐諸公對儒道實踐精神的空前張揚,以及歐陽修、孫復、胡瑗、李覯、劉敞等人以發掘“義理”爲先導的經學探索,已經包含着“革新政令”和“創通經義”的雙重意涵,可謂“宋學”先聲。嘉祐以後,以“新義”探索爲契機,在超越與重建中漸告成熟的各種儒學新派相繼登場,他們不僅實現了由“我注六經”到“六經注我”的學術轉變,更將“古文”創作推進到一個空前繁榮的新階段。不過,隨着蜀學、新學乃至朔學的相繼衰落,原本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古文”創作,最終只能在“心性”探索的保守語境中走向衰落。需要説明的是,類似的討論必然會面臨思想史與文學史相互扭結的困擾,但其雙向拓展、交互發明的學術價值則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