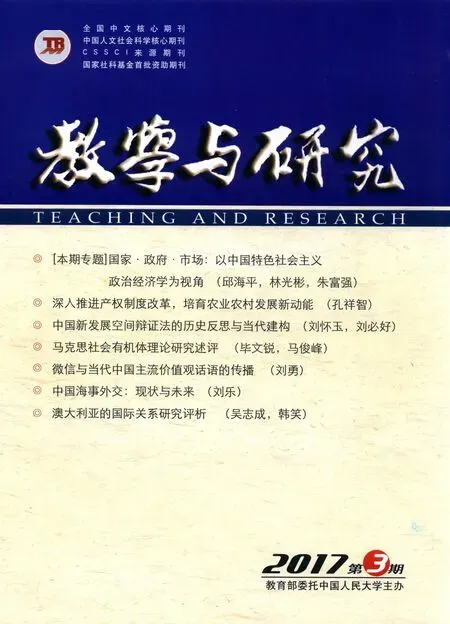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
孙清华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
孙清华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批判
在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有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粉饰剥削、愚弄民众、垄断精神资源以维护反动统治的真实目的,并对剥削阶级所实施的宗教灌输、哲学辩护、道德教化、舆论宣传等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批判思想对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创始人,他们不仅通过创立马克思主义而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基础,而且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些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还有一个方面被人们无意中忽视了,这就是他们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不论是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思想政治的灌输和教化。剥削阶级的这种活动实质上便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对人们进行精神奴役的本质,并且对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展开了批判。
一、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 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精湛的论述,构成了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石。与此同时,他们在关注现实问题、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对剥削阶级采用各种手段奴役人民群众的教化行为也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思想,是他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批判论述既确证了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历史存在的事实,侧面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为我们正确看待这种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术语,但他们关注到客观存在着的实践活动,多使用“宣传工作”、“鼓动”、“政治教育”、“宗教灌输”、“道德教育”等提法来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论述从侧面为我们了解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历史材料。他们揭露剥削阶级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精神奴役的事实,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伪善性,这些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我们在看待和研究历史上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时所要坚持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并未持片面否定的态度。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化相对进步的一面也予以肯定,如马克思曾肯定过英国相对的言论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很有限,“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着像在英国那样通行的广泛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对的”。[1](P575)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与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阐释互相补充。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批判论述从侧面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下属性: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工具属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让人民群众形成与一定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属,剥削阶级也有自己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不宜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起点局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而应该从观念中确认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也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领域。这种观念的树立有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及比较研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增强学科研究的历史感和学术性。第二,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根源还在于剥削阶级所旨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只要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那么,它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便具有这种粉饰剥削的伪善性。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的头脑,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根本性质上有鲜明的区别。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的过程,也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包括正面的积极举措,“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报刊为阵地宣传党的理论和主张、深入工人群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2](P117)同时,也包括他们对错误思想观点的犀利批判,这其中不仅涉及无产阶级内部的错误观点,还有统治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及教化。批判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突出特征。他们正是在对现实生活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揭露剥削阶级的伪善面目,从而引导人民群众与传统所有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使其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优越性。因此,这个揭露和批判的过程,也是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批判
揭露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实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批判中最首要的内容,也是他们多次强调、反复论及的要点。相关批判论述散见于多篇文献,贯穿于他们理论研究的一生。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剥削阶级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巩固、维护自己反动统治的根本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批判剥削阶级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粉饰和遮蔽剥削,为自己的压迫统治辩护。剥削阶级的辩护手段非常广泛,涉及宗教灌输、哲学辩护、道德教化、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对此,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中写道:“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3](P282-283)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辩护手段来维护统治,其根本在于它用以辩护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这种意识形态试图将生活的真相隐藏起来,极力向人们营造这样的假象,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统治阶级似乎在为所有社会成员说话。“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P552)
其次,批判剥削阶级宣扬愚民精神,让人们甘愿忍受其压迫统治。在剥削阶级看来,宗教灌输也是落实愚民精神的绝佳方式,可用来造就“木头般”的劳苦群众,使他们面对现实压迫,只会一味顺从、甘愿忍受痛苦,期待“来世”的幸福,进而习惯这种奴隶般的生存状态,甚至还为此感激戴德。例如,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以基督教的社会原则为例,揭露并批判了剥削阶级的这一意图,尤其批判了基督教社会原则宣扬剥削的必要性,颂扬愚民精神。“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弱、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5](P218)
最后,批判剥削阶级垄断精神资源,压制人民群众的反抗思想。剥削阶级主要利用舆论宣传手段垄断人们的精神资源。他们充分发挥官方或半官方言论来主导舆论的方向,并严格限制舆论自由,通过书报检查、查封、出版法等各种制度封禁革命思想,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将人民群众与革命思想隔离开,压制对自己统治不利的反抗思想和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分析革命前普鲁士的基本情况时,揭露了剥削阶级对精神资源的垄断,“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6](P362)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批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当剥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时,一定社会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虚假性和伪善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和批判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涉及广泛,多集中在宗教灌输、哲学辩护、道德教化、舆论宣传等方面。
(一)对宗教灌输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灌输的批判,最根本、首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宗教的本质特征,揭露了宗教的虚幻性、欺骗性。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4](P3)也就是说,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具有的虚幻的意识而已。它所编织的虚幻幸福能让人对其迷恋,因为“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4](P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阐释了宗教的本质,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7](P333)正因为宗教本质上所具有的这种虚幻性、颠倒性,它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所具有的欺骗性和维护剥削的反动功用便充分体现出来。马克思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4](P4)它从精神上麻痹饱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让他们甘于贫苦的生活,放弃革命的斗志。恩格斯认为“宗教的第一句就是谎话”,宗教具有强烈的伪善性,是剥削阶级一切谎言中最为突出的典例。“所有这些谎言和不道德现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神学是其他一切谎言和伪善的蓝本,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像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首创的那样,把神学这个名称扩大到当代一切假话和伪善。”[1](P518)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宗教灌输进行了批判。宗教因其伪善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受剥削阶级的青睐。无论这个剥削阶级的特征和目标如何、是否和宗教的内在精神相违背,宗教作为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分析道:“他(即资产阶级——笔者注)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8](P513)“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8](P520)
(二)对哲学辩护的批判
哲学是一种高层次、抽象性强、辐射面广的社会意识形式。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意识形态的根基,需要哲学上的辩护者。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批判了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辩护哲学。其中,恩格斯早期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较为典型。
1841年,恩格斯服兵役时常到柏林大学旁听讲座,时逢著名的哲学家谢林在该校讲学。这一系列讲座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性活动,封建的普鲁士政府为了遏制新兴的青年黑格尔派进步思想,打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邀谢林来“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的凶龙”。[9](P335)恩格斯敏锐捕捉到谢林宣扬的启示哲学和神秘主义中的封建反动意味,利用报刊文章和小册子(《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的方式展开了及时的批判,揭露谢林晚年思想为封建当局辩护的真面目。“想必他是要拿自己的体系来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因为他的从未完成的东西,在国王一声号令下,居然立即完成了”。[9](P342-343)恩格斯批判谢林沦为基督教哲学家,使自己的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谢林恢复了美好*恩格斯此处用“美好的”,实为褒词贬用,运用了讽喻批判的方式。为了躲避普鲁士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恩格斯采用这种写法,让书报检查官和出版商以为他是在正面评价谢林,实则为批判。的旧时代,当时理性为信仰所左右,世俗智慧像奴仆一样听命于神学,听命于上帝智慧,从而变为上帝智慧。”[9](P402)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件(1843年10月3日)中也曾强调:“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10](P69)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汲取其思想精华,也进行过犀利的批判。尤其对黑格尔晚年哲学中反动保守观点为封建普鲁士辩护的功用进行了揭露。黑格尔推崇等级森严、反动封建的普鲁士政府,运用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来证明普鲁士王国是“绝对理念”的最终体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倡导国家理性至上,贬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观点。揭露其颠倒精神理念与现实关系的唯心主义实质。从而动摇了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至上性辩护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对君主权力的推崇,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却“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臭架子”。揭露黑格尔作为封建专制的辩护士所具有的浓厚官僚味道,“所差的只是黑格尔还没有要求等级代表通过可敬的政府的考试。黑格尔在这点上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显然,黑格尔彻头彻尾地感染上了普鲁士官员们那种讨厌的妄自尊大,他们由于官僚的褊狭性而傲慢地蔑视‘人民的主观意见’的‘自信’。”[1](P155)
(三)对道德教化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上阐明了剥削阶级道德的阶级局限和社会功用,揭露其落后性与反动性。剥削阶级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实为其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为了起到社会整合、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得不披上“全部利益”的面纱。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剥削阶级道德的“伪善性”,批判它使不平等的剥削合情理化。“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11](P492)
马克思恩格斯又从微观上对统治阶级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譬如,剥削阶级惯用的施舍恩德(慈善道德)、将剥削“高尚化”的禁欲主义、对金钱的过度膜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粉饰不平等的等级特权思想等。慈善道德的背后所遮盖的是剥削阶级对劳苦大众堂而皇之的盘剥和压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谈到,“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来举办了。”[12](P247-248)“禁欲”是历代剥削阶级所力图向人民群众灌输的重要道德理念。因为社会资源大多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被剥削的群众处在资源相对缺乏的状态下。为了让受剥削的社会成员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处境,剥削阶级便从道德上宣扬“禁欲”的思想,将遏制欲望的“无奈”粉饰为道德上的“高尚”。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资本家提出的”。[13](P244)等级观念则是封建阶级用以维持其统治的常用思想武器,马克思曾用“抽屉”来讽喻批判不同的等级划分。“在实行单纯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即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里,人类简直是按抽屉来分类的,那里伟大圣者(即神圣的人类)的高贵的、彼此自由联系的肢体被割裂、隔绝和强行拆散”。[14](P248)
(四)对舆论宣传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以往统治阶级舆论宣传的专制性、欺骗性等本质特征,批判剥削阶级利用特权,垄断宣传渠道,限制言论自由,抨击官方或半官方报刊诋毁革命进步思想,掩盖事实矛盾,粉饰剥削统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批判剥削阶级的书报检查制度。以马克思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的批判最为典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1840—1861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他表面上顺应时代潮流,推行“开明自由”的政策,但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封建君主,实施思想专制。马克思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新颁布的书报检查法令。在这个书报检查法令中,威廉四世故意虚伪地责备检查机关过分地限制了写作,指示要执行1819年的书报检查令,但实际上1819年的法令恰恰是剥夺言论自由的法令。马克思逐一揭露了新法令在逻辑上的种种矛盾,批判了书报检查法令的伪善本质,“好的外表不应当用来掩饰任何坏的思想,但检查令本身就是建立在骗人的假象之上的”。[14](P123)“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14](P114)
2.批判剥削阶级的书报查封制度。《莱比锡总汇报》(1842年被查封)、《莱茵报》(1843年被查封)、《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份独立日报,同其他被直接查封的报纸相比,其遭遇的情况更为复杂。创刊后不久就遭到封建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1848年9月26日被封建当局以“戒严”为由勒令停刊,后于10月12日复刊。封建当局在以诉讼案的形式迫害该报未果之后,以迫害编辑部成员、抓捕发行人等极端方式终迫使该报于1849年5月停刊。(1849年被迫停刊)等先进报刊先后均被封建普鲁士当局查封。恩格斯在1852年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中曾提及,“大陆上最后残留的一些独立报刊也都被查封了”。[15](P256)所查封的主要理由莫过于报刊的政治言论有反对国家现存体制、危害社会秩序之嫌。实际上是封建当局限制新闻自由,害怕革命进步思想危害自己的剥削统治。对此,马克思指出,“《莱茵报》从来没有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相反,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14](P427)“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14](P430)
3.批判反动报刊对进步思想的诋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反动报刊诋毁进步报刊、丑化工人运动、污蔑革命人士。例如,力图获得封建当局器重的《科隆日报》,多次曲解、诋毁、攻击《莱茵报》。马克思戏称“我们至今尽管不把《科隆日报》看作是‘莱茵知识界报纸’,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莱茵情报广告报’而加以尊重”。[14](P206)又如,恩格斯揭露伦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刊将发动巴黎“六月革命”的工人污蔑为“盗贼”和“杀人犯”。当工人革命失败后,该报欢呼鼓舞,将这次起义定义为“绝大多数人”反对“一群野蛮的食人生番、强盗和杀人犯”的斗争。[15](P160)还如,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尚处于审理期时,伦敦两家有名的报刊《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却信口开河地把共产党人描写成游手好闲的无赖和骗子。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批判其是“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和喉舌”。[16](P549)
4.批判剥削阶级伪善的宣传策略。这些宣传策略违背了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如捕风捉影、以假乱真,散布虚假的舆论;小题大作、大题小作,依据剥削阶级利益的需要来控制舆论;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在宣传时采用前后相冲突的论据和立场观点;表里不一、伪善修饰,试图掩盖自身的阶级本质,标榜为“超阶级”的报刊;演唱双簧、沆瀣一气,剥削阶级通过不同的宣传工具互相配合,一唱一和或假装对立来影响舆论。还如,“沉默阴谋”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17](P197)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如此感叹资产阶级试图用沉默来抵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宣传和销售。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上,对教育方式的批判相对较少。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中,方式手段的工具性更突出,受阶级的影响更小。也就是说,一些剥削阶级采用的教育方式手段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和采纳。我们还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批判往往和对内容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下选取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批判相对集中的例子加以分析。
1.批判强行灌输宗教教义和训令的教育方式。剥削阶级十分注重对受压迫的青少年强行灌输宗教教义,从小播下宗教奴役的种子。恩格斯曾批评道,“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4](P424-425)剥削阶级还以宗教训令的方式要求人民群众忍受剥削,践履各种“宗教”义务(实际上是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义务)。如“另一个起源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法律规定:凡没有正当理由星期日不到教堂做礼拜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规定要到圣公会的教堂,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不承认非国教徒的小教堂),课以罚款或监禁。”[1](P574)
2.批判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灌输方式。非理性主义的传道方式,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它和宗教虔诚主义紧密相连。虔诚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的伍珀河谷一带非常盛行。非理性主义传道方式为虔诚主义者所青睐,它主要就是采用夸张、神秘、感性的宣传方式,借助各种表达技巧,通过营造特殊神秘的氛围,让听众受到感觉冲击,进而接受那些充满欺骗性的内容。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对此有过详细的阐述,并用生动讽刺的语言进行批判。“他(克鲁马赫尔牧师——笔者注)的朗诵有些地方十分动人,他那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手势往往也很得当,但有时总使人觉得过于做作和乏味。朗诵时,他在讲台上来回乱窜,身子四下摇晃,拳头击着讲台,脚像战马的蹄子一样跺着地板,而且还拼命地嘶叫,震得玻璃直响,吓得路上行人张口结舌。”[9](P49-50)
3.批判利用庸俗的儿童读物进行道德教化的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注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欧洲颇为流行的一本儿童读物——罗霍的《儿童之友》。这本书“到19世纪初已经再版了30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分发这本书,并且指定国民学校普遍地把它作为读本。”[7](P192)这样一本流传甚广、影响面较大的儿童读物,却蕴含着剥削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教化民众安分守己的反动用意。它是剥削阶级利用庸俗的儿童读物进行道德教化的写照。恩格斯曾写道,“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7](P192)
4.批判用法律训令取代道德教化的粗暴方式。“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14](P119)道德教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行为上的依从,而是通过增强道德认知、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在道德规范内化的基础上养成道德精神和品质,并外化为行为。但剥削阶级吝于对工人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利用法律和训令将道德简单化为行为上的依从,用外在的强迫和规范代替道德品质的养成。恩格斯曾批判道:“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摒弃和忽视。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4](P428)马克思在《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出租马车——爱尔兰——俄国问题》一文中讽刺剥削阶级为了自身利益,用法令强迫马车夫们做一个所谓的“高尚者”,宣扬充满剥削意味的“6便士道德”。“据说,这些马车夫对无人保护的女士们和大腹便便的实业家们的勒索必须加以制止,车费应该从每英里1先令降低到6便士。现在6便士道德感已经风靡一时……看来这是要用强制的办法把马车夫变成不列颠高尚品德的标本。”[18](P254-255)
五、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批判的当代启示
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不同,当前是网络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发生了新变化,无产阶级也在部分国家上升为统治阶级。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探索多年。尽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批判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但我们要把握住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批判的精髓,不宜以断章取义、简单对应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具有特定的话语环境和历史背景,我们在探讨启示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
首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它成为维护剥削、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相比之下,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变质不堕落。或许这一启示看起来是理所当然、无须强调的,但放置于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却是非常有必要重申的。从国际上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经济合作,经济利益上的共识掩盖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冲突。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关注重点多放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上,对于阶级问题、意识形态话题的兴趣相对较小,有些人甚至持消极的回避态度。与这种国际国内的环境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潜藏着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为了尽可能扩大共识或对话交流,便淡化阶级性和政治性,回避立场问题,来增强学术性和专业性。这既体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虽然这并不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主流状况,但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
其次,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发挥育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剥削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教化进行精神奴役、维护剥削统治的根本目的,并揭露了一系列反动性功用——粉饰剥削、迷惑群众、培养奴性、遏制革命思想。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后所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应截然不同。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提高人的素质,促使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19](P62)这一目的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同历代剥削阶级具有本质区别。不同于剥削阶级借意识形态教化来维护统治秩序,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育人方面的价值,应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通过育人功能的积极发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摒弃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糟粕,借鉴利用积极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虽然彻底,但并不是片面否定的,也肯定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对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批判,也恰恰说明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实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实效性上具有优势。否则,马克思恩格斯无须对此注入大量的精力。这都说明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精华可以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和利用。当然,这种借鉴必须是辩证的,对于糟粕,尤其是阶级剥削的成分应坚决抛弃。例如,剥削阶级重视宗教祷告的教化价值,强调潜移默化中感染人们,净化心灵,培养德性。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利用,发展宗教教育,更不能宣扬蒙昧主义,但是这种渗透性的教育原则合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切合受教育者身心需求,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利用仪式、物质环境、社会实践等载体,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最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思维,抵制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体现着他们的批判精神、思维方法和方式策略,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前正处于各种思潮混杂、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针对让群众误解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等,通过恰当的批判,让受教育者认清真面目,学会取舍。完成这一任务急需学习经典作家的批判思维和批判方法:其一,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时的理性态度和揭露的深度。纵使他们言辞犀利,感情强烈,但均是建立在理论分析之上的指责,绝非似是而非或者纯粹情感上的反对。教育者自身必须对错误的思潮有深入清晰的理解,包括它的内涵、现象、起因、危害等等。其二,批判错误思潮时应考虑到建设性,不能让受教育者手足无措。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批判,并不仅仅只是“批”它错误的地方,更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阐明了用以克服错误观点的正确思想,“破”完之后还重视“立”。其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错误思潮的敏锐度。教育者要对各种思潮保持敏感的“嗅觉”,提高洞察力,及时进行批判。1875年3月,马克思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哥达纲领草案》时,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进而对拉萨尔主义进行清算。其四,学习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批判策略。如他们常用的“归谬”讽喻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克思在《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中利用威廉四世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来批判当局查封《莱茵报》的非法性。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李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9] 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李文苓]
On Criticism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Past Ruling Class
Sun Qinghu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Marx; Enge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riticism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which is the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ast. Marx and Engels have revealed the fact that the exploiting class u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whitewash exploitation, to fool the people, to monopolize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so as to safeguard their reactionary rule. Marx and Engels also deeply criticized the religious indoctrination, the philosophical defense, the moral education, the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critical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品牌计划“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文献与基本问题研究”(项目号:10XNI009)的阶段性成果。
孙清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