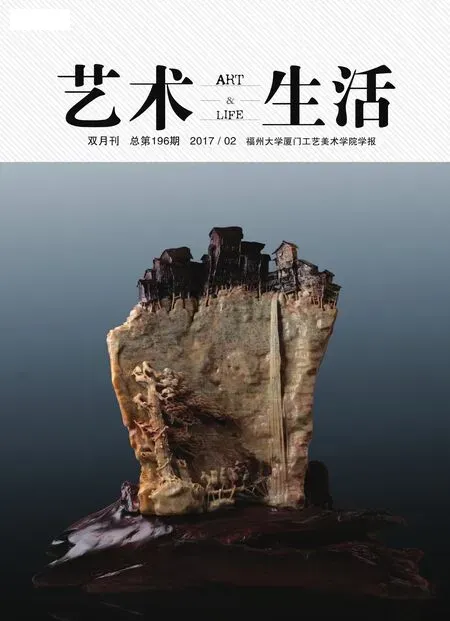“笔底家山”
——20世纪艺术家的精神家园
潘丰泉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00)
这些年来,一些围绕艺术创作或艺术现象的所谓评论文章,尤其对于某个艺术家风格的形成乃至于创作上取得的各种成就,在作深入浅出的剖析时,都会将其现象或个体经验,归之于艺术家长期对哲学或宗教的修练或感悟的结果。比如山水画家创作的每一件作品的背后,是其对传统哲学精神中的某一点“天人合一”的认识;至于另一些从事抽象绘画表现的现代艺术家们,则与宗教意识扯上某种关系。于是从这些现象中,可归纳的不外乎是由哲学或宗教构成其艺术风格所在,并且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似乎是在这些玄而又玄、故弄玄虚的作用下,才可以推动艺术家创作的行程脚步,至少漠视了那些实实在在存在于艺术家个人的内心情感所在。
故,对于艺术成就风格的各种评论,往往是从当下的品评风尚或标准去设置的。而对于创作风格的真实性存在,那些源自于艺术家“笔底家山”而成就的一幅幅画面,常常是避实就虚或视而不见,被有意淡化。
如果说齐白石进入北平后给艺术界最初的印象,就是在他55岁之前画的那些作品,倘若按照旧有的文人画标准显然是不入流的。当时在京城艺术界较有权威的陈师曾先生曾给了他诸多建议,要齐白石放弃以前的东西改学文人画。虽然,他虚心接受这一切,并且掌握了与文人画艺术密切相关的技法要领,但齐白石老人就不全然去重复那些日复一日为后人所诟病的老一套题材。在日后创作的大量写意花鸟画作品上,他拒绝了对于一般传统题材的简单重复。比如,不再直接以“梅兰竹菊”作为卖画送人或者像多数传统型画家一样用四条幅形式表现,致使画得最多或为齐白石个人嗜好所故,如梅,如兰菊也是赋予一种新的笔墨形象符号。就像被学术界推崇备至的“红花墨叶”这一大胆探索,其意义就在于这样的对比结构一下子与传统长期不变的表现样式完全不同。齐白石摒弃了以往墨色过于淡灰的调子,而是引入明快单纯响亮的黑白对比关系,这正好与一些民间艺术处理特点有某种相似,即鲜明悦目的视觉感,这可能是人们更喜欢齐白石花鸟画艺术的原因之一。
虽然,一生率性的齐白石老人创作了无数这样的花鸟画题材表现,有对于市场客观需求而被重复不已的老一套题材,确实是因生活所迫而无可奈何。不过,他仍巧妙地利用了早年在乡间生活刻过的雕花和干过的木匠活,包括在他眼里母亲和乡亲们心灵手巧地剪出的各种窗花等好看的画面图案,这都是出自于乡野的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虽显得“粗枝大叶”甚或简陋,却潜移默化地形对他一生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刻骨铭心的引领作用。
齐白石画过无数让百姓喜欢的题材,它们多是在传统花鸟画题材里没有的,比如蟋蟀、蝌蚪、知了和蜻蜓等草虫,所画的水牛憨态可掬、小老鼠再不那么讨人厌等等。至于那些栖息于树上的八哥、喜鹊这些属于人们印象中较为高雅的花鸟画题材,一下子拓宽了一千多年来传统绘画题材从没有过的新天地。甚至比起曾经让他顶礼膜拜的青藤、八大和缶翁的写意艺术,他仍不失为一位活跃在20世纪现代写意花鸟画领域处处标新立异的开拓者。更出乎意料的是,形成这些画面时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画境一派轻松活泼,情趣表现鲜活灵动,大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情状。白石老人把那种爱玩耍调皮捣蛋的人性一面,借手中一把毛笔画出了童真世界的可爱之处,满画面就是在回忆他小时候乡间的生活,对于一草一木的深情致美,率真生动一点一滴地写将下来,不再重复以画“梅兰竹菊”的手法去构造这些新的题材,“老瓶装新酒”式去求得文人画的那种迂腐气,皆顺其自然创造出一种前人所不曾有的,被后人奉为艺术圭臬的花鸟画天地。平淡天真的艺术所为使得其写意花鸟画艺术,相对于传统文人画有着非常了不起和引人注目的开拓性成就。
人民艺术家齐白石老人那一幅幅来自于“笔底家山”的画面,是构成其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精神家园之所在,那么与当年较早的那一批曾游学于欧洲,受之于西洋文化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他们的绘画经历与齐白石或许有所不同。如果说齐老先生70岁后在艺术上的吐故纳新,完全是从一种更符合中国百姓文化生活的审美图式出发,钟情于“俯察品类之盛”所映射出一种别致的唯美境界,那么另一位大家赵无极则善于用抽象绘画艺术语言,构筑起一幅幅别样精彩的画面。虽然无清晰可辨的具体形象,却依稀可见有来自于他本人对家国、故土一草一木款款深情的思念。他之所以游刃有余地借助现代艺术形式之一的抽象绘画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而且艺术感觉与当时的西方抽象画家的价值取向多少有所不同,显得别出心裁,原因就在于“人在他乡”的一种不忘家国、故土的内心情感呈现,化为艺术创造的原动力。这使得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寻觅到画里画外那种富有东方情调的精神家园,以及飞越千山万水那般对家国、故土的艺术感怀,在这些抽象画面里,赵无极先生时而温情脉脉时而如山洪爆发地向观众展现了不同的抽象画境,画面间流动着的虽然是满眼一派的萧瑟秋风,但却是一种极目太空宇宙的精神构造,“仰观宇宙之大”。赵无极先生通过其现代抽象画图式的大胆创新,最终能有一个大的形式突破,实现了运用抽象画这一新的现代表现手法,也可以创造出一种内涵深刻、境界高超、十分理想化的艺术图式。
另一位艺术家张大千先生,时下的网络媒体正连篇累牍登载其早期一些以精细笔法模仿传统不同时期的名家绘画,其实在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件巨幅创作《长江万里图》。他自中年就离开家国、故土,也曾筑园于巴西、印度,再到台湾,因一些原因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于是,晚年便借创作巨幅画面的动力,表达其思念家国、故土的一段挥之不去的内心情感。在这一幅气势万里的画面上,人们看到艺术家以其雄健苍劲的笔力泼洒出变化丰富的墨色,描画了家国、故土那种气象万千的壮美风貌。虽是几十米长的横幅画面,但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体百里之迥”的艺术容量,将家国、故土那一段段的大好河山,以思接千载的艺术情怀展现,无不勾起海外游子一种“故国神游”的情思。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艺术家能够突破以往的表现模式,无论是借鉴他人还是自身形成的手法?那就是画家“笔底家山”的艺术情怀,才最终促使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大逆转”和语言上的新突破。
为什么“家国、故土”这一千载不变的题材,根本不需用华丽的语句去展示它们的价值所在?那是因为在百姓心目中,家国、故土,永远是一个关乎生命意义的人文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一直强调叶落归根,无论人生道路何其漫长,事业何等辉煌,但家国、故土永远是每个人无法忘怀的精神之处。艺术家与常人一样,永远是这一份情感的守护人。无论是描绘故土还是他乡的一幅幅画作,都有一份藏于内心永动不已的真实情感——对家国、故土的深情眷念。正是对这一份情感的认同和坚持,才有了文化艺术长廊中那琳琅满目的一幅幅画面——流淌着艺术家对家国、故土深情表现的传世佳作。这一追求和效果同样出现在傅抱石、潘天寿和李可染等一批成名于20世纪的艺术家作品里。
如果说借助这种意识企图去诠释艺术行为中的某些玄念神秘感等,还有商榷之处,而那些带有血腥恐怖气息成为污染视觉心灵的行为艺术,它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其艺术价值又何在?所以,相对于那些被评论得玄而又玄或故弄玄虚的关乎现代艺术现象话题里,只有一段来自于对家国、对故土挥之不去的艺术情感,才能真真实实撑起艺术家的一片天地,夯实艺术创作根基。或许某些所谓高深莫测的哲学理论和宗教意识,可以让一些艺术家在不知不觉中触摸到画以外的东西,但对于一个以真情实感拓展艺术天地的艺术家来说,再没有像家国、故土这一永恒的主题,能够真真实实植入于他们的精神领域,去丰富充实人们的情感世界。
在讨论20世纪中国出现的各种艺术现象的时候,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笔底家山”这一深植于艺术家创作家园的表现主题呢?因为20世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人们告别长期闭关锁国走向开放的现代进程中,包括文化领域中的多元艺术观点催生不同的价值观时,总有光怪陆离或莫衷一是,总会出现一些言不由衷的形式语言,画家在面对纷纷攘攘的艺术现象极易迷失立场。所以,只有一如既往坚持“笔底家山”这一创作主题,才可以让艺术家自由“任性”地创作,切入现实生活主题。所以,无论涉及到艺术表现的哪一方面,“笔底家山”永远是艺术家的精神家园,永远是关乎时代社会的表现主旨和核心。
参考文献:
[1]冯湘一.绘画审美特性试论[J].美术,1981(07).
[2]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3]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4]张大千画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5]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 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绘画发展的渐进型特征研究
- 彝族(撒尼人)刺绣工艺研究文献综述
- 权力运作的场域
——世界博览会的政治学 - 《艺术生活》稿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