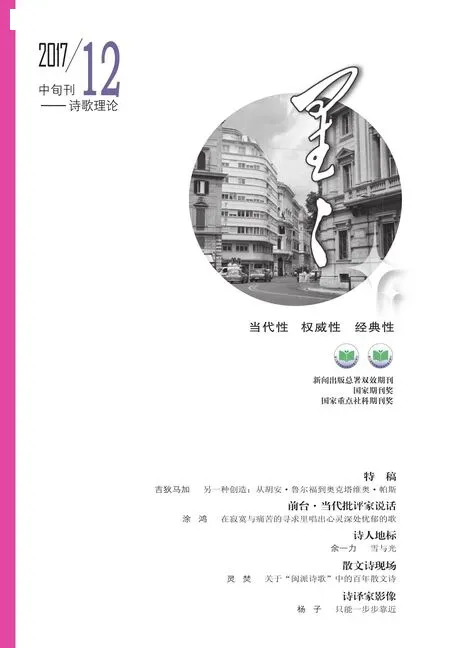只能一步步靠近
——我的诗歌翻译之路
杨 子
杨 子
1982年4月和6月,在南开大学,大二第二学期,我试着翻译了十七首叶芝的诗歌,其中一首《白色鸟》发在我和几位同学的油印诗集《六弦琴》里。
亲爱的,愿我们是白色的鸟儿
在海的泡沫上!
愿我们是流星的火焰的轮子,在它
熄灭逃避的时光;
薄暮蓝色星星的火焰,低低
悬在天边,
已经唤醒我们的心灵,我爱,悲哀
不会死亡。
原版叶芝诗集是文科系高级英语班(我和中文系八零级另外两位同学是该班学员)薛琛老师帮我从图书馆借的,具体哪个版本,我当时没记下来。比照裘小龙的汉译,最后两句应该是译错了,后来也没修订,这里暂且改为——
已经在我们心中唤起,我爱,永不
消亡的悲伤。
还有一首《死之梦》:
我梦见那人在一个奇僻之地死去,
在陌生土地那边。
他们将棺盖钉上,遮住她的面庞,
那块土地上的农民
一边惊诧,一边把她安顿进黄土,
在覆盖她的土堆上
两块木板钉成的十字架竖起来,
四周种上青青松柏。
我刻下这些文字,
便扔下她,让她与高空冷淡的星星在一起:
她比得到你的初爱时更美了,
如今长眠在地下。
可能是1990年,我又翻译了叶芝的两首诗,一首是《纪念艾娃·高·布思和贡·马凯维奇》,另一首是《本·布尔本山下》。这些搁置多年未作修订的试译,现在读来当然稚嫩,却有一种令我惊诧的神奇的美——
夜的光芒,丽萨黛尔,
巨大的窗户朝向南方,
两个女孩身穿丝绸和服,两个都很美,其中一个像瞪羚。
而咆哮的秋从夏天的花冠上
砍下鲜花;
大的已濒临死亡……
……
我不知小的梦见什么——
没准是模糊的乌托邦……
——《纪念艾娃·高·布思和贡·马凯维奇》
从大二到大四,除叶芝外,陆续试译过《雅歌》、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丁尼生、罗塞蒂兄妹、史文朋、维切尔·林赛(《中国夜莺》)和麦克里希。这个路径有点怪,有点摇摆——迷恋济慈,却先翻译了现代主义的叶芝,又从叶芝回到浪漫主义(也译了几首年代更久远的托马斯·纳什和托马斯·查特顿),再离开浪漫主义,一头扎进现代主义。
翻译《中国夜莺》时,得到我的学年论文导师、中文系教授张镜潭先生指点。《中国夜莺》发表在中文系学生自办刊物《南开园》上——这是整首《中国夜莺》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进入中文(赵毅衡的节译收在他那部影响极大的《美国现代诗选》里,1985年我才读到)。同一期上发表的还有我翻译的艾米·洛威尔的诗。
大学期间,我写过三篇有关济慈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学年论文,可见当时济慈对我影响之大。但济慈的诗我译得最少,三篇文章都是依据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济慈诗选》写的,这大约是八十年代中文系本科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娴熟地阅读原文的能力。
有时我会逃课去图书馆看本科生不得外借的原版英文诗集,将济慈诗歌抄在笔记本上。印象很深的,是我借阅的那些原版诗集的借书登记卡上,仅有的借阅者的名字总是查良铮,他的名字后边一片空白。
张镜潭先生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曾去美国西雅图留学,建国后在南开外文系执教,“文革”中因外文系人事震动转到中文系,是和查良铮、巫宁坤等一同离开外文系的六位教师之一。张先生对我极友善,爱跟我唠嗑,爱对他的胖孙子说,要向杨叔叔学习,可能觉得我爱读书吧,其实我没那么上进,我的英文在中文系还可以蒙人,其实很一般。有时他会跟我提起七九级一位喜欢外国文学的姓梁的师兄,或许是觉得我跟他有点像。这位永远笑眯眯的先生,在人群里就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给我们教公共英语的倪庆饩先生也在。倪先生告辞的时候向张先生鞠躬,保持鞠躬的姿势,倒退着出门。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一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中年教师对一位老先生执弟子礼的情形。
我记得,张先生提到他和柳无忌先生的交往,给我送过一部《柳亚子诗选》。抗战期间,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南开中学迁往重庆。在重庆像在天津一样,张先生是柳无忌的搭档,他们一起编了几部英文课本。他给我看过他翻译的柯勒律治那首未完成的杰作《忽必烈汗》,还手抄了一份送给我。可能因为他译得少,他的译诗没引起我的重视。2017年我从孔网订购了柳无忌和张先生合编的那本《浪漫主义诗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这才知道我这位老师非常厉害!才恍然醒悟,原来南开大学是英国诗歌翻译的重镇之一——朱维之翻译《失乐园》,查良铮翻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再往后就是柳无忌和张镜潭的这项成就——应该是在1980年代后期,柳无忌召集南开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几位教师——多半是他早年在南开任外文系主任时的同事、学生或后来加盟南开的教师,分头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曹鸿昭译华兹华斯,张镜潭和黄燕生译柯立奇(柯勒律治),柳无忌译拜伦,倪庆饩和周永启译雪莱和济慈。巫宁坤是迪兰·托马斯诗歌的著名译者,但不知那几首是不是他在南开期间所译。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译者,在查良铮之外,还有几位显赫人物,大多未能像查先生一样产生持久影响。柳无忌召集的这支小分队实际上非常重要。令人吃惊的是,这几位民国人的译笔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窒碍,给人一种通透的解放的感觉,读来非常愉悦。可惜最后只出了这一部译诗集,未能深入下去,扩大战果。
书中所收张镜潭译诗不多,但柯勒律治大名鼎鼎的《忽必烈汗》和《老水手之歌》(《古舟子咏》),就出自他的译笔!
水,水,到处是水,
所有的木板都萎缩,
水,水,到处是水,
但是一滴也不能喝。
连海都霉烂了:基督啊!
事情竟糟到如此地步!
只看见,在混浊的海水里,
爬行着沾满泥浆的动物。
前后左右,不停地旋转,
死亡之火狂舞在夜间,
海水燃烧如女巫之油,
绿色,白色,又一片蓝。
……
度过了一些难熬的日子。
人人嗓子冒烟,眼神发死。
难熬的日子!难熬的日子啊!
人人熬得眼神发死!
……
——《老水手之歌》
细读张先生的翻译,我惊喜地发现,这就是我热爱的译文,这就是我渴望的境界,他是柯勒律治最好的中文译者之一!这让我心中涌起极大的欢喜,也让我感觉到莫名的悲伤和愧悔——大学毕业后很多年,我一直隐隐约约念叨着,我没福气成为查良铮的学生,那无疑是一种做作的妄念。现在我懊悔的是,我本可以更多地向张先生求教,即便在我毕业以后,那样多少可以免除日后漫长的停顿和难堪的跛行,但我没有珍惜已有的福气。
好像是在大四那年(1983/1984),读到林以亮编选的《美国诗选》,应该是港版,因为三联书店的引进版出版于1989年。毫无疑问,这是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译诗集——爱伦·坡、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希、康拉德·艾肯等我喜爱的美国现代诗人,都是从这部诗选中第一次读到。我一下子被这几位诗人迷住了。我给写诗的朋友朗读麦克里希的《不朽的秋》,给艾肯的《空中花园》写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文章,而坡的《给海伦》、《安娜贝尔丽》、《尤娜路姆》、《大鸦》荒凉海岸钟声般的音调,从此在我心间回荡,只要提起他的名字,这声音就会立即在我心中响起。
麦克里希和坡都是余光中翻译的,艾肯的《空中花园》是林以亮翻译的。《空中花园》第一句——“而在那悬在空中的花园里,从午夜/到一点钟正在下着雨”,读来非常新鲜,这可能是中文读者第一次领教一首诗奇崛地以“而”字当头,可以说是许多专家提到的翻译可以大大拓展母语的一个小小实例吧。
这部《美国诗选》,加上袁可嘉主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以及不久以后赵毅衡翻译的那部《美国现代诗选》,强有力地推动我,让我暂别浪漫主义(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一头扎进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阅读和试译——先译美国诗人和英国诗人,多年后又从英文转译了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奥地利诗人策兰和几个东欧国家的诗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三十多年,我的诗歌翻译有过长时间的间歇,却从未放弃,积攒了大量初译,但因为出版艰难,大部分至今仍未修订。
九十年代开始,我的译诗先是发表在我和几位朋友编辑的《大鸟》、黄灿然主持的《声音》等同仁刊物上,接着又陆陆续续发表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诗潮》、《诗江南》、《诗建设》、《文景》等杂志上。这是一份跨度很大的名单:美国印第安诗人、塔特·休斯、马克·斯特兰德、盖瑞·斯奈德、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费尔南多·佩索阿、查尔斯·西密克、唐纳德·贾斯蒂斯、西奥多·罗特克……
2002年,楚尘的“世界诗歌译丛”项目启动,以“诗人译诗”为号召,我有幸一下子与他签了六部译诗集的合同。随后就是在短时间内同时增译、修订其中的四部——曼德尔施塔姆、佩索阿、罗特克和斯奈德。我当然不能为最后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和《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中的很多遗憾找任何借口,但这的确是一次欢喜和痛苦参半的体验——两部译诗集受到大量读者错爱,但那些白纸黑字的问题终究挥之不去。现在我宁愿读者忘掉它们——我相信修订本会给他们更多的喜悦。
有了这两本书的教训,后来出版《盖瑞·斯奈德诗选》时我慎重多了,无论是对原作的理解还是对文本的推敲,我都尽了努力。显然,这一部比前两部好得多,尤其是解决了前两部一些作品中存在的原文理解、语感乃至节奏的大问题。
2017年,我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的修订,解决了初版中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翻译从来都是无底洞,一不留神,我们不是掉进这个洞里,就是卡在那条缝里,大部分译者或许只能做到大体无碍,而在挑剔的行家眼中,永远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这的确是一个必须战战兢兢的工作,因为陷阱经常就在看上去一马平川尽可放胆驰骋的地方,那些我们以为初学者都懂的字眼,经常会出其不意地捉弄我们。很多时候,即便精通外语,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陌生民族及其文化。早年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黑太阳》时,temple一词我译成“教堂”。这次修订,我留意到temple在这首诗里译成“教堂”是有问题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犹太人只有会堂,没有教堂,这里的temple显然应该译为“会堂”。我从书架上找出美国学者撒母耳·S.科亨的《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徐新、张利伟等译,2009),在有关宗教践行方法那一章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解决了temple的问题,也加深了对这首诗的理解:
作为一个社区中心和学校的犹太会堂,首先是一个礼拜场所,犹太会堂因此成为犹太宗教生活的源泉……作为一个精神中心和聚集场所,每个犹太会堂都把它周围的单个犹太人统一到有着共同理想和目标的群体中,进而把他们与所有以色列人联系起来。在它的礼拜活动中,个人把自己与自己的民族联系在一起……
中国近代以来翻译实践的最高律令“信达雅”,如今已很难完全令人信服。说到诗歌翻译,我更想将它比作一种演奏——高超的翻译应该在严守本意的同时,完美地呈现原作的音调、色泽、明暗、轻重、姿态、表情等等,原作里的“新年第一天”不能发明为“大年初一”,原作里的哥特式教堂不应偷换为大雄宝殿,原作里的基督教牧师不可像中国佛教僧侣。这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对位法,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衔接与进入,尽管我们不得不牺牲那些精微的不可译的部分,但我们首先不可牺牲的是原作的整体音调和精神,色泽和气息。
音乐性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核心特质,无论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古希腊的史诗或悲剧,还是中国的诗经,都将音乐性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近代诗人马拉美更将诗歌的音乐性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墨西哥诗人帕斯说,“词语经过我们的耳朵出现在我们面前,倾听一首诗是用我们的耳朵看这首诗”。俄国小说家普宁同样深谙“声音”之重要,“我命中注定是要写诗的,屠格涅夫也首先是诗人。对他来说,一篇小说中最主要的是声音,其余都是次要的。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去寻找声音。一旦找到了声音,其余的也就水到渠成了”。普宁所说的“声音”,就是音调,也可以说是飞翔在字面和字面意义上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的构成元素中既有纯粹的声音和节奏,亦有抒情和叙事营造的氛围,正是它们的完美合成构造了诗歌的音乐织体。这样的原作对于译者提出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必须是高超的演绎和演奏,而不是一个字眼一个字眼地翻译,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和一个韵脚一个韵脚地搬运,因为绝不可能对诗歌做说明书式的翻译。
我们的诗歌翻译之所以会出现令人蹙眉的变形变调和变味,原因不一:或者因为译者在中文上的无能,只好做僵硬的直译;或者因为译者太能,一味炫技,从原意中漫漶出来甚至远离原意;或者因为译者误以为诗人合法地用所谓诗歌的语言说话,于是笔下徒见辞藻,原作惨遭侵蚀。很多时候,优秀的散文译者偶尔翻译诗歌,也比他们做得好得多,他们只是朴素地翻译,不增不减,谨守克制美德,绝不虚张声势,朱景冬翻译帕斯诗歌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一位外国诗人,只要我们手头有多个译本,往往刹那便可判别优劣。前几天,我在一天时间里集中读了三位翻译家翻译的波德莱尔,这里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神奇的是,我恰好先读到译得较弱的那位,觉得离波德莱尔有点远。接着读到译得较好的那位,感觉接近波德莱尔了。直到我读到第三位的翻译,才体验到这大约是真正的波德莱尔——汉语里转换得接近圆满的波德莱尔。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实验性阅读,或许以后应该经常做这种实验。当然要付出代价,因为诗人只应读最好的翻译,只应读质地纯正的作品。
一个人翻译散文尚可,翻译诗歌却无能到令人震惊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一个人一辈子专译诗歌,也可以一败涂地。我们有过太多这样的阅读经验,翻译过来的文字可能意思都对,但原作的气息、音调、色泽、质地,一应俱无,原作的神采荡然无存——其实不用读完,读到第一句,第一节,就可以基本判定我们遇到的是怎样的翻译——只能说这是完全失败的演奏,这是在杰作面前的残疾。最晦气的是我们珍爱的诗人被惨不忍睹的翻译蹂躏。我们总是心有不甘,总会在把它们扔到一边很久以后又拿起来,试图在里边找到珍宝,却永远不能如愿。这样的翻译只能败兴,不可能给人滋养。布罗茨基的某个译本是这样,艾吕雅的某个译本也是这样。
译诗之难,之挣扎,只有翻译诗歌的人知道。林以亮在《美国诗选》序言里提到的这部优秀译诗集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诗歌翻译中永远有难以完成的任务,至少是这一次难以完成:翻译这部诗集的时候,余光中的任务之一是狄金森(狄瑾荪),最后交稿的十三首中,五首换了别的作品,与原定篇目不同,“只好重新申请翻译的版权”;罗威尔(艾米·洛威尔)最成功的那首《格局》多次修订,无法满意,只能割爱;林本人承担的四首艾略特,他觉得不理想,最后放弃。
译诗之难,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后的成品给读者的愉悦远远大于译者?译者很难一步到位,如果一首诗经过多次修订,那么他在定稿前一遍遍读到的自己较逊色的译文,对他难道不是一种折磨吗?翻译马克·斯特兰德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那种顺畅和速度给人的快感,但是一遍遍修订曼德尔施塔姆,一次次发现之前的错误和不妥,一次次在自以为解决了以后又发现新问题,的确令人痛苦。但即便如此折磨,在一个个问题解决之后,仍有大快乐。唯有一个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找到一点演奏的感觉——这是他的声音,来自俄国大地和天空的声音,这是他的音调,曼德尔施塔姆,一个无法归类的独创性诗人的音调——不是别雷,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不是阿赫玛托娃,也不是赫列勃尼科夫。要在中文中实现这一目标,太难了!或许永远不可抵达,只能一步步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