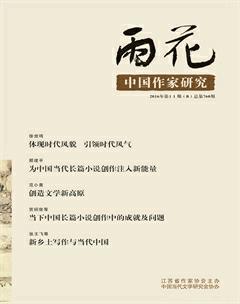悲悯与沧桑
王雪莹
作为中国新世纪的一名海外移民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严歌苓的小说善于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人物生命史的叙述,表现出时代的变幻莫测、人性的复杂多变、命运的反复无常,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悲剧效果,寄托自己深切的同情。读严歌苓的小说,不难感觉到她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对回忆国内生活的描述,还是对海外移民生活场景的描绘,或者是从一定的高度对人性、命运的思考,都有一种隐藏于其间的情绪,这种情绪可归结为悲悯,即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悲悯情怀。悲悯情怀是一种创作姿态,是作家对所表达的种种人生现象最深切的人性关怀,是对于人性弱点的一种宽容宽恕的态度。严歌苓在对人生、人性、命运的展示中赋予了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可是在这种沧桑与悲悯里却又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也没有厚道质朴的好人,只有人性的复杂。这悲悯产生于一种巨大的荒凉感:没有敌人,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天地亘古无言,人就被突然地抛进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境里。这或许也是她的小说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一、个人生命的悲情体验
严歌苓出身在几代书香之家,从小徜徉在文学和艺术的海洋里,这种知识分子家庭的氛围熏陶培养了她对人生和社会的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力。因为她那位才华横溢的祖父在抗战前的自杀,所以她说“我们这个家庭出来的人都带有某种没落敏感的天性”①。然而正是这份天性的没落与敏感,使她具备了一种文学家的气质。另一方面,严歌苓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给她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严歌苓的少年与青年时代正是处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作为个体生命,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时代的狂风暴雨中。严歌苓七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人性空前疯狂的运动中,她目睹了种种“人性的大自杀”,所以这十年的浩劫留给严歌苓的记忆是创伤性的、永久性的。十二岁时严歌苓以一名文艺兵的身份进入了部队,做了八年舞蹈演员。之后她又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接着又成为一名军旅作家。她上过战场,下过牧场。1989年,严歌苓移民至美国,成为一位美籍华人。此时她深切体会到了边缘人生的悲苦,所以“她多次说移民是一次‘生命的移植,‘移民的过程对内心来讲是个很大的创伤,‘移民不是件快乐的事。”②严歌苓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和她对那些弱势群体的悲苦生活的深入了解使她看透了人性的悲悯与沧桑,也因此形成了她悲观的人生观。
在严歌苓将个人悲剧性的经历和熟悉的生活素材转化成一个个动人的文本的过程中,她这种特有的观察人生的视角和感悟人生的姿态,使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多作家所没有的悲悯效果。严歌苓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说过,“有力度的审美活动往往带着深刻的痛苦体验,而痛苦又大多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强烈敏感。作家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挣扎出来,在宣泄和诉说的过程中,将强烈的痛苦转化为震撼人心灵的艺术审美愉悦。”③
通过对人生苦难与心灵困境的悲情描写,严歌苓以宽容和悲怜的特有姿态来解剖人性的丰繁复杂,并能巧妙自如地运用多种叙事技巧来表现自己悲悯与沧桑的创作角度。
二、为弱者悲歌
题材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材料,也就是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作者的世界观、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以及一部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都影响和制约着题材的选择。就题材来说,严歌苓小说题材的选择是独辟蹊径、别具一格的。她的笔触总是伸向处在苦难与困境中的弱者,这种选材取向与她的个人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作为一个热血军人,还是作为一个漂泊海外的边缘移民,严歌苓都能凭着她敏感的天性和写作才情把熟悉的社会生活反映到小说中去。在她构建的弱者世界中,有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牺牲品(如《金陵十三钗》中的窑姐们),有移民海外处在生存或精神重压之下郁郁寡欢的边缘人(如《扶桑》中的扶桑,《少女小渔》中的小鱼),还有生活在底层的平凡卑琐的小人物(如《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小环),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成为她关注的焦点。严歌苓并不刻意拉开小说与她生活的距离,她的小说创作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开始,如写少年时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与事,移民后又写“海那边”的人与事,而在这些沧桑的人与事无一不蕴含着作者对弱势人群的同情与关怀。
(一)特殊时代的受害者
特殊的历史时代是严歌苓构建小说所依附的背景,可以说历史只是人物舞台的背景和道具,但恰好迎合了严歌苓关注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境遇和描述人性复杂的目的,如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等。《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情感史就是历经革命战争和土改、四清、文革等国家政治运动而起伏发展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历史风云变幻,小菲在舞台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时代人物,而她自己却始终置身在大历史中,在一个女人的小格局里左冲右突,演绎着惊天动地的情感史。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1937年的南京城,一座美国天主教堂闯进来一群避难的“窑姐”。“窑姐”们在死亡阴影下的活泼、风骚、狂欢引起了神父和唱诗班女孩的轻蔑与敌视。但是,当疯狂的日军找到了教堂要带走唱诗班的女孩们时,“窑姐”们却挺身而出冒充唱诗班女孩,并藏着武器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小说的最后写道:“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④在这一瞬间,这些曾被视为下流、贱命的弱女子勇敢得让人心痛。再如在她的近作《小姨多鹤》也是个鲜明的例子。历史只是一個舞台,而潜藏于历史中的人性才是舞台上的主角。同时“作为历史观出现的人道主义,其实质内容是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人性——人性丧失——人性复归的历史”⑤。所以严歌苓在张扬美好人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延伸出人道主义精神。《小姨多鹤》通过两个女性——竹内多鹤和朱小环三十几年的遭遇牵引出一幕幕温情而又辛酸的故事,再一次地向我们展现出了“小”历史中的“大”人性,一部人性史通过个人史、心灵史、民族史得以演绎出来。
严歌苓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都是在漂泊海外后写成的。她在小说中重拾这些记忆,讲述一个个时代痕迹浓重的悲惨沧桑的故事。严歌苓用“戏剧性”来概括自己及身边整代人的生活,这一概括反映了她的心态——一种事过境迁后的宽容,惟有内心怀有深深悲悯的作家才能做到这一点。难怪她会说:“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⑥
(二)移民海外的边缘人
严歌苓在1989年移民美国,生命的“移植”给她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身为作家的她,不可能不把这些写入小说。严歌苓在小说集《海那边》的台湾版后记中写道:“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⑦严歌苓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甘苦了然于心,这自然成为她执着地表现海外边缘弱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从20世纪来美的中国妓女到20世纪末的大陆女留学生再到移民美国的家庭妇女等,严歌苓都有涉及。在这类边缘小说如《扶桑》《少女小渔》《花儿与少年》中,严歌苓对移民的悲苦和他们“千奇百怪的活法”都作了细致的描绘。面对移民在异域艰难的生存,面对他们处于边缘而无力改变的弱势,严歌苓悲其所悲、苦其所苦,因此在读她的小说时,我们很难平静。
移民初入他国时,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早期移民的生活环境是极端恶劣残酷的,他们承受着种族的歧视与压迫,以及很多美国人的排斥与仇视。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以自己坚韧的决心不断努力。而对于众多的女性来说,处境更是悲惨,她们如同物品一样在市场上以斤两论价被买进或卖出,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她们被凌辱、被践踏,生命被透支过度而过早地消亡。百年沧桑,命运跌宕,他们于沉浮中尽现卑微。严歌苓的《扶桑》就是要再现那段被淹没的历史。以华裔妓女扶桑的命运为主线,作品通过扶桑被拐卖到美国沦为妓女身心饱受异族凌辱的沧桑故事,来表现身处排华运动中华人真实的悲惨遭遇以及一个充满神性的妓女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多舛命运。扶桑是严歌苓小说中一个奇特而又独具魅力的女性,她美丽、温顺、任劳任怨,却又显得愚昧、麻木、没心没肺;在她身上既充满温顺、宽恕、怜悯的母性光辉,又深藏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扶桑饱受磨难的苍凉人生透过异国少年爱慕者克里斯的眼睛观察出来。少女时的扶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出国淘金者,在一次出门洗衣的路上被诱拐到美国做妓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她坦然地面对人们无尽的蹂躏,没有丝毫的反抗和怨恨。她那柔弱而慷慨的怀抱承受并消解了一切的苦痛和罪恶,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存活——“她在那个充满敌意的异国城市给自己找到一片自由,一种远超出宿命的自由”⑧,她留给人们的是那下跪时神秘而温顺的脸庞上散发出来的对世人的宽恕和悲悯之情。
严歌苓在《扶桑》中是借助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来讲述早期移民的艰辛,传达自己作为一百年后的新移民的迷惘。在与弱女子扶桑的深情对话中,“我”寻找自己与扶桑的异同、体会心中的悲伤与无奈。中国早期充满血泪的沧桑的移民史正被时间渐渐淡化其中的血腥,严歌苓重新将它拾起、描绘,将这种强烈的痛苦与无奈转化为撼人心魄的艺术审美形式,以此来表达自己深切悲悯的人性关怀,显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严歌苓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色彩太浓烈了。”⑨
因此在她的小说里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悲惨和心灵的困惑的描写:
“像你这样美丽的娼妓是从拍卖中逐渐认清你的身价的。当我从一百六十册唐人街正、野史中看到这类拍卖场时:几十具赤裸的女体凸现于乌烟瘴气的背景,多少消融了那气氛中的原有的阴森和悲惨”。⑩“你不同于拍卖场上的所有女子。首先,你活过了二十岁。这是个奇迹,你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到活过二十岁的。我找遍这一百六十本书,你是唯一活到相当寿数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11“这时你看着20世纪末的我。我这个写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头。我从来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有人把我们叫做第五代移民,你问我为什么单单挑出你来写。你并不知道你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入一百六十部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是作为最美丽的一个中国淑女被记载的。”12相对于扶桑生活的时代,现代的“新移民”(无论是穷困的女留学生,还是为了“绿卡”嫁到国外的家庭妇女及孩子)的生活要丰富精彩得多,尽管她们这些微薄的“幸福”要建立在同物质匮乏或精神匮乏的抗争之上。例如《花儿与少年》,来自大陆的九华走入由母亲晚江和继父组成的家庭,在第一天的晚餐时,本来英语就不好的九华对于美国社会家庭成员之间客客气气地对彼此说“请”、“对不起”、“谢谢”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一种陌生感和文化自卑感使得他无法融入这个以美国文化为主的新家庭,个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晚江想,我为什么不放过九华?人们为什么不放过九华?九华就一点乐子,熬夜看几盘俗不可耐的肥皂剧。就为这点乐子,我也跟他过不去。凭什么有个路易,就得按路易的生活去生活?有个仁仁,就得拿仁仁作样本去否定九华?九华能认输,也是勇敢的啊……”13最终九华选择了逃离。每一个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是为了在这片新大陆上寻梦。在面對迥然不同的美国文化时,他们身上又承袭了中国文化,这使他们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所形成的传统不可避免地要与之发生冲撞。这种冲撞使他们迷惑与痛苦,而要把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祖国文化完全剥离,他们却又不得不经过凤凰涅槃般的痛苦。
《少女小渔》就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绿卡婚姻”的经典之作。在这段“绿卡婚姻”过程中,小渔用自己的善良温厚感化了萎缩失意的意大利老人,让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同时她也用近乎母性的宽容和关爱来容忍男友的抱怨和发泄。这里的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14严歌苓认为移民不是件快乐的事情。她选取海外“边缘人”这一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是因为她深深地领悟到了这种移民所带来的伤痛。严歌苓对这一群体的人生际遇投以恒久的关注,表现出一个海外移民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哀底层民众
严歌苓还将她悲悯的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芸芸众生。这是一个庞大的无人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艰难地生,寂寞地死。幸福、快乐好像总在与他们捉迷藏,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任他们怎样苦心孤诣、竭心尽力地去抓,可总也抓不到,徒劳无获,活得动物一般麻木。他们都是在各自人生里沉浮而身不由己的弱者,弱小到一种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步。他们的现状是灰色的,前途是迷茫的,他们是社会的“零余者”,只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默默地存在。在作品中,严歌苓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再现他们在苦难的深渊中无奈的挣扎的苍凉图景,显示出作家对于人、特别是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深切的悲悯。
《小姨多鹤》就是严歌苓奉献给世人的又一曲吟唱人性美的赞歌。小说《小姨多鹤》以时代发展为轴线,结构恢宏,情节波澜起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琐碎处。历史的发展过程及重大事件在作品中都有所涉及但又只是作为背景浮现,使作品除了具有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精致外,还呈现出巾帼女子叙写历史的磅礴大气和宽阔胸怀。“这小说看似只写了一个很单纯的一小家子的悲欢离合的生活经历,却可以折射出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15
小说着力塑造了两个女主人公——日本女孩多鹤与中国女人朱小环。十六歲的多鹤随其家人跟着日本“垦荒团”来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战败,多鹤被装进麻袋卖给了中国男人张二孩,她的人生也就此翻到了另一页。这个命运多舛的日本女孩将经历怎样的人生?她与中国男人张二孩的原配女人朱小环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严歌苓用女人感同身受的细微体察,通过对两个女主角多鹤与小环的塑造,完成了她对人性的歌咏和对人情的赞美。日本女孩多鹤历经战争洗礼、几次死里逃生,以七块大洋卖到张家,处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过着非妻非妾的生活。她内敛、天真、坚韧,“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16但可悲的是制造出来的亲人却只能称呼她“小姨”。每制造一个亲人她都会悄悄向死去的父母跪拜,这种心酸的坚持让人心疼又感叹。她哼着日本儿歌哄着大孩、二孩,坚持与孩子们用日本话交流,似乎这是他们之间的纽带,是任何人都无法加入也无法剥夺的部分。骨肉相连的母子亲情让她与孩子之间有了某种默契,也成为她最大的安慰,是她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尽管她在张家无名无份,但她接受命运,甚至爱上了张俭,并给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她凭借自己卑微而弱小的身子,努力扛起生活的重担,在贫穷、简陋的张家不停地辛苦着、忙碌着。她沉默隐忍地过日子,同时也固守着流淌在血脉中的记忆。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多鹤的隐忍中始终透着顽强与不屈。
作者将多鹤和小环的遭遇置于“极致”之境,从而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她们在极度苦难的状态下人性的本质。多鹤的遭遇令人叹惋和同情,但读者并不会因为她是日本人而鄙夷她、嘲笑她甚至唾弃她,也不会对她遭遇的苦难而麻木不仁,人性之美在此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人性之光早已超越了种族、国界甚至宗教信仰而大放异彩。对多鹤而言,这个日本女人最终爱上了张俭这个中国男人;对张俭而言,他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日本女人;对读者而言,可以生发出对弱者命运的同情、关注甚至是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发生在畸形时代的非畸形故事,是最正常、最自然的人间故事,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宗教的界限,人性是其共同之根。作者借助多鹤这一个人物,形象地阐释了自己对“人”的理解。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中国女人朱小环,是作者精心刻画的典型。作者将她置于矛盾的中心点:她爱丈夫,却不能为他生育后代,作为妻子,她又不得不将丈夫送到多鹤屋里,借多鹤之腹为张家传宗接代,这是何等难堪之事!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小环的明媒正娶的“妻”之地位,但这并不能减轻她内心深深的痛苦与担忧。
小环的身上有着超越民族、凌驾于血缘之上的人间大爱。她爱着她的丈夫张二孩——这个在她难产时宁愿违逆父母、背起断子绝孙不孝子的骂名大吼“保大人”的男人。尽管她一再提醒丈夫:“等她生了儿子,就把扔出去”,但多鹤丢失,她却四处奔走找寻。她帮多鹤接生,月子也都由她照顾。小环一辈子“我儿子、我女儿的”地唤着,也唤出了她最深厚、最无私的母爱,她扒心掏肺地爱着三个孩子,甚至到了老年,仍为筹张铁赴日本的路费而加班加点干活。她所有的狠和硬都在嘴上,而心里却是一团善良,唯独抛下了自己。她爱着张俭,护着多鹤,照顾着孩子们,支撑着这个奇异的由三人组建又似乎少了谁都会坍塌崩溃的家庭。作为张俭的原配,朱小环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与自己分享丈夫,但当多鹤的孩子出生,她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她整日地抱着孩子,视如己出。她担心躺在身边的丈夫真的对多鹤产生了感情,盘算着还得再需要多久,才能“把张俭彻底收服回来”,“收服回来的他,还会是整个的吗?”粗中有细的小环,已经看到张俭的移情和对多鹤的痴情。如果说多鹤的哭让人心痛,那么小环的笑更让人心酸,而这种酸涩苦楚又无从诉说。
小环的一生,守着丈夫,护着孩子。可是,那丈夫是一半,孩子是一半,爱情也只有一半……她在貌似一切都有的正常里独自品尝着自己的一无所有。
小环与多鹤——两个敌对而又难分难解、最后走在一起的女人,相依相伴着完成了她们各自的人生使命,度过了她们充满坎坷、苦难而又平淡的一生。时间忘却了一切,洗刷了恩怨,留下的只有人间情义。这两个女人,在吐纳之间织成了人世间最温情的网,网住了张俭,网住了孩子们,也网住了读者的心……
严歌苓“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她挖掘着女性心灵之美,谱写人间大爱。“对人性的审视、剖析和反省,是严歌苓小说的创作核心和兴趣所在。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17她以超越民族、国界、时代的胸怀和眼光,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情感世界和生存状态,令人震撼又发人深思。
三、悲悯的意味
严歌苓是悲观的,“我对人性是比较悲观的人……我的经历使我认为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18这种悲观的意识使她以一种看透命运之后的豁达来探讨人类的最终命运,其悲悯情怀就渗透在对人生的彻悟中。而这种悲天悯人式的人性探讨,在透露着沧桑感的同时,又反过来促使她更加关注人的本身。
严歌苓很好地将这种悲悯融入作品中,就像水吸收了盐一样,成功地化解了。只有在闭卷回味中,才能体会到她的关切。悲悯,使作品有了深度,也有了高度。沧桑,使人物悲凉,也有了历史感。她的作品外表美丽光滑,内里却是炸药——它动摇人们传统的欣赏方式,更撼动着人们的心灵。她止于描述人物的内心、行为、言语,无意指责任何人,但是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我们能发现她的关切。她勇于扯破人类的遮羞布,使人类鲜红的伤痕暴露无遗。
所幸的是,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尖锐的思想并未损伤其艺术性。小说形式的完美,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严歌苓将小说编织得十分细密,有伏笔,有照应。小说技巧高,却又不露痕迹、浑然天成,以至于看上去没有技巧。她的作品极度地凝练,水一般的无色无臭,却有着酒的浓烈质地。严歌苓用词快、狠、准,优美又利落,字字落到要害。
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严歌苓的悲悯与沧桑来自于她的悲情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因为深知人类存在的悲,所以她能逼近生命的本质,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人类身陷孤独与困境的宿命,也因此严歌苓的创作才获得这种深沉而永恒的审美姿态——悲悯。因为领悟到人处于弱势的悲苦,所以她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弱者的世界,无论是国内特殊时代的受害者还是海外边缘人生困境或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都以一种悲怜的眼光来关注,也因此为弱者悲歌,成为严歌苓始终不变的创作情怀。
注释:
①严歌苓:《随和如风——严歌苓对话录》,《百花洲》, 2005年版,第1期。
②严歌苓:《随和如风——严歌苓对话录》,《百花洲》,2005年版,第1期。
③张琼:《此岸/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华文文学》,2004年版,第6期。
④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⑤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
⑥严歌苓:《严歌苓文集》,第5卷,《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⑦严歌苓:《严歌苓文集》,第5卷,《海那边》,台湾版后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⑧严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⑨严歌苓:《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⑩严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1严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2严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3严歌苓:《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14严歌苓:《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5公仲:《人性的光辉现代的启示——评〈小姨多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版,第17页。
16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7翟晓甜:《一曲吟唱人性美的赞歌——读严歌苓新作〈小姨多鹤〉》,《昌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8严歌苓:《随和如风——严歌苓对话录》,《百花洲》,2005年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