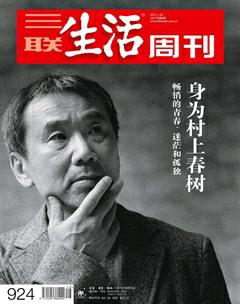人们在期待怎样的《降临》?
苗千
美国电影《降临》(Arriving)在中国过年期间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影片,人们在阖家团聚的同时热衷于在网上讨论对这部电影的观感。因为涉及一些科幻元素,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并不容易理解,因此很容易引发讨论,而同时它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上也达到了8.1的高评分。一部科幻电影在票房淡季取得这样的佳绩难免会让人感到意外,尤其是电影中并没有太多未来感十足,或足以乱真的特效,这让它的观众们更乐于讨论的,是其中所蕴含的超出生活常理的情节和哲理。
电影《降临》改编自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Ted Chiang)出版于1998年的中篇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这部小说的情节较为平淡,尚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电影,因此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加入了大量可以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大片”情节。所幸这些增加的情节并没有影响特德·姜原著的精髓,这种精髓正是这部表面看上去波澜不惊的小说吸引到电影导演,最终赢得众多观众的真正原因。
时间线索怎样才能被打破?
小说《你一生的故事》题目略显直白。整部小说是以一位母亲向她的女儿讲述其一生故事的口吻撰写的,似乎是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自言自语。在女儿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电影中这个女儿得了一种怪病,不幸早逝),母亲记录着她的点点滴滴,生命不再是一个从始至终的单向过程,而是变成了一幅早已被展开的画卷,小说以及其改编电影的主旨正是通过作者这种别出心裁的叙述方式被透露了出来:当我们生活的时间线索被打破,过去和未来的界限消失,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
时间线索怎样才能够被打破?人们早已习惯了时间这种看似循环往复,实则一直向前、永不回头的行进方式。每个人从降生开始,就会逐渐衰老,直至死亡,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这条规律就是:时间有一个箭头。
关于时间旅行的科幻作品早已多如牛毛,要么是回到过去,见证一段早已湮灭的历史,要么是到达未来,见识奇妙的未来世界。问题在于,毫无依据,甚至是违背基本科学理论的幻想早已显得陈腐,也越来越难以吸引到读者的兴趣。
限制人类进行时间旅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110多年前发现的狭义相对论。根据相对论的描述,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是真空中的光速,只有没有质量的粒子在真空中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而在理论上,只有超越光速才有可能“回到过去”——这样的一个悖论确保人类无法逆着时间箭头的方向进行时间旅行;虽然以极快的速度行进有可能进行顺着时间箭头的时间旅行,但是其效果往往微不足道,根本无法被人所感知,想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提前进入未来世界,在理论上需要近乎无限的能量,在实际中其实无法达到。
100多年来,狭义相对论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感知到的单方向的时间箭头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保证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因果律可以不被破坏。不仅是科幻创作,人类物理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被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束缚,没有取得根本上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意大利的OPERA实验项目在2010年报告发现了超光速中微子时,整个科学界迅速沸腾,物理学家们急不可待地畅想起超越相对论的新物理学,可惜最终证明测量到超光速中微子只是因为实验仪器的误差,相对论依然值得信赖。
在《你一生的故事》中,特德·姜巧妙地避开了进行时间旅行与相对论之间的冲突——他化解时间箭头的方式,是引入科幻创作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桥段,随后把故事推入到目前物理学研究尚不明朗的一片泥潭之中。在科幻作品中,除了时间旅行之外,另一个常用的主题和桥段则是人类与外星生命的首次相遇。特德·姜在进行了一些有关语言学的必要的情节铺垫之后,让形似海鲜的外星人“七肢桶”降临地球,外星人的介入成了时间维度被展开的原因。
在电影中形似墨鱼的外星生物“七肢桶”有着圆形对称的结构,这显然是作者对于外星生命感知时间方式的一种隐喻:在“七肢桶”的感知系统中,时间的表达方式与人类并不相同,而更类似于人类对于空间的感知,没有先后次序,不存在因果关系,时间可以如同画卷一般被展开。
在同样的物理世界中,为什么外星生命对于时间的感知方式与地球上的生命完全不同?在尽量不违背相对论的基础上,作者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办法:语言决定了生命感知环境的方式,而“七肢桶”们使用的是一种并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语言,他们所感知的时间也就不具有明显的箭头,而是一种同时包含过去和未来的表达方式。这种展开时间维度的能力并不需要特殊的生物构造或是物理定律,只要通过学习“七肢桶”的语言,学习他们感知周围环境的方式,就自然可以获得。文中的女主角、语言学家班克斯博士正是通过学习外星语言,获得了感知未来的能力——在适当幻想的基础之上,人类坚实的物理定律并没有被作家轻易抛在一边,而作家建构在幻想之上的故事也得以展开。
时间旅行和意识的本质
科幻小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当然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创作自由,不必过分受种种物理定律的束缚,这样也就不会因为作品太过荒诞不经而被读者嫌弃。另一方面,特德·姜在避开与狭义相对论的直接冲突之后,把小说情节中最关键的涉及物理学的矛盾,由时间旅行不知不觉地引入到了对于意识本质的辨析之中。
人脑何以产生意识,人究竟是如何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区别,建立起一种二元论的认知方式?意识的产生是否可以归结为大脑中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意识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对于物理学来说则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意识的本质涉及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理解,在多年没有实质进展的状况下,这已经成为大多数物理学家甘愿埋头做计算而不去触碰的泥潭。特德·姜可能正在无意之中把故事中潜藏的科学问题的焦点转移至此。
从时间的维度来讲述一个科幻故事,想要让作者尽可能地自圆其说,为自己的故事找到相应的“科学依据”绝非易事。另一位美籍华裔科幻小说作家刘宇昆针对当年侵华日军的恶行,也创作过一篇重现过去的短篇科幻作品《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在这个故事中,时间虽然未能倒流,但往日的情景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刘宇昆在文中虚构出一种基本粒子,这种只会成对出现的粒子忠实记录了人类历史发生过的一切情景,并且有可能被人类捕获,从而成为人类重温往日情景的时间机器。
在《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过去的时光并非无条件地展开,而是恰如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被这种虚构的粒子对记录下来。但这种粒子被观察(测量)的一刻,也既是其状态被毁掉的一刻,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过往时刻的观测只能进行一次,且无法被复制,因此请谁来见证“完全真实”的历史,就成了这个科幻故事中最核心的矛盾。
《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的长度比《你一生的故事》更小,不可能设置一个细节更加丰富的科幻背景。但是在“回到过去”的情节中,为了不与狭义相对论发生冲突,刘宇昆同样巧妙地利用了目前在物理学研究中一个尚无定论的研究领域来摆脱相对论的束缚,这就是量子纠缠。量子纠缠被爱因斯坦描述为一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當其中的一个被人类所观测到,那么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也随之确定。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即刻发生,不受到相对论的制约。虽然这种现象早已被物理学家们所熟知,但是其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至今尚未得知。利用这样的物理学现象,假想出一种弥漫在地球周围的粒子对,其中的一个用以和周围的环境发生反应,得以像录像机一样记录曾经在地球上发生过的一切,而另外一个粒子则在同时开始脱离地球。在多年后,当人类捕捉到当时逃脱的那个粒子并且加以测量,历史便得以重现。
可以说,在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读者和观众对这些作品是否有足够扎实的科学理论支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科幻作家们也就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来摆脱百多年来不变的各种物理理论的束缚。完全架空现实的玄幻小说可以随意想象,让主人公可以随意置身于任何环境,科幻作家们却不同,他们想要在时间的维度上有所作为,只能用迂回的方式,幻象也罢,主观感受也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
那么,即使是在物理学家最遥远的想象中,回到过去或是大幅向前的时间旅行究竟是否可能实现?首先这可能取决于物理学家能否突破狭义相对论的限制,建立起一套新物理学,在另一方面,这也取决于时间的本质以及人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尽管物理学理论大多与时间有关,而且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预测”未来,但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时间始终让人感到虚幻。
出于这个原因,也有物理学家进行没有时间概念的物理学研究,他们认为时间只是一种人类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实体,因此试图建立起一套不含时间概念的理论体系。这种尝试当然无法得到主流物理学界的认可。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批评道:“对于‘时间这样的概念,毫无疑问是我们描述世界的一部分。关于‘真实的理解只是一种无害的探讨。时间或许是某种显现,或者是基础性的,但是无论如何它都在那里。”
尽管人类基础物理学在几十年来没有重大进展,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浪漫想象受到的束缚一时也无法改变,但时间的本质和意识的本质这两个问题为科幻小说作家同样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近年来,科幻创作很难再出现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那样史诗般壮阔,天马行空般浪漫却相对来说缺乏科学基础的作品,但像《你一生的故事》这样短小精悍又能够在科学上尽量自圆其说,蕴含着哲学道理的作品却层出不穷。
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的本质与人类在心理上对于时间的感受是否相同?这类问题自然还没有答案。在《你一生的故事》中,作者回避掉时间的本质问题,转而把生命现象对于时间的体验等同于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对于时间体验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生活固然还无法摆脱物理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当时间在人的感知范畴被展开之后,生活的悬念也就被降到了最低。这种情况在真实生活中虽然不可能发生,但人们凭借知识和生活经验,总是能够对于未来的生活有所预测和期待,这种预测和期待反过来又会对于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如此说来,《你一生的故事》只是把人们对于生活的预测能力推到了极限,而随后又自然而然的地产生出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已经完全被预知的生活值不值得被体验?女主角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尽管已经看到了生活的种种不幸,她仍然选择了继续生活下去。
电影《降临》与原著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中外星人的作用。在小说中,外星人的来去全无征兆或理由,他们乐于回答人类的问题,也不介意让人类学习自己的语言(人类后来却又感到什么都没有学到),而当离去时又不带走一片云彩,似有禅意。特德·姜这样的处理让外星人的形象更接近于一种象征符号,尽量淡化了两种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种种冲突的情节,让小说显得精简。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勒弗把外星人的形象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外星人到地球来是因为有求于地球人,而作为回报,他们愿意赋予地球人看到未来的能力。出于种种的误会,地球上各国的军事力量又险些与外星人开战——这些如果付诸文字会显得有些画蛇添足的情节,让电影在尽量保持原著精髓的基础上,成为一部“好莱坞大片”。
特德·姜在后记中提到,他是在学习变分原理的过程中萌发了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想法。变分原理在自然界中有各种体现,它即使是在人们所熟悉的光学和经典力学领域中也会展现出令人迷惑的一面:大自然为光线或物体选定的运动轨迹似乎事先已经预料到起点和终点,并且总是能选出最为经济实惠的那条路线。这个原理也曾经让处于中学时期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感到迷惑不已,他后来把这个原理运用到了量子力学领域,建立了费曼路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