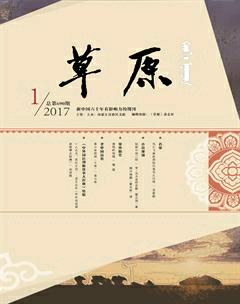乌热尔图:鄂温克民族自我声音的阐释者
访谈印象:2016年8月25日上午九点,我们有幸与鄂温克族著名作家乌热尔图老师访谈两个多小时。8月的海拉尔刮着夏天里少见的大风,在清晨的阵风中,乌热尔图老师戴着墨镜,骑一辆山地车,如同他一直轻松自如、随心所欲地驾驭着文学与生活一般,如约来到访谈地点。初见乌老师觉得他和蔼可亲,在谈到文学中的问题时,又发现他极有威严,对待相关内容态度往往一丝不苟。相继向乌老师提出的关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上的诸多问题,他都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地一一作答,虽然不巧,逢着乌老师患重感冒,说话伴着浓重的鼻音,但也丝毫没有影响到访谈效果。乌老师语速缓慢又始终具有一种控制着的节奏感,思维深刻又有独创性,尤其在说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作品———《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时,完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角度,将人们眼中带有刑事案件意味的故事阐释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这既是作家的解读,也是学者的解读,更是一个在世易时移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与文学选择的鄂温克人的解读。
采访者: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崔荣,本科生张泽愿、白璐璟、王晓悦、欧雅晗、鸿格尔珠拉、以下简称小组。
受访者:著名作家乌热尔图(以下简称乌)
一、写作的缘起
崔:您能具体谈一下写作的缘起吗?
乌:其实对于我来说,写作是由很多机缘共同推进的。我曾经在大興安岭腹地当过猎人、工人、警察、乡宣传委员,是这些扎实的生活经验为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在我初任乡宣传委员时,正赶上1973年之后拨乱反正,当时有很多记者来到边远的敖鲁古雅乡进行采访,我经常陪同这些新结识的记者朋友和他们聊一些往日的见闻,自然也要讲述一些森林里的狩猎故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心中的愿望被唤醒了,开始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也觉得自己记忆中的一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森林生活经验,一下子变得有价值、有趣味了。这样一来二去,我变得爱读书,喜欢思考了,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放在文学上了。在敖鲁古雅乡生活和工作的那几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由于受到外地来的文化人的影响和刺激,不久之后我便悄悄地尝试着在稿纸上东写西画了。
最初,因为我接触到的只有几本儿童文学作品,阅读的视野真是很窄,所以动起笔来也是先从简单、短小的文章开始。大约是在1975年,我试着写了一个儿童故事,这个短小的故事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情节十分简单,情感很是稚嫩,等这个小故事发表出来的时候,编辑给它起的名字是《大岭小卫士》。当自己涂鸦般的习作变成刊物上的铅字时,不管怎么说,心里还真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觉得这事儿不怎么难,之后我写作的兴趣更足了。
1978年初,时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是著名诗人李季先生,他提出要在10月号推出一期少数民族文学专刊,这在当时来说,是新鲜事儿,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为此他派了编辑分头到全国各地去组稿。恰好,当时我手中有一篇未完成的习作,这篇习作得到了前来组稿的编辑的认可。可当时这篇习作还没有结尾,于是就跟着那位编辑一同去了北京,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我抓紧时间写好结尾,抄写清楚,顺利地交稿。等到《人民文学》的10月专刊出版时,我的那篇作品果然刊登在上面,篇目排序还比较靠前,这让我心里一阵高兴,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准确点说,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就是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教授编选了一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他很关注我的这篇新作。我记得,那本短篇小说选集是冰心先生写的序言,冰心先生对这篇作品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虽然那只是短短的几行字,但书写着老一辈作家对初学者的殷切希望和寄托。这对我来说触动很大,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潜力,认为自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也值得投入一生的精力去探索。后来的日子,我在文学上投入的时间更多,当然主要是寻找和阅读文学类的书籍。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的感受是:不同民族之间良好温馨的文化交流,对边远地区文学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1980年,在呼伦贝尔盟文学界老前辈的关照下,我调到了呼伦贝尔盟文联工作,开始一心一意地琢磨文学了。告别敖鲁古雅乡的那一年,我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一职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年纪刚好28岁,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想象和抱负,我也知道自己推开了眼前的一扇门,随即关上了身后的那扇门。
二、避免重复性写作
崔:您在1993年发表了《丛林幽幽》之后,更多的创作就转向了非虚构写作,那么您以后还有再继续写小说的想法吗?
乌:1993年,我写了中篇小说《丛林幽幽》,把自己对大兴安岭森林的想象,还有对鄂温克猎人精神层面的描述,一股脑抖落出来。当然,这篇小说在我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进行了探索。等完成这篇作品,我就搁置了小说创作,此后出现了一段小说创作的空白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也不时回过头来琢磨当时的情景,追忆和回味当时的心态,记得当时,我心中有那么一点忧虑,这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其实是局限在森林一隅,时空过于狭窄,文化色彩也显得单一,这就很容易出现重复性描述和表达,而真要想挖一口深井,那就先攒足身上的力气。当时我搁置小说写作,本意是为了更新自己的创作思维。恰好就在这时,我的老朋友李陀,他催促我为《读书》写几篇文化随笔,我知道李陀老兄希望我在文化批评的平台上,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对于我尊敬的兄长提出的好建议一定要响应,正好在人类学方面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阅读兴趣。接下来的几年,我先后在《读书》《天涯》《视界》等刊物,发表了《声音的替代》《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生态人的梦想》《大自然,任人宰割的猎物:麦尔维尔的1851》等一系列读书随笔。虽然这些文章篇幅不长,数量不多,但还真是耗费精力,因为你要适应新的表述方式,要换一个套路,还要借用新的腔调来发声和共鸣,这样几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这一段时间,我还为自己的族人做了纪实类的资料整理工作,比如出版了口述实录的《述说鄂温克》一书,编撰了几本民族风俗类的图书。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等你静下心来,就可以将自己的劳作分为两部分来进行对比了:一类是虚构类的写作,另一类属于非虚构类的书写。前一类作品的商品属性比重大,社会传播和接受的速度快;后一类作品的商品属性比重小,属于单纯性的文化基础工作。我呢,自然喜欢上了后一类的非虚构类书写,还乐此不疲,忙乎了好一阵。我认为,对于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的后来者来说,他是肩负着责任的,有义务在文化建设方面为族人做一些事情。而对于自己一度置身其中的虚构类写作,我当时认为,进入日益活跃和开放的商品社会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都来得太快,你的想象、你的观察、你的思考,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在色彩斑斓的现实面前,个人的虚构和想象变得苍白无力。这主要说的是我个人。另外,在文学写作方面,我身上还有一个顽疾,那就是一旦动起笔来,从来不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也不考虑有无读者阅读。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涉及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
现在,我需要一段时间修补对虚构类写作的感情,也就是回过头来修补对文学创作的感情,提高这方面的兴趣和亲近度,只要我的身体状况允许,或许还是有机会进行努力的。
三、写作的转向
崔: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作品,能具体谈一谈吗?
乌:刚才谈到,我个人的小说创作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就出现了停顿,这一停顿原本是一次修整,是短时间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停顿之后竟变成了搁置,搁置的时间一长就带有放弃的意味了。我也思考当初搁置小说写作的原因,其实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很多的,比如,我一直认为自己写作之初并没有准备妥当,就仓促地跨上了出征的猎马,所以在写作这条陌生的山路上,难免要走走停停,边走边看,而不是一鼓作气地直奔那个既定的、最终的目标。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或许与我个人的性格和心理因素有关,我觉得在森林中当猎人的那段难忘经历一直影响着我,至今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密林中练就的成手,一个学会了以传统方式狩猎的猎手。而那在青春期铸就的性格,将要伴随你的一生,它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那么一个猎人的行为特征是什么呢?可简单归纳为:随意、迅捷、游动。当这些潜在的素质投射在心理上的时候,其负面因素难免要表现出来。这是我对前面话题的补充。
你要是问到,我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在过去这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就成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我的小说创作从整体上看,数量不多,分量也不重,还远没有达到放到大秤上掂量掂量的那个体量。简单一点说,我对自己的创作表现谈不上满意,所以要从中挑选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真是有点难。但是,写作风格的变化还是有的,认真地探索也一直在悄悄地进行。比如说,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收获》想要约你写稿,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答应了他。果然,几天后《收获》主编李小林女士打来了约稿电话,李小林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文学主编,她的文学态度及人格令人敬重,她们的刊物想要开辟一个“西部地理”的新栏目,一下子想到了我。好在我的手头正存有三篇小稿,我原本打算等凑齐二十多篇,找一家出版社结个集子出版。但现在为了“西部地理”这个新栏目,只能把这三篇小稿临时起个《昨日的猎手》的题目,交了稿。在这三篇小稿中,我使用了真名实姓,写了不久前故去的猎友的往事,我把写作的焦点放在他们生命终结的瞬间,主要思考当一个人生命终结时留下什么样的启示。这三篇作品,我是借用人类学调查报告的笔调来完成的,把描述性的文字及小说的味道压到最低点,让人读起来别有一种滋味。对我来说,这是写作方式的一个变化,一个新的开端,可惜没等我起身奔跑,就自己踩了刹车,因为其他缘由自我放弃了。在写作上,拖延往往就等同于放弃,因为时过境迁,你的写作情绪会发生变化,也很难再次进入和情绪上的复原。这是一个教训。
可以谈上几句的,还有一部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纪实性作品。这部作品其实是朋友逼出来的。多年前,我的老朋友来电话,说他们正在组织写70年代的稿件,要通过书写个人史来汇集有关那个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他一再强调这很重要,不应该扔掉像我这样带有边远区域和森林色彩的人。这事我实在推脱不了,但还是拖了近一年时间,才动的笔,它就是那篇最初刊登在《今天》上的《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完成这篇文章之后,我感到写点纪实类的作品,也是挺有趣的事情,当你回头重读它的时候,也会让你感慨万千的。
四、经典作家的影响
崔:在您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外国作家的身影,比如可以感觉到福克纳、海明威、屠格涅夫的影响等,您的笔下也出现了类似于海明威的硬汉精神,可以谈谈外国作家对您的影响吗?以及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对您有很深的影响吗?
乌: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一时想不出具体的例证。至于具体到作家个人,我想说的话很多,至今,我对老作家王愿坚先生心存感激。
那要說到1981年,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学习的时候,那时校方为我邀请的写作辅导老师是王愿坚先生,他是一名有军职的老作家,平易近人,性情温和,和蔼可亲,尤其是循循善诱,在几次小范围的辅导活动中,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些温暖的画面让我终生难忘。我想说的是,他为人十分慷慨,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用一生积累下来的有关写作的经验,一股脑传递给你,那可都是经验之谈,句句如金哪。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他同你交流的过程中,会很自然地帮你树立起自信心,帮你挖掘自己的创作潜能。如今,我也有了一把年纪,如果你要问我从王愿坚先生的人格风范中学到了什么,我只能说学了很多很多,但我与之相差太远。
对于一个以写作来谋生的人来说,阅读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他写作的初期阶段。那他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找到自己的良师益友,找到一个可与之进行对话的心灵对象,这也好像你独自在密林中闯荡,渴望遇到一位同行的有经验的伴侣,渴望找到一条走出迷途的便捷之路。我所指的阅读,说的是要深读那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经典作家的作品。那些经典作品,能够让你感觉到,大师是如何完成自我训练的,清晰地了解他们是如何运用思想的,如何来表达感情的,以及他们怎样磨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写作,当然也是一门技术活,真正的写作爱好者,最终是要找到自己的“影子导师”的。说到我的“影子导师”,那还真有几位,比如说杰克·伦敦、海明威、屠格涅夫,等等。谈到杰克·伦敦,我个人也有感受极寒气候的生活经历;谈到海明威,我认为他是相当棒的酷爱大自然的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猎手;说起屠格涅夫,我真喜欢他描述的草原和森林,那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谈到这些,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学习的话题,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终身摆脱不掉学习的困扰,他要不停地向创作上的成功者学习,更主要的是向日新月异的生活(历史与现实都包括于其中)学习。
对于个人所喜欢的经典作家的那些好作品,要开出的书目当然会很多,如果要我举一个例证,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会是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应该说那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作家在这篇作品中向读者讲述了什么呢?他讲述的是美国南方小镇上一位受人尊敬的传统女性,她年轻时暗自迷恋了一位男性,后来这专一的恋情达到了病态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她将死去的恋人藏在卧室之中,一切都尘封起来保持原貌,任其枯干成为一具僵尸,而这一极端个人化的隐秘过程,直至这位女性晚年离世才得以揭晓。这是故事的大意。让我感兴趣的是,福克纳这位写作大师处理生活素材的特殊能力,思想上的透视力,常人难以企及的同情心,真是令人敬佩,他把自己的情感和同情心通过文字传递,献给了那位在常人看来很是病态的艾米丽。这样一种情感姿态,这样一种不加掩饰的人生态度,恰好就是这一点,给读者带来了震撼。作家在这一规定的情景中,把那位孤傲的、冷僻的女性塑造成保护传统、尊重传统的化身,把她怪诞和疯狂的行为,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极致化的对传统的恪守。写这样的东西确实需要勇气与魄力,只有文学大师才写得出来。
五、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建设者
崔:在您的文化随笔中说到“鄂温克族是历史的巨人”,那您有没有想法,要为自己的民族构建一种形象呢?
乌:记得早在写作的初期,我在一篇谈创作的感言中,写下了“鄂温克族是历史的巨人”这样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鄂温克民族的子孙,脱口讲出这样的话,明显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也含有直觉推断的意味,但如果从历史角度上看,相比较而言,这句比喻还是比较贴谱的。当下的鄂温克族虽然人口很少,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她的历史行程相当的长,她并不是一个年轻的、新兴的民族,应该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在历史文献中,却很少留下她的足迹,就是在鄂温克民族内部,有关祖先的起源、部族的迁徙、早期族群的变迁,也都是大面积的记忆缺失,我们的早期历史记忆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和空白。你不会想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鄂温克人是那片土地的早期开拓者,也是那片大森林的主人;你不会想到,鄂温克人还是极寒地区寒带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你也不会想到,在《蒙古秘史》和《史集》中记载的声名显赫的“弘吉剌部落”,竟是鄂温克族群的一个分支;你也不会想到,在大清王朝的中期,由鄂温克人组成的“索伦劲旅”,为了大清版图的完整而浴血奋战,死伤无数,以至于人口凋零,等等。谈到这些话题,自然要涉及鄂温克族为数不多的写作者,他们要尽自己的努力来进行民族集体记忆的修复工作,对此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1999年前后,我个人邀请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来呼伦贝尔,请他来研究和解读呼伦贝尔的古地名。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举动呢?因为我看到,随着市场经济及商品大潮的来袭,随着流动人口的涌动,呼伦贝尔这片古色古香的土地,并没有做好文史方面的基础准备,好多东西都处于散在的、无定论状态,也出现了一些扭曲地方史,临时编织伪文化的倾向。但是,让我始料不及,同时也是最为痛心的是,当这个研究课题接近尾声的时候,乌云达赉先生不幸患上脑中风,不久就去世了。乌云达赉先生是一位博学的人,他为后人留下了那本宝贵的《鄂温克族的起源》一书,这部专著充满历史洞见,有独特的历史发现,但因为曲高和寡,资金匮乏,还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族内同胞的声援,他的学术观点未能对外传播,知其研究成果者寥寥无几。
之后,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写作计划,来研读乌云达赉先生的遗作,尽自己的可能读懂他的历史见解,感受他的个人智慧。一晃过去了几年时间,没想到的是,在乌云达赉的智慧之光照映下,我也完成了《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专著,大体上传承了乌云达赉先生的学术观点和个人智慧,为修复缺失的集体记忆,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有时我也在想,一个常以编故事和塑造人物为荣的人,最终他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现在觉得,那些编故事、塑造人物的人,在变幻不定的潮流中也是被社会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无论他怎样的特立独行,自以为是,都要以不同的侧面應对社会的需求、应对来自族群的渴望和呼唤,并调动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其相呼应,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充实的是他自己,这也使他丰富了自己。
【作家小传】
乌热尔图,1952年出生,鄂温克族作家。原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是鄂温克族,母亲是达斡尔族,自幼受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民间文化、汉族文化的多重影响。“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这对乌热尔图的思想乃至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也促使他在文学创作的路上不断地进行挖掘与探索。1968到1978年,他到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敖鲁古雅乡生产队经历了十年的猎手生活,这让他对鄂温克族世世代代游猎生活的森林有了一种归属感,并且将他这十年真正的猎手生活与感情融入作品创作,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猎手形象和猎人生活正是这段生活经历的体现。他最初觉得一切要从简单开始,于是早期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如《大岭小卫士》(1976)《森林骄子》(1981)。随着民族意识与思考的深入,他开始创作反映自己民族生活习俗的中短篇小说,如《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琥珀色的篝火》(1993)《你让我顺水漂流》(1996)等。在他慢慢从虚构小说创作转变为非虚构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他曾一度搁置了小说创作,发展非虚构写作作品《林中猎手的剪影》(1998)和《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2012)等。之后的若干年,他还出版了多部文化随笔及学术专著,如《鄂温克史稿》(2007)等。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道路上,乌热尔图的作用是独特又富于启示。他追求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的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差别的血质;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听到我的民族跳动的心音,让他们看到那样一颗与他们的心紧密相连的同样的心。这是因为唯有在人的心灵上才能刻上历史的印迹,时代的烙印;这是因为心是人的生命的标志,力量的源泉。”(乌热尔图,《写在〈七叉犄角的公鹿〉获奖后》,《民族文学》1983年5期)其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1982、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老人与鹿》获得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