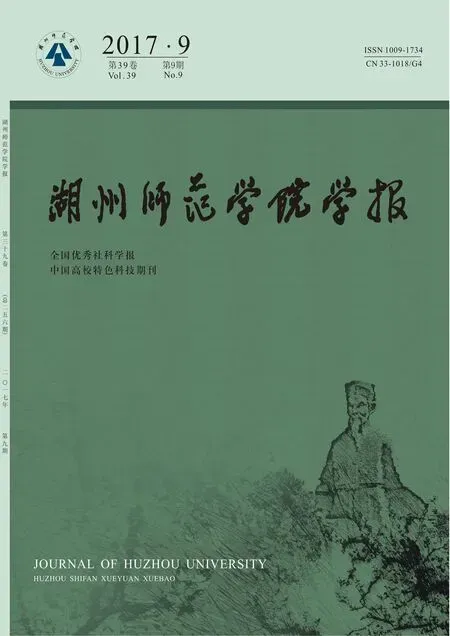张载“民胞物与”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凡明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张载“民胞物与”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凡明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张载以“乾坤父母”阐释人与自然万物的同源性,由此提出“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成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为天地立心”强调人的主体性与道德责任,“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阐释了生态伦理的实践问题,把“与天为一”作为生态伦理的最高目的与终极价值追求。张载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可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独尊主义的桎梏,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壁垒,而且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强化人的生态伦理责任与道德义务。
张载;生态伦理;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体物
在当代高科技全面主导之下,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然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而由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与观念引领,种种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行动也已全面展开。当此之际,重温中国先哲的生态伦理思想,寻找其中的生态智慧,探寻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应对之策与解决之道,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生态伦理观独树一帜而又极具远见卓识,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乾坤父母”:人与自然万物的同源性
张载在其《西铭》中开宗明义,既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又确立了这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源就在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同根同源性。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P62-63)
张载一生苦心力索,以期建构“气”一元论的宇宙本原学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在张载看来,乾坤就是父母,就是万物之源。张载为什么说“乾称父,坤称母”呢?乾坤本是《周易》中的卦名,代表天与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1](P206)这里,乾坤作为天地的代名词,指的就是自然界。而所谓“易”,已不单单指《周易》这部书,而是指自然界的造化。乾坤之所以称为天地父母,实则在于其造化之功能。所以,张载说:“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犹言神也。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体,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阴阳言其实,乾坤言其用,如言刚柔也。乾坤则所以包者广。”[1](P177)乾坤本来指天地自然,但不说天地而言乾坤,在张载看来,二者意指是不同的。天地意指有形的实存世界,乾坤则是意指无形的万物生成的形上本源。从功用上来说,乾坤是无形无象的,故神秘莫测。乾坤的功用实则是造化万物,而乾坤如何造化万物的呢?
“乾之四德,终始万物,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推本而言,当父母万物。……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则有体,言乾坤则无形,故性也者,虽乾坤亦在其中。”[1](P69)
乾坤的功用正是通过元、亨、利、贞四德来“终始万物”,即造化、成就万物的。张载在这里又进一步诠释了言乾坤不言天地的原因,就在于乾坤的无形无象,体现出造化之神妙。而这无形无象的乾坤,恰恰浑然处于“性”之中。不惟如此,乾坤就是天性。“天性,乾坤、阴阳也。”[1](P63)在张载那里,“性”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即可言人性,也可言物性乃至天性。因此,“性”就具有多种特征。“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1](P63)但凡有、无、虚、实、神等都是对性之特征的具体阐释,由此看来,张载对性之普遍性特征的阐释似乎带有某种矛盾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性并非是有形之物,它只能存在于气物之中,对人的五官而言,它是显得‘虚’、‘无’的;另一方面,性又需在气物的‘动静争相成’中表现出来,‘性者,感之体’,所以性又是‘有’与‘实’。”[2](P154-155)正由于性与乾坤都是无形无象的,都具有造化之功、生物之能。所以,张载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焉。”[1](P21)天地之性是人与物的共同本源,人与万物皆源于性。“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1](P64)“合虚与气,有性之名。”[1](P9)张载认为性是万物之源,而所谓性乃是气之性,是太虚与气的统称。若说性与气之分,则是“假有形而言”的。张载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1](P21)对于由气聚而生成的有形之物而言,“性”超乎气之外,而“通极于道”。但气又是没有内外之分的,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皆为一气,因此,所谓“通极于道”之性也还是气之性。所谓“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根据王夫之先生的诠释:“无,谓气未聚,形未成,在天之神理;此所言气,谓成形之后形中之气,足以有为者也。”[3](P329)
由此可见,“性通极于无”之性指的是天地之性;而“气其一物尔”之气是指气质之性。所以,《西铭》中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P177)“天地之塞”显然是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是物质性的气,而气的凝结而聚为有形之物,这是指形体而言的。而“天地之帅”显然是指统帅天地万物的天地之性,因而它是生命价值之所在。因此,现实世界的人与物皆是由气构成的,气在凝聚过程中,既赋予人与物外在的物质性的形体,又赋予其内在的精神性的生命价值。但从本源上而言,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皆是由气凝聚而成。张载称“乾坤父母”,把乾坤作为人与万物的本源,正是以乾坤的功用,也就是阴阳二气的造化功能来阐释人与万物的同根同源。在此意义上说,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基于乾坤是宇宙创生与造化万物的根源之性。
二、“为天地立心”:生态伦理的主体性与伦理责任
关于“天地之心”的概念,最早是在《周易》复卦的《彖辞》中明确提出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4](P87)复卦把天道的运行看作是一个往而复返的循环过程。蒙培元先生认为:“复卦处于冬尽春来之时,便意味着生命的开始。春天万物生长,从卦象上说,即从复卦开始。所谓‘天地之心’便具有生长或生命发生的意思。”[5](P272)张载对《周易》关于“天地之心”的观念特别重视,认为“天地之心,……此义最大。”[1](P113)张载为什么这么高度重视“天地之心”?在张载看来,“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1](P113)即是说天地之心是生物,而雷复于地中也正是生物,因此,“复”即是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之心。事实上,天地作为自然性的存在,其本身是无心的。这一点张载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天本无心,乃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此曰:天地之仁也。”[1](P266)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天地,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因此,其生成万物的功能,乃是一种无心之用。“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1](P185)这样说来,天地生成万物只是阴阳之气运动的结果。天无意志无忧虑,只是鼓万物、生万物。尽管张载将此称之为“天地之仁”,也只是一种人为的意义赋予。“天不能皆生善人,正以天无意也。”[1](P189)如果说天地作为自然性的存在本身是无自我意识的,那么,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释生物进化过程时,提出了自然界自我意识的问题。他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是从最低级的原生生物一步步进化到高级的脊椎动物,“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这就是人。”[6](P273)也就是说,自然界自我意识的获得尽管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却是通过人而获得自我意识的。所谓“天地之心”,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界自我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载才说“天无心”、“天本无心”。
张载首先肯定了自然界自我生成的意义,天地自然在创生生命的过程中,尽管存在自然性的一面,“即无目的无意志无情感的一面,但是,就其内在的生命之德而言,则是向善的,这就是天地之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无心而有心,心即是目的。”[5](P274)因此,张载提出“人为天地立心”,不是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来为天地立心,赋予自然界以伦理意义,恰恰相反,张载是通过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天地创生万物的生生之德得以自然流行。因此,张载在诠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也,能继继体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犹言能继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则必俟见性,是之谓圣。仁者不已其仁,(始)[姑]谓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姑]谓之知;(此)是[谓]致曲,曲能有诚也,诚则有变,(化)必仁知会合乃为圣人也。……饮食男女皆性也,但己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举动,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梦而死者众也。”[1](P187)
天道的流行化育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从本体意义上来说,天道就是天德,即生生之大德,或者说是“天地之仁”。这就带有目的论的意义,因为善本身就是目的论的范畴。张载把“能继继体此不已者”、“能继此者”称之为善,“继此”与“体此”均是指天道与天德。人若能“继继体此而不已”,就能成就其德性,成为圣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天地之心”,虽说这种自我意识是通过人而获得的,但它并不是由人来确立,而是天道自然本身的大化流行。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1](P256)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其核心就是立人之心。在张载看来,心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范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儒家传统观念认为心具有思维、认识的功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7](P335)张载从心的认识论意义出发,把知觉、主观思虑看作是心的内涵。他说:“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P9)“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之所从来而后能。”[1](P25)心的知觉是一种德性之知,具有人伦道德的属性。心固然包含知觉,但不能以知觉为心,知觉只是心的功能或作用。而心的恰当内涵只是心的内在规定性,对此,张载则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孟子说:“仁,人心也。”[7](P333)孟子以“仁”为“心”,使心具有了人伦道德的属性。张载在此基础上,从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心之人伦道德精神。陈谷嘉先生从张载“太虚者心之实也”[1](P324)的规定出发,推导出“心之实”即是“心之诚”,认为心的本质是以诚为主旨的人伦道德精神。[8](P32)由此可见,张载对人心的内在规定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一方面,张载确立了“天地之心”就是人之心,就是仁,就是诚。换而言之,就是天道与天德。而这并非是人为的主观赋予,而是天地自然内在的价值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张载又赋予人心以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是自然赋予的,人所独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思虑、谋划等等各种人为活动,这种活动的根本目的便是实现天德之性,天地之仁,此即所谓以人谋成其天能,以人能成其天性。”[5](P275)因此,在张载看来,就人与天的能力而言,二者是不可替代的。“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圣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1](P17)但这并不是说人在“天之良能”面前无所适从,人可以通过“穷神知化”而位居天德。所谓天德或天之良能,都是自然所固有的。它在一阴一阳之道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并且与人的生命活动共存共在。因此,人是可以在其生命活动中去感知、认识天地自然的神化过程。“凡言神,亦必待形而后著,不得形,神何以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则亦须待人而后能明乎神。”[1](P208-209)天地自然造化万物的神妙功能借助人而得以发现,天德也是通过人而实现的,所谓“待人而后能明”。这恰恰说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尽管是自我生成的,但是需要借助人才能真正承继与体认天地自然的生生造化之功。“人为天地立心”既强调了人与自然互为对象而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共存共在的一体性,又凸显了人与自然的主体性。天地自然化生万物是自生自成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地自然生成的过程就是自然界主体化的结果。而人在自然生成的生态系统中又扮演着主体性的角色,通过为天地立心,展现自然界自我意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立心”就是立德,而立德的目的在于立人。人正是在为天地立心的过程中,成性成德而实现“成人”、“立人”的目的。这也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何以把 “立天、立地、立人”作为张载伦理思想纲维之所在。他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说:“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神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3](P4)
三、“体天下之物”:生态伦理的实现途径
张载把“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成物的生生之德看作是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天德良能,无假人为。但是,人通过自身具有的认知能力来谋成天能,成其天性。这就是张载提出的“体天下之物”的思想。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未有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P24)
张载提出“体天下之物”之说,按照蒙培元先生的观点,“表现了张载强烈的生态意识。”[5](P281)那么,“体物”之“体”当作何解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这里的“体”确有两重含义。“一是体验之义,二是体恤之义,二者实际上是统一而不可分的。”[5](P281)体验既是一种情感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是知情合一的概念。如何才能“体天下之物”呢?张载提出了“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观点。
这里的“大其心”,张载引用孟子的“尽心”说来加以阐释。孟子一方面从心的功能把心规定为天生具有思维、认识的功能,另一方面认为心是人天生的内在的道德情感。孟子提出“尽心”就是要把人的内在道德情感扩而充之,充分发挥心的认识功能,认识人的善性,实现人的德性。张载正是继承孟子“尽心” 之说,提出了“大其心”的观点。所谓“大其心”就是“尽心”,就是充分发挥人心的认知能力,而心的这种认知能力不是对客观外物的简单认识,那样就会失之偏狭。张载称这种认知为“闻见之知”或“物交之知”,这种认识事物的结果就是造成心是心,物是物,心与物的两隔。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德性之知,是心对自身德性的体悟与自悟,反映的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水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德性之知不仅可以发现自身内在的道德良心,而且可以体认天地自然的生生之德。
张载“大其心”的主张强调内外与主客一体,实则是打破了心的限隔,把闻见之心转化为德性之心,把有外之心转变为无外之心。这样就把认识的对象还有外在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外物与我为一体的内外统一,即所谓“视天下非一物非我”,这样也就无所谓物我内外之分了。但是,这种认知的高度并非人人皆有。一般的“世人之心”往往还局限于闻见之知,陷于知识见闻,“累其心”而不能自拔。因此,张载“大其心”的主张就是要破除世人的闻见之狭,“不以闻见梏其心”,使德性之心明于天下。为此就要“知心之何从来”。他说:“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累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1](P25)“尽其心”当然就是“大其心”,就可以“知心之所从来”。而“心之所从来”又是什么呢?对于此问题,张载是有明确答案的。他说:“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所自来也。”[1](P63)心既是有形的存在,又是无形的、无限的;既是存在于人身之内,而又是向外的,不受内在形体的限制。因此,心是有无、内外的统一,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正是心的无限性与内在性,使得心具有了“尽心”、“大心”的可能性。“大其心”的最终目的是要“体天下之物”,简单来说就是“体物”。“体物”的过程既是一种认知的活动,也是一种情感活动,体现的是情与知的统一。因此,“体物”离不开心对外物的感应,是主体的内在德性融入于外物之中,把天地自然的生生之大德与自身的德性交融于一起,达到“视天下非一物非我”的状态。张载的“体物”观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感应关系,心如何感应外物?张载说:“感之道不一,……感如影响,无夫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故曰感速也。”[1](P125)也就是说,感的特征犹如如影随形,是感者应,应者感,没有时间先后。这种“体物”之感使人的情感投入得到天地自然的情感回应,人与天地自然成为了一种有机统一体,真正达到了一种物我一体的境界。
真正实现以心体物,实则是以仁体物。“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1](P13)以仁体物,就是以人心合天心。“天地之心”就是天地自然生生之大德,在张载看来就是“天地之仁”。人心即是仁心。仁既是人所具有的普遍的道德情感,也是宇宙本身所具有的普遍品格。这样,以仁体物才能使仁爱之心的投入得到天地之心的感应与回报,产生共鸣。张载认为“仁统天下善”[1](P50),仁可以统摄天下一切之善,因为仁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是一个具有全德之称的范畴。仁爱的实施是一个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过程,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转换成张载的说法,自然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要以心体物,以仁体物,必须保持一颗常爱之心。“安所遇而敦仁,故爱有常心,有常心则被常爱也。”[1](P34)保持常爱之心才能“体物不遗”。爱则常爱,既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一种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长久不息。
四、张载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以“民胞物与”化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张载生态伦理思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而是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把人与人、人与万物纳入到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加以考察。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一方面从人与自然万物的最终根源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太虚之气聚散变化的产物。“乾坤父母”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万物在本源上的一致性,二者同根同源,共生共存共在于同一体中。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万物的价值的同源性上来说,人作为德性的存在所具有的仁德,其价值之源应归之于天德,因此,人在成就自身的德性,实现仁德的价值追求,也要把知性与知天结合起来。故此张载认为“思知仁不可以知天”[1](P21 ),如果“贪天之功为己力”,则“吾不知其知也”[1](P25)。这就确立了人与自然界在价值上的本源性,从而在价值层面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更消除了人类独尊主义的狂妄。
以“为天地立心”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二元思维。现代性运动意味着主体与主体性的确立,而主体与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客二分的存在为基础的。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并非是要把人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恰恰相反,而是以“天地之心”为“人心”,首先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其创生万物的生生之大德就是“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仁”,就自然界自我意识的自生自成而言,天地自然就是主体,而非客体。而人“为天地立心”,同时展现着自然界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人“为天地立心”又并非是人按照自身的德性“为自然立法”,而是顺应自然生成之德性,即“天地之仁”以实现天德,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由此不难看出,在张载的生态伦理意识中,人与自然不是所谓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二者既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是一种主客相混溶的结构模式。正是这种结构模式,消解了主客二分的所谓理性迷思,使张载的生态伦理意识更为强烈。
以“体天下之物”消除了人与自然的情感限隔。在消解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二分的主体性思维过程之中,张载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设定为一种感应关系,这种感应关系是以双方的情感投入为前提的。张载提出“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思想,把人的认知活动与情感体验统一起来,强调心物一体,把认识的对象即外在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外物与我为一体的内外统一,“视天下非一物非我”,打破了心与外物之间的阻隔。体物的内容就是以仁体物,打通了仁人之心与天地之心的壁隔,使仁爱之心由人而遍及于物,建立了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以仁心对待人与万物,实现天地万物的生生之道,最终达到“与天为一”的理想境界。
[1]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 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周辅成.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陈谷嘉,唐亚阳.论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义[J].伦理学研究,2005(5).
[责任编辑杨 敏]
ZhangZai’sEcologicalEthicsof“LoveforLivingThingsandPeople”andItsContemporaryValue
WU F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Zhang Za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mology of man and nature by “Qian Kun being parents” puts forward the ecological ethic of “people and things” and becom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its 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 “Keeping fait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is used to emphasize the subjectivit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ople, and “Being tolerant to bear all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explains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Fusing oneself into nature” is taken as the highest goal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value. Zhang Zai’s ecological ethic thought can not only eliminate the shackles of anthropocentrism, human dominance and the emotional barrier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raise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strengthen human’s ecological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moral obligations.
Zhang Zai; ecological ethics; universal love; keeping fait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bear all the things
2017-09-15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理学的伦理之维”(12ZX09)。
吴凡明,教授,哲学博士,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
B82-058
A
1009-1734(2017)09-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