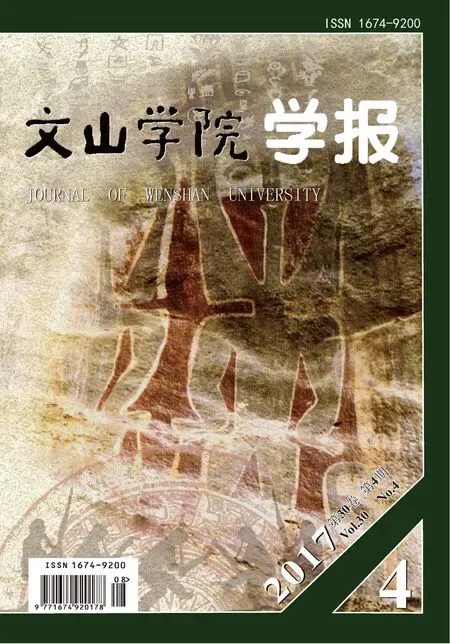从《美丽生存》一书看中国式田野调查的当代创新
杨秋萍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从《美丽生存》一书看中国式田野调查的当代创新
杨秋萍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自“马林诺夫斯基革命”标志这一方法的确立以来,民族学家倍加重视,堪称是民族学家的看家立命之本。然而,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田野调查方法仅是适用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时代在不断变化发展,田野调查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地创新,民族学才能绽放出新的生命力。通过对《美丽生存》一书的研读,对当代中国式田野调查的新动向获得了一个梗概性的认识,它为21世纪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新视野、新视角、新方法。该书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追踪式调查研究、以文化生态为主题研究、跨文化横向对比研究三个特点,是21世纪中国式田野调查的新尝试,可以为当今的田野调查提供一个参考范式。
田野调查;创新;中国式;《美丽生存》
自“马林诺夫斯基革命”确立了田野调查成为民族学必备研究手段的传统以来,常年住居在调查地点,对整个民族文化开展面面俱到的调查就成为公认的传统。这一传统对中国影响深远,凌纯声、伍况麟、杨成志、杨汉先、吴文藻等早期民族学家,基本都是按这一传统对民族文化开展调查。[1]万事万物皆在变化,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而《美丽生存》一书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式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指导下的尝试之作。
一、《美丽生存》其书其人
《美丽生存》一书是杨庭硕、罗康隆等学人多年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开展全面且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形成的成果,该书于201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二章,内容十分丰富,包含贵州多姿多彩、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千姿百彩、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的生态环境等等。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该书涉及的民族有苗族、瑶族、侗族、水族、壮族、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回族、汉族等,内容涵盖了这些民族的农业种植、牲畜业、林业及美食、村落、服装等文化事项,触及到的生态类型包括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阔叶针叶混交林、高海拔疏树草地、亚热带藤蔓丛林、亚热带湿地和高原水域等,牵涉到的地形地貌有河谷盆地、喀斯特山区、高原台地等。涉及气候类型有亚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等。涉及的生计方式有游耕、林牧采集、林粮兼营、农牧并举、多畜种混合放牧等。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治理石漠化灾变等本土生态知识。可以看出,作者的田野调查涉及地区范围十分广泛。
全书贯穿了人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制衡,进而探讨各民族美丽生存的文化生态思想。贵州各民族丰富多样的生态智慧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可以提供多层次、多视角的启迪和借鉴。
该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文字清晰、资料翔实,读起来十分流畅,可以万里一息、一饮而尽,并且不会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笔者阅读该书之初,对此书为何如此精彩百思不得其解,后通过对本书多次研读,并与该书作者早年的作品进行对比后,发现该书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与早年有别,这应是该书会如此独具一格、异常精彩的原因。
《美丽生存》作者早期是按照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民族学研究,同时也对贵州的苗族文化展开过深入的探讨,如对贵阳市高坡乡苗族的葬俗进行调查研究;[2]对麻山地区苗族悬棺葬和洞葬研究;[3]以及苗族以贝为首饰的成因探析。[4]然而,《美丽生存》一书却一改旧貌,运用了新的田野调查方法对贵州民族文化开展创新式的研究,从而科学地把自古以来贵州人民生态的、绿色的生存智慧展现给了世人,这是作者创新田野调查方法后形成的全新文化生态作品,从而使得作者对贵州民族文化的剖析大有入木三分之感。
笔者通过研读后,认为该书作者运用的田野调查方法主要有三种:追踪式调查方法、以文化生态为主题的调查方法、跨文化对比研究方法。以下仅就这三个方面略加分析,并求证于海内贤达。
二、追踪式调查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典籍史料浩如烟海,记载各民族详细文化的史料即使可能只言片语,数量却也是汗牛充栋。加之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们的辛勤调查,使得田野调查资料也堪称宏富。因而,要在此基础上找寻未被学人研究过的民族文化领域十分艰难,填补学术空白更是天方夜谭。《美丽生存》一书的调查方法则另辟蹊径,不是致力于发现新的民族文化事实,而是致力于发现跨民族的相似文化事项之间的关联性,为了实现这一新的调查使命,该书作者很自然地要以此前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展开新一轮的追踪式验证性调查。其调查目的有三,一是验证此前已有调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二是要查证文化事项在当代的依存事实;三是要在历史过程中发现不同民族相关文化事项发生和并行的具体过程。最终能够揭示各民族之间相关文化事项的内在关联性,并揭示跨民族相似文化事项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这样的田野调查是以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因而可以统称之为追踪式田野调查法。
在贵州境内,很多民族都有“认干亲”的习俗。即如果孩子生病了,或遇到意外事件的打击,父母就带上香烛纸钱和丰厚的祭品,对选中的古树进行祭祀,让孩子认古树作义父或者义母,以庇佑小孩一生平安。[5]142与此同时,该书还提及了在贵州各民族中,还普遍存在着“神林”“神山”等文化事项。查阅文献典籍后不难发现,上述几种文化事项的历史记载可以上溯追踪十几个世纪,较早的如《隋书·地理志》[6]长沙郡下的“蛮左”和“莫瑶”就涉及到相关的文化事项的记载。其后,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7]172也涉及“仡佬”的习俗。明清以后更是史不绝书,田汝成的《炎徼纪文》、田雯的《黔书》、鄂尔泰主编的乾隆《贵州通志》、陈浩所编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即后人所称的《百苗图》)都有零星记载。此外,民国年间的国内外知名民族学家吴泽霖、罗荣宗、鸟居龙藏等的研究中都有相关记载。
纵观前人的研究,有如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相关的研究都是把此类文化事项的某一特点认定为某一民族的文化事实,很少关注不同民族相似习俗的内在关联性。二是他们都将这样的习俗称为“原始”“迷信”“愚昧”。很少有人细究类似文化事项背后的信仰逻辑,比如罗荣宗就是把这样的文化事项泛称为多神信仰和祖宗崇拜的表达。[8]三是前人将类似的文化事项视为需要加以取缔和扬弃的社会现象,因而很少关注其当代价值。
《美丽生存》一书的作者则另辟蹊径,他们是立足于“万物有灵”[9]信仰的内在逻辑去展开实地调查,去深入探究类似文化事项与“万物有灵”信仰的关联性,且都是该信仰的演化形式。在这一问题上,上述各种文化事项与外来宗教信仰所导致的寺庙、道观、祠堂的神灵配置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后一种现象是“一元神”宗教信仰派生的产物,与“万物有灵”信仰无关。至于贵州各少数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祖宗崇拜,则是“万物有灵”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汉族传统的祖宗崇拜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基于以上认识,该书作者注意到,在贵州各民族中尽管相关文化事项在当代都具有生态维护的价值。但他们的来源却各不相同,具体定型的时间也各有早晚,从文化变迁的视角看,不能混为一谈。这将意味着,即使是表面相似的文化事项,其性质和演化脉络也客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单就共时态的表面去下定义,肯定不符合文化事实的内涵。为此,《美丽生存》一书除了强调相关信仰和习俗的当代生态价值外,还将这两类不同的文化事项有意识地分别加以讨论,并揭示其间的区别,从而使得《美丽生存》一书从字面上看,写得流畅生动,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在流畅的文字背后,却能将具有深刻理论含义的相似文化事项做出明细的分辨,值得读者在阅读时细加品味,最终才可能意识到该书作者在田野调查方法上已经做了极大的创新。
三、凸显了文化生态主题
此前的田野调查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从衣食住行、伦理道德、按照文化的结构每个层面进行面面俱到的调查。如马林诺夫斯基对西太平洋的调查形成的多本著作,都是强调参与式的田野调查,以全面地获取当地的所有文化事项的资料。凌纯声等人对湘西苗族开展调查形成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0]涉及苗族的地理分布、经济生活、家庭及婚丧习俗、政治组织、屯田、巫术与宗教、歌谣、语言等各方面。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斐然。然而,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追求面面俱到,反而会使其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浅尝辄止,很难深入到人与自然的依存制约关系。然而,在生态持续恶化、可持续发展受阻的今天,要使民族学的研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重点关注人类如何通过文化的力量去与所处的自然生态打交道,以求得两者的辩证统一与和谐共融,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民族文化研究在这一领域内的探讨则愈加必不可少。《美丽生存》一书的作者便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把文化生态确立为新一轮田野调查的主攻方向,以此凸显文化生态的特殊价值。
食物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食品偏爱。贵州的布依族便对酸味食品情有独钟,他们制作的酸笋是饭桌上的必备佐料。作者通过调查,发现形成这种口食偏爱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布依族居民就地取材,因为他们栖息的河谷盆地是非常适宜竹子生长的地带,竹笋数量多,生长速度也快;其次是由于布依族的生息地常年高温湿润,动植物生长旺盛,以及微生物的滋生活跃,导致食物很快就会腐坏变质。因此,将竹笋制成酸味,不仅能够长期保鲜,还能确保菜肴在不同季节供给的均衡;其三,酸味食品除了自身能够长期保鲜外,还能够抑制不同食物的异味,同时也能提高人的食欲,帮助人的消化。[5]93由此看来,布依族居民的酸笋巧妙地运用了自然赋予他们的资源,是人和生态系统互动制衡中克服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的饮食健康与饮食环境完美和谐的一种必备手段。
此前,有研究者对他们大规模的消费竹笋提出了诘难,认为会给绿化工作带来重大损害。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们居住的村寨周边,竹林始终苍翠欲滴。原因在于,他们对竹林的维护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们认为竹子是一种会自己壮大和繁衍的生物,只要利用适度,对竹林不仅没有伤害,反而是一种更加积极的维护。因而,他们对待竹林既要砍竹,又要挖笋,同时也要培肥土地,甚至长出的竹笋和竹子不仅人要用于制作美食和编制为工具,其他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消费竹叶、竹子、竹笋,当地乡民也不会简单的把这些动物赶开,而是允许它们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取食,他们认为这才是维护竹林的最好手段。[5]95-98该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描写,原因在于他们认定人与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互动制衡关系,如果其间产生了各种不协调,人类就得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加以调试,而调试的手段便是民族文化,这应该就是该书作者所理解的文化生态。他们正是使用这样的主题去展开民族文化的调查,形成的结论才更符合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实情。在他们看来,布依族与竹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加生态的关系,而是文化与生态融为一体的共同体。
对于布依族的这一生存智慧,此前的田野调查仅停留在布依族居民爱吃酸的文化事实的表象上。而作者通过这种确立文化生态为主题的调查方法,却揭示了布依族居民爱吃酸的实质,还说明了这一文化事实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保护环境的智慧,因而布依族能够实现美丽生存。这恰好是创新田野调查方式的结果,这种调查方法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也不是系统地掌握整个文化,而是单就人和自然交往的生计方式、技术操作层面的东西去做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这个主题上去搜集资料,就非常有指向性,能避免把一些无用的、无关的资料夹杂进来,所以能够破除常识性的误判,进而揭示民族文化的实质,把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揭示得更加深入。
因而,当代民族学家们的研究应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精益求精,创新思路与方法,而这种确立文化生态为主题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学人提供借鉴和参考,这是对当代田野调查的又一新思路。
该书中以文化生态为主题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例证,如黔西北高海拔地带的彝族、苗族、白族酷爱炙烤,[5]93荔波县茂兰镇水庆村水族的“九阡酒”[5]101等等,都是当地居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动适应导致的美丽生存下的产物。
四、强化跨文化调查
基于前人对各种各样单一文化的丰富研究,该书作者还采取了跨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方法,并以此指导新一轮的田野调查工作。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该书作者对同一文化事项的深入调查,都不会局限于某个单一民族内,而是将其他民族的类似文化事项展开横向的比较,进行多方面取证和多渠道的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能够对即使是一项简单的文化事实也能做到发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其间的内在关联性。
“免耕法”是当代美国及西欧国家大力推崇的农作方法,“免耕”是指在一定年限内不仅免除播前耕作,也免除中耕等作业。这种种植需要培育新的免耕作物品种、以及高效的除草剂和机械化水平。[11]可见其成本的高昂和对环境的危害性。实际上,免耕种植的创意在中国早已有之,明人田汝成在《炎缴纪闻》中已记载麻山地区的苗族乡民“耕不挽犁,以钱鎛发土,耰而不耘”的免耕法。[12]明朝万历年间江进之所著的《黔中杂诗》云,“耕山到处皆凭火,出户无人不佩刀”与“绝壁烧痕随雨绿,来年禾穗入春香”,[13]也记载了苗族乡民实施免耕这一方法。今天,贵州省紫云县宗地乡的乡民沿袭了这一方法,他们“将杂草灌木割掉架空晾干后,放火焚毁,不等柴灰冷却,就顺着岩缝,撒播小米、天星米或者荞子。即使不用化肥农药,庄稼也照样长得好”。[5]47而其他民族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计方式,对其科学性表示怀疑。作者根据田野调查得知,该地实施免耕法是因为该地生息在石多土少、基岩裸露的喀斯特山区,坡面十分陡峭容易导致水土流失,而实施免耕法可以抑制土壤流失,辅以火焚能加快成土的速度,从而缓解土壤稀缺的不利条件,这是乡民为适应当地恶劣的生态环境而实施的有效对策。作者通过跨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能够促进人们纠正对这一民族的文化偏见,苗族的“免耕法”并不落后,而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它较之于美国提倡的“免耕法”,反而科学百倍,它不仅可以增加土地资源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还能减少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抑制水土流失,使生态系统重归于平衡。如果不是将苗族的文化与其他的民族所倡导的“免耕法”相比较,苗族传统耕作技艺的合理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调解作用,都无法得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这是以往仅单独研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不能发现的新见解。因而,跨文化的横向对比研究是一项田野调查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是对中国式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新探索。
同样是来自于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罗伊·拉帕波特对新几内亚一个少数民族的祭祖之猪宗教仪式的调查实例,证明了人类拥有能动调控环境,使失衡的生态系统重归于平衡的天才智慧。[14]《美丽生存》作者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生活于月亮山腹地孔明乡的苗族人民的“牯藏节”也同样具备这种智慧。
“牯藏节”是苗族最隆重的节日,每隔12年举行一次,每个家族都要宰杀公水牛献给祖先和过去十二年中过世的亲人。[5]137这个节日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宰杀水牛来祭祖,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非议。然而,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的乡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与当地种植水稻十分艰难有关。孔明乡水田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种植水稻需要牛来维持阳光与水田的关系,而水牛过多或过少都将影响到水稻的产量。所以祭祖杀牛其实是为了控制牛的数量平衡,只要留下对他们种植水稻最合适的数量即可。而外界却并不深究苗族人民的祭祀活动与生态调控之间的关系,是不懂得“牯藏节”宰牛祭祖习俗里面所含有的生态制衡观念而形成的误解。
新几内亚民族的杀猪祭祖与孔明乡苗族人民的杀牛祭祖,同样是宗教行为,通过跨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发现相隔一万多公里的两个国家的两个民族的宗教行为背后,却同样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能动调控能力。因而,不同民族的宗教行为不仅是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人与环境协调共生的必备举措,要发现这一点,只有通过跨文化比较的田野调查方法。这种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能给人们认识宗教行为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是对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又一探索。
在该书中以跨文化横向比较研究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贵州乌蒙山区的乌蒙马与蒙古马、河曲马的比较,[5]61黎平县九龙村侗族干栏式建筑的生态维护功能与三都县水东村干栏式建筑的趋吉避凶功能。[5]108-117囿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结语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十分艰辛曲折,从蔡元培先生开始,至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杨成志、江应樑、梁钊韬等人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田野调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民族学的研究和田野调查。[15]可见田野调查方法对民族学研究至关重要,而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准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然而,田野调查不是金科玉律的教条,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尤其是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21世纪,田野调查更应该创新。《美丽生存》一书所反映的田野调查就是一个创新的典范,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追踪式调查、紧扣当代现实确立的以文化生态为主题去展开人与生态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开展的跨文化横向对比研究,这些都可以视为21世纪中国式田野调查的新动向。
[1]刘锋.民族调查通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79-87.
[2]杨庭硕.贵阳市高坡公社苗族葬习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1981(2):21-30.
[3]杨庭硕.苗族习俗结构刍议[J].思想战线,1988(6):64-70.
[4]杨庭硕.以贝为饰习俗成因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53-56.
[5]杨庭硕,罗康隆.美丽生存[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6](唐)魏征.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172.
[8]罗荣宗.苗族歌谣初探 贵阳高坡苗族[M].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184-201.
[9][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04.
[10]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1]祝修恒.国外免耕法综述[J].新疆农业科学,1978(3):43-45.
[12](明)郭子章.黔记·诸夷考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37.
[13]杨庭硕,皇甫睿.对江进之《黔中杂诗》所涉明末贵州民族文化与生态背景的再认识[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5-52.
[14]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8.
[15]陈兴贵.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贵州民族研究,2007(6):99-106.
(责任编辑 王光斌)
On Modern Creation of Chinese Field Work by Re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Existence in Guizhou
YANG Qiup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Field work is considered as the basic method for ethnology research and the basic approach for primary source.Ethnologists have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is metho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fter “Bronislaw Malinowski Revolution”. However, this field work method established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is only applied to his epoch. Field work method should change with the times for a new life of ethnology. The book,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Existence in Guizhou, presents a general cognition on new tendency of Chinese field work, and provides a new view,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new method for field work of the 21th Century. The field work method provided in this book, which contain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raceable investigation, cultural-ecology-theme and transcultures comparison, is a new attempt and referential model for modern field work.
field work; creation; Chinese model;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Existence in Guizhou
D633.1
A
1674-9200(2017)04-0008-05
2017-03-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16ZDA157)阶段性成果。
杨秋萍,女,苗族,贵州铜仁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016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