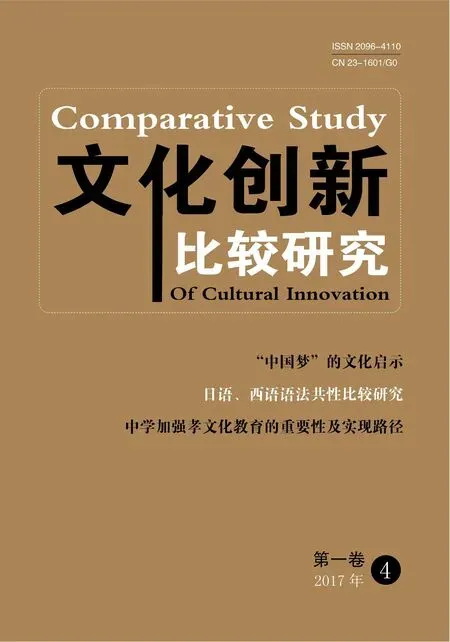从福柯女性主义压迫视角解构凯特·肖邦的《觉醒》
杨 茜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6)
从福柯女性主义压迫视角解构凯特·肖邦的《觉醒》
杨 茜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6)
凯特·肖邦的《觉醒》发表于1899年。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位已婚的年轻女子艾德娜·庞德烈如何拒绝传统父权思想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成长历程。本文运用“鸟”的象征意义,描绘艾德娜如何通过不同阶段的自我重塑摆脱“鸟笼”般的父权制度而获得自由。同时,文章运用福柯女性主义理论、玛丽莲·弗莱的压迫理论以及桑德拉·李·巴特基的内化理论探究女性压迫的本质,论证女性为了摆脱父权制度的压迫必须具有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对自我身体的控制。
凯特·肖邦;《觉醒》;女性压迫
凯特·肖邦(1850—1904) 的《觉醒》发表于1899年,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位已婚的年轻女子艾德娜拒绝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追求自我独立和性自由的成长历程。凯特·肖邦在《觉醒》中所描绘的是上流阶层的白人女性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克里奥尔女性所受的压迫,肖邦以此为例说明西方女性主义的斗争目标主要是实现自由。哈利·布莱德认为否认平等和博爱就会把女性排除参与社会活动[1]。哈利强调平等和博爱是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家庭主妇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自由,而要实现自由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有完全的支配权。虽然有很多评论家采用了肖邦的“鸟”的象征意义来解析艾德娜的觉醒,但是本文运用新的理论把文学与文化批评结合在一起,通过玛丽莲·弗莱的压迫理论、桑德拉·李·巴特基内化理论探究女性压迫的本质以及福柯的权利现代化理论解构这位激进女性主义者是如何挣脱父权制度般的“鸟笼”。从而论证女性为了摆脱父权制度的压迫必须具有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对自我身体的控制。
1 “鸟”的象征意义与女性形象关联
“鸟”的象征意义被看成是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很好诠释。罗伯特·贝克在提到社会文化如何定义女性形象时,他提出大部分描绘女性的术语把她们看成“非人类”或者“少数群体”。在贝克的书中,“鸟”被描述成“金丝雀、鸽子、小鹦鹉”以及“蜂鸟”等各种形象。他在书中这样写到,“除了‘蜂鸟’,其他所提到的‘鸟’都被看成是弱小的和可爱的。所有的鸟都是驯养的,被看成宠物。她们没有攻击性,不太聪明、不太高尚[2]。”贝克对“鸟”的描写揭露出社会对女性的固有偏见。女性往往被看成弱者或他者,她们不能主宰自我命运,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思想被禁锢在牢不可破的枷锁中,永远感觉不到一种理性意志的尊严。
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玛莉·沃斯通克拉夫在其《妇女权利宣言》一书中也用“鸟”的形象来暗指女性在父权文化下所受的压迫。她在书中这样描述,“女性被关在笼子里,就像带有羽毛的种族,她们整天除了用漂亮的羽毛装饰自己,什么都不做。带着可笑的尊严在自己的栖息地潜行[3]。”书中用“关在笼子里的鸟”暗指女性被束缚在婚姻里,这也正是艾德娜所面临的困境。19世纪末美国社会婚姻观认为,在婚姻中女性被当作他人的物品而不是自我命运的主体,女性不过是男人的私人物品。叶英教授在文章中也提到,“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到故事发生的19世纪90年代,婚姻历来被视为女人最理想也最应该的生活模式,对男人的依赖也被看做是女人味的一种体现。社会总是极力提倡温顺、居家、已婚的妇女形象,认为女人的社会功能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4]。”书中艾德娜意识到雷昂斯·庞德烈仅仅把她当作任凭他处置的有价值的私有财产,而非独立有思想的女性[5]。世纪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莱把女性的压迫比喻成“笼子里的鸟”,她的压迫理论也是基于这个比喻。在《觉醒》中,凯特·肖邦运用了大量这样的词汇和意象,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理解女性的压迫和她们对自由的渴求。
小说开篇描写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形象,“屋外笼子里的鹦鹉,黄绿相间,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走吧,走吧,走了才好!’它会一点点西班牙语,也能说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当然挂在大门另一边的那只嘲鸟是个例外。微风中,嘲鸟发疯似地鸣奏着它风笛般清脆的曲调[5]。”书中所刻画的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鹦鹉是孤单的、禁锢的。正如艾德娜一样,虽然她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克里奥尔人,但是在婚姻中,她也象这只鸟一样经历同样的孤独无助的心境。小说开篇之处,艾德娜与一群新奥尔良的富商太太在避暑胜地格蓝岛度假时,结识了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艾德娜发现她与作为克里奥尔社会典型完美女性的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在思想上有很大差异。“像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这一类女人宠爱自己的孩子,崇拜自己的丈夫,将抹煞自我、充当孩子和丈夫天使般的守护者视为神圣的特权。她们的天使翅膀不是用来飞翔和抗争的,而是为她们的丈夫和子女服务的[6]。”相反,艾德娜告诉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她永远都不会为孩子或任何人舍弃自己,她要为自己而活。
玛雅·安吉罗在《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一书描绘到,父权社会的语境让女性丧失了自由表达她们思想的权利,女性应该从压迫和沉默中寻求自我[7]。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是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行,她们被当作生儿育女的机器和丈夫的个人财产。她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虽然表面生活华丽衣食无忧,但却困在笼中毫无自由,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行。把女性与笼子里的鸟联系起来正是女性渴求反抗的体现。弗莱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你只看到笼子里的其中一根线,你就看不见另外一根;如果你的视线只是你眼前的焦点,你就看不见另外的景象,也就更不能看到为什么一只鸟不能飞到它想去的地方[8]。”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像阿黛尔一样的已婚女性看不到她所遭受的压迫。就像这只笼子里的鸟,她的视线只局限于笼子里,她总是与遭受同样压迫的女性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下。类似的生存环境让女性看不到自身所遭遇的压迫,从而丧失对自由的追求。然而在格蓝岛度假时,罗伯特的出现让艾德娜彻底觉醒,她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被完全激发出来,她开始思考自我的存在价值。于是艾德娜下定决心走出“笼子”和她熟悉的环境,她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被罗伯特的爱所唤醒。
小说接下来写到艾德娜独自与罗伯特的母亲雷布伦夫人在一起谈论克罗伯特·雷布伦。她们通过语言表达了彼此的愉悦,因此福柯把她们之间的对话称为“思想与灵魂的碰撞”[9]。艾德娜也拜访了拉蒂诺尔夫人和莱茨小姐,与她们交流彼此的思想。从她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艾德娜内心并不赞许她们的生活。她并不赞同像拉蒂诺尔夫人一样成为传统的贤妻良母,也不期望成为莱茨夫人一样离群索居的老处女。艾德娜开始清楚的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她试图打破这种束缚,勇敢追求自我价值,重构女性的权利。当罗伯特离开美国去往墨西哥以后,艾德娜不再理会丈夫与旁人的感受,决定搬出家,住进不远的小屋。她从远处眺望自己“地牢般的家”决心永不回头。艾德娜已下定决心从“鸟笼”般的婚姻中解脱出来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除了自己以外她永远不属于任何其他人。
2 女性压迫本质探究
《觉醒》书中所描绘的拉蒂诺尔夫人和莱茨小姐的女性形象早已被社会定义。前者是一个典型的克奥尔贤妻良母角色,后者是一位白人老处女形象。她们两者都无法自由的选择她们的社会角色。事实上,她们成为了社会所认可的两种不同女性模型。拉蒂诺尔夫人被定义为“完美女性”,很好诠释了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因此受到社会尊重。莱茨小姐虽然行为有点古怪,但因为她的音乐才华仍然被认可为一位出色的艺术家。桑德拉·M·吉伯特与苏珊·古巴尔把莱茨小姐定义为“女性怪物”,因为作为一位艺术家,莱茨小姐具有男性的技能即创作能力。另外一方面,她们把拉蒂诺尔夫人看成是“女性天使”或者是“经典女性形象”[10],这些社会所标签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女性寻求自身定位,使得她们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与“他者”。书中所描绘的艾德娜的婚姻生活在物质上是幸福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压抑和迷失的。
桑德拉·李·巴特基把女性的精神压迫分为三种类型:“社会枷锁、文化定义、性对象”[11]。正如被殖民的人们一样,女性的精神压抑也被内化,这迫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种内在的压迫是微妙的是逐渐的侵蚀。以莱茨小姐为例,她被社会斥责为太独立、孤立,难以与整个社会融合。虽然她并不像拉蒂诺尔夫人那样完全被社会所束缚,但是她还是会参加聚会因为这是她唯一一种方式被社会接受。莱茨小姐才华横溢的音乐才能并不能得到社会的称赞,她仍被社会批判太另类。拉蒂诺尔夫人却因为她的贤妻良母形象被社会接纳与尊重。社会认为女性唯有的美德便是对男性(特别是丈夫)的恭敬服从。女性理所当然应当把父亲和丈夫的话作为必须遵循的教条加以无条件的接受。由此可见,女性文化是根植于父权制度,她们只有创造父权文化所定义的“乌托邦式生活模式”,她们才被社会所认可。
3 福柯现代权利理论分析女性压迫
福柯认为经济并不是所有罪恶的源泉,国家控制或调节也不是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法。他意识到压迫并不源于上述原因,每个人的压迫方式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但是当一个人把压迫内在化以后,他或她就陷入被压迫者和从属者的冲突角色。福柯更加关注权力对不同性别的人是如何运作和形成的,而不是去探索权力作为一种需要摧毁的消极力量是如何起源。正因为这样,福柯声称:“身体是铭记事件的层面,是自我拆解的处所,是一个一直处于风化中的器物。谱系学,作为一个系统的分析,因此连接了身体和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12”
谁来决定女性的社会身份构建?福柯用他的权力知识学说分析知识在社会政治控制下的角色。如果社会是父权制的,女性的自我知识便成为了其反抗的阻力。女性对知识的渴求就会加重自身的压迫。早在18世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可称作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先导之作的《女权辩护》中,对女性的教育模式和理念进行了宣战。在受教育这个问题上,女性被打上固有标签,社会对女性的定义为不具备理性思考即抽象思维的能力,女性也不应当培养这样的能力。当启蒙时期规训力量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时,女性的身体被控制成为工厂的产品,这似乎成为了历史的趋势。女性的身体需要社会对其规范或者为了小家庭去适应父权制度下的社会文化。家庭单位似乎成为了女性成功的标志,也成为了女性生产和再生产的价值中心。换言之,女性的教育应该集中在家庭生活,父权与夫权理应成为女性受教育的源泉。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社会的很多机构,例如学校,精神救助站,监狱开始规范人类身体活动使其能够遵守社会规则。这些机构成为抑制人类欲望的机构,直到人们学会抑制他们所谓邪恶的思想和追求。福柯认为,“政治医疗机构给人们开了一系列的处方,不光针对他们的疾病而且关乎他们的存在方式和行为(饮食,性行为与生育能力以及居住条件)……医生这一行业便成为伟大的顾问和专家,虽然不是统治的艺术,但至少可以观察、修正和改进社会个体[13]。在《觉醒》书中,当庞德烈一家返回新奥尔良后,艾德娜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重点之所在,变得更加注重自身的享乐。她渐渐脱离了社交圈,放弃了一些传统母性应尽的职责。雷昂斯担心她精神异常,为她请了医生。医生对他说,“她是有点古怪,她不再是她自己……她的脑袋在思考女性的永久权力。[5]”医生实际发现了艾德娜隐藏的女性主义思想,从而就像疾病一样对其进行诊断和治疗。在医生和雷昂斯看来,女性对自由的幻想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会侵蚀女性缺乏理性和推理的大脑。艾德娜知道父权制度将会诊断她的“疾病”,因此她向一位朋友自白,她的丈夫一旦发现她会离开他,一定会认为她是“疯子”[5]。在医生建议艾德娜住院之前,她就决心要搬出家。在家里艾德娜感觉她残酷的被身边每一个人甚至她自己监视,因为她总是被迫意识到自己家庭主妇的角色。这种内化的监督和压迫正是她从社会所学到的如何成为一位优雅女性的规范化行为结果,而这些规范控制了女性的行为举止,禁锢了女性对自由的欲望。
4 女性追求自由之路
如果说父权制度充斥着权力和知识,那么艾德娜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否可以从现代权力的规范中摆脱内在压迫呢?依笔者之见,艾德娜的自我主体意识实际已经被唤醒,但是她的自杀证明了她并不愿意和她希望实现的自由妥协。她不断寻求自由的步伐把她从一位优雅的女性变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不再穿紧身衣佩戴耀眼的首饰,不用每天化妆,搬到独立的小屋,学会自我决断,用各种方式解放自我身体和自我意识。艾德娜把罗伯特理想化,并把他和其他男人区别开。她希望从与罗伯特的愉快交往中恢复自我内心的声音和自我身体的解放。
艾德娜期望罗伯特能够理解她的内心,把她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来对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罗伯特从墨西哥回来后,他被艾德娜的自我意识转变所震惊,同时被艾德娜的自我独立宣言所击退。当罗伯特向艾德娜表明他会从雷昂斯身边带走她时。艾德娜回答说:“当你讲到雷昂斯会给我自由,你真是个傻瓜,把你的时间浪费掉,梦想那不切实际的事情。我现在不再是雷昂斯任意摆布的财产了,我决定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如果他说‘嘿,罗伯特,你把她带走吧,快乐去吧,他是你的了’,我会同时嘲笑你们两个。[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艾德娜不再是“笼子里的鸟”,而是“一只自由的鸟”,她从自我意识角度审视她的“旧笼子”,她决定再也不想住进类似的“笼子”。
罗伯特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他选择了逃避与退缩。艾德娜也清楚地意识到罗伯特和其他男性没有本质的不同,没有男性能接受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新女性。既然艾德娜不能拥有她想要的生活,她就变成了“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从空中坠落于水中。她赤裸裸的走向大海,“就像新生的人类。[5]”艾德娜应该是19世纪时期较早从死亡中寻求自由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需求独立自由之路是受到社会道德、法律与伦理的约束,小说结尾让读者独自去想象她的死亡到底是自由还是重生。她飞向未知世界并不是文学所批判的行为,反之,由于艾德娜的女性自我意识使她拥有对自我身体和思想的控制权,所以她敢于摆脱丈夫、小孩、社会的束缚。她有权利自我定位同时超越社会对一位已婚女性的框架。因而,她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没有自我和尊严地活下去。
5 结语
综上所述,艾德娜敢于拒绝接受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定位,敢于从身体和精神压迫中解脱出来,已然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新女性的代表。从艾德娜最开始决定独自一人搬出家,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抗其内在的压迫,到后来她意识到如果她独自呆在这样的“鸽子笼”,她只能成为另外一个莱茨夫人。于是,艾德娜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来抵抗,她以放弃生命的代价拥有了自我,获得了新生。这样的艾德娜从身体和精神上获取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与自由。但仍有很多像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这样的女性默默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从而笔者认为,要打破女性内在压迫和争取女性的自由与平等,唯一的方式就是女性的团结。只有女性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提高自我觉醒意识,学会如何在更深层次基础上加强联系而不是表面的交流,这样女性才能冲破父权制度的束缚。同时,艾德娜的悲剧也应该唤醒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和尊重,社会应该更多的聆听女性的内在需求,更多关注女性的精神压迫,并找到新的方式打破这种压迫。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
[1]Brod, H.‘Profeminist Men’s Movement: Fraternity,Equality, Liberty’, [M].in Kourany,J.A., Sterba, J.P.& Tong, R., Feminist Philosophies: Problems,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 2nd ed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1999:504.
[2]Baker, R.‘“Pricks”and “Chicks”: A Plea for“Persons”’[M].in Kourany, J.A., Sterba,J.P.& Tong,R., Feminist Philosophies: Problem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2nded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NJ, 1999:38.
[3]Wollstonecraft, M.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M].Hagelman, Jr.,C.W., W.W.Norton, New York,1967:98.
[4]叶英.是社会规范的叛逆者还是遵循者?——从文化视角看《觉醒》中单身女人赖茨的生存模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130-131.
[5]Chopin, K.The Awakening [M].2nd edn, ed.Walker, N.A., Bedford, Boston, MA,2000 :300.
[6]刘瑜,张丽.觉醒的艾德娜——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肖邦的《觉醒》[J].时代文学,2008(20):173-175.
[7]Angelou, M.I Know Why the Birds Sing [M].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New York,1969:65.
[8]Frye, M.‘Oppression’ in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M].CrossingPress, Trumansburg, NY,1983:4.
[9]Fou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Hurley,R.,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4:20.
[10]Gilbert, S.M.&Gubar, S.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CT,1984:21.
[11]Bartky, S.L.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M].Routledge,New York,1990:23.
[12]Foucault, M.‘Nietzsche, Genealogy, and History’ [C]//The Foucault Reader, ed.Rabinow, P., Pantheon Books,New York,1984.
[13]Foucault, M.‘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The FoucaultReader, ed.Rabinow, P.,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4:283-284.
Z228.4
A
2096-4110(2017)02(a)-0100-04
杨茜(1982.1-),女,汉,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美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