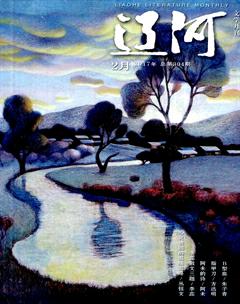黑洞
迟庆波
1
我走进篱笆院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天空中飘着细雨,隐约能听到“杀杀杀,杀杀杀”的声音,我不知道脑海中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这个不祥的词汇。走在我前面的傅国华扯了一下我的袖口,用眼神示意我赶紧进入房间。
我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用迟疑的目光打量着周边的环境。火车站储煤场的探照灯的余光扫进院子,能清楚地看清眼前细细的雨丝。篱笆墙有一米二的高度,用的是原木劈成的有棱有角的柈子。黯淡了的灯光和储煤场的余光释稀了篱笆墙的惨白。我摸了一把杖勒子,是针叶林中那种细长的日本松,主人用十号线把它和杖柈子捆绑成一个整体,无疑是牢固的。我依旧不放心,手掌用力压了压,给我的信息回馈是:即使两脚踩上去,绝对不会出现我意念中的那种意外,并且能够迅速地逃离现场。多年以后,退休了,细细想来,如果出现了某种意外,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傅国华挽起我的胳膊,把我塞进了篱笆院的门。
篱笆院是这家饭店的名字。我不知道老板为何做了这样一个土得掉渣的招牌,不过,和这个环境倒是十分匹配,也许,意念中的返璞归真会在篱笆院中得到慰籍。
餐厅的卫生还没有打扫,有些杯盘狼藉;水泥地面上仍留有斑斑驳驳的泥脚印,显示着夜晚中推杯换盏的辉煌与灿烂。有两男一女正在墙角的一张餐桌上斗地主。其中一男子看见傅国华,急忙站起来,慌乱中碰倒了一只水杯。无人顾及的杯子,在桌面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啪”的一声摔碎在地面上。
男子只顾扭动着腰肢,越过餐桌旁边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子,握住了傅国华的手。
傅所长,这大半夜的,来吃饭?
傅国华说,值班,饿了,所以就来了。
傅国华在撒谎。我暗想,警察撒谎,脸都不红。
傅国华是矿山派出所的所长。男子递给傅国华一支香烟,点燃。又递给我一支,说,您是金龙煤矿的总矿长吧?
我一怔,问道,您怎么认识我?
男子答道,矿工们经常说起您,经常说起您。他无意中加重了语气,嘴角翘起的同时淹没了偶尔露出的狡黠。我摸出打火机,冲他一咧嘴,点燃了香烟。
那男子说,傅所长,在老地方就餐?
傅国华摇摇头,单间也不方便,就在李梅的房间吧。
那男子对着手里握着一把扑克牌的女子喊道:李梅,去把你房间收拾一下。她就是李梅?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她两眼。李梅站起来,瞅了一眼傅国华,迅速地收回了目光。我隐约感觉到,李梅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究竟是什么,我又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我和傅国华跟着李梅,穿过一道逼仄的走廊,来到后院,进了李梅的房间。
灯光是淡红色,房间里就显得浪漫而温馨。炕上的被子没有叠起,一少半被角儿重叠在红色的被面上,露出了洁白的褥面。 淡红色的灯光浸染了褥子的洁白,暖色基调就在我的脑海中氤氲成一片梨花带雨般的画卷。窗子开了一扇,夏季后半夜的风依旧有些瘦硬,带着细雨的湿润,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咕咚”一声砸在了炕上。
李梅匆忙把被褥卷起来,双膝跪在炕上,关闭了窗子,拉紧了窗帘。这一系列动作相当娴熟。这是一个十分麻利的女人。
李梅冲我笑笑,转身出了房间。我爬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看了一下外面的环境。细雨中的篱笆墙若隐若现;篱笆墙不远处是火车站,能清楚地看到或红或绿的信号灯。我想,如果有意外,可以跳出窗子,翻过篱笆墙,迅速地消失在夜幕里。
2
夏夜是寂寥的。
我拿起手机,拨打了傅国华的号码。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二十三点。我问傅国华在哪儿,他说在派出所睡觉,没有值班。他问我什么情况,我说寂寞,能否出来聊聊。他说哪儿,我说在“人民桥”上。
我倚在桥栏上,抽了三支烟,傅国华才来。他问我,多久没回家了,我说,有一个半月了。他又问,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得等到雨季过了。
傅国华点燃一支烟,笑着说,你就是胆小,井口又不是你们家的,该回就回。
我把两肘顶在护栏上,桥下的江水“轰轰轰,轰轰轰”甚是骇人。
傅哥,去年下游的江堤决口,淹没了一座煤矿,死了七十六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傅国华不做声,仰视着天空。
天空一片狰狞,没有一丝星光。傅国华叹道,是啊,所以,我也不敢回家。我问他,傅哥,你不敢回家,是为公还是为私?
傅国华把尚未燃尽的烟蒂弹出去,亮光划出了一道漂亮的抛物线。他淡淡地说,我说为公,你信吗?
我说,我信。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别扯淡了。
我说,傅哥,你要不当矿山派出所所长,你弟弟的煤窑能开成吗?
傅国华哈哈一笑,说,兄弟,没有你,我弟弟的煤窑能开成吗?
我觉的,傅国華这个人不简单。天空中滚动着的乌云压在了我的心头,要下雨了。
我和傅国华沿着江堤漫无目的地走了好久。我真佩服他的脚力,尽管他比我大了十七岁,仍然把我拖累得有些疲惫。
傅国华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问,去哪儿?傅国华说,喝茶去。我跟着他上了车。
傅国华对司机说,去篱笆院。
我的心陡然间提到了喉咙,上不去,也下不来。
出租车的灯光像黑夜里幽灵的眼睛,能看见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不停地摇摆,“沙沙沙沙”的声音刺穿了我的耳膜。
房间里是寂静的,“沙沙沙”的声音似乎一直跟随着我,我分不清是雨刷器的声音还是雨水的声音。
房门轻启。李梅把茶具放在炕上,我不敢相信,在这偏远的煤矿小镇上,还会有这么精致的茶具。是李梅的,还是老板的? 我摇摇头,想这些干嘛呢?既来之,则安之。
李梅端来了两碗肉丝面,傅国华吃得很快,大约两分钟的时间。我不清楚是饿了还是做警察养成的习惯。
当我吃完的时候,傅国华一杯茶已经喝完。李梅坐在靠窗子的一边,拿起茶壶,为我斟满一杯茶,茶杯很小,比牛眼珠子大不了多少,翡翠色的杯壁晶莹剔透。杯与壶的色泽似山谷涌泉,自然流动,合二为一。尽管房间里的灯光是黯淡的,依旧能看清茶水通透而不浑浊,我把杯子端在唇鼻之间,芳香涌入鼻腔穿透肺腑,恰如空谷幽兰一般。杯子的厚重与茶水的柔软相拥,温暖了我鼻梁上的镜片,悄然间升起了两片薄雾。薄雾朦胧了李梅,我忽然意识到,她,就是那朵空谷中的幽兰。
傅国华呷一口茶,双目的余光射向我,问李梅,你认识他吗?
李梅把目光投向我,双手捧着杯子,笑着说,傅哥,不认识。你给介绍一下呗?
傅国华把我做了极其简要的介绍。李梅笑着,伸出了手。我轻轻地握了一下这个女人的指尖。对于这个女人,我早有耳闻,在矿工宿舍里无数次想象着她的模样。在井下以及和工友的会餐后,很多人总是把这个女人挂在嘴边,甚至绘声绘色地毫无遮拦地描绘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很多时候后,在和我爱人同床共枕时,也经常浮现出意念中的李梅的影子。呼风唤雨之后的宁静,我经常在黑暗中自责,这种看不见的犯罪感吞噬着我,直至梦幻中的另一个世界。
3
傅国华走了。
李梅的外衣薄如蝉翼,高耸的乳房笼罩着朦胧的面纱,额头上渗出细碎的汗珠。她说,哥,现在做吗?
我知道,她说的“做”是指什么。我摇摇头。
李梅一怔,说,是没准备好吗?我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过,眼前的这个女人和我意念中的那个影子比较起来,更具有女人的味道。何况,这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比起那个影子要更现实更丰满更具有诱惑力。
是第一次吧?
我点点头。
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来的次数多了,就习惯了。
李梅脱去外衣,一片洁白泻下来,像挂在空中的瀑布,房间里顿时明亮起来。她站起来,解开牛仔裤的腰带,裤子一点一点往下脱落,瀑布一点一点在升高。慢慢地,慢慢地,瀑布真正的悬挂起来,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嚯嚯嚯,嚯嚯嚯”的流水声从天国传来,像天宫里奏响了悠扬的音乐。
房间的隔音并不好。隔壁传来了一个女子“啊啊啊,啊啊啊”的叫声。我猜想,也许是篱笆院的老板是故意把房间设计成这样的格局。“啊啊啊,啊啊啊”的声音迅速膨胀了我的荷尔蒙,把我一脚踹进了那一片洁白之中。流水沐浴着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倾泻而下的瀑布的速度加重力把我深深地砸入水潭之中;舒缓的音乐从水面拂过,覆遮了所有的波澜壮阔。
我感到有些窒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气息湿润了她的前胸,如雨后的梨花挂满了水珠。
我昂起头,不敢看李梅漂亮的眼睛,她的眼睛会说话。冥冥之中,我听见李梅轻轻叫了一声,哥。
哥?我对这个字特别敏感,特别是女人说出这个字。我急速膨胀了的血管里的血液直灌头顶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快速地瘪了下去。
我忽然看见小妹站在教室的门口,鞋子和裤脚都湿漉漉的,她一只手擦着小脸上的汗,一只手把装满干粮的篮子递给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哥。然后,转身,向学校的大门口跑去。我知道,小妹还得跑十五里的山路回家干活来供我读书。还没等我叫一声小妹,她的影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年,她十二岁。
我整个身躯疲软下来,全无斗志。
我坐起来,双手捧在脸上,拭去汗水中溶入的李梅的体香。
李梅也坐起来,眼睛传递给我的是莫名其妙的询问:哥,你怎么了?
别叫我哥!我低沉的声音喊道。我自己也感觉到,目光里射出的一定是犀利的寒光。这束寒光里隐含的信息是对李梅最严厉的警告。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警告对于李梅来说是毫无意义,也是毫无道理的。她知道什么,她又能知道什么呢?我不能这样对她。我摸到枕边的眼镜架在鼻梁上,对着李梅笑了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道歉是真诚的,但我又觉得玷污了“真诚”这两个字。
显然,我的举动把李梅吓着了。她赤裸着身体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说,李梅,对不起,刚才,我想起了小妹,她,曾经和你一样,做着相同的职业。我仿佛看见了小妹胳膊上那块紫色的疤痕。
4
翌日,我在办公室接到了傅国华的电话。他问我,“做”了没有,我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问他,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不会是害我吧?他在电话里压低了声音,正色道,你把一块采区划给了我弟,这是多大的恩情,我怎么会害你?我说,不要再提采区的事,这件事到此为止,让矿上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傅国华问,你说话方便吗?
我说,我刚从井下上来,办公室就我一人。我再一次提醒傅国华,不要再提采区的事。
傅国华说,我就喜欢你谨小慎微的这股劲儿,和你这样的人办事,最稳妥。你把各种不利因素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晚上我请你吃饭,老地方。不等我回答,傅国华挂了电话。
我对着电话喊了一句:我又犯不到你手里,你牛B个鸟?
孔乙己酒館是小镇上最不起眼的饭店。傅国华喜欢这里,我也喜欢。最重要的是这里清净。傅国华最大的优点是不喝酒,我的酒量是半瓶啤酒。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滴酒不沾,他说,他参加过珍宝岛战役,本来要提升排长的,因为酒后偷了部队一千发教练弹,然后就复员了。虽然他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傅国华点了两个菜,一个雪中送炭,一个醋溜腰花。雪中送炭,就是山楂罐头和银耳的组合,傅国华最喜欢这道凉菜。
我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傅国华要了一瓶冰糖雪梨。
傅国华说,李梅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也没做,说你是个好人,今晚请你去喝茶。
我说,傅哥,你别忽悠我,李梅怎么能有你的电话?
傅国华喝了一口冰糖雪梨,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什么人的电话都得有。
我半信半疑,一时又找不到反驳他的证据,只是感觉到他和李梅的关系不一般。我暗自思忖,我和李梅的接触,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傅国华是精明的,他说,兄弟,我不会害你,我弟弟还要指你挣钱呢。
我觉得胡乱猜测朋友,有些不地道,就开玩笑说,你弟弟的井口,不会是你的吧?
傅国华一脸的严肃,说,我只是帮我弟弟一点小忙,怎么会是我的呢?
傅国华转移话题,不谈井口,又提起李梅,说,你要去,就后半夜,前半夜,她要“干活儿”。我说,我懂。
李梅领着我穿过逼仄的走廊,来到她的房间。炕上的被褥很整齐,就像军营的“豆腐块”,棱角分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昨晚被褥的凌乱。李梅读懂了我的心思,说,我今天没“干活儿”一直在等你。
我说,是没有“活儿”?
李梅莞尔一笑,说,“亲戚”来了。我先是一怔,继而读懂了她莞尔一笑里暗藏着狡黠,明白了她说的“亲戚”是什么意思。我说,昨晚,对不起。
李梅给我斟满一杯茶,递给我。我刻意躲避着她的手指。
我又吃不了你,不用这么拘谨。
我吸了一口茶,能听见满屋喉咙响。
你和老傅很熟?
李梅喝了一口茶,说,不是很熟。
你怎么有老傅的电话号码?
哥。李梅停顿了片刻,我的心紧了一下。
哥,你别问了。李梅的眼睛瞅向别处,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说,你是个好人,昨晚……
我暗自好笑,我是好人,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打断了李梅的话,说,昨晚,我有心理障碍。
是因为你妹?
嗯,我看到你,就想起我妹妹。我妹妹也曾干着和你一样的“活儿”,她遇见一个变态的人,每次的时候,那个人就抽打我妹的臂膀,他从她痛苦的叫声中寻找着快乐。
你妹可以拒绝他啊。
那个人很有钱,我妹为了钱……
我的牙齿咬住了杯子,让茶水升腾的薄雾挤压住眼眶中的潮湿。准确地说,小妹是为了读大学的我。
李梅未必能理解我,但她一定能理解我妹妹。她好久没有说话,眼睛直视着我,但目光中没有了摄人心魄的清澈和神韵,出窍的灵魂仿佛游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知道她为了谁。
游离的灵魂也许走得太远了,彼此的默默无语似乎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尴尬。
你和很多人不一样。李梅像是自言自语。我意念中的李梅应该是不拘小节的甚至是狂放不羁的。这种意念的来源并非起于傅国华,尽管是他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识了这个女人,但是,我还没有了解她。或者说,我面前的李梅和工友嘴中的李梅判若两人。一个是三十出头风韵十足且狂野的站街女;另一个是温婉的忧郁中略有羞涩的小家碧玉。我分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李梅,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尽管我喜欢这个女人,尽管我有着生理上某种十分渴望的冲动,但在心灵深处的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没有被这个女人完全占领。我必须在有了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之后,才能完成向往已久的美妙瞬间。我必须顺着李梅的自言自语和她继续聊下去。
有什么不一样?我反问李梅。
你像文化人。李梅给我斟满水。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念了几年书。
你以前是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突然觉得,我问了一句废话。
你别管。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去了煤矿?
我可以抽烟吗?
李梅从包里拿出一盒烟和打火机递给我。在火苗和烟卷亲吻的瞬间,我想:李梅怎么知道我的过去?
我深吸一口,咽了下去,让烟雾在我的腹腔内慢慢循环,而后,从鼻腔中徐徐飘出。我说,我领着学生踢足球,把一个孩子的腿踢残了。所以,我就到了煤矿。
李梅问,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说,有。但煤矿挣得多。我和你殊途同归,都为钱。
李梅笑了,说,今晚“做”吗?
我说,你家“亲戚”不是来了吗?
李梅说,我骗人的,为等你。“亲戚”每个月月末来。
5
下过一场中雨,又下过两场小雨,天气便一直晴好。
我去李梅家是两周以后的事情了。
通化市和通化县县市重名,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我是通化市人,李梅是通化县人,我所在的煤矿坐落在通化市和白山市交汇处的驼峰岭,翻过驼峰岭,就是白山市地界了。李梅的家和辽宁省接壤,仅有一桥之隔。我的家安在通化市区内,李梅的家在农村。
李梅领着我来到一家靠近大道的农家门口,告诉我这就是她的家。夕阳的余辉洒在暗红色的铁门上依然能感受到一股燥热袭来。铁门虚掩着,有一扁指宽的缝隙。围墙是村里规划过的,整齐划一,红色的琉璃瓦在夕阳的余晖里熠熠生辉。李梅推开了一扇铁门,门轴的旋转在铁与铁的摩擦之后发出一股刺骨的寒流。房子的外墙壁上贴着橘红色瓷砖,流水般的光亮在辗转腾挪,和房顶的琉璃瓦的颜色形成错落有致的动感。窗子很大,是那种白色的塑钢材质,像两池清澈见底的湖水分列在房门的两侧。花墙上有两盆“浪不够”正开得娇艳。我暗自思忖,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家,那么,李梅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种职业呢?现在的问题是,容不得我有太多的思考,我所面临的,是如何面对李梅的爱人。
李梅拉开房门,请我先行,我在迟疑的同时,看见一老妪正在烧火做饭,水蒸气从铝锅盖的边缘窜出,发着“嘶嘶嘶嘶”的声响。老妪手握玉米秸送入灶坑,灶坑里立刻光亮起来。老妪见有人来,急忙想站起来。她手把灶台,努力往上起,没有起来。她一只膝盖跪在灶前,又进行了第二次努力,依旧没有站起来。
李梅从我的身边挤过去,双手搀起老妪,轻轻地叫了一声“妈”。
老人家瞅瞅李梅,又瞅瞅我,眼睛里满是歉意和尴尬,说,你看看我这腿,就是不争气,平时不这样,越有客人来,怎么还这样了呢?梅啊,快把客人领到屋。梅,你把拐棍递给我。
李梅把一根山里红树杈做的拐棍递给了她,對我说,这是我婆婆。
我仔细端量着这位老人的腿,已经严重弯曲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O”。她的脚离不开地面。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
我扶着她,进了李梅的房间。李梅在厨房里忙着。
我问李梅的婆婆,你这腿?
她说,老毛病了,滑膜炎。大夫说是什么“膜”没有了,要手术,什么进口的国产的我也弄不明白。只是苦了李梅这孩子。
李梅的爱人就在家种地?
现在是。地也不多,就六亩。光靠这点地不解决问题。孙子在镇上的中学念书,住校。需要钱啊。又加上我这老病,硬是把李梅这孩子“逼”出去打工了。
我发现,这老太太十分健谈。我又问,为什么儿子不出去打工呢?
我两个儿子,原来都在石膏矿。大儿子在矿上做运输工,翻车,把腿砸折了,就被矿上辞退了。二儿子,啊,也就是李梅的对象,是石膏矿上的掘进工。这个工种挣钱多,这孩子太拼命,结果,得了矽肺。老太太又说,矽肺你懂吧?
我说,我懂,是一种职业病。这种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无法治愈。我的喉结蠕动了一下,把后一句话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院子里传来一阵急速的咳嗽声。“咳咳咳,咳咳咳”惊起一阵尘土,把斜阳压下去,红霞托起来。
李梅的丈夫回来了。
6
夜幕携燥热熄灭万家灯火。
空旷的炕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李梅和丈夫挤在了婆婆的房间。我在想,是否是我的到来,破坏了他和她的久别重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我在或明或暗的烟蒂中询问着答案。
这个答案我不知道寻找了多久,只觉得眼睑有些沉重,冥冥中有人在晃动我的胳膊。是李梅。
李梅把一根手指放在我的嘴巴上,另一只手在拉我的胳膊。
我和李梅在夜幕中向村西头走去,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来到了和辽宁省接壤的石桥上。石桥周围是一片一片的玉米地,“啪啪啪”正在拔节。不知名的虫子“亲亲亲,亲亲亲”地正在兴头上。凉风从河面上走过,露在半截袖外的胳膊陡然间铺上了一层细碎的小米粒。李梅靠近了我的臂膀,感觉到她的体温从肌肤上向我传来,霎那间温暖了心头的震颤。她告诉我,再走两米,就是辽宁省的地界了。
李梅说,你敢跨越吗?
我说,你敢我就敢。
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说,我和他谈过了,愿意和我走。我想起了跪在灶台前的老妪。我说,你婆婆怎么办?
李梅说,大哥和大嫂可以照顾她,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的身体状况你也看见了了,别让他种地了,你能安排一个不出力的活儿吗?李梅的手握紧了我的手,我感觉很有力量。
我说,就他的身体状况,安排在矿上是不可能了。她的手没有了力量。不过,我接着说,我可以安排在外包队,工资两千。 她的手又有了力量,手指间藏有一种余晖脉脉的温情。
李梅说,会不会累?
我说,这个你放心。我又试着问她,为什么不求一下傅国华呢,他说话比我有力度。
李梅说,他操我的时候什么都行,提上裤子,我就是个夜壶。
李梅的心情忽然沉郁起来,紧紧抱住了我的腰。她昂起头,对着我的嘴唇,轻轻地叫了一声“哥”。她的腹部在用力,用力,一直把我挤到正在“啪啪啪啪”拔节的玉米地里。
如果说李梅是煤矿上的一眼井口,那么,此时的我就是一名掘进队员。当年,我手握凿岩机在岩壁上作业的时候,为了让岩屑快速地从眼孔里吐出,不断地用一米八的钢钎快速地抽插。凿岩机的反作用力撞击着我的小腹,“两弹一枪”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此时,我很想把李梅当做一眼井口来开采,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搂紧了她的细腰。
李梅的手握紧了我的手,慢慢地,慢慢地,把两只手向上抬起,抬起,直至她的胸前。李梅反转了我的手背,把我的手心一点一点温柔地覆遮了带有温度的山尖。她的手引领着我的手,在山尖的周围一遍又一遍的上下左右地覆遮。
玉米一片一片地倒下。
一张绿色的大床是那样的柔软,软得似乎把她和我掩埋起来,瞬间变成了垂直的自由落体,下沉,下沉。血管迅速膨胀,汹涌澎湃的大河把这张绿色的大床温暖。“两弹一枪”颤抖起来,凿岩机的钢钎深深地插入岩壁之中……
虫子“亲亲亲,亲亲亲”地在星光下演奏着动人的乐章,任由美妙的音符在夏夜里四处流淌。
7
婆婆坐在院子里,嘴角上烟卷的燃烧一明一暗,高高扬起的脸庞和星斗进行着无言的对话。
李梅胆怯地叫了一声妈,声音在喉腔里打了一个结,颤抖着从唇边挤出来:您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
婆婆把手指放在了嘴的正中,另一只手急速地摆了摆。
李梅搀扶着婆婆回卧室,我忐忑地站在黑暗中,听见婆婆说,你快睡吧,我和你媳妇在院子里聊天呢……
8
矿山派出所坐落在驼峰岭脚下,省道303从旁边穿过,顺着蜿蜒的山路再走五百米就是火药库。我每次领取矿用炸药和雷管,都到傅国华的办公室闲聊一会。
我停下车,看见傅国华正领着一帮人在砌大门垛。其中有七八个人我都认识,还有几个也面熟,但叫不上名字。
我问傅国华,你怎么把我的矿工弄来给你干活?
傅国华笑着说,里面说,里面说。
我端着傅国华递过来的水杯,眼望着干活的矿工。傅国华说,别瞅了,都是你的人。嫖娼。
傅国华看我满脸的疑问,说,这不前几天下雨,山水急,把大门垛子冲歪了,我重新砌一下。
我说,你直接跟我要人不就妥了吗,何必破坏人家的“好事”?
傅国华说,管你要人, 那不得欠你人情啊!
我说,你怎么能抓这么多人?
傅国华呷一口茶,没有直接回答我。
你想把他们怎么处理?我又问了一句
你放心,我又不罚款,干完活就让他们回去了。傅国华又说,你把李梅的爱人弄到外包队了?
我说,你消息挺灵通啊?
傅国华说,水泵房这个活儿,适合他干。李梅给你好处了吧?
我睨视一眼傅国华,没有说话。
拉完了炸药,下了矿井。我没有直奔采区,爬过一道“上山”,去了水泵房。兩台“B80”水泵“轰轰轰,轰轰轰”地喝着水,把四周的岩壁震得瑟瑟发抖。127灯泡要比矿灯亮得多,我关闭了安全帽上的矿灯,看见李梅的丈夫蹲在蓄水池旁,用一根杏条棒在潮湿的地上翻蚯蚓。矿井下的蚯蚓长不大,不像田地里的蚯蚓那般红润。李梅的丈夫用雷管的红绿导线把蚯蚓拴起来,吊在防护支架上。蚯蚓在空中“勾勾呀呀”地蠕动。一条,两条,三条……共九条。他一边翻找,一边欣赏着吊在空中的蚯蚓。有时候他会注视很久,连眼睛都不眨。
他没有发现我的到来,他太关注那些吊起来的蚯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把蚯蚓吊起来。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哆嗦了一下,冲我笑笑。我指了指蓄水池,用手做了一个反转的动作,大声说,别掉下去!
机器的轰鸣淹没了我的声音。我把手高举过头顶,意思是水很深。他显然是读懂了我的意思。惨白的脸露出一点笑容,手,摆了摆,意思是不会。
他站起来,嘴张成“O”型,两腮剧烈地抖动。他弓下腰,我隐约能听到“咳咳咳,咳咳咳”的声音。
9
下过两场小雨,又下过一场透雨,东北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驼峰岭上的山杏和梨花次第开放。粉红和银白相互浸染,芳香顺着大山的褶皱“嚯嚯嚯”地流淌,把整个山川的瘦骨嶙峋掩埋。
李梅的丈夫死了。
是掉到水泵房的蓄水池里淹死的。
李梅委托我全权代理有关事宜。我和外包队队长进行了交涉,为李梅讨到了十六万元的赔偿费。外包队队长很委屈,说,他一定是自杀,心理有问题,经常摧残他挖出来的那些蚯蚓,正常人能这样吗?我说,去去去,他那是寂寞。队长迫于我的权利,没有和我争辩。煤矿死个人,像死只蚂蚁一样简单。民不追,官不究,斯人已逝矣,唯有金钱来平衡彼此的利益。
我问李梅,十六万元的赔偿费是否满意,她说,哥,我真的十分感谢你。我自言自语地说,他究竟是死于意外还是自杀?
李梅说,哥,石膏矿还有一种职业病。
我问,什么病?
李梅说,在石膏矿一线的工人,连续干多年,不能生育。
我一惊,脱口而出:那孩子?
李梅读懂了我的意思,她没有回答。
李梅丈夫的死,很快被矿工们遗忘了。因为他们又有了新的话题,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更加令人关注。不久,矿上贴出了募捐通知。要求矿工每人200元,领导干部每人500元,上不封顶。工人的捐款,由单位代捐,从本月的工资里扣除。
一天, 我正在办公室里换工作服,当地政府送来了一封表扬信。表扬信用一张大红纸
写成,表彰我捐款两万元。我莫名其妙,什么时候捐的两万元?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说,不会,名单里确实是你的名字。
我仔细品味着表扬信的每一句话,希望找到一丝端倪。红纸上的字的确不敢恭维,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像野獸。
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便给傅国华打电话,问他是不是你搞的鬼?傅国华一头雾水,对天发誓,说,我绝对没有“毛病”。
我看他不像撒谎的样子,也不便继续追问。
我把电话打给高中同学,他在镇政府当副镇长,让他帮忙查询一下事情的原委。两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怕这是一个圈套。
傍晚,我接到同学的电话,说是一位女同志代捐的,由于数额巨大,当时的工作人员让她留下姓名,就写了你的名字。
可能是我做贼心虚,立刻想到了李梅。
傍晚,我打破常规,直接去了篱笆院。老板说,李梅昨天就走了。
篱笆院老板见我发懵,就说,篱笆院再没有李梅这个人了。他摇着头,去了后厨。
我出了篱笆院,拨打了李梅的电话。无人接听。
我连续打。最后听到的是: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我很郁闷,沿着江边走了很久。
在孔乙己小酒馆,我拨打了傅国华的电话。傅国华说,让我等半个小时,正好有事要找我。这时,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我扫了一眼,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内容是:不要再和傅国华来往,千万不要再把矿上的采区划给他。切切!!
我的眼睛中立刻有了李梅的影子。问,为什么?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在焦躁中期待着手机屏幕上出现想要的答案。
李梅回复:我给傅国华做了两年的线人。哥,我惧怕顶在额头上那黑洞洞的枪口。
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些砌大门垛子的矿工,同时,看见了李梅那双惊惧的眼睛。
我的手指划动了一下手机屏幕,那两个刺眼的感叹号像子弹穿过枪膛留下的划痕。
李梅又回复:哥,记住篱笆院,不要找我。另外,那座小煤窑,不是他弟弟的。
我突然觉得恐惧,脑后似有冷风袭来。我本能地躲闪,一回头,看见傅国华正站在门口阴鸷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