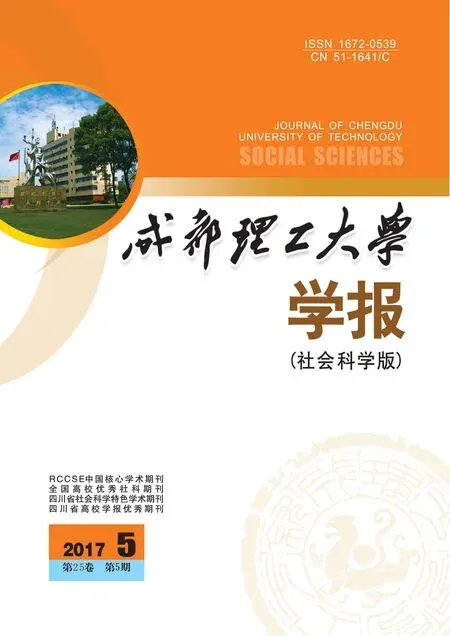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检讨与适用
刘江伟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检讨与适用
刘江伟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关于有限公司股权之善意取得,我国《公司法》未做一般规定,而是在司法解释中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形式出现,规定较为简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股权善意取得仍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规范下,通过对比及规范分析,可以发现股权有适用善意取得的现实性。然而,在工商登记的公信力受到双重弱化的情形下,股权善意取得之权利外观基础是薄弱的,导致其不能简单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需要引入可归责性要件,对第三人的善意认定需要考虑对价是否合理、是否查阅公司章程、是否有相关股东会决议、行为人是否是商人等因素,以完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
股权善意取得;股权变动;工商登记;债权
有限公司股权何以能被善意取得以及如何善意取得是公司法学长期热议的话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第27条规定了股权善意取得,并将适用范围限于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和一股二卖两种情形,同时规定具体规则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对以上两个核心争议予以回应。然而,这不仅没有平息问题的争议,反而适得其反,不断被学者所质疑与诟病[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06条是对动产和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所作的一体规定。立法之初就有学者认为应当严格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2],《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对该条款争议未曾消弭。而股权既不同于动产,也不同于不动产,不能完全按照动产或不动产的方式来对待,其“准用”能否真的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规定不无疑问。根据通说,《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无权处分”[3],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股东资格认定采取形式要件标准的背景下,公司关心的是以谁的名义出资,而非出资来源于何处。股东身份是相对于公司而言的,应来源于公司的确认[4]。就此,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应属于有权处分。第25条却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参照《物权法》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显然已溢出了“无权处分”这一前提,不具有合理性。一般性立法规定的缺失和司法解释的漏洞不止引发学说争议,更使司法实践无所适从(1)。
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有限公司股权的善意取得仍有许多疑义亟待澄清。目前学者们疑义和分歧的节点主要在于对股权变动模式与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认识不同,前者更深层次上涉及到股权性质之争。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认识的分歧都会影响到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笔者试图立足于现有制度规范与理论基础,通过分析股权变动模式、现有规范和股权性质,并将股权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作对比,对股权善意取得规则做相应检讨,希望对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与适用有所裨益。
一、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
按通说观点,股权转让要适用善意取得,则出让人的行为须是无权处分,这关系股权何时发生转移,致使出让人再次处分股权时构成无权处分,进而适用善意取得(2)。背后实质上涉及股权变动采何种模式的问题。举例以言明,《物权法》第10条、第23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转移方法,动产物权以交付为转移方法。未登记或交付之前,出让人仍为所有权人,其再次将动产或不动产让与其他第三人,仍为有权处分,不存在善意取得适用的问题,产生的仅是动产或不动产多重买卖下合同履行顺序与违约责任的问题,股权转让同样如此。
(一)学说介绍及评析
目前我国学界对股权变动模式存在不同认识,第一种观点主张采“债权形式主义”,即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出让人负有将股权转让于受让人的义务,股权是否发生转移取决于股权转让行为,不过学者们对股权转让行为看法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只有经股东名册变更之后股权才发生变动,变更工商登记则股权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5]。另有学者认为,只有在工商登记变更之后股权才发生变动效果[6]。第二种观点主张股权变动应采“债权意思主义”,认为原则上若无其他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股权即发生变动。但其中有学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只有经其他股东均同意且放弃优先购买权,此时股权转让合同才能生效并产生股权变动的物权效力[7]。第三种观点主张采“修正的债权意思主义” ,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即产生股权变动效果,但其效果仅限于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只有在通知公司股权变动的事实,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后受让人才可以行使其股权权利”[8]。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们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与完善之处。其一,《公司法》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依文义解释,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可以根据记载被推定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然此推定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即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可以根据记载免除举证责任,与实体权利的真实状态没有绝对关联。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未必就没有股东资格和不享有股东权利[9]。在未变更登记或登记错误的情形下,权利人仍可通过举证纠正登记,其股东资格并不必然被剥夺。换言之,“股东名册不是设定股东权利的名册”[10],仅具有证权效力,不具有像票据一样的设权效力。如果认为只有经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股权才发生变动,则必须建立在股东名册具有设权作用的基础之上。并且,《公司法》第73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易言之,第73条已言明,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股权便已经转让,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仅为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性要件。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股权变动要件,将会和现有规范产生解释上的冲突。同样,在《公司法》第32条第2款采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下,认为变更工商登记后股权才发生变动,更是和现有制度规范相违背(3)。因此,“债权形式主义”在现有规范下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其二,学者将“过半数股东同意且股东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当作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条件,是对《公司法》第71条第2款之规范目的有误解之处。该条款是基于维护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而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11],质言之,乃是对股权处分权的限制。而股权转让合同乃为负担行为(Verpflichtungsgesch?fte),不以处分权为必要(4)。除非当事人将上述条件特别约定为合同生效条件,否则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即生效。从反面看,如果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得不到满足合同未能生效,受让人受到损害的,只能依据缔约过失主张信赖利益赔偿。而在合同成立即生效的情况下,未满足条件致使受让人不能取得股权的,受让人可依有效合同要求出让人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履行利益赔偿。利益衡量之下,该模式对受让人的保护有不周之虞。其三,“修正的债权意思主义”顾名思义,其修正针对的是“债权意思主义”。该学说从公司利益的角度考虑,认为在公司不知股权变动的情况下,不能任由受让人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这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因而附加了一道程序,即需要经过通知和变更股东名册,才能向公司行使权利。但实际上,修正的债权意思主义所修正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因为该程序原本已内化在债权意思主义内涵当中(5)。其四,德国法上,股权让与采债权意思主义模式[12],因为德国法上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除了公司章程予以限制之外,原则上没有限制[13]。我国则与之相反,从《公司法》第71条规定来看,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除了公司章程规定没有限制之外,原则上受到限制。在满足限制条件下,股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不成问题,但未满足限制条件时,债权意思主义模式能否适用就值得商榷,这事关在股权转让多重法律关系中如何维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
(二)股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模式
要确定股权变动采何种模式,需要界定股权的性质。股权性质的界定事关股权何时发生变动。现实中,股权是以权利束的样态出现,其中有核心权利,其他权利围绕核心权利展开,乃为目的权利和手段权利的结合[14]。有学者认为,剩余分配权是股东所有权利中的核心权利,进而认为股权是指“股东对公司的剩余财产所享有的权益”(6),显然是对“剩余索取权”概念的误读。虽然股权有时被称为剩余索取权,但并非指剩余分配权。剩余索取权与剩余分配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剩余分配权是指公司解散或破产时,在完成对公司债权债务清理之后,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请求分配的权利。剩余分配权行使的前提是有“剩余财产”可供股东分配,在公司资不抵债时,剩余分配权对股东来说毫无意义。而剩余索取权本质上是股东对利润的索取。股东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其出资设立公司或认购公司股份,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公司的良好经营获取收益,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用剩余分配权解释股权明显有违股东出资换取股权的初衷。从这一层面而言,请求公司支付股利,即利润分配请求权才是股权的核心权利,其他权利是为了保障最终目的实现而配置的手段权利。股权核心权利中“请求”表明股权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性关系,股权之行使只能向公司为之,对公司之外的人行使股权是没有意义的。这在比较法上有迹可循。德国通说认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成立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特别关系,法律性质上属于“相对性法律关系”,股东权利义务仅能向公司主张,使得股东与公司关系类似于债权关系[12],股权的性质趋近于债权。此外,萨维尼(Savigny)债权和物权区分说认为,物权和债权的主要区别在于权利客体不同。物权是对物的事实支配,债权所支配的客体则是“其他人格的具体行为”[15]。依照此区分理论,虽然股权具有支配性,手段权利中存在管理性权利。但笔者认为这些手段权利并非是对公司或公司财产等的直接支配。相反,股东行使管理性权利需要通过股权会表决,形成股东会决议,即公司意志。之后再通过公司的行为去具体实施决议内容,例如股东选举董事、监事权利的行使。股东个体独立意思在转化为团体意思之前,并不产生当然的法律效果[16]。与其说是对公司或公司财产等的直接支配,毋宁说是通过支配公司的行为间接支配公司财产等。在区分理论下,股权与债权是相近的。如果将股权当作是物权,无疑忽视了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主体性。这种僵化的物权思维在处理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以及股权转让交易中容易忽视公司利益,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可见,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请求权属性。股权和债权的法律性质实际上没有巨大差异(尤其是优先股股权和债权差异性更小)。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差异从实体论上看,也仅是融资途径的差异造成的[11]。
有鉴于此,按照“相类似案件应作相同处理”的原则(7),股权转让可类推适用债权让与之规则。原则上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股权即发生变动。但考虑到有限公司人合性之性质,有维持股东之间密切信赖关系的必要,以及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若事先未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则股权变动的效力仅限于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对公司并不当然发生效力。其他股东可依据《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介入,与出让人(转让股权的股东)缔结合同,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且其他股东和转让股权的股东之间所形成的合同的履行先于转让股权的股东和先前受让人之间所形成的合同(8)。受让人则可通过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或要求出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等方式保护自身利益。
就此,通说认为,债权不具有社会典型公示性,无法形成善意取得需要的权利表征,不适用善意取得[17];股权变动类推适用债权让与规则下,股权却能适用善意取得,岂不构成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股权与债权不同之处在于股权具有公示性,能够形成权利表征(9)。因为权利不断向着有体化发展,“从外部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方式将之确定下来。”[18]股权也不例外,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通过证券化表现为股票;有限公司中股权则通过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对股东的记载来表征。因此,股权适用善意取得自无疑义。有疑义的是以何者来表征有限公司股权的权利外观。
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之权利外观——工商登记?
法律制度的功能在于优化社会结构,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地满足个人偏好[19]。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其功能在于促进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满足个人信赖偏好,从而使现代社会日常发生的商事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作为一项法政策的选择,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所在[20]。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是建立在权利外观之基础上,当真实的权利状态和表象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相信表象的权利状态反映的就是真实的权利状态;将“虚当成实”。在动产善意取得中,第三人信赖的是在占有公信力基础上通过占有所形成的“占有推定为所有”的权利外观;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第三人信赖的是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基础上通过登记所形成的“登记之人为真实权利人”的权利外观。至此,股权善意取得既然是为了保护股权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其善意取得的适用也应当在权利外观的基础上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答《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记者问时阐释到,“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实权利人”(10)。并且,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1款规定,“一股二卖”是在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时发生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将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参照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其权利外观围绕登记展开,建立在“工商登记”的基础之上。德国学者卡纳里斯认为,商事登记的法律后果应区分设权作用和公示作用,前者旨在使法律事实只有通过商事登记才能成立;后者仅指被登记法律事实本身并非通过登记才成立,登记仅在于公示该法律事实[21]。在我国《公司法》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已言明股东工商登记仅在于公示股东资格。而股东资格与股权有着密切联系,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22],对股东资格的公示背后也是对股权的公示。至此而言,工商登记能否作为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基础,为股权善意取得提供足够的支持,需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前置性问题:公示作用下所形成的工商登记的公信力能否支撑起第三人合理信赖与善意的产生?
在不动产中,登记通常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只有经登记之后不动产物权才发生相应的变动效果,这使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权利表象作用,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属状况与登记记载的权属状况往往是一致的。并且不动产登记常采实质审查原则(Grundsatz der Sachpruefung)(11),同时附带有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等配套制度,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权利推定效力(12),这些都将登记错误的概率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增强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能为善意第三人合理信赖的产生提供足够的支持。与此不同,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登记并非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在登记之前股权就已发生了变动,使工商登记不能保证股权的归属与登记所记载的股权归属相一致,降低了权利表征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合同生效股权即发生变动,到变更股东登记前,不排除出让人再次转让股权或无法排除出让人多次处分股权的行为[23],股权变动的时点与登记时点的不一致弱化了工商登记公信力。除此之外,虽然《公司法》第32条第2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4条为有限公司设置了义务性规定,有限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但是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看,对登记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的责任主体为有限公司,说明公司登记机关对股东登记和股东变更登记只做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在有限公司不申请或提供虚假的股东变更申请材料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并不能保证登记所记载股东资格的正确性,这进一步弱化了工商登记的公信力,在现有制度规范体系下,股东工商登记的可信性程度远不如不动产登记。因此,我国工商登记(股东登记)的公信力实质上受到“双重弱化”。于此情形,在“双重弱化”的制度缺陷下,登记所表现出的权利推定效力被弱化,第三人可以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实权利人的结论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弱化了的工商登记的公信力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善意取得适用所需的权利外观,成为股权善意取得适用的致命弱点,这势必影响到股权善意取得的相关构成要件。
三、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及第三人的善意
(一)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
1.可归责性要件的引入
善意取得制度通过在真实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以牺牲真实权利人的权利为代价,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在权利外观工商登记的公信力受到双重弱化的现实下,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需要纳入其他考量因素,对相关构成要件予以完善,否则将会过度损害交易的安全,造成利益失衡。其中首当其冲应当考虑的是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因为可归责性与可信赖性是相联系的[24],是信赖保护的前提之一。并且,根源上,善意取得制度是以外观主义作为法理基础,而外观主义由外观事实、相对人信赖和本人与因三个要件构成(13)。其中“本人与因”亦说明了在对外观事实和相对人信赖进行判断与认定时,考虑本人的可归责性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国在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中需要引入可归责性要件,以弥补权利外观基础公信力之不足。这在比较法上也能寻找到依据(14)。
可归责性要件的引入,一方面,可弥补登记公信力弱化的不足,提醒真实权利人保持警惕,谨防工商登记出现外观权利和实际权属的不一致。对此,应在股东工商登记中类推适用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并将申请登记的主体扩大到真正权利人,不局限于公司,使真正权利人可以通过更正登记等措施纠正股东登记不正确的状态,降低实际权属和外观权利之间不一致产生的可能性,使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得以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可归责性要件的引入为在真实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提供正当性依据。将不可归责于真实权利人的情形剔除,避免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扩大,对真实权利人的利益保护不周。因为善意取得作为利益衡量机制,不仅要考虑第三人善意的可救济性,还需顾及权利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期实现利益平衡。如冒充处分股权行为,此类行为不仅损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对公司法律制度的破坏性极大,不应适用股权善意取得。
2.可归责性的判断
商法上可归责性的判断并不总是以过错为标准,风险负担的观念对可归责性的判断亦有影响[21]147。股权善意取得中可归责性亦不以过错为标准。以过错为标准,真实权利人仅就在自己主观上有过错而导致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过错须由相对人举证,对相对人保护不利。股权善意取得中的可归责性更多的是风险分配理念的运用。对于交易风险的防范,真实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相比处于截然不同的地位,其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能够以较少成本控制和防范风险,而善意第三人则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弱于真实权利人,并且成本亦较高[25]。因此,就成本收益理论而言,理应由真实权利人承担风险。真实权利人在取得股权后,疏于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是否被正确记载,所出现的权利外观之错误即可归责于他。《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7条规定一股二卖善意取得是因为受让人取得股权成为真实权利人后,疏于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是否被正确记载,未及时变更登记所致。已或隐或现地透露出可归责性的要求及风险分配理念判断标准。但作为一般性要求,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其在构成要件中予以规定。
(二)第三人的善意
股权善意取得中,第三人信赖的是工商登记所记载的股东。但在工商登记公信力弱化的困境下,对第三人信赖的要求须有所提高。并非第三人所有的信赖均需要保护,只有以善意为基础的合理信赖才有保护的必要。登记公信力强度的差异会导致对善意要件的内涵要求不同[26]。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登记簿所表征的真实权属状况与登记记载的权属状况高度一致性使得对信赖保护已被强烈地形式化和客观化,不再考虑登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只要第三人查阅了登记簿并未明知,就可依据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取得相应的物权[27]。在工商登记的可信赖度远不及不动产登记的情形下,股权善意取得中对善意的要求显然不能简单适用“未明知”即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第16条规定将“善意”规定为不知且无重大过失。具体到股权善意取得中,不仅要求第三人不知,还要求其是无重大过失而不知。“不知且无重大过失”认定就需考察第三人是否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首先,一般而言,第三人进行股权交易时需要查阅工商登记。查阅工商登记是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最基本标准,即“善意”的判断须基于第三人查阅工商登记的客观行为(15)。其次,对“无重大过失”的认定还需综合考虑整个交易背景以及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来判断。尤其需注意的是从事股权转让交易的双方当事人多为商人,较之一般民事主体,其通常具备较丰富的交易经验和风险识别能力,所以其注意义务程度更高。但对“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解释需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不能过于宽泛。如果范围过大,会否认工商登记存在的意义,甚至会在实质上使第三人负担一种探求登记背后法律关系的义务,有损于交易便捷。就此而言,在具体的个案中,对价是否合理、是否查阅公司章程、是否有相关股东会决议等均可成为判断善意的考量因素。之所以将股东会决议、是否查阅公司章程等纳入善意的判断之中,是因为股东之间被期望为一个长期的关系,股权善意取得之适用应有助于保持并促进此种关系的延伸,以维护有限公司人合性。并且《公司法》为维护对有限公司之人合性,就对外转让股权做出了法律上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应推定《公司法》上的相关法律是为公众所知悉的,特别是正在从事交易的当事人。这是维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需要,也是第三人应当尽到的合理义务。此外,将合理的对价纳入善意的判断,在股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中就无须再像《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将合理的对价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予以适用。
四、结语
有限公司股权的善意取得背后涉及出让人、受让人、真实权利人、其他股东和公司等多方主体利益,面临合同关系、物权关系、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等多重法律关系。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法律关系易使人心生困惑。在我国规则林立的法律体系中,我们往往缺少对基础理论和规则的反思与检讨。在解释股权善意取得时,习惯于单从公司法思维或者物权法思维思考解释问题——如错把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也适用善意取得,对股权性质、股权变动模式、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基础等善意取得适用的理论基础尚未完全理清。基于薄弱的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股权善意取得规则难谓合理。在根据股权性质将股权变动定位于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需要善意取得制度来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但是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确立的股权善意取得规则的检讨可知,我国股东工商登记的公信力受到双重弱化,支撑善意取得制度的权利外观基础是脆弱的,并不能够使第三人产生足够的合理信赖。法律制度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此语境下,权利外观的不足势必影响股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弥补权利外观的不足,股权善意取得需要引入可归责性要件,考虑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同时第三人善意的认定需要注意行为人的身份,商人的注意义务高于非商人,相应地,在认定商人的善意时,往往要求也更高,但在具体认定中还需谨慎,需要考虑对价是否合理、是否查阅公司章程、是否有相关股东会决议等因素,以限制股权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大,使得股权善意取得制度能得到更好、更合理的适用。
注释:
(1)参见北京恒亿盛世葡萄酒有限公司与李伟革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825403。该案中,审理法官并没有用善意取得原理解决股权转让纠纷,而是转而采用商法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理。
(2)参见马鞍山纵横置业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兴海置业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法宝引证码:CLI.C.1499858。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需履行完毕股权才发生变动,不支持适用善意取得。
(3)《公司法》第32条第2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这一规定表明,工商登记只是股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4)关于负担行为的详细论述及与处分行为的区分请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155页。
(5)债权意思主义核心观点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股权即发生变动。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股东名册登记事项发生变动的,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办理股东名册的变更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通知的效果。
(6)该学者认为表决权、选举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非财产性权利都是为保障股东的剩余财产权的最大化而存在的,参见梁娇龙:《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刍议》,载《研究生法学》2012年第4期。
(7)在缺乏具体法律规则可资适用,存在法律漏洞时,可以类推其他相类似情形之规则进行处理。参见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8)此种其他股东和转让股权的股东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先履行的效力来源于《公司法》规定的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优先效力。
(9)实际上,不能将债权不适用善意取得作绝对化理解。若债权具有社会典型公示性仍有适用善意取得的余地,如出示债权证书的情况下让与债权,第三人有善意取得之可能。参见吴国喆:《债权让与中的受让人保护——以债权善意取得为中心》,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0)“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答记者问”,http://www.148com.com/html/4450/488971_2.html,访问日期:2016年7月28日。
(11)参见《物权法》第12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18条、第19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5条、第16条。
(12)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介绍可参见余佳楠《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13)外观主义的三个构成要件是紧密联系的,对任何一个要件的判断都会影响到对另外两个要件的判断。具体可参见叶林、石旭雯:《外观主义的商法意义——从内在体系的视角出发》,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4)德国法上,作为权利外观基础的股东名单同样存在公信力弱化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基础。See Christian Altgen, the Acquisition of GmbH Shares in Good Faith,GermanLawJournal, Vol 09, 2008, p. 1150.为此,德国法在股权善意取得中引入了可归责性要件等。股东名册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远没有像在德国法上那么重要。实践中甚至出现有的公司根本不置备股东名册的情形。因此,在我国工商登记构成了公司外第三人了解公司股权结构的唯一公开途径,但我国目前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基础同样与德国法上的股权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基础一样面临着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15)参见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黄坤生、杜伟、李跃明、孙建源、王国强、蒋德斌、尤春伟、忻健股权转让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2454398。该案中,从一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中可知查阅工商登记是受让人应尽审慎审查义务,善意形成的基础。
[1]陈彦晶.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质疑[J].青海社会科学,2011,(3):112-116.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6,363.
[3]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10):3.
[4]叶林.公司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8-81.
[5]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26.
[6]朱庆.股权变动模式的再梳理[J].法学杂志,2009,(12):128-129.
[7]王欣新.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23-224.
[8]李建伟.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的程序构建为中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23.
[9]奚晓明.公司案件审判指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60.
[10]王保树.有限公司股东的两种不同登记[J].工商管理研究,2005,(8):24-26.
[11]邓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75,286,287.
[12]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J].环球法律评论,2014,(2):158.
[13][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M].高旭军,单晓光,刘晓海,方晓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92-494.
[14]江平,孔祥俊.论股权[J].中国法学,1994,(1):72-81.
[15]金可可.私法体系中的债权物权区分说——萨维尼的理论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06,(2):139-151.
[16]叶林.商行为的性质[J].清华法学,2008,(4):40-54.
[17]傅鼎生.不动产善意取得应排除冒名处分之适用[J].法学,2011,(12):45-55.
[18]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J].法学研究,2010,(2):36-58.
[19]Nicholas L. Georgakopoulos,PrinciplesandMethodsofLawandEconom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1.
[20]郭志京.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基础、作用机制及适用界限[J].政治与法律,2014,(3):14-28.
[21][德]C.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M].杨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4.
[22]张双根.论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制度的构建为中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5):67.
[23]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J].法学家,2016,(1):134-144.
[24]石一峰.非权利人转让股权的处置规则[J].法商研究,2016,(1):98-100.
[25]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4):13.
[26]姚明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造[J].政治与法律.2012,(8):86-87.
[27]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246.
编辑:黄航
The Review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y
LIU Jiangwei
(Economic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out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Law did not make the general provision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rovisions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is apply to 106th provisions of the property law, but the provision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still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Under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we can find out the rea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equit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double weakening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the basis of the right appearance of the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is weak. It means we cannot simply refer to the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106th.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e application, the factor of imputability needs to be brought in. In considering the third person of goodwill,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consideration is reasonable, whether access to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whether to have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the shareholders’ committee resolution, whether the offender is merchant,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shares transferring;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ntract right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11
2016-12-15
刘江伟(1993-),男,云南普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商法与金融法。
D922.291.91
A
1672-0539(2017)05-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