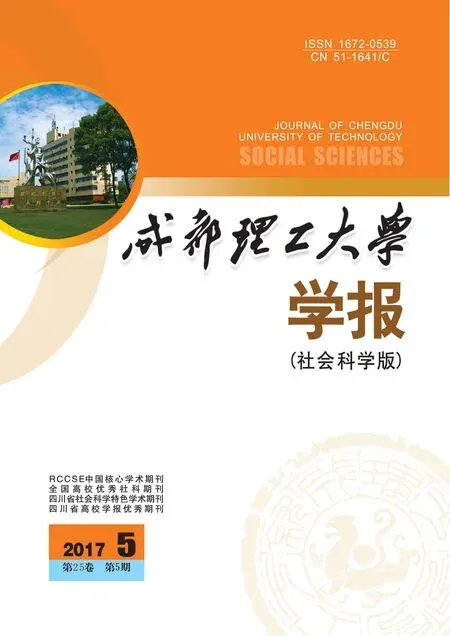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
——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王发奎
(攀枝花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现代性的复仇母题及其革命能指
——以《李有才板话》为考察中心
王发奎
(攀枝花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切入,探讨传统文化中的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复仇行为在现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复仇的主人公从个体英雄转向所有的贫苦大众,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复仇母题具有了启蒙和政治引导的革命“能指”。
复仇母题;《李有才板话》;阶级复仇;“革命”能指
一、原型母题的几个含义
“母题”,来自于英文“motif”的音译。最早出现在法国浪漫派的理论文章中,歌德将“母题”定义为:“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1]138并且,对母题之于情节的作用做出了不同的划分。后来,“母题”被引入到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之中。美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认为,母题是在民间传说中能够辨认出来的故事叙述的最小单位,以此对民间文学进行分类。在比较文学著述中,“母题”是作为主题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出现的。但在不同版本的著作中,“母题”被赋予的含义却又是各不相同的。有时被指称为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基本概念……”。[2]189有时候也被解释为:“一个主题、人物、故事、情节或字句样式;也可能是一个意象或原型……,使这个作品有一脉络……;也可能成为作品中代表某种含义的符号。”[3]3不仅在文艺理论中,学者对“母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每一个批评家对“母题”大都有其个人独特的理解,多是不加规范的使用。这使得“母题”成为一个时髦却含义模糊的学术词语。
对于母题或曰“原型母题”的界定,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原型母题”是指一种文学原型,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于传统中的故事,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艺作品中,具有一种持续性。这意味着,“母题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任何一种时代里它们都有可能实现。”[4]88其次,从“母题”这一概念的演变考察,“母题”应该是一种叙事研究,它是与故事、情节、叙述分不开的。英语单词“motif” 本身就具有“简单或重复的式样或颜色”的意思。那么,一种“原型母题”就应该含有一种母题叙事的原型模式和基本结构。正如谭桂林先生所言:“每一种文学母题为了在历史的不断进展中同时使自身规定性得以维持,它必然会在叙事或抒情的结构形态方面积淀一些基本的原型模式……。而叙述的基本模式一旦形成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稳固性。”[4]92当然,稳固性并不是恒常性,作为一种原型的“母题”是一个不断变形的有机体,其表现形式即叙述模式不是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母题也会有变体,不变的是母体系统赖以生成和更新的内在机制。第三,文学母题不断重复和较为稳定的原型模式背后,潜藏的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流脉。而同一母题在演变中形成的一些叙事模式的变异,都暗藏着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面貌和思想形态的冲突。鲍特金说得好,“有一些题材具有一个特殊形式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文化中一直保存下来;并且,这个形式或模式是与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人们心灵中的那些感情倾向的某一模式或搭配相应的。”[5]121
二、常中生变的复仇母题
复仇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它渊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成员尊奉的原始正义的观念。学者王子野曾指出:“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6]67并提到,“人使自己的激情神圣化和神圣,特别是当这些激情可以帮助他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上保存自己的时候,‘对血的无厌的渴求’,被提升为神圣义务的复仇变成了一切义务的第一位。”[6]69显而易见,复仇原型意识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产物,它的核心内涵是人类正义思想和公平意识的自我确证。英国人L·T·霍布豪斯曾经提到一个观点,说原始人一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平分食物和财富,而这种平等的本能同时也创造了同等的报复取向。在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进程中,面对种种不平等和压迫,人类的复仇行为也从原始本能的无意识复仇上升到了自觉的、有理性的、有谋略的复仇行为。因而,自觉复仇也就含有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因子,对传统文化思想显露出了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传统的伦理观、生死观、道德观都凝结在了自觉复仇的过程中。
复仇的方式有很多种,主要可以分为血亲复仇和非血亲复仇两大类。而这其中,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家族复仇又是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时代最重要的复仇行为。血缘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人伦关系,而且是人际关系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型。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不仅仅是伦理关系的基础,更是政治关系的根基。这也就是说,在宗法制家庭关系中,为亲情复仇是氏族成员的确认,复仇就成为这个社会基本的准则。恩格斯指出:“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同氏族人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其复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凡伤害自己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的。”[7]83中国古代,提倡“舍生取义”的儒家开复仇自觉意识之先。孔子就主张为亲人复仇,《礼记·檀弓》篇记载:“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8]81这有效确证了原始血族复仇的心态。至于非血缘复仇,它虽基于儒家“忠”的道德出发点,但在儒家思想中,忠孝一体,孝悌为本,提倡“移孝为忠”。因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替他人复仇,仗义救国的侠义复仇,也都是血缘宗法社会的英雄行为。这使得,在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中,复仇这一行为能够获得国家民族意义。血亲复仇和非血亲复仇才能具有同质同构的可能性,才能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报德报怨”,小则关系个人荣辱,大则事关国家兴亡。这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价值为核心,复仇行为全然取决于个人的意愿与行动,形成了截然区别。
典型的生活情境推动文学典型的应运而生,而生活的真实必须走向文学的真实,人类文化、思想、历史传统才能由隐潜走向开放。因此,复仇原型母题便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地复制和传播。“它释放着人类历史积蓄的复仇心理能量,把复仇的自卫、本能、条件反射与伦理道德理念转化为审美快慰。”[9]10反过来说,复仇观念又通过复仇这一叙事母题的演绎和播撒内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中,复仇母题的叙述都构成了一种深远的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复仇母题本身就是一个承重的问题,因为复仇首先就意味着这悲剧的诞生,而且还是先天的,是一切故事的根源,历时而不可改变。”[10]211经典如《哈姆莱特》、《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赵氏孤儿》、《铸剑》、《伍子胥》,等等,都是复仇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场中的精彩演绎。在复仇母题原型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进程中,复仇模式开始成熟和稳定。一个完整的复仇故事大致包括仇恨形成、反抗暴力、拯救者或曰帮助者的出现、复仇成功等四个步骤。同时,这一母题又具有“海纳百川”的囊括性。使复仇母题模式能够“常”中生“变”,从传统向着现代迈进。
三、阶级复仇和《李有才板话》的“革命”能指
在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中,复仇母题的书写开始发生变革,时代的碰撞和思想的浪潮在文学的园地里尽情绽放。尤其是在左翼之后的革命文学中,复仇母题也开始跳出传统复仇结构模式,散发出了革命的讯息。而通过赵树理小说中复仇母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因素的这种现代进化轨迹。
首先,与传统的复仇叙述模式相比,在《李有才板话》中,复仇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身负家国之恨的个体英雄;而是阎家山老槐树下的所有的贫苦大众。他们也不具有传统文学尤其是武侠作品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和心性。相反,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显得麻木甚至愚昧,对复仇没有足够的决心。比如,小说中的老秦,他虽也深受压迫,天然地应该是一个满腔仇恨、寻求解放的复仇者,但他却忍气吞声,不敢反抗,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安分守己的“小农”形象。
其次,复仇方式由个人复仇向集体复仇、阶级复仇转变,阶级意识得以构建。传统的浩如烟海的复仇母题叙述,多是以个人复仇为主导线索,尤其是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复仇主人公虽然身负个人荣辱和国家兴衰的双重责任,也常常可以从近亲那里得到支援。但无论是血亲复仇还是狭义复仇,个人的成长都是推动复仇进程的内核。在《李有才板话》中,所有的复仇行为都是集体行为,因为每个人的仇恨都有相同的来源和对象,自然而然地由个体凝结为一个群体,并因为其革命翻身的意义而拥有了阶级复仇的特性。同样的,阎恒元、喜富、广聚则形成了一个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天生的对抗和斗争。针对这种状况,恩格斯早有判断:“……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7]343-344按照无产阶级的斗争理论,阶级意识的建构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超越,个人复仇终将被阶级斗争取而代之。
同许多革命小说家一样,赵树理作为主动践行大众文艺和革命文艺的小说家。他的文艺创作自觉地承担起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历史使命。其小说作品几乎都注入了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内涵。阶级对立在《李有才板话》中,从一开始就是叙事的起点。而集体复仇的成功意味着革命的从弱到强,由挫折向胜利的过程。既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一种新的秩序建立起来,这也是“阶级革命”的本质含义。唯有革命,方能解救劳苦大众脱离苦海。另外,因为政治内容的强化,在《李有才板话》的政治叙述中,“拯救者”的身份和功能同时得到了强化。县农会主席老杨可以说是老槐树底下的“破落户”们复仇成功的直接参与者和指导者。而他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团体。他的行为的完成正是以共产党取得解放区的领导权为支撑的。所以,《李有才板话》里复仇行为的拯救者,即是取得了政治权力的共产党。角色身份的这种强化,很自然地引入了“革命”的能指。老杨指导阎家山贫苦群众建立农救会,推翻压迫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启蒙:一种具有革命意义和阶级意识的政治引导。
其实,复仇母题的现代化演变,并不是始自赵树理创作的一系列阶级复仇故事,也不以此为终结。这里,我们简单将《李有才板话》同贺敬之等人编著的新歌剧《白毛女》和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进行比较。考察相同原型母题和革命语境叙述的不同建构方式。三部作品同样是历史语境与时代话语的双重言说,革命时代的阶级复仇对传统产生了颠覆和逆转,革命与阶级的能指被释放出来。不同的是,在《李有才板话》中,“革命叙事”(阶级复仇)是唯一的线索和程式,历史与时代在这部小说中完全融合。压迫/反抗的阶级对立从一开始就是被突出的。历史与时代的全部任务和意义在这部小说中都可以归为由革命走向解放。正如前述,在这部小说中,不存在革命的个体或是跳出革命范畴的社会组织单位;只存在为革命复仇应运而生的对立阶级。反观歌剧《白毛女》和长篇小说《红旗谱》,其复仇母题的表述方式都具有二重结构。在《白毛女》中是白毛女个体结构和革命结构,在《红旗谱》中是革命结构和传统家族结构。而且,其中的革命结构是隐藏于个体结构和家族结构这条明线结构背后的一条暗线,对明线故事发展具有导向性。但丰厚的明线结构是故事发展的主干,明线包蕴了暗线。
概括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因为其急于宣传革命的“功利性”和“教育劳苦大众”的需要,在诸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故事中,他对传统复仇母题的改造稍显急功近利。进步的时代性要强于艺术审美的现代性。且因为赵树理创作资源的局限性,使得他的创作很难取得如《白毛女》和《红旗谱》等作品的宏大效果和厚重感。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证:追求正义与惩恶扬善的人类天性和集体无意识,对他阶级复仇故事的叙述和“革命教化”任务的达成都起到了归纳、整合、规范的作用。
[1][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乐黛玉.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C]//陈召荣.流浪母题语西方文学经典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谭桂林.论长篇小说研究中的母题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88-93.
[5][英]M·鲍特金.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M].叶舒宪,编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王子野.思想起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G]//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钱玄,钱兴奇.礼记(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1.
[9]邹菡.红旗谱: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复仇模式变革[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2):9-13.
[10]应尤佳.复仇的困境——〈原野〉的母题分析[J].世界文学评论,2006,(2):210-212.
编辑:鲁彦琪
The Motif of Revenge and Revolution of Modernity Signifier:Take“Rhymes of Li Youcai”as the Center
WANG Fakui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617000,China)
Behind the literary motif repeated and relatively stable prototypes, the hidden is a national commo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stream. Based on Zhao Shuli's “Rhymes of Li Youcai” , The act of revenge in the sense of the 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odern China began to change, and sends a message of revolution. The hero of the revenge from the individual hero to all the poor people, the way of revenge from the personal revenge to the collective revenge, class revenge. Revenge motif has guided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signifier”.
the motif of revenge;RhymesofLiYoucai; class revenge; “revolution” signifier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16
2015-11-30
王发奎(1986- ),男,河北涉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G05
A
1672-0539(2017)05-008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