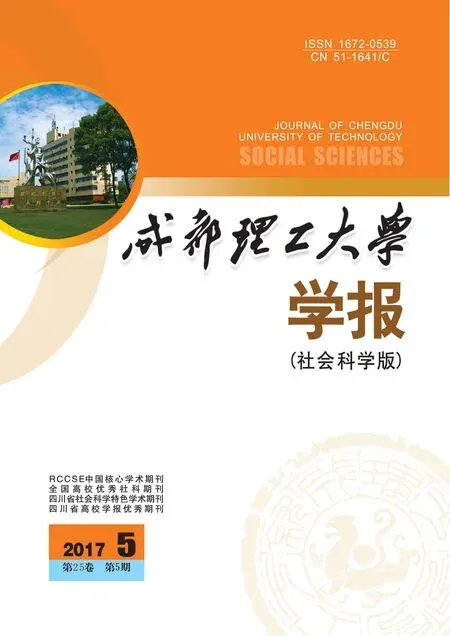论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狂欢艺术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宁 810007)
论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狂欢艺术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宁 810007)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富有狂欢色彩的小说之一,作者主要以卖妻、酒宴、庭审和讦奸四次狂欢广场为基础,借助三类人物的特殊文学功能,通过对主要人物进行反复脱冕与加冕的狂欢化艺术手法,展示了主人公迈克·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剧人生,深刻揭示了人生多变和命运无常的人生哲理。狂欢化不仅是反映作者人生观的途径,更是诠释主人公人生沉浮的叙事手段,亨察德在屡次狂欢中走向没落。
狂欢艺术;广场狂欢;脱冕加冕;物品反用;三类人物
纵观《卡斯特桥市长》的研究史,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分析、原型学说、社会变革等视角对小说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也有人从性格与环境的角度或从希腊悲剧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笔者看来该小说的狂欢化艺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哈代继承了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怪诞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从人本主义出发描述了羊市卖妻、酒家欢宴、法庭闹剧、讦奸游行等广场狂欢景象,并借助骗子、小丑、傻瓜三类人物特殊的面具功能以及吹嘘谩骂、诅咒发誓等非主流语言形式营造了激情的广场狂欢氛围,在狂欢语境中通过对主要人物升格加冕和降格脱冕的反复交替,展现了主人公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剧人生,深刻揭示了世事多变命运无常的人生哲理。卡斯特桥狂欢看似热闹怪诞的表象下潜伏着悲苦心酸,繁荣与凋敝接踵而至,悲与喜、沉与浮、庄与谐形成了鲜明的二重性和不确定性。亨察德的人生历程中的每一次大的波折都伴随着一次色彩鲜明的广场狂欢,也就是说,亨察德是在作者历次狂欢化书写中走过了他的悲剧人生。小说中的狂欢化书写既是反映作者人生观的途径,更是诠释主人公人生沉浮的叙事手段。
一、广场狂欢与加冕脱冕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文化源泉是古希腊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狂欢节。酒神既是死亡之神又是再生之神,因此狂欢节具有鲜明的两重性,酒神精神是狂欢节、狂欢化的精神根源和心理基础。狂欢式没有舞台,无演员和观众之分,具有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插科打诨等特征。狂欢式在文学中的文本反映就是文学的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节上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象征意义、表现狂欢节世界观的感性形式的语言,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文学的语言[1]158。狂欢式的文学表现就是狂欢化,狂欢化形式多样,“他以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乌托邦的理想、广泛的平等对话精神、快乐的相对性、双重性等为基础。”[2]79狂欢化有严格的时空特点,以广场等群众集结的环境为场地,一般为一个民族的节庆仪典,民间节庆活动是狂欢文化的主要载体,广场是展示民间狂欢文化的主要舞台,“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化的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了两重性、两面性,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2]166在巴赫金看来,文学作品中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甚至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2]166狂欢化文学在西方由来已久,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法国作家拉伯雷为代表的怪诞现实主义作家掀起了狂欢书写的高潮,哈代为拉伯雷精神的追随者和践行者[3],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将民间广场的欢闹氛围和文化精神根据情节需求巧妙植入文本叙事之中,在一连串有因果关联的狂欢化书写中演绎了亨察德的悲剧人生。狂欢化书写成为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语境和内在动因,亨察德的传奇人生与四大狂欢场面息息相关,其中的加冕与脱冕促成了他命运的根本转折,故事情节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拓展。
(一)羊市卖妻
羊市卖妻是《卡斯特桥市长》的开篇狂欢,亨察德在小说中一出场就带着狂欢人物的色彩,在狡猾的卖粥妇的诱导下狂饮醉酒,失去理智后上演了一出离奇荒诞偏离常规的卖妻闹剧,在羊市拍卖了妻子苏珊和女儿伊丽莎白,羊市卖妻反映了怪诞现实主义的根本理念。在本次狂欢中,卖粥妇扮演了女骗子的角色,她一生所悟出的生意经是“正正派派做生意赚不了钱”,必须“耍滑头,搞欺骗”[6]26,她始终奉行这种荒诞的人生哲学,她的诡秘行为给卖妻闹剧增添了狂欢色彩,从叙事逻辑上为亨察德醉酒提供了似乎合理的理由。狂欢化书写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布里格斯在《英国民间故事和传奇》中收集了一则“鞋匠卖妻”[4]的故事,内容跟《托马斯·哈代的事实笔记》中记载的发生在作者家乡多塞特地区的三则真实故事大致相同[5],从以上民间故事以及真实故事中都能发现亨察德卖妻的影子,格林斯莱德指出哈代笔记记载的希尔羊市就是小说中韦敦——普瑞厄兹村羊市的原型,它是当地最盛大的传统集市,汇集了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有休假的短工,闲逛的士兵,农村小店的老板等逛市的人,还有各类民间艺人和生意人,有拉洋片的、卖玩具的、做蜡像的、有通灵的怪物、游方郎中、赌套圈的、卖小摆设的、还有算命先生,这样一个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环境从客观上为狂欢创造了条件,民间集市本身就是一个喧哗吵闹、众声齐鸣的杂语世界,颇具狂欢色彩。民间文学般的卖妻闹剧在解构常规伦理的同时蕴含了终与始、生与死的二重性,亨察德和苏珊婚姻的终止孕育了纽森和苏珊的开始,一段婚姻的死亡催生了另一段婚姻的新生,表现了狂欢化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卖妻丑闻是与亨察德命运有关的第一次狂欢化书写,为亨察德进行第一次脱冕,为他的日后悲剧埋下了伏笔,从叙事的角度为情节发展留下了诸多悬念,为苏珊寻夫和纽森寻妻创造了条件,也为伊丽莎白的身世之谜留下了线索。
(二)酒家欢宴
另一个狂欢化书写是王徽旅馆镇上政要和富商欢聚的宴会,这里亨察德已从昔日穷苦的打草工变成了声名显赫的一镇之长,众星捧月,权高位重,这是对亨察德的唯一一次升格加冕。作者没有按传统的时间顺序细述主人公的发迹过程,而采用跳跃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多年后主人公事业发达,春风得意的另一番景象,彰显了他人生的戏剧性变化。但是,在看似一片繁荣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宴会结束时已怨声四起,市民们对亨察德卑鄙的经商行为颇有微词,对亨察德的品行开始产生怀疑,预示了亨察德人生在经历了短暂的繁华后即将到来的萧条,其悲剧没落的结局隐约可见,大起必然孕育着大落,起落有序,荣枯有秩是生命的真实轨迹,颓势将至,恶兆先行,这次显形的加冕实际上是一次隐形的降格脱冕。除了彰显主人公命运的起落波动外,这一狂欢化书写在文本叙事上起了承前启下的纽带作用,就在这此欢宴上作者安排苏珊和亨察德相遇了,这一环节在小说情节发展上起到了链接和推进作用,从此情节更加曲折多变,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微妙。在亨察德的情感场域,苏珊的登场必将导致露塞塔的退场,进与退、新与旧之间形成了狂欢化二重性。为庆祝一个特殊的日子而进行的民间娱乐会是小说另一个具有狂欢意蕴的场面,市长亨察德为市民准备了传统游乐节目,天不遂人愿,那天大雨滂沱,会场显得非常狼狈,无人光顾,而法夫瑞那边却热闹非凡,歌舞音乐,人们趋之若鹜。从故事情节上来说这一片段固然并不重要,但在故事的整体脉络上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它预示了民心已向代表新世界、新观念的法夫瑞那边倾斜的迹象,而代表旧世界、旧观念的亨察德开始被人冷落。从狂欢化理论分析,这是对法夫瑞的加冕,对亨察德的脱冕,新旧对比,升与降之间为文本增添了动感张力。
(三)法庭闹剧
卖粥妇在法庭上揭穿亨察德的卖妻丑闻的事件是《卡斯特桥市长》最关键的狂欢情节。亨察德因为是上届市长,所以担任治安法官参加轻罪审判,对微小过失进行及时审判和处理。这次庭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卖粥妇当庭揭发了亨察德隐匿了近二十年的卖妻罪行,这一举动一下子颠倒了亨察德和卖粥妇之间的关系,原来的法官成了罪犯,罪犯成了法官,审与被审瞬间换位,加冕与脱冕共存,高高在上的“国王”瞬间变成了“奴隶”,“奴隶”成了主宰乾坤的“国王”,实现了民间对官方的戏谑解构,体现了狂欢化主张生死荣枯、新老更替、起落交错的变化的精神内核,旨在呈现一个变化的世界和流动的人生。三类人物的道具功能为本次狂欢增添了狂欢筹码,小丑治安警察斯塔伯德的猥琐懦弱和骗子卖粥妇的机智果敢间形成的反差使狂欢变得更加诙谐幽默、滑稽可笑。因卖粥妇诡秘地透露了风声,引来了异常多的围观者,所以引起的轰动“大得无法形容”[6]249,哈代没有极力渲染这个动人的狂欢场面,但读者可以感受到令人捧腹的热闹气氛。这个出人意料的法庭闹剧给了亨察德沉重打击,他很快就“名誉扫地”,从此他的气运骤然下降,社会地位“急转直下”[6]296。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亨察德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丑闻暴露使他身败名裂,又因固执偏信商业上惨遭挫败,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踏上了悲剧之路。祸不单行,亨察德爱情上也受到重创,因为丑闻使露塞塔看清了他的“真面目”[6]222并决意弃之而去,他们的爱情危机导致露塞塔写给亨察德的情书落入赵普手中,成为讦奸游行的重要素材,因此庭审狂欢在文本叙事上是讦奸游行的前提铺垫。
(四)讦奸游行
讦奸游行是《卡斯特桥市长》中起关键作用的另一个重要狂欢情节,也为小说掀起了又一个高潮。讦奸游行是英国古老的民间广场现象,也叫司奇米特(Skimmington Ride)或粗糙音乐(Rough Music),是社区成员组织起来揭露惩治有悖于道德规范行为的一种民俗事象,主要针对伤风败俗的男女不正当关系或家庭暴力, 这类民间自发的惩罚活动具有相当大的社会约束力,它从舆论的角度维护正常规范的男女关系和家庭伦理。《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讦奸游行策划于被作者称之为米克森巷的教堂的最低等的彼得手指客店,讦奸游行的发起者小丑似的人物赵普在他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后公然透露了他的意图——“寒伧寒伧”“本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这种穿着绸缎、蜡人儿似的、盛气凌人的东西”[6]320,讦奸游行的矛头直指露塞塔,这个“花里胡哨”、“水性杨花”、激起民愤的没有口碑的上等人。南斯说她丢了她们的脸,卖粥妇恨她没有感谢她,朗威斯认为她罪有应得,考克松大妈觉着她是讦奸会绝好的主角,“彼得手指”老板娘坦言,拿这样的风流事搞讦奸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6]323。总而言之,生活在卡斯特桥市最底层的人都不想辜负了露塞塔和亨察德的这段孽海情天,不愿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打算借此机会“好好乐一阵子”[6]324。讦奸游行除了给民众提供了酣畅发泄、娱乐狂欢的机会外,还为他们搭建了挑战权贵的最佳平台,作者指出这不只是一场开心的玩笑,而是“一顿报复”[6]333,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报复。搞臭露塞塔也就搞臭了她的丈夫法夫瑞,一个“当了市长又成了有钱人,一心想着男女之事,而且野心勃勃”[6]332的人,一个一当官就变了脸的人,讦奸游行使露塞塔癫痫病发作,流产死亡,为伊丽莎白和法夫瑞的结合创造了似乎合理的条件,而亨察德的命运更是雪上加霜,江河日下。
值得注意的是,讦奸游行恰好定在皇室贵胄前来访问的当天,旨在趁卡斯特桥的头面人物们兴致正浓的时候,以讦奸狂欢的形式“给皇室的访问收场”[6]333,让权力萎缩,斯文扫地。“给那些身居显位的人开开玩笑,让他们丢丑,对于辗转于他们脚下的人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淋漓痛快的享受”[6]372。这是一场以赵普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向以法夫瑞、露塞塔,甚至王室显贵为代表的上层发起的没有流血的战争,也是最低等的彼得手指向最高级的王徽旅馆发起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亨察德这位昔日权贵的历史清算,它以下层人物对上层人物的戏谑脱冕为娱乐目的,表达了狂欢式颠覆等级、主张平等的世界感受。卡斯特桥讦奸游行反映了狂欢化的精神内核,它是社会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发起的挑战,是底层民众为昭示其存在而发出的强音。另外,从某种意义上透视了以赵普、卖粥妇和“彼得手指”老板娘为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仇富、仇权、仇美的心理,暴露出卡斯特桥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狂欢理论与酒神理论均肇源于酒神精神,但它们属于两个概念,酒神理论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表露,狂欢化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是从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宗教与世俗相对的角度提出的,是西方二元对立文化的集中反映,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政治诉求。
二、物品反用与逆向原则
物品反用是《卡斯特桥市长》狂欢化书写的又一个表现形式。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介绍了反用日常物品以颠覆常规、消解成章从而暂时摆脱制约和束缚的一些常见的狂欢形式,例如“反穿衣服,裤子套到头上,器具当头饰,家庭炊具当作武器,如此,等等。这是狂欢式反常规反通例的插科打诨范畴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脱离了自己常规的生活”[1]165。讦奸游行中被惩罚的男女双方的模型背对驴头,面对驴尾,游行者通常敲击破盆旧壶、盘子或铲子,吹口哨或牛角号,摇拨浪鼓,狂叫怒吼,不时伴有色情言语,在“粗糙音乐”所营造的欢闹气氛中,在一片诙谐满足的笑声中,参与民众以半娱乐的形式对目标人物进行戏谑降格。“背对驴头,面对驴尾”表现了对常规的颠覆,“敲盆击锅”等形式符合狂欢式物品反用的原则,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缺乏正统器具的现实条件下常常会就地取材,用身边的日常用品来代替高雅正统的器物,常见的有以敲击锅盆、碗筷来代替高雅乐器,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解构正统、颠覆高雅、消解主流的意识。卡斯特桥的讦奸游行中,被惩罚的亨察德和露塞塔的模型背对驴头,面对驴尾,“屠刀、钳子、铃鼓、小型提琴、临时拼凑单弦或双弦琴、粗制滥造的笛子、蛇形管、羊角喇叭以及有史以来各式各样的乐器的喧哗鼓噪”[6]348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粗野的大型民间交响乐,这种原始粗犷的民间审美颠覆了长期以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一高雅审美理想。物品反用反映了狂欢化逆向观世界、颠倒看人生的思想原则。
三、三类人物与面具功能
骗子、小丑、傻瓜是狂欢化文学营造狂欢氛围不可或缺的三种特殊艺术形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扮演开心国王、王后的角色,三类人物是中世纪社会底层与正统文学相伴而生的讽刺性和讽刺模拟性民间创作和半民间创作中出现的,对后来欧洲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的三个具有各自标志性形象的人物。三类人物拥有自己“特殊的世界、特殊的时空体”[7]354,在小说中他们凭借特殊的面具功能揭露和戳穿人际关系中的虚伪和谎言,从而帮助小说家表达本不可以表达或难以表达的个人观点和态度。他们是狂欢化文学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被主流社会所鄙视的边缘人物,他们以鲜明而独特的、被官方正统文化所不齿的形象与官方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形象间形成对抗,通过颠覆正统文化所欣赏的理想形象戏谑正统人物达到娱乐和狂欢的目的,以此暂时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巴赫金指出,在滑稽剧和讽刺模拟的系列作品里,三类人物担负着反恶劣常规和揭穿人们关系中的谎言的任务,他们与那些僵化的制度和谎言相抗争的力量“是骗子清醒、风趣而狡黠的头脑,是小丑讽刺模拟式的嘲弄,是傻瓜心底忠厚的不解。对付弥天大谎的,是骗子风趣的小骗局;对付利己主义的假造和伪善的,是傻瓜并无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对付一切陋习和虚伪的,是小丑进行揭露的综合形式”[7]351-352。三类人物在小说中“通过特殊的途径恢复了文学与民众广场之间被割断了的联系”[7]354。
《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成功塑造了骗子卖粥妇、小丑古斯塔夫和傻子阿贝·卫特狂欢化三类人物艺术形象,他们在文本中充分发挥了道具功能和情节过渡上的润滑作用。巴赫金指出,“小丑行为”、“扭扭捏捏”、“装疯卖傻”、“怪癖行为”都属于三类人物典型的行为表现。治安警察斯塔伯德像《还乡》中的老阚特和苏珊·南色一样扮演了小丑角色,他形象猥琐,性格懦弱,行为古怪,亨察德指责他说话罗嗦像个女人,卖粥妇骂他“老萝卜头”、“该死的傻瓜蛋”、“狗娘养的”,在庭审现场他对卖粥妇的指控继而跟她的公堂对簿使本该严肃的庭审显得滑稽可笑,让人忍俊不禁,增添了该场面的狂欢色彩,在讦奸游行当天因害怕被人发现他和搭档把政府警棍塞到了水管内,躲在巷子里,不敢吱声露面。身为警察的斯塔伯德猥琐形象、庭审现场的丑态和面对讦奸游行时的萎缩逃避是对官方形象的降格颠覆。阿贝·卫特在小说中虽出场戏份不多,但具备了傻子的一些形象特征,他“溜肩膀”、“眨巴眼”,大凡受到一点点刺激,他的嘴就会“微微张开,好像没有下巴来支撑似的”[6]117,露出一副十足出神的傻相,大家都叫他可怜的阿贝。他自称天生的笨脑瓜,一念祷告脑瓜就像死木疙瘩,这种表述无疑是对上帝的亵渎和对宗教的解构;他行为滑稽怪诞,睡觉总过头,上班总迟到,为了能按时起床跟上早班,他在脚趾上栓一根绳子,绳头放在窗户外,靠伙伴拽绳子来叫醒他,特别是受到亨察德的惩罚,大清早只穿裤头狼狈跑过街道的情景更是一出典型的滑稽闹剧,与正统文化形成了对话,以此来消解高雅文化,因此,他也隶属于三类人物,是类似于《还乡》中的克锐、《远离尘嚣》中普格拉斯和《绿荫下》中的里福的“乡村傻瓜”[8]。三类人物在小说中虽然只是道具人物或福斯特所谓的扁形人物,但他们与主人公的命运存在密切关系,骗子卖粥妇既是亨察德悲剧的始作俑者,又是重要推手,傻瓜阿贝·卫特陪伴亨察德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卖粥妇以女骗子形象出现在卡斯特桥的文本狂欢中,她机智诡异,圆滑狡黠,言语粗俗,喜欢自吹自擂,说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懂得怎么跟这地方上最有钱讲究吃喝的大肚子打交道”[6]26,知道牧师、花花公子、城里人和乡下人等各色人物的口味,发誓诅咒、吹嘘谩骂、油嘴滑舌是典型的广场语言形式。她无视官方禁令偷售私酒,不顾宗教戒律公然在教堂边上撒尿,并以污言秽语辱骂政府警察。她行为不轨,累教不改,哈代说她出庭的次数比审问她的法官还要多得多,在法庭上她当众指责法官亨察德并暴露了他的卖妻隐私,把他从法官的高位一下拽入了罪犯的深渊,实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戏剧性逆转,完成了狂欢式“加冕”与“脱冕”的瞬间变化,使严肃的庭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可笑的狂欢闹剧,法庭闹剧使亨察德颜面扫尽,社会地位坠入低谷。在某种意义上,卖粥妇就是亨察德悲剧的制造者和有力推手,亨察德的一生命运都与这个“脸上斑斑点点”、全身像“油水里浸泡过一样”[6]245-246的、形象滑稽、行为放荡的女骗子有关。在现实生活中,三类人物被主流文化所不齿,属于边缘化的人物,但狂欢文学中他们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往往是推动故事情节变化和主人公命运逆转的关键因素,卖粥妇偷售烈酒致使亨察德卖妻以及在法庭上揭发他的丑闻这两个举动构成了亨察德悲剧的关键环节。因此,卖粥妇这个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狂欢文本中却转化成了操纵主人公命运的“大人物”,体现了狂欢化的逆向原则。总之,女骗子卖粥妇从以下三个层面实现了对官方、宗教和权威的脱冕,“偷售私酒”颠覆官方制度,“教堂边撒尿”解构宗教,“戳穿法官隐私”消解权威,充分发挥了三类人物在狂欢文学中的面具功能。她的行为是对维多利亚妇道的挑战,她的在场是对英格兰淑女形象的颠覆。
狂欢化是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比较常见的艺术风格,富含狂欢色彩的《卡斯特桥市长》堪称其中之最。小说中作者书写了卖妻、酒宴、庭审和讦奸四个狂欢广场并借助三类人物的特殊文学功能通过对主要人物进行反复脱冕与加冕的狂欢化艺术手法展示了主人公亨察德起伏跌宕的悲剧人生,深刻揭示了人生多变和命运无常的人生哲理。狂欢化不仅是表现作者人生观的艺术途径,更是诠释主人公命运沉浮的叙事手段,亨察德就是在一次次狂欢中走向没落,因此,《卡斯特桥市长》也是亨察德的命运狂欢曲。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2]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Hardy,F. E. Life of Thomas Hardy[M].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7:134-135.
[4]Briggs, Katharine. British Folk-Tales and Legend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289-290.
[5]Hardy, Thomas. Thomas Hardy’s ‘Facts’ Notebook[M], ed. William Greenslade. Aldershot: Ashgate, 2004:175.
[6]哈代.卡斯特桥市长[M].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8]Sutherland, John. So You Think You Know Thomas Hard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82.
编辑:鲁彦琪
On the Carnival Art in Hardy’sTheMayorofCasterbridge
CHEN Zhe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Xining Qinghai 810007,China)
InTheMayorofCasterbridge, Hardy describes four square carnivals, sale of wife, banquet, trial in court and Skimmington, which serve as the big turns in the capricious life of Henchard, the protagonist, and creates a heavy carnival atmosphere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Three Funny Characters in carnival literature. Carnivalesque is both the means to demonstrate the writer’s life view and the narrative way to unfold the hero’s tragic life.
carnival art; square carnival; degrading and upgrading; opposite usage; Three Funny Characters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17
2016-12-30
陈珍(1967-),男,青海湟中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2-0539(2017)05-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