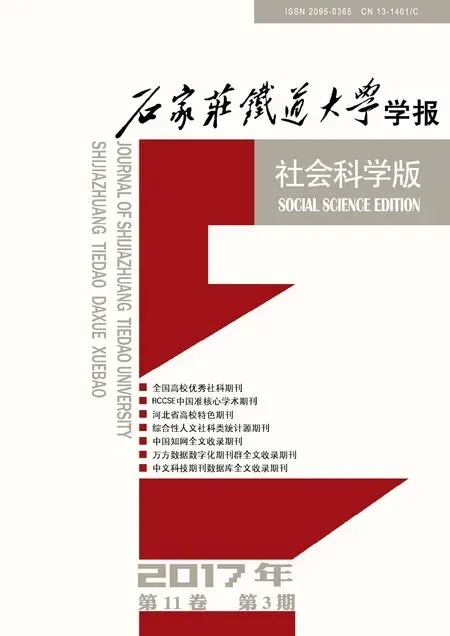规避与借鉴:法治中国视角下发展乡规民约的理念变迁
赵 霞, 刘依霖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规避与借鉴:法治中国视角下发展乡规民约的理念变迁
赵 霞, 刘依霖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乡规民约是由乡民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原则制定并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传统乡规民约曾经作为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蕴含着建设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成分,在一定意义上培养着农民的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权利义务意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也存在背离现代法治精神的因素。例如,过于强调自治而漠视国家法律的权威,倡导息讼厌讼理念而抑制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父权制下的性别歧视冲击着女性权利平等的观念。因此,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必须对传统乡规民约加以改造和完善,既要吸收借鉴其有益成分,更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基本理念,由国家法对其进行现代法治整合与引导,使其更加契合国家法律和现代法治精神,代表和保护广大村民的共同利益。
乡规民约;法治精神;法治中国;规避;借鉴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乡规民约产生于国家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之时,是在一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乡民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原则制定并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非国家强制性。乡规民约普遍被认为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和延伸,处于国家法律的从属和附和地位。当前,站在法治中国的视角深刻分析乡规民约存在的当代价值及其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表现,发挥其积极作用,对于推进依法治理社会,建设“人的新农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乡规民约中契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成分
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史可以看做是中国乡村法治的发展史。作为乡村社会内生的行为准则,乡规民约通过教化、伦理以及相关惩罚机制的约束,培养农民规则意识,化解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持着传统乡民社会秩序。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乡规民约不仅有着社会秩序“超级稳定器”的作用,更与法律精神相辅相成,是对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
(一)传统乡规民约蕴含建设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
法治需要思想观念的文化支撑,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行,同时道德的深厚底蕴为法治精神提供丰厚滋养。“不知耻者,无所不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一个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社会无法培育出遵守法治的社会环境。传统中国由官僚中国和乡土中国构成,[1]并有“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传统。官僚中国体系内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家法保障中央的绝对统治;乡土中国则由乡绅根据乡规民约等民间法的社会教化作用维持乡村秩序。乡规民约倡导淳美的社会风俗,以村民公约、家规家训、议事合同、禁忌规范等为其表现形式,在文字表达上通常使用家常化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包含诚敬谦让、立德修身、勤俭持家等内容的以伦理道德评价机制为主要手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对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明显有悖的行为如赌博、偷盗、溺女婴等,则根据情节轻重相应地作出了包括经济处罚和精神处罚在内的惩处措施,使乡民产生畏惧心理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乡规民约通过道德教化化解矛盾、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形成了乡村最基层的兼顾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治理体系。
例如,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最早成文的乡规民约,其内容非常注重教化,重心在于引导、劝告、督促乡民言行,提倡生活中相互合作帮助。《吕氏乡约》对乡民的教化简约而且具体,可归为四条大纲: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德业相劝下规定: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2]过失相规中规定:“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的行为均为违反道德的“不修之过”。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规定中也详细描述了如何以道德准则来规范乡民的日常言行。明朝时期的乡规民约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官办乡约成为地方教化的主要手段,对当时的风气转变和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明代乡规民约的活动中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宣读明太祖《教民六谕》,二是彰善纠过。《教民六谕》是整个明代实行教化的指导性文件,从“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3]这六个方面对乡民进行道德教化。《南赣乡约》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为指导,参酌继承和发展了《吕氏乡约》的教化意义,用道德的惩戒和舆论的压力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清朝时期的乡规民约基本已经演变为国家政权的道德教育制度,顺治的《六谕卧碑文》、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等都提倡“敦孝弟以重人伦,明礼让以厚风俗”,所涵盖的道德内容包括孝悌、和睦、节俭、守法、热爱劳动、重视教育等各个层面。
(二)传统乡规民约培养农民的规则意识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
法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是秩序,秩序既可以是通过国家的强制调控作用而形成的法律秩序,也可以是人们在长期的相处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自发、原生秩序。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赖于人们对规则的遵守和规则意识的确立。通常情况下,规则意识的确立和对规则的遵守依赖于社会的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通过教育和宣传,首先使人们了解社会生活准则与社会规范的基本内容,知晓遵守这些规则的意义,把规则当做自己行动的理由和动机,[4]使既定的规则内化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标准,把“遵守规则”养成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的自觉要求。在传统乡村社会,国家层面宏大的意识形态话语由于距离乡村日常生活实践太远无法真正影响村民对于规则的自觉遵守,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乡规民约生发于乡村社会更贴近于地方社会的实际,突出的是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调控,具有自我实施的效力,其乡村自治的功效使其在农民中具有权威地位,成为乡民自觉或不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规则。当乡民的行为超出乡规民约的规制范围时,就会受到道德舆论的限制和评价,最终起到“令人知事”和“规矩绳墨”的作用,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当道德舆论不起作用时,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法律就会采取行动对其加以制裁,这同样会培养起乡民的规则意识,内化乡村社会的规则价值观念。
事实上,传统乡规民约的某些基本理念与国家法的原则是相通的,所确立的地方道德体系与国家的道德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这是因为,乡规民约的主要制订者和具体实施者是乡村精英阶层,他们经常邀请国家政权参与到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并通过“报请官府审批、钤印颁布、径直送官等方式求得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5]。例如,黔东南茅贡乡寨母侗寨有一块道光二十五年所立的石碑,碑文记载:“朝廷有禁律,闾里有乡条,均所以约束人心,而近风俗也”。民国大理世德堂张氏祖训中记述了“十戒”“十宜”的教诲。“十戒”包括不危害国族、个人利益,不违背祖先教诲,不扰乱地方公事,不奸盗淫邪,不斗狠好讼,不贪图安逸,不虚荣奢侈,不妄言毁谤,不自矜自伐,不滥交损友。“十宜”则包括奉行孔孟之道,勤奋读书,力行八德,勤俭持家,和睦乡里,不贪大位,多做公益,持平接物,安贫守志,居温行让等。[6]综上可见,乡规民约与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则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从而使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有效地渗透入乡村社会。
(三)乡规民约培育农民的契约精神和权利义务意识
乡规民约是经过一定群体内部协商一致和普遍认同的规则,其社会整合力来源于村民的整体利益,是全体村民对自身部分权利和自由的让渡而形成的公共权力,体现了民众相互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及诚实信用的契约精神。中国古代的契约常以合约的形式出现,既有国与国之间订立的合约,也有社会组织间订立的合约,而乡规民约则属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自治合约。以传统徽州为例,人们事无巨细,常常“央中为凭,白纸黑字”,体现出强烈的契约意识。例如,明清时代徽州民间就有“族内合约”、“族外合约”、“封禁合约”、“甘服合约”等民间合约,分别用于调整宗族关系、保护生产资源以及惩戒过错等方面。[7]苗族通过召开“议榔会议”而制定的“榔规”、羌族通过集体议决村寨公约处理案件的“议话”、河北于家石头村的《柳池禁约》等乡规民约也都是一种盟约,是乡民们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而订立的“合约”。这些合约的制定都遵循了严格的制定程序,以协调乡村公共秩序为己任,将乡村社会中人们之间共同进行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规则以“合约”的方式加以规范,体现出乡村民众之间互利互惠、利益均衡、公平正义、义务互负的基本关系,从而培养起正义观、公平观及是非观。
当然,在乡规民约的条文规定中很难看到使用“权利”等语言表达,但是其中的“不准”或“准许”等禁止性表述和义务性表述以及它的处罚力量,都表明了它在不同生产生活领域内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实质性的“分配”。例如,《吕氏乡约》中的“乡里之约”或“犯约”规定了乡民应当担负起在道德上相互督促、生活上相互扶助等的义务。甘肃腊子口乡的乡规民约不仅规定了村民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还规定了侵犯他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之后的后果。如:为保护林地,禁止各家在“神山”上伐木,如有乱伐者一经查实,其要种植新的树苗或增加一次巡逻守山的义务;若多次伐木或一次伐木众多,按每棵树苗的双倍罚款。只不过,传统乡规民约以义务为本位,在强调义务本位的前提下重视权利义务的对等。但是在讲求尊卑贵贱的严格等级秩序的封建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有限度的。
二、传统乡规民约中背离现代法治精神的历史因素
传统乡规民约是以民间的礼俗、情理、道德等为基础,由乡民根据本地域乡村社会实际制定出的要求乡民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和价值观念,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活的法律”——乡规民约在中国法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宗法礼教观念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传统乡规民约中必然存在着较之现代而言的保守、落后甚至是野蛮的规定。
譬如针对沈从文所说的鲁迅的“憎恨”,聂绀弩先引用了鲁迅1935年针对沈从文而写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1]然后议论说:“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何以如此?他认为,“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荡开笔墨:“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所当爱。”[2]63-66
(一)过于强调自治而漠视国家法律的权威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典型特征是“家国同构”,乡民与官府之间发生关系的只有两件事:完粮纳税与科举考试。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必须依托于“绅权”通过乡规民约来实现治理。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是当时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真实写照。“皇权”治理国家靠的是“国法”,维护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绅权”治理社会靠的是“乡规民约”,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注重的是道德和人伦的礼法秩序。一般而言,乡规民约的制定宗旨与国家法律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巩固既定的社会尊卑等级秩序,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但是,由于乡规民约过于强调在私人领域的自治能力和自治权威,在国家话语与民间表达方面并不始终与国家法保持高度协调与一致,经常出现与之相背离的现象。
例如,明万历年间的《祀产条例》对盗卖祭祀田产的行为做出“捶杀”的规定:“如有不孝不义、盗卖祀产,听自为首之人检举,责令取赎,仍行犯一赔九。如有敢恃强梁,听众立文排名花押,告祖捶杀之。”明末歙县也有用私刑残害奴婢的俗例:“徽俗:御婢之酷,炮烙、挺刃习以为常。”歙县潭渡村《潭滨杂志》也记录了三桩宗族以“沉塘”和“聚薪活焚”族人的案件:“吾族缒水之事,此外尚有风闻者一、目击者一。风闻则某以乱伦,故为族众缚而沈之于水者;目击则某本无可杀之罪,特与同堂兄弟素不睦,大清兵初入徽,府县有司俱未具,族众俱避乱入山间归守,视者不过十余人,遂为从兄弟二人所执絷其手足,盛以布袋,肩而沉之水舌。……近年,稠墅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捶杀、沉塘、活焚等处罚本应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府才能够具备的刑罚裁定权和执行权,出现在乡规民约中由非正式的国家组织宗族来实施,明显与国家法相抵触。尽管有些乡规民约中明确指出:“家法治轻不治重,家法所以济国法之所不及,极重至革出祠堂,永不归宗而止。若罪不止此,即当鸣官究办,不得僭用私刑。”“山乡恶俗,有重责伤人及活埋者,此乃犯国法,非行家教也。”但是在传统乡村社会,由于法律往往被统治阶级用作抑制私欲、消灭争诉的工具,而不是维护个人权利、解决乡民之间纠纷的手段,[8]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其地位也总是被忽视。
(二)倡导息讼厌讼理念而抑制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
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礼俗社会,讲求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村民个人意识、宗族意识和家族意识比较强烈。面对邻里冲突、家庭婚姻等纠纷,农民更愿意选择温和的、不伤害感情的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非诉讼方式的总原则是以儒家纲常伦理对乡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劝导,讲究情理,以情动人,使当事人不再为“财货细故”而相争讼,从而缓解矛盾,息讼罢争。于是,乡规民约就承担起调节乡村民间纠纷、维护基层秩序的主要功能。王守仁的《乡约法》规定,“一应斗殴不平之事,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石末镇乡约碑记》中记载:倘有户婚争斗,一切小忿,互相劝什,或闻之约长、保副,从公问其曲直,与之明白,两相输服,以杜后言,勿使轻讼。明初在各乡设“申明亭”,择公正可任事的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词讼,“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判决。”清代《圣谕十六条》中的“和乡党以息争讼”成为当时处理民间纠纷的最高准则。
从诉讼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以及风险成本的角度来看,乡规民约由于是站在“情”和“亲”的立场进行调解和劝导,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给乡民们提供了最为节约的成本投入,从而达到了息讼、止讼的目的。“由提倡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处息讼,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的较好的方法,其制度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实施之广泛,在世界古代法制史上是仅有的。”[9]但是,由于受乡规民约中息讼、止讼观念的影响,百姓耻讼、惧讼、畏讼、厌讼、无诉有德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冲淡了权利意识。人们在面对民事纠纷甚至是刑事案件时,总是选择请宗族内部德高望重的长者调解而回避诉讼。“息讼、止讼”的观念维持的仅仅是社会表面的平静和稳定,实际上却造就了社会纷争得不到公正审判。人们迫于情与理的道德舆论压力,在调解的过程中不免要让渡自己的部分正当权利,致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惰性,社会处于“死水一潭,波澜不光”的状态,使得人们难以形成“法律信仰”。
(三)父权制下的性别歧视冲击女性权利平等的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其生产特点决定了人们必须选择“男耕女织”的劳作模式。男性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支撑力量,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照顾者”的角色,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在乡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对以“父权制”为中心的封建意识的体现,也就必然存在着歧视、损害、限制女性权益的规约,造成男女两性在乡村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控制力不断加强,剥夺了女性的政治、经济以及人格独立权等权利。
明以后的乡规民约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大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烈观,要求女性坚守“夫为妻纲”,将女性“夫亡改嫁”的行为视同罪恶,以维护国家封建纲常礼教的权威地位。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多个乡规民约中就规定已婚女性应该从一而终,“妇人之道,从一而终,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如果“不幸寡居,则应丹心铁石,白首冰霜”。同时,家族内部也认为贞洁烈妇能够获得朝廷的“旌表”是整个家族至上的荣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乡规民约对违背“一女不事二夫”封建伦理思想的妇女,作出“轻则公堂不齿,重则告祠除名,或屏之外氏之家”以及“再嫁者不得入祠”等耻辱性的惩罚规定。而对于“失贞”女子的惩罚更是严苛到施以沉塘、火烧甚至凌迟处死等程度。同时,传统乡规民约将夫妻之情和父母之情置于对立的两级, 鼓励丈夫专心于孝敬父母,放弃夫妻情分,“人若失了妻子,妻可再娶。如若伤了父母,哪里再得个父母?”这些规定或者被每日宣读,或者由家中长者定期讲授,在反复的熏陶和灌输下女性认同了自己的从属和依附地位,自觉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作为日常行为的根本信条,从而丧失独立人格。
三、理念变迁:法治中国视角下制定现代乡规民约的传统借鉴与规避
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完善行业规章、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乡规民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村落的日常生活秩序,尽管在当下乡村社会中已失去主导性地位,但作为一种原生性的乡村文化体系,乡规民约的继续存在及其现代适应性改变,对于形成更加有序的乡村社会秩序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现代乡规民约要以法治中国为背景,在内容、形式上逐步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体现出理性化和制度化,既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效的规制条则,审慎地摒弃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的规制内容,还要以顶层设计体系和国家法律法规为主导,秉承保护群众公共利益的原则,在广大村民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村民会议等方式制订和修改,真正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有益补充。
(一)借鉴传统乡规民约的道德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现代乡规民约的完善
传统乡规民约中能够为法治所用的部分,是其具有的强烈的教化色彩和道德伦理目的。2014年,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四次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文化营养。”[11]传统乡规民约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旨在弘扬德教、促进和谐,既是农民进行自我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重要源泉。“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12]现代乡规民约中的道德标准与道德习俗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体现的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农村的价值认同,适应的是现代新农村的发展需求。因此,现代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要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看到传统乡规民约的教化功能,关注乡民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诉求,传承其中的诚信理念、善良风俗、礼治观念等精华要素,并伴随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需要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因此,现代乡规民约的完善还应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结合,打造乡规民约发展的时代风尚。应充分吸收和借鉴胸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追求,树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秉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从而做到法治与德治的协同发力,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对乡规民约中存在的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协调、不“合拍”甚至相悖的内容要及时修改或废止;对乡规民约的道德教化效果要进行评估,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风险,发挥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对侵害乡村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及时予以规诫遏制,以期祛恶扬善。
(二)摒弃传统乡规民约对国家法律主导地位的漠视,强化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
在现代法治中国,乡规民约可以填补法律空白,但不能替代法律,更不能与现行法律和法治精神相悖。因此,针对传统乡规民约过于强调自治而漠视国家法律主导地位的弊端,制定现代乡规民约应以法治中国顶层设计体系和国家法律法规为主导,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的法律地位与正当程序,使乡规民约具有突出的规范性、民主性、实用性、时代性、合理性的特征。[13]现代乡规民约应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合作和互动的产物,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14]事实上,我国关于乡规民约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乡规民约的制定必须由国家法律加以整合、引导和制约。
首先,按照法律规定,现代乡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是村民,由村民会议行使。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制订实施者是乡村精英阶层,而现代乡规民约则应当反映全体村民的意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现代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参加村民会议的村民年龄必须是本村村民且年龄在十八周岁以上,到会村民的比例必须过半数,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这样的规定既承认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地位,也彰显了乡规民约的程序严肃性。其次,现代乡规民约的内容应符合国家法的原则和精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规民约的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应当剔除传统乡规民约中违背法治精神的落后迂腐的内容,更多规定契合乡民实际生产生活,调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乡民素质提高、乡村环境美化等层面的自治行为规范。例如,剔除家长制、性别歧视、暴力以及舞台化、场景式的惩罚机制等内容,增加遵守法律、保护山林、合理使用土地、爱护环境、加强禽畜管理等内容,要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出发,建设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再次,应有效借力传统乡规民约在调解民事纠纷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传统乡规民约追求和谐无讼、讲究息事宁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部分村民的权利,抑制了人们的“法律信仰”生成,但是民间调解机制具有灵活高效、节约农民诉讼成本的优势,是乡村社会化解纠纷的重要渠道。在现代乡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应借鉴其积极成分,将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基层治理规范中充分融合。
(三)规避传统乡规民约中对村民利益的忽视,代表和保护广大村民的共同利益
传统乡规民约总是在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博弈和互动中完成着自己的历史演进。农民是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约束对象和参与方,他们对乡规民约究竟是持认可还是否定的态度决定着该乡约能否最终获得顺利实施和执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凡是得到农民阶层价值肯定和认可的并满足农民阶层现实需要的乡规民约都能够顺利实施执行;凡是受到乡民抵制和否定的脱离乡村社会实际与农民实际需求的乡规民约都逃不脱失败和废止的命运。因此,制定现代乡规民约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真正代表和保护广大村民的共同利益。惟其如此,现代乡规民约才能在法治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分析我国现代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不难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忽视农民主体地位,剥夺农民话语权和参与权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乡规民约依然被认为是新的乡村精英(乡镇政府和村干部)意志的表达。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村民自治只是停留在形式上。伴随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选择远离家乡进城务工,这种空间的阻隔使得青壮年农民无法真正参与到乡村自治。而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孺因为缺乏文化修养和远见卓识,也会主动放弃参与自治的权利。于是,多数村庄的乡规民约就不得不交由村干部进行讨论和制定,无法体现和代表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统一的乡规民约范本,在内容上千篇一律,体现不出任何地域特色,甚至成为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翻版。尽管它们与国家法律和政策相适应并在理论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由于反映不出本村村民的利益诉求,缺乏现实针对性也就无法切实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其存在也就形同虚设。
因此,为确保乡规民约能够得到顺畅的贯彻和实施,并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其权威地位,就要求将乡规民约融入到乡村实际社会生活中想农民所想,所制定的内容要充分反映农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并切实使农民的各项权利得以保障。只有这样,乡规民约才会真正发挥其教化、规范、引导、评价等作用,在村民集体中形成权威性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准则。例如,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顿庄村对原来的村规进行了修订,废除了对妇女不平等的部分条款,新增了11条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体现了对女性的人性关怀。
[1]徐勇.政权下乡: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J].贵州社会科学,2007(11):4-9.
[2]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31.
[3][作者不详].明太祖实录: 卷二五五[M].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4]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内马斯的批判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7: 125.
[5]党晓虹.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J].中国农史,2010(4):100-105.
[6]赵旭东,朱添谱.乡规民约与新乡土秩序的建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7):24-27.
[7]付微明.习惯法精神及其对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作用和影响[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8):114-118.
[8]张文香.传统诉讼观念之怪圈[J].河北法学,2004(3):81.
[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83.
[10]林济.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J].中国农史,2003(3):23.
[11]陈旭峰.现代乡村需要乡规民约的文化滋养[N].学习时报,2014-12-29.
[12](法) 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学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4-65.
[13]傅珊.重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N].人民日报,2014-04-23.
[14]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J].东岳论丛,2004,25(4):49-56.
AvoidandReference:OntheLegalValueandDevelopmentoftheTraditionalVillageRulesintheRuleofLaw
Zhao Xia, Liu Yilin
(College of Marxism,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Village rules are some codes of conduct formulated in history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abou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villagers. As a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idea of constructing the rule of law,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ules used to be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national laws.It helps to cultivate the rules consciousness, the "contract spirit"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onsciousness, and service state ideology.Bu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ules also exist some factors that deviate from the spirit of modern rule of law.For example,too much emphasis on autonomy over the authority of state laws; advocating the idea of disgusting suits and dropping suits which inhibits the formation of legal beliefs; the sexism under patriarchal system impacting women's equal rights. Theref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valus of socialism, we should reform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ules, making it more suitable for national laws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rule of law, protect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rs.
Village rules; spirit of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in china; avoid; reference
2095-0365(2017)03-0063-07
2017-05-25
赵 霞(1975-),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社会治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5YJC710078);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HB15MK014)
:C912.82
:A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7.03.12
本文信息:赵 霞,刘依霖.规避与借鉴:法治中国视角下发展乡规民约的理念变迁[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