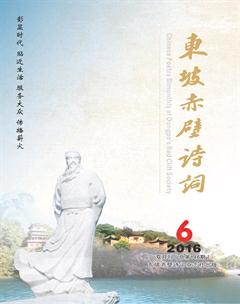槛外谈诗(一)
夏元明
1.钟嵘《诗品》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也。”
赋、比、兴之说,古已有之。钟嵘此论,最给人启发者,在于他对比兴和赋在运用上的区别,不独旧诗如此,新诗亦然。写诗而专用比兴,其意往往隐藏较深。隐藏的好处在于含蓄,在于余韵悠长。但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导致过于隐晦,甚而至于晦涩。比如李商隐,喜欢他的人在于他的曲折含蓄,有不尽之意,富多样解释。而不喜欢他的人,也在于他的不易求解。林黛玉不喜欢李商隐,只称道他的一句诗:“留得枯荷听雨声。”然“留得”一句,恰恰在于它的浅白易懂。比较而言,赋体则相对质直,但运用不好,又易流于浮浅,文字也易于散漫,仿佛飘荡之舟,无所依傍。这也是初学者易犯的毛病。赋、比、兴三种手法必须有所调和,要之在于“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既不能忽略风骨,也不能失之于文采,各种元素须得和谐。当今写新诗者,所谓“先锋派”则多用比兴,病在晦涩;而“口语体”随意举事,病在浅俗。故新诗能动人的优秀作品极少。写旧诗者往往自认为风雅,多瞧不起玩新诗的,殊不知两者往往犯同一错误。诗非易事,新旧都当慎之。
2.钟嵘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诗最忌讳的是无病呻吟。但古往今来,无病呻吟者多矣。诗应当是情动于中,而言行于外。所以非常佩服一些为诗者,遇事都可以来一首。其实,这大多不是诗,文字游戏尔。但文字而能成为游戏,从文字的把玩中获得一种快乐,也是为之聊胜于无之事。所以,我们对某些只会排列平仄的人,也不能责之过苛。如果不是真的无聊和肉麻,玩一下平仄也无不可。但说到真正的诗,还是要有真正的生命。就如钟嵘所说的,“生命不谐,声颓身丧”,方能写出真诗,真正打动人。当然,我们也不能都像李陵,有那种非同寻常的经历,也不必非得“声颓身丧”而后为诗。这只是一种特例,要义在于必须有真正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受。这是真正诗歌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有艺术修养和锻炼。其实,艺术修养也有天才的成分,不是宵衣旰食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另一话题,姑且放下。
还是说诗的内容。我们读屈原,爱杜甫,除了他们的诗才,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精神情感,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们对生活和生命,对时代和人民的特殊感情。在当今的新诗人中,我们也特别推崇昌耀。读昌耀的诗,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也与昌耀苦难的人生密不可分。昌耀的成功,既有他的苦难,也有他的境界,也有他敏感的诗才。只有这样的诗人能传之久远,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
3.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到底是大师。杜甫的诗有些写得非常细致,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观察非常之精细。但我更佩服杜甫的大气。杜甫的诗,哪怕是写眼前的景,境界也非常阔大,而且不是硬吼出来的。有些人写诗,喜欢用大词,装腔作势,“瘦猪婆屙硬屎”,这不是真正的大,是李鬼而不是李逵。就以这首小小的绝句而言,“黄鹂”“翠柳”“白鹭”“青天”“雪”“船”,都是眼前景,不会写的人,顶多也只是一幅小画面,清新雅丽而已。但杜甫却写得很有气势。这个气势有动态的,四个关键动词“鸣”“上”“含”“泊”,不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事物的特征,更营造了一种气氛。特别是“上”字,将白鹭和青天的关系表现得十分开阔,有游目骋怀之感。再就是静态的,更是杜甫的拿手好戏。雪不是普通的雪,是“千秋雪”,是经年不化的积雪,给人一种时间上的久远感。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自有一段思古之幽情。船也不是普通的船,是东吴的“万里船”,又给人一种空间上的辽阔之感。眼前小景,轻松道来,却是浩然旷渺,历史时空。这是真正的大手笔。以小见大,《绝句》是很好的典范。
4.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香菱学诗,说有些诗句看起来没有道理,比如“大漠孤烟直”,烟怎么会是直的?而有些却又似乎完全不必说,如“长河落日圆”,有什么必要写?但就是这没有道理或不必说之中,讓人感觉到真切的画面。香菱所言极是。不独于此,旧诗中有些感触简直是虚构的,并不是真实的心理。比如王安石的这首《梅花》。王安石是不是被白梅所欺骗,将其误认作了雪?但诗人又说得清楚,“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因为有暗香,大老远就知道那不是雪。可这说了岂不等于没说?说了有什么意思?加上前面两句铺垫,分明交待是梅花在那里凌寒自开,更不可能产生错觉。所以,这首诗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做作”的,并无诗意。拿来和李白的《静夜思》比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种错觉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且后面的感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并不凑合。这样的诗才有诗味,是好诗。可是王安石的这首诗历来为人们所喜爱,看来读者已经认可,诗的逻辑与日常逻辑是有区别的,不能拿生活逻辑要求诗的逻辑,否则诗没法写。常听到一种说法:“这是写诗!”如果批评《梅花》不是诗,人家就要说你是钻牛角尖了。
5.袁枚《随园诗话》:“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
很多作家谈创作体会,都讲向群众学习语言,袁枚也懂这个道理。不仅向高于自己的人学习,更向普通老百姓学习,所谓“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但袁枚的境界终嫌狭小,“霜高梅孕一身花”尚可,“月映竹成千个字”就没多大意思。这里似乎也观察得细,但细得略近无聊。远不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之类的句子来得有情趣。看来学习语言不错,但如何学,学什么,还是取决于学习者的心胸和才情。尖细狭小之人,只看到了语言本身的一点趣味,而没法形成生命和艺术的大境界。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作家协会会员、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