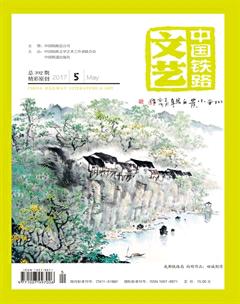北京的春
一
从花鸟市场买了盆蔷薇,平日里摆在外面,进了冬月,搬进了卧室,摆在南窗处,没想到正月里居然开了花,红红的小花球们压满了枝头,低调而繁盛。窗台上的那几头水仙也刚好开了,闹得屋子里春意盎然。看看日历,正值立春。
屋里的春,似乎与北京的春没什么关系。
北京的春,最早也要到二月中旬,七九八九,才能从鹅黄的、变软的柳条上寻着些踪影,这还是有些雅兴的人。多数的人们,则是边犹豫着在这乍寒乍暖的早春是否要脱去冬衣,边抱怨着北京的春天风沙实在是多。几阵春天才有的热干风,贴着地皮,打着旋儿,携沙而至,才几天,就把人们连跑带颠、迷迷瞪瞪地刮进了夏,而春早已无影无踪。那些有雅兴的人,只好站在五月绽开的蔷薇前,想象着被风刮跑的春的模样。
老舍在《骆驼祥子》里写道:“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脱了棉的,几乎用不着夹衣,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北平没有多少春天。”
就是这样,北京的“春脖子”很短。
在北平住过20年后,周作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袷可以随意倘佯的时候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
北京的“春脖子”不仅短,还要让人们在“春脖子”里把“风”味尝个够。
林斤澜在《北国的春风》里说:“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那时候的北平,街道修整得很不好,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和长安街等几条主要的街道是石子铺路外,大多数都是黄土路,更不用说胡同里了。黄土路被过往车马捣腾得已成了浮土路,一脚下去黄烟四起。梁实秋在书中如此描绘:“无风三尺土”,“刮风时像大香炉”。
莫说那时候的北平,20多年前我初来北京工作,那些个春天,跟大师们过的没什么两样。春天极短,似乎从没享受过春光美,就跑步进入了夏天。北京的风,冬天没刮够,就跑到春天来刮,经常是借着随处可遇的土路、荒地,急火火地裹上沙土,贴着地皮疾跑,又没个方向,四处乱窜,遇见人了,就把沙土狠狠地扬你一脸。
“春脖子”短且不说,风沙不说,春天的景致也没看到什么。杨树、柳树、黑黑的槐树,老三样,没什么其他花木,就连城区里的杂草,也被勤快的人们消灭了,到处光溜溜的。槐树最懒,秋天落叶子最早,到了春天,已经杨柳依依了,槐树却还是黑杈杈的,把个仅有的春意也给抹煞了。
难怪,写了一辈子北京、爱了一辈子北京的老舍,能把北京的年味写得那么细致和浓郁,能把北京的夏趣写得那么热烈和鲜活,能把北京的秋果写得那么水灵可人,却没舍得多赞美两句北京的春。就連大大咧咧的虎妞都郁闷了:“现在,火炉搬到檐下,在屋里简直无事可作。院里又是那么脏臭,连棵青草也没有。”
二
但那已是过去的年月了。
这些年,北京的春,变了。
京城花木深。不知怎的,北京的花木就多了起来,有意中透着无意,搞得春实在令人感动。
二月下旬,春寒料峭,我走到木樨地的河边,无意中顺着“营城建都”滨水堤岸向南远望,忽然发现沿岸垂柳已换了春装,嫩黄嫩黄的,随风摇摆的枝条如烟似雾,撩拨得心里痒痒的,这才发觉原来是春天叩响了心扉。
三月初的一天,上班路上的那些迎春花开了,冲着阳光露着笑脸。妻子说,她们公司建国门附近的迎春花上周就开啦!唉,春来,也不找个招呼。随后的半个月,你可以随处随意地欣赏着京城里的迎春花。
当我还在从满眼的黄色中试图分辨出迎春与连翘时,不经意间,白色、紫色跃入了眼帘,一株株,一片片。那是玉兰,肥厚妖冶的玉兰。北京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玉兰,竟敢开得如此大胆张狂。京城早春三分色,二分无赖在玉兰。
真正把浓浓的春意唤醒的,是早起的布谷鸟。寂静的早晨,那声声“布谷,布谷”从楼下的小树林里悠扬地传进了家里,也唤来了清明。
清明春意浓。清凉清爽的清明前后,北京的春最为绚丽生动。花,花,花,到处都是花,紫荆花,榆叶梅,紫叶李……不消说玉渊潭的樱花,就连路边随处可见的看桃与杏花,也不输樱花几分姿色。每当走过中央电视台到公主坟这一带时,我都要细细欣赏一下夹在长安街与自行车道之间的这片桃花。
当樱花和杏花纷纷飘落的时候,海棠正恰当时,北京体育大学的那几株硕大的海棠树,着实惊艳。红花碧桃也来凑热闹。最喜浓郁芬芳或紫或白的丁香,一丛丛,一片片,香气四溢。
这个时候,别忘了看看水。昆明湖,什刹海,北海,被风吹皱的春水荡漾出了心头的那份活泼。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冲洗着角楼的倒影,散发着清明的洁净气息。
人们被春鼓动了出来。公园里的合唱团,唱响了春的旋律。那些舞者,跳起了春的节律。要是去天坛公园,你会惊诧于那些踢毽子的怎么会有那么敏捷的身手和高超的技艺。而此时咿咿呀呀、蹒跚学步的孩子向你走来时,你就会惊叹于春的伟大了。
三
是啊,春带来了生气。春,也带来了吃食。
“该出去挑野菜了。”
每到清明假期,母亲就会提醒着在春光里打盹的我们。于是,全家坐着公交车,来到四季青的旱河路一带挑野菜,开启了“吃春”序幕。
荠菜已经过了景,最好的时候应是在惊蛰春分。三月三,苦菜钻天。现在正是苦麻菜,曲麻菜……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也不太会挑。但回家后清水一洗,蘸着豆瓣酱吃起来,我吃得比谁都多,吃得比谁都美。这苦味,苦得清爽,苦得舒坦。这苦味,带着回甘,让人踏实,觉得这才是春的味道,这才是生活的味道。要是再用早些时候挖的荠菜包顿饺子,那鲜亮劲儿,那整个春的味道,一下子盈满口腔。
路边有棵榆树,摘下一把浅绿的榆钱放进嘴里,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最美不过香椿。清明前后正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或者用水焯一下直接凉拌,如果再撒上一些毛虾拌一拌,更是美味。据说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吃香椿。那天晚饭,母亲又端出了一盆用水焯过的树叶子,拌了面酱,吃起来清新亲切,忙问这是什么。母亲说,今天小区修剪柳树,从地上的柳枝摘下来的叶子,正嫩。在母亲眼里,春就是野菜、榆钱、柳叶,春就是给我们做春菠、春韭馅的大饽饽,春就是边拆洗棉被,边惦念着老家那棵又要找人修剪一下的老香椿树。
不知不觉到了四月下旬,很多花谢了,落英满地,正伤感之中,却惊喜地发现小区里的金银木已然悄悄开花,雪白的洋槐花也是挂满了枝头,就连前日里科学院大学的那一排排看着还枯枝满架的紫藤,怎么不经意间也在老干上挂满了紫葡萄般的花朵,难道是要给那些粗心的人们一次补偿赏春的机会?对了,如果你是南方人,不妨去海淀田村,那里种了一片油菜花,黄澄澄的,花香浓郁,让你不必下江南,就可幽思家乡的春了。
如果有机会去胡同里转转,你会发现古香古色。高大老旧的泡桐树,枯枝满树的,却在老枝头挂上了新“喇叭”,白里透着紫,飘来阵阵香气,甜甜淡淡的。有的泡桐树还半遮半掩地藏在青砖老屋后面,探出半个身子,招揽着赏春之人。仰起头,看看蓝天映衬下的喇叭状的泡桐花,还有花旁那团大大的穗状老枝头,沧桑中透着新意,愈发动人。清风吹过,花儿簌簌飘下,掉到房顶,落在路上。不知这花朵繁复、花香甜淡、树姿优美、高大沧桑的泡桐,算不算是老北京的“古香古色”,能不能代表胡同里的恬淡春色。
到了立夏,春还留恋在北京,占着位置不肯让夏挤进来。可不是,想当初立春的时候,凶巴巴的冬也是占着春的位置。
二环路、三环路中间的隔离带,艳丽而肉墩墩的矮牵牛迎风招展,雍容华美的重瓣月季,吸引着人们再看一眼春,让匆忙的路人在匆忙的路上不再那么匆忙。
四
是啊,慢下来,看看风景,春就在楼下等你呢。小区里的各色花木全都有,这儿一棵,那儿一枝的,大氣而随意地妆点着阳光下的视觉空间。太自私,把个春全都招揽到了小区里。都说“向阳花木早逢春”,是不是“向阳心情多春意”?
无意间,我忽然发现了春的底色,一下子弄懂了春的画笔描出来的春景为什么会这么可人优雅。在二月份就从墙边钻出来的小草,在大型花木之下静静开满整个春天的二月兰,随风摇曳的蒲公英,还有无处不在的也是开满整个春天的擎着小黄花冲你招手的苦麻菜……这不正是春的底色吗?它们在风中,在土里,无人修整,无人搭理,甚至连张相片都没有。正是它们,给了春不张扬、不繁复的底色,给了春不矫揉、不造作的底色,给了春之所以能称之为春的底色。当那些大型花木的繁华褪尽时,它们,依然在风中,在土里。
北京的春,美吗?如果没有“风”韵,还不够美,仍缺点味道。还是那么强烈,还是四处乱撞,是的,风来了,北京春天的风来了。只有这熟悉的风舔着我的脸,还用“似花还是非花”的柳絮杨花迷着我的眼,才让我体会到这才是熟悉的春,这才是北京的春,它是如此地实在,如此地真切。与那年月不同的是,世道变了,风不太好找沙土扬我了,只好胡乱裹着各种花香和落英,扑向我跟我胡闹。
有了底色,有了风韵,北京的春才活了。
还觉得缺点什么?是书香吧。那就去逛逛北京的春季书市吧,书香溢满京城。如果觉得书市太闹,那就带孩子去鲁迅、茅盾、老舍的故居看看,看看他们写在稿纸上的端庄秀雅的毛笔小楷,看看他们栽的树,看看孩子能不能答对老舍故居里的那10道选择题。想更清静些,就去潭柘寺、大觉寺、八大处坐坐,沏上一碗粗茶,看看山寺桃花,手捧老书,慢慢展开,细细读来,品味禅意北京……
作者简介:田绵石,男,1972年生于河北,1994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现就职于中国铁路信息技术中心。曾在《秦皇岛晚报》《唐山晚报》《唐山劳动日报》《燕赵都市报》《人民铁道》报《中国交通报》等文学副刊以及《湖南散文》《中国铁路文艺》《散文选刊》等文学杂志发表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