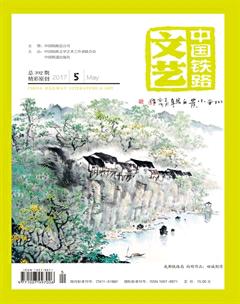静静的吊钟岭
刘景明
一
吊钟岭实在小,信丰县版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我循着先前的晨钟暮鼓余韵,设法追寻它的内在本源。
它是安西镇太平村的一座山岭,当地人称之为庵高,通往安远、寻乌、广东梅州等地要道,南面近两公里处为始建于宋末元初的海螺寨。据考证,南宋高宗的后裔赵时赏、赵溍、赵宗鐖在此扎营驻兵,文天祥也到过这里。可以想象,海螺寨或许死了个皇室要人,他们停下来吹打举行安葬仪式。安西民众为纪念他们,寨上供奉着“三堡老爷”,有了“老爷会”习俗,于是便有了“安息”(安西的原名)之名与太平之名。从上迳水库溢洪道沿山路北行,进入大坑屋场地界,朝东边就能望得见吊钟岭。大坑又名叫梧桐岗下,1965年兴修上迳水库,一部分库区居民移至于此繁衍生息,男丁清一色姓曾,与同期搬离到邻近的大屋、禾树山有着相同的宗族。我的爷爷奶奶在此先于他们31年开基,爷爷1957年过世埋葬在吊钟岭的一个山坡上。
今年清明时节,我携小儿跟随父亲去了他的坟茔前祭扫。车行大坑屋前小道,一棵古樟粗壮如桶,叶片吐露新绿。盖青瓦、粉石灰的土屋错落有致,却不见炊烟,也不见人影,仿佛仍在晨曦中沉睡。一辆带斗工具车在路中间停放着,我按响喇叭提醒。一位老人从一间矮屋里出来,卷上烟丝舔着烟纸,跑小步走近。父亲上前与他握手打招呼,相互叫对方的乳名。老人说,前几天车主去吊钟岭的脐橙山地,返回途中车子出了故障,车主去叫人修理还没回来,我们一起向前推车挪开位置。他说,村子里40多户人家,好多年前搬到圩上或县城去了。父亲告诉我,他是位孤寡老人。1955年9岁开始,父亲走十多里路去太平小学读书,他和父亲是上下年级。解放初期,太平小学是一至三年级的办学制,父亲有十多个同学,譬如做过民办老师的曾祥忠,还有成为我岳父的曾祥连,他们过后转到兰塘小学读完四五年级,继而升入圩上初中。父亲对儿时往事记忆犹新。父亲说,他看到外面有许多村庄,人家的房子整齐,为什么自家住在孤零零的山上?我们的祖先究竟在哪里?
过了一座拱桥,父亲说此处叫高叉坑,小时候听老前辈讲过许多红军英勇作战的故事。父亲指着边上的一堆砖土泥墩,有一位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埋在下面。我联想起有关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堂部3个师和1个独立旅,已在塘村、龙布、重石、版石、金鸡、新田、安西一带筑碉堡重兵防守,一支长征的红军先头部队在信丰新田、古陂、安息一带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新田百石、古陂圩和安西桐梓岗与国民党粤军守敌打了几场恶战,百石一仗是红军长征第一仗,红四军师长洪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桐梓岗战役打得尤为惨烈,敌我双方各伤亡四五百人,红军作战科科长郑伦阵亡。红军打过桐梓岗战役后突围到大坑,再与堵路的白军打了一仗。1935年3月3日,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等人领导赣南省党政机关和部队2000余人编为3个支队开始突围,从于都上坪山区到信丰、安远沿线,遭到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堂部的阻击。3月6日,阮啸仙率部突围到达信丰安西上迳时打了一场恶仗,阮啸仙牺牲了,时年38岁。
阮啸仙生于1897年8月17日,是广东省河源县义合区下屯村人,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临时中央政府领导。1934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人民政府第一任审计主任和新中国审计工作奠基人。我问父亲,阮啸仙烈士有没有可能是在高叉坑中弹负伤的?父亲沉默了,没有直接回答。关于阮啸仙牺牲地的记载是:阮啸仙中弹后,牺牲地为上迳枫树庵的一个土埂上,而他在哪里中弹负伤,却没有确切位置。有一种民间口述略微详细:1935年3月5日,上迳水库坝首边上的铁针寨那边枪声激烈,一位腰挎红军银元、金条等军饷的红军战士,把身负重伤的阮啸仙背進一座茶亭里躲藏,然后出去与敌继续作战。傍晚时分,奄奄一息的阮啸仙哮喘病复发,被国民党兵发现了,几个士兵得知他是红军大官,把他捆绑放到木板上,抬去赣州向国军领赏。抬到枫树庵地段时,阮啸仙停止了呼吸,士兵丢下了他。还有一说法,铁针寨那边有个山洞,牺牲过一位红军将领,当地人把他就地掩埋,这位红军将领是否阮啸仙不得而知。而那位背阮啸仙的红军战士,被打散后躲进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托户主保管好军饷,他再去营救阮啸仙。他到了茶亭,却不见阮啸仙的人影,便急急返回那户人家取军饷,可是,那户人家的大门锁上了。他蹲在屋边等了几天几夜,哭了几天几夜,无奈他一边讨饭,一边打听阮啸仙的下落,最后他离开了大坑不知去向。当地老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捡过子弹壳,小孩子穿个弹壳孔装上硝当火枪玩具。枫树庵、铁针寨这两地与吊钟岭仅隔一两座山的距离,只不过是方位不同。
二
其实,爷爷是阮啸仙突围战斗的亲历者之一。爷爷何许人也?从他留下的遗书中,我清楚了他的身世。爷爷1898年生于会昌县晓龙口乡晓下村老屋下,真名叫刘林三,又叫刘明翔,按照房族辈分“道德光明同、礼义家声振”排列,爷爷属“明”字辈。爷爷有三兄弟,爷爷排行第三。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参加了武装起义。次年2月11日,由当地党组织领导人郑永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上级党组织培训,在模范营训练。他担任过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乡政府主席,会昌中心县模范营第一连连长,经常到会昌县和江西省委集训,到瑞金中央苏维埃政府开会,见过毛主席头戴烂斗笠,脚穿草鞋,开会作报告。有首宣传红军的纪律歌是这样唱的:“红军纪律最严明,一切行动听指挥,捆禾草上门板,买卖要公平……”这首红军纪律歌,爷爷教父亲唱过,父亲至今都记得这首歌的音律:“25——36532,16132——,532132,162765”。爷爷参加福建长汀阻击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之战,右脚中弹受伤被抬回会昌治疗。之后任会昌县高排区裁判部长、会昌县政府裁判部调查员。1934年革命形势处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孤军作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爷爷脚伤未愈,不能跟随红军长征,继续留在当地搞地下工作,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出卖了党的机密。当天,国民党匪军包围了晓龙口,大部分革命志士、党员被害。爷爷的两个哥哥和嫂嫂全被抓杀,爷爷的前妻也被杀害,他们都是在一个戏台上被枪杀的。当晚,爷爷到麻州区做调查工作,与国民党兵交战,被包围在晓龙口圩上,无路可逃,求圩上一家打铁店的郭生昌师傅救命。郭师傅二话没说,马上拿一只木炭笼将爷爷罩着,上面用铁锹铲木炭盖着,才幸免被进店的白军抓捕。
次日清晨,郭生昌取出一套大面襟便衣和宽脚便裤,让爷爷换上(爷爷的金属党证、党章全留在那件换下的衣服里),又挑出一担炭笼,给爷爷挑上,并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了,以后你的身份就是烧炭佬,赶快离开,并给爷爷两块银元。当天中午,爷爷路过邻近屋场桂林岗,遇见本屋场的王友发,她的娘家在桂林岗,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又得知爷爷的妻子被害,就跟着爷爷一起逃走,后来与爷爷结为夫妻。他们白天躲在山上,晚上赶路,一路上乞讨,过信丰新田罗汉石、古陂,来到安息乡桐梓岗。爷爷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红军与白军在桐梓岗也打了一仗便停歇下来,被桐梓岗屋场头子陈祖禛家收留,帮他家干了一段时间的零活。过后,陈祖禛打发爷爷奶奶离开,介绍他们去吊钟岭吃斋念经守庙,这个庙叫金莲山庙。爷爷从此改名换姓为钟远兴,奶奶改成刘二妹。爷爷在此烧香拜佛,习武收徒,医治病人,开垦农田,生活了长达23年。
前年清明,我从过世的伯伯遗物中,看到了他收藏的爷爷遗留的几本毛笔手写经书,其中有对阮啸仙烈士的悼念、缅怀、歌颂等,里面的内容鲜为人知。一个被埋没、忽略的红军失散人员怎么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工作奠基人挂上号?爷爷是受中央苏维埃地下党组织秘密派遣,为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保存革命火种而潜伏下来的吗?
當天,阮啸仙部队在突围过程中,从上迳水库东侧边打边退,牺牲了四五十名红军战士,爷爷带着大屋、稳陂、禾树山等二十多个习武的、做道土的徒弟,手持木棍、大刀从金莲寺庙赶来接应增援红军(当地老一辈的人有口述,有多位徒弟的后人也口述过)。国民党兵撤离后,爷爷与徒弟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在铁针寨、枫树庵等地挖土坑埋葬牺牲的红军战士。爷爷和做道士的徒弟们为阮啸仙的牺牲改编了他们的经文,“头七”在吊钟岭做法事悼念,天天从早念到晚,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爷爷和道士们都要拿出经文念,举办纪念活动,这种情形一直到安西解放。
三
爷爷为什么会接应并帮助突围的红军队伍,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又为什么能以阮啸仙的经历而形成经文?我从中判断,爷爷在会昌、瑞金期间与阮啸仙有过交集,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而爷爷的入党介绍人郑永全是什么人物呢?那位救爷爷并提供盘缠的打铁师傅郭生昌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有一次,爷爷同几个上迳朋友赴安息圩,路上遇见自称是会昌那边过来的人,拍拍爷爷的肩膀,你是刘林三同志吗?旁边的朋友马上打掩护抢先回答,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钟远兴师傅,那几个人没再打探下去。爷爷与一个乳名叫“机会保”的同龄人关系密切,他是瑞金人,红军失散人员,住在金盆山坪掌,他时不时来吊钟岭与爷爷商讨一些秘事。解放后,他成了五保户,大约在1970年过世。爷爷带了几个念经徒弟,比如稳陂屋场的刘永崽(又叫永华古),大坑的共产党员曾华荣(如今约90岁),大坑的曾华琳(80多岁),田垅大树下负责点香烛的一个蓝姓哑巴。这让我联想到,安西圩解放的前两年,外面就陆续来了拉二胡的、唱古文的艺人,打铁的、弹棉花的手艺人。在安西中山公园的国民党一被缴械,这批艺人就被宣布担任新中国的安西政要。其实这是我们共产党早已策划好了的,先派人化装进驻,然后前呼后应。爷爷与这种情形是否一样呢?
父亲回忆,吊钟岭斜对面有块禾场,爷爷一早练拳读古书,冬天坐在椅子上喝茶晒太阳。庙边有棵大杉树,立了“社官”,“文革”期间被人砍了,枯干的树墩上缠绕着长出的枫树,下面堆着一圈砖头,插着未燃尽的香烛。离吊钟岭庙一百多米有条三岔路,往东面与金盆山交界,过去是山口屋场。奶奶曾经告诉过父亲,她与被杀害的前夫于1932年生过一个女孩子,名叫刘财秀,寄养在会昌垇背一户人家,奶奶的哥哥叫王老二崽。父亲满一岁那年,爷爷和奶奶从安息圩上收养了一个女孩(解放前,从外面逃难过来的人家,把养不下的孩子放在圩上,让人家挑回去留条后路),女孩叫蔡良姣,1936年出生,比父亲大10岁,随父母从广东逃难来的,父母不知去向。她17岁那年腿脚浮肿,爷爷采了草药医治渐渐好转,可是有次来了孙屋的客人,奶奶炸了豆腐招待,蔡良姣吃了炸豆腐后,喝了几碗冷水下肚,感觉腹部难受,又呕又吐,生命垂危,奶奶背她到火土潦。临终前,她不停地叫“阿伟”(土话,妈妈的意思),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她被埋葬在后山岭脚下,正对面的半山腰是爷爷的墓地。
爷爷过世后,爷爷门下的一位徒弟,父亲叫他“南康老叔”,懂风水,他选了那块四周呈“回龙”形的山脉,山底“玉带”清水流过的位置做墓地。当初,爷爷的墓地为一个土墩,二十一世纪初,伯伯和父亲择了吉日添砖加石修葺。如今这一大片山岭,栽种了松树、杉树,镇里兴起了脐橙开发,山脚新修了一条公路,转个U型弯上坡路旁是爷爷的墓地。爷爷过世半年后,“南康老叔”同奶奶结婚,在吊钟岭又生活了十年。上迳水库修成后,爷爷奶奶开垦的田土极大部分分给了大坑村民。1967年,“南康老叔”和奶奶带着伯伯和父亲搬迁到兰塘村牛角龙,父亲过继给了后爷爷家里做裁缝手艺,母亲是后爷爷、后奶奶带的童养媳。伯伯过继给后爷爷的堂弟,传承了奶奶的做香烛手艺和爷爷的诵经技能,哪里造神或办丧事,他会主动前去帮忙。奶奶1987年过世,“南康老叔”先于奶奶6年过世,两人都埋葬在不同坐向的朝天岗。后爷爷刘锦华1966年就过世了,埋葬在禾场限口(旱塘坎上);后奶奶蓝冲秀,畲族,1908生于于都,年轻时漂泊于赣州,1992年过世,埋葬在下首地段。
老家刘氏家谱没上爷爷奶奶的名字,我们每年清明都去墓地祭祀,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