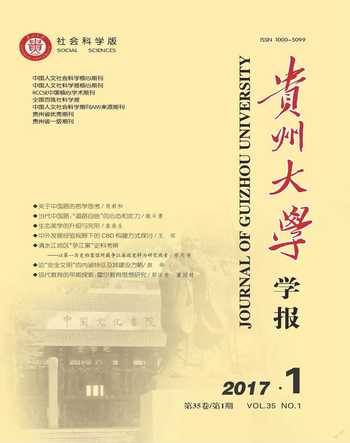“慎终追远”衍义
刘静
摘 要:喇叭苗是贵州众多民族的一支,他们同安顺的屯堡人同源,都是屯堡文化的产物,但其文化的最终展现形式却不一样。虽然被认定为苗族,他们却依然坚持着对原初文化的保持。喇叭苗以华夏农耕民族“慎终追远”的文化特性来展现自己的文化自觉。通过对现象的研究开启对喇叭人文化“体”的追寻,通过寻求他们文化的源远流长性,来探讨喇叭苗对自身文化的认可和对本民族的认同。以期用其文化的“体”的来支撑其民族文化的“用”,并从中阐述喇叭苗人文化自觉的特性。
关键词:喇叭苗;慎终追远;祖先崇拜;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1-0099-0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1.16
“慎终追远”是华夏农耕民族文化特性同是也为一个民族的认同奠定了极具现实性的心理基础,它更是百姓在“安身”之时的精神寄托,是一种终极的“立命”之求。无论在何时在何地,“慎终追远”对中国人都有着广而久的影响力。而民族的文化自觉则包括对自己民族的认可,文化的认可也包括对其他文化的一个融合,其实是一个民族文化合金性的一种发展。贵州的喇叭苗是一个时代特殊经历的存在,他不同于安顺的屯堡人,虽然二者的成因极为相似,要么是驻兵屯田的后人,要么是移民开拓者的后人。喇叭人大多生活在贵州北盘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特性,贵州喇叭人在1983年左右才正式被定为苗族,在此之前,他们都自称为“喇叭人”。虽然生活环境艰辛,但喇叭人从未忘却自己的来路,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并用自己的方式克绍箕裘。他们游离于各族之外,又与各族生活在一起,与之不断发生文化的碰撞。由于一种固执的坚持,让他们成为了有别于汉族,又有别于传统苗族的存在。下面将从“慎终追远”的角度寻找喇叭苗的文化的“体”或是他们文化的源头,通过喇叭苗人在文化上的自觉来阐述其文化的特性,以期对其民族文化的“用”有所支撑。
一、“三洞桃源”:“追远”的祭祖文化
曾子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50,不管是“慎终”还是“追远”,皆要求后人以严肃的态度,以极致的悲伤体现对过逝父母的敬爱,对远逝先祖的追念。换而言之,“慎终追远”培养了一个民族最为基本的感恩情怀。在丧中“尽其衰”,在祭中“尽其敬”的过程中形成温柔敦厚的品质。它强调的是“孝”“悌”的终端,从所求的立场以精神寄托的方式来践行“厚”的品德。毕竟,淳厚的道德品质依赖的是后天的教化。在民间,“慎终追远”的一系列仪式便充当了礼义教化的承载体,在诚心正意的祭祀礼仪中潜移与默化,从而形成了一个温和敦厚的民族。
贵州的喇叭苗是一个喜欢“追远”的群体,他们是军事迁徙的产物,史书上有载在普安县一带“有老巴子”他们“亦苗类”,大多由“湖南”移居于这一地区,这些被称之为“老巴子”的人“服饰与汉民同”[2]228语言也相对通俗易懂。在贵州府县志辑的记载则相对详实一点,据载当年来自于湖广的兵士们肃清当地的匪患后“不思迁乡”,很多士兵选择“赘苗妇”[3]就在本地安家建业,繁衍生息。经过长时间的文化融合,他们的男子仍然坚持着汉人服饰并坚定的认为自己是汉族的后人,故也被周边的人称之为“老汉人”或是“湖广人”,而女子因母族的原因则守住原本的红苗仡佬的服饰风格。喇叭人是个坚持的群体,他们在对先祖的追怀上从不含糊。无论是屯兵后人还是开荒的平民,都证明了喇叭苗是一种移民文化的衍变,他们的先祖都烙印着农耕民族的标志,而温柔敦厚的人格正是农耕文明最具特色的产物,这种人格的培养是希求稳定减少社会动乱的一个心理诉求。《左传·成公十三年》曾有载,一个国家的大事“在祀与戎”,国家之大事一般有二,一是祭祀,二是战争。“祭”代表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对共同祖先的崇拜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凝聚之力与向心之力,能使人从血亲上的“祖先认同”走向一个民族的认同。明洪武时期的屯兵行为促成了喇叭人族群建构的原初推力,但是一个族群的建构还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慎终追远”则为喇叭人提供了一个安身的崇德心理。在今天喇叭苗人家中基本都有神龛,里面供着“天地君亲师”及先人的位牌,以此表达喇叭人对宇宙天地、家乡故地、父母先师的情感认同和精神皈依。
喇叭苗还有一种特别的祭祀存在,即“三洞桃源”与庆坛风俗[2]229。因喇叭人的先祖大多来自湖南西部的桃源洞一带,他们不光是在口音上带有湖南邵阳的湘方言,后人还专门设定一些仪式去祭祀先祖。由于族群繁衍和迁移,喇叭人离开了原本居住的地方,为了表示对先祖的“追怀”,他们用三节竹子代替祖先居住的桃源洞(此洞分为三层分别为上洞、中洞、下洞,供奉着过逝的先祖与神灵),将其打通,在内里装入大米、黄豆、白银等,再用五彩线装饰裱上红黄纸,安插在神龛处,以便在家中侍奉祖先,在对先祖与神灵的敬畏中希求他们的庇护。必要时喇叭人还会专门开庆坛仪式,在家堂屋里安立娘娘坛来纳吉避凶。庆坛活动一般是以傩戏的形式再现先祖的丰功伟绩及族群的迁移史。在过去他们将庆坛时间定为三年一大庆,一年一小庆,通过各种法事及重新书写祖宗的牌位等行为来表示对先人的敬畏,對旧土的缅怀。庆坛仪式一般由专门的人来主持,喇叭人称之为“端公”。在仪式上,端公头戴花冠,身着法衣,主持一系列的法事,诸如有欢度小妹仙娘、采花合神、子孙为祖宗上粮等程序。无论哪种仪式,先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相当于近似神的存在,子孙们通过膜拜近似于神的先祖,来有所敬畏,有所期求。喇叭人的“三洞桃源”与湖南湘西的“庆娘娘”有些类似。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民族的“追远”和“求安定”的行为,具有准宗教性的功能与内容。他们将祖先神化,在“慎终”的过程中追怀先祖,以达到“民德归厚”的教化功能。不过现在很少见到这种民俗活动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的民俗基本沦为一种历史资料被保存起来。喇叭人的庆坛活动虽然成功的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后续的传承却成为了一个问题。
由于当年的各种原因,迁徙过来的喇叭人一般会以血缘或是同乡关系不离散地形成“共井”的小聚居生活空间,因而现存在的喇叭苗自然村落基本是一个姓氏,拥有着共同的祖先。喇叭人也特别喜欢修定家谱或是族譜,一来可以“慎终追远”便于共同祭祀,以加强群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二来以此彰显与周边民族的不同之处。
不管是“慎终”还是“追远”,它们在世俗当中的承载体便是“孝”。“孝”本身也是品德形成的一个基础,可谓仁之本。在过去,统治阶层强调孝治天下,利用血脉亲情去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喇叭苗的产生本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产物,历经了背井离乡的战争与迁徙,他们更能体会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何其的重要,而“追远”的祖先情节便成为了子孙们克绍箕裘最为朴素,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最为乡土的文化认同。
二、丧葬习俗:以“孝”为纽带的“慎终”文化 祖先解决了来路问题,那么一个族群的何去何从则是一个当下之人要慎重思考的问题了。而“慎终”最好的方式则是教化,可谓“孝悌行於家,而后仁爱及於物”[1]48,以“孝”作为仁德的根本来教化民众,这是儒家最常用的手段。喇叭苗的丧葬习俗最能体现“慎终追远”的现实载体——“孝”。喇叭苗同本地的其他族群不一样,他们并不主张花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时间地去办一个葬礼,他们奉行的是“丧与其易也,宁戚”[4]53,一般选择量力而行。他们在丧葬仪式上会有一个报恩仪式,唱颂一些《报恩歌》、《孩儿祀》等报恩古文,譬如如果是女性亡故,在做法事的过程中会唱《怀胎记》,其内容如下:“正月怀胎在娘身,无踪无影又无行,三朝一七如露水,不觉孩儿上娘身。二月怀胎在娘身,共闷眼花路难行,口中不说心里想,儿在腹内母知音。……十月怀胎在娘身,娘在房中受苦辛,儿奔生来娘胎奔死,命隔阎王一张纸。”通过对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的唱颂,一面表达对老人生养之恩的感激,一面期翼逝者生生世世安康。喇叭人在整个丧葬仪式中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悲戚的情感,他们在仪式之后还强调长时间的纪念,譬如在喇叭苗有些聚集地就规定孝子们在逝者入土为安之后还必须守孝120天,且在守孝期是不可以剃头的,以示感怀父母的生养之恩;在老人过世的三年内,年节期间要在门上贴“孝对”即不用红纸写对联,改用绿色或是黄色的纸写对联,以表示对逝者的缅怀,且生者在大年初一都要带上酒肉和水果去坟头给逝去的长辈拜年,要连拜三年。供养父母是一切善的源头,在《孝经》中也有言,以孝来报父母之恩,这是道德教化的根本,善事父母,是爱人的基本,而爱人则是人之为仁的方式之一。这种约定俗成的丧葬风俗习惯让他们无形地教化着后辈子孙,让其形成一种最为淳朴的善恶观。通过“孝”来规范小辈的行为范则,本身便是慎重的对待族群的来路,以一种最本性的方式展望族群的去路。喇叭人从孝的践行中达到“仁”的品质,从而实现社会教化的功能,并在这个过程中强化族群的凝聚性。
当然他们仍然坚守着“质有其礼”,当“俭戚”不能够担当时,便要“与礼之本相近”[4]53的规则。喇叭苗特别注重墓碑文化,他们以墓碑作为“慎终”的载体,在先祖的墓志铭上详实的记载了家族来自于哪,经历了什么大事件,由此来教化子孙。他们将“孝”定为建立在血缘链条之下的伦理约束,为逝者守孝不仅仅是期盼逝者能有一个好的灵魂归宿,更是后人对慎终追远的伦理诉求。他们在悲恸中又充满了希求,在追远中思索“终”的归宿,因为逝者是回到了祖先的怀怉,从此享受子孙的祭拜让灵魂回归到永生般的归宿地,便可作为祖先神的存在而庇护子孙。喇叭人的丧葬以“称情而立文”为旨,只有这样才会“至痛极也”。[5]371毕竟“丧礼,衰戚之至也”[6]252其内涵也是通过丧礼将民众的情感加以引导,使之在“衰戚”中不断记忆过逝父母的生养之恩,不忘却先祖的开疆之功。喇叭人将丧葬习俗由外而内,形成了敦厚朴实的民风,这在本质上是从人文角度对喇叭人的生活进行一个合宜的价值引导,在日常当中加入了道德的赋义。以此自觉培育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展现喇叭人的文化自觉,从而对整个族群的道德风华起到一定的作用。喇叭苗便是通过对先祖、父母的敬重来加强现实中各群体的联结,最终达到一个教化的功能。因为慎终追远的文化不是单单连通着先祖,它也连通着子孙,乃至整个家族成员,这也是中国农耕民族“齐家”文化的体现,当然这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在最初,喇叭苗的先祖是因战胜了本地的仡佬族,获取了有利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对社会的稳定性要求更高,寻找一条具有相当稳定性的联系纽带。从这个现实的角度出发,早期的喇叭人不得不寻求家族的庇护、祖先的祝福,他们沿用了先齐家再谈治国的套路。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人、朋友,便可立足于世了。而齐家文化的开展,其必要前提就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家族的凝聚。“孝”便是建立在血亲的生命链上,通过祖先、父子、子孙而达到源远流长的目的,使大家族制社会化,这正满足了喇叭人的需求。
中国的农耕民族习惯在追求安身的居所时也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立命”之处。“慎终追远”的情怀则为喇叭人提供了一个共同族群所认同的情感寄托。他们能通过孝来亲自体证“追远”从而“慎终”的情感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体祭祀中达到一种族群的认可。由于喇叭人这种极致的故土情节,让他们在丧葬习俗中感受了强烈的回归心理。这种建立在共同祖先下的“追远”文化让他们进一步认可现世中的身份,从而“慎终”,能够独立于其它民族,未被本地的仡佬族或是布依族所淹灭,乃至形成了特有的族群——喇叭苗。
三、婚嫁民俗:对传统“礼”文化的维系
婚嫁对与任何一个民族来就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着种族的繁衍,不仅可以从客观上反映着当时人的精神,也可从微观上呈示着那个时期社会的经济、民族心理、审美意识、伦理道德、宗教观念等诸种因素发展变演的轨痕。对喇叭苗来说,婚嫁的民俗则体现了他们对传统儒家礼制的维系。礼义的教化只是为了引领喇叭人在社会秩序的普法性,一则是为了现下社会的可秩序性;一则是为了“追远”自己祖先的文化。当然“盖礼先由质起,故质为礼之本也”[4]P53,任何“礼”都必须有 “质”的维系。虽说当年由于繁衍后代的需求,很多男子娶了当地仡佬族的女子为妻,但他们仍固执的认为自己是汉人的种,却又在服饰上被仡佬族同化,而成为一种特别的民族。不过他们在心理上对自己的族群身份从未放弃过。这也是从文化上对族群的“始”与“终”的慎重,本就是喇叭人特别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平时所崇尚的“礼”及伦理制度便无形中将个体、家庭凝聚在一起,从“质”上与“文”上对“礼”进行维系。所谓“人情者”无非要求大家“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 [6]618,人们的情感是人教化人的根基,礼制必然建立在人情之上,喇叭人的婚嫁习俗则体现了这点。他们传统的婚姻习俗基本保持了迁徙过来时的特性,受到了儒家礼教的影响。嫁娶的早期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经过挂八字(又称写红)、认亲、挑酒(提亲)、送日子、结亲、发担(接亲)等程序,类似于《仪礼》当中的士昏礼,以人性情感的层次来强调家庭的价值,以规定的仪式来使婚姻符合道德的要求。譬如,他们在接亲里,会用“白话诗”来表达对“礼”、“义”的维护,其中有首递戥诗:“左拿戥来右拿坨,戥坨原来是公婆,相依为命不可缺,百年相好子登科”就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儒家的人伦情感,用戥坨来比喻公婆,以强调婚后生活的礼制。再有一首拜父母诗 “父母生身德地天,一心栽培费心田,受今儿女一素拜,万望宽心放海涵”,在新妇进门的同时不忘父母的恩德,这是喇叭人用最直接最朴实的情怀来安正礼义人伦。姻亲关系将缔造一个小型的社会,如何让这个小社会存世呢?喇叭人不谈明天道,致至法,但深切的明白道德教化是为人的一种责任,要将一个族群延续下去,就得遵守先祖的礼法,保证现下社会的可秩序性,本身就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态度。
早期的喇叭人不仅在婚俗的仪式上遵循礼制,在意识形态上也强调以夫家为主的婚姻观。他们强调父系权利的重要性,主张冠夫姓,可娶外来女子为妻,但男性必须维系父系的传统及文化,因而子孙基本能够保持迁徙过来时的汉文化。这也是他们自认为是“汉人种”的表现。当然由于一些地域原因,喇叭苗的婚俗也有着自己的特性。譬如,他们在对恋爱对象的选择上,传统的喇叭人会选择以对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恋之情。当然随着社会的前行,人们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会有所改变,喇叭苗的婚姻观也会随之有所变化。
婚嫁代表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展望,预意着吉祥与美好。但是无论是哪种习俗都不能缺失道德礼义的牵制,规矩之下才会有方圆。婚嫁习俗是喇叭人文化的一种镜像,通过它可以折射出族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喇叭人的婚俗是通过对昏士仪式的保存来展现出对族群繁衍的重视,把家族价值放置于人性情感之中,并以此作为教育的方式来维系礼文化及寄托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正因为喇叭人对“慎终追远”文化的坚持,才得以确认自己族群的存在,并为自己的群体确定方向和意义。
四、结语
孔子有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106,当年的喇叭人没法选择不入危、乱之地,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他们用几代人的心血在屯兵战略之后开辟出一处风俗仁厚的“里仁”之处来安身,这同他们本身所带来的汉文化及他们所受的人文教化是不可分割的。“慎终追远”的文化让他们“本立”从而“道生”[1]48,孝悌的血缘亲情成为朴素社会秩序的一个基石。他们也将这种精神往外推衍,喇叭人深知“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5]592他们追怀先祖,却也慎重地对待子孙,喇叭苗历来注重以“礼”教化后辈,以一种朴素的方式承担着“诗礼传家”的传统。虽然地域偏僻,甚至可称之为贫困,但喇叭人从来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喇叭苗与周边其它苗族、彝族的一个最大差别。一个传统喇叭人聚集的村寨,后辈年青人大都是依靠读书而出人头地。一旦离开村寨,喇叭苗亦十分重视反哺生养之恩,在喇叭苗的村寨都会花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修撰族谱强调家风家训,在“追远”的过程中不忘来路,不忘感恩,从而在“慎终”中不忘教化,以达到“民德归厚”的状态。
但在今日之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村正经历着一种自然原初文化的迷失过程,社会的变迁、现代化的转型一直在破坏和解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无非是村民们自然形成的风俗、生产方式等等,而现代化的进程让原本自然而成的主体不知道如何自处,丧失了个性的主体,文化便无载体可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体”“用”的自处,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何以为“体”何以为“用”。一种丧失了“体”之源的文化,势必会导致无以为“用”现象的出现。一些民间的文化习俗或是传统要么就寄放在博物馆成为纯学术缅怀的对象;要么则沦为经济的婢女,变成无根、無本的存在。贵州喇叭苗的文化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现代化的元素打开通向外面的大门时,他们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这种过渡直接导致了文化之“体”的沦丧,在一些自然的民族村落里甚至形成一种文化的真空地带,年青的喇叭苗并无多少民族文化上的自觉,很多民众也开始渐渐忘却自己的来路,心灵缅怀的对象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世代坚持的文化并没有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自觉,很多地方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放任自流的消极无为状。喇叭苗文化的源头正是其文化的“体”,只要能继续“慎终”的“追远”,独特的喇叭人必能够为其文化的“用”寻找到有力的支撑,并将其文化踵武赓续,让它以一种新的形态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杨传溥.贵州府县志辑.民国普安志[M].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2006:553.
[4]刘宝楠.诸子集成:论语正义·八佾第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5]〔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荀子·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