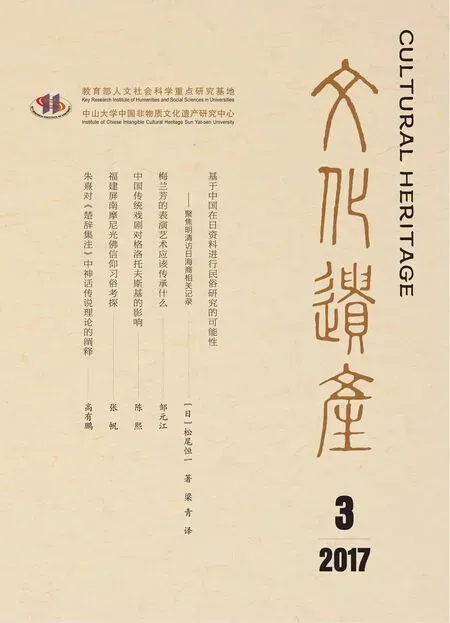日本民俗学的中国研究:1939年的转折*
王 京
日本民俗学的中国研究:1939年的转折*
王 京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界而言,日本民俗学既不陌生,诸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也已经是老朋友了。但日本民俗学自其诞生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从何时起,有着怎样的中国研究?对中国的态度及具体研究对于日本民俗学本身,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以至于对于日本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了解自身,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关注日本民俗学确立初期的20世纪30年代,以其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月刊《民间传承》、《旅行与传说》等杂志为材料,尝试将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进行量化,揭示出以1939年为界,这一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事实,并挖掘相关资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向,剖析日本民俗学内部存在的张力,力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这一转折所具有的意义。
日本民俗学 一国民俗学 柳田国男 中国 战争
前言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界而言,日本民俗学既不陌生,诸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也已经是老朋友了。无论是较为传统的传说、民间故事等领域,还是后起但渐成主流的村落、仪式调查、以至于较为前沿的话题讨论,如公共民俗学、日常研究等,都能看到中日民俗学者共同的身影。日本民俗学会自第27届理事会(2007-2010)起增设负责国际交流的理事一职,正式开始探讨与海外民俗研究者及团体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而无论是举办谈话会、国际研讨会,还是会刊的“海外民俗学专辑”上,与中国民俗学之间的往来一直都是其“国际事业”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然而,日本民俗学自诞生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从何时起,因何种理由,有着怎样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的态度及具体研究对于其学问本身,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以至于对于日本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自身,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日本民俗学的学史研究迄今既没有系统的整理,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多日本民俗学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成立的设问。对日本民俗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民俗学,用大家熟知的一个词来表现,是“一国民俗学”。其特点是将日本全国视为一个均质的文化范围,对民俗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事例,进行分类与比较,并将各地的地方差异转换为发展阶段的差别,从而构筑国民整体生活的变迁史。尽管在柳田的民俗学理论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的时代,日本已经是跻身列强的“大日本帝国”,但柳田构想中作为其学术范围的“一国”,却既不包括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等当时日本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就连今天来看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本土”的北海道也因为开发较晚、文化传统较浅而被排除在外。此外,柳田虽然将冲绳地区看作是保存着日本文化古型的宝库,但在具体研究中通常将冲绳地区与所谓“本土”区别对待。
“一国民俗学”中的“一国”既然主要指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区,那么作为“一国民俗学”的日本民俗学,自然不应该与中国有什么联系。于是在不少日本学者心目中,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联系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但真是如此吗?
20世纪30年代,对于日本民俗学,是值得纪念的年代。柳田经过十多年的摸索*王京:《柳田国男与“一国民俗学”的成立》,《日本学刊》2013年1月。,于30年代中期确立了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而1935年夏天“民间传承会”的成立和之后会刊《民间传承》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民俗学全国性研究组织的诞生。从1934年开始,以柳田的嫡系弟子“木曜会”成员为中心展开了历时3年的“山村调查”,可以说是在柳田理论指导下的首次全国规模的民俗学资料收集活动。之后,以柳田为中心的日本民俗学主流的实践活动,基本上都在“一国民俗学”范围内展开。的确,确立之初的日本民俗学,与仅仅一海之隔的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1937年起那场历时8年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使得日本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由从军作家组成的“笔部队”,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会、民族、经济调查,以及在占领地区开展的日语教育、历史教育等等,都有大量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关与其中。*近年日本学界也对此展开了反思,其成果例如『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全8巻)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而作为日本学界,或者日本社会的一个部分,日本民俗学的具体情况是否真的如同想象那样依然严守“一国”的范围?
为了避免在论述学史问题时常见的印象式的评论,本文尝试将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进行量化。从结论而言,我们能够略带惊异的发现,大致以1939年为界,这一关系发生了较为重要的转折。而这一转折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文后半将挖掘相关资料,以丰富对此的理解。
一、日本民俗学杂志体现的变化
量化操作需要一些统计的基本材料,就在日本民俗学史上的地位而言,“民间传承会”的会刊《民间传承》(创刊于1935年9月,月刊,1944年发行7期后停刊)*『民間伝承』東京:民間伝承の会,1935-1944年。当然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但为了更为客观准确地得出日本民俗学整体的较长时段的趋势或变化,我们还需要其他资料作为参照,最好它能够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最好是一本以民俗学内容为主体的学术气息较浓的杂志;
2.发行量大,在同时代的日本社会和日本学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3.撰稿人范围较广,题材较丰富,不偏向于特定的机构或团体;
4.发行期间较长,发行状况稳定,中间没有较长的空白期。
幸运的是,《旅行与传说》*『旅と伝説』東京:三元社,1928-1944年。恰好符合以上的条件。
《旅行与传说》创刊于1928年1月,1944年1月因战中管制主动宣告停刊,其间共发行193期,几乎是坚持每月刊行。柳田也曾提到他“在其发刊到停刊的16年中,我是一期不落地通读了的”*[日]柳田国男:「月曜通信——『旅と伝説』について」,『民間伝承』10-3,東京:民間伝承の会,1944年3月。。
该杂志最初是接受了铁道省的经费资助而得以创刊的。铁道省的本意,是想办成一本具有观光指南性质的杂志,结合当时日益高涨的观光热潮,为国民充分利用铁路做一些宣传工作。*[日]松本信広:「日本民俗学界鳥瞰」,松村瞭編集代表『日本民族』,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11月。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但刊登在创刊号上的社告《征集乡土介绍、传说、民谣及照片》,实际具有发刊词的性质。
在对泰西文明的过度陶醉中,值得骄傲的我大和民族固有之面貌日渐湮失,祖先遗于我们的宝贵艺术及传说也正随之濒临消亡,实乃憾事。如今虽有若干有识之士为传说之保存而奔走,但尚未形成各地民众合力保存的民众运动。为此,本杂志愿意开放全部篇幅,与读者一起支援他们,并为研究尚不为人所知的传说而努力。为达此目的,现特向读者诸君募集传说(广义而言,包括民谣、风俗、特产、名胜古迹及相关照片)。……*「郷土紹介 伝説民謡並に写真募集」,『旅と伝説』創刊号,東京:三元社,1928年1月。
从以上的内容看,编辑者一开始就具有与铁道省不同的视野。杂志的目的是在倾倒于西洋文明的社会潮流之中,回归于日本的固有文化,并且认为这一目的要依靠“民众运动”来完成。而杂志的定位,是兼有以收集为代表的启蒙性,和以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性。
创刊半年后的8月号上,刊登了柳田国男《木思石语》的连载第一回,柳田正式介入杂志的编辑。与之相应的是,杂志的征稿范围也扩大为“一切有益研究的,或是尚未为世间所知的事物”*『旅と伝説』8号,東京:三元社,1928年8月。,学术气息也变得更加浓厚。以这一期杂志为开端,柳田在《旅行与传说》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1928-1930年初以《木思石语》连载为代表的传说研究,1930年以后的故事研究,以及1933年开始的《年节活动调查标目》连载。柳田不但自己撰稿,还将中山太郎、早川孝太郎等重要民俗学者介绍到该杂志发表文章,并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人脉,计划并编辑了故事、婚姻习俗、诞生与葬礼、盂兰盆节、民间疗法等多次专题特辑。
《旅行与传说》的执笔者中,还包括折口信夫及其指导下的国学院大学的研究者,以及高桥文太郎等涩泽敬三指导下的“阁楼博物馆”(后更名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成员,覆盖了当时日本民俗学的主要阵容。杂志开设的“交欢台”、“新书介绍”等栏目,也起到了积极介绍民俗学动向,沟通、联络各地民俗学活动的作用。
1930年的统计显示,当时该杂志的订阅者已近2500名。*「会員名簿」,『旅と伝説』3-4~12,「編輯後記」『旅と伝説』3-12,東京:三元社,1930年4-12月。考虑到“民间传承会”在创立10年后,会员激增的1944年,会员数才突破了2000名这一事实,*『民間伝承の会会員名簿』(1944年12月),東京:日本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蔵。《旅行与传说》在民俗学的社会普及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可轻视。
从创刊到1935年《民间传承》创刊之前,《旅行与传说》一直是日本民俗学运动最大和最重要的信息中心。柳田门下“木曜会”结成时,《旅行与传说》的主持者萩原正德也是早期成员之一。而在1935年《民间传承》创刊之后,《旅行与传说》也是篇幅较长的民俗学论文、调查报告的主要发表场地。《民间传承》作为坚守“一国民俗学”的全国民俗学组织的会刊,《旅行与传说》作为方针更为灵活的民俗学大众杂志,二者一硬一软,一偏精英一重大众,可谓相辅相成。
与《旅行和传说》不同,《民间传承》作为以发展柳田主张的“一国民俗学”为宗旨的学会会刊,其主要课题是对国内研究素材的收集、整理、分类与比较,理论上并没有与中国产生关系的必要。创刊之后的1935-36年,几乎全年都找不到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日本民俗学的主要精力,放在集中建立并巩固“一国民俗学”的基础上。例如1938年11月《民间传承》4-3以告会员书的形式,号召所有会员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确立“毫无遗漏地由全国各地收集作为学问基础的资料”的“最终网络”,在当时还没有正式会员的全国各郡级地域发展新会员。并列举了“尚无会员的郡名”,其中长野县5处、爱知县8处、石川县2处、福井县8处、枥木县3处、琦玉县6处、神奈川县3处、千叶县8处。
但是,如果我们将《民间传承》中有关中国内容(包括封面、新书介绍、编辑后记等)的篇数,按照年度进行整理和统计,将该杂志显示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联量化(请参照图2),会略带惊讶地发现显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似曾相识的曲线。
1935-36年在极低的水平上徘徊,到1937年突如其来的出现一个高峰,但马上在1938年又有所回落,显示出前一年数字的应激性和暂时性。以1939年为分界,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关篇数急剧增长,39年急剧上升至29篇,相当于创刊至1938年4年总篇数(14)的2倍多,此后每年也都保持在20篇以上。停刊前一年的1943年,这一数字接近40篇。这一切,都与上面《旅行与传说》杂志所显示出的趋向基本相同。1944年《民间传承》也因为停刊,无法准确显示出当年的实际状况,但其停刊在7月,比《旅行与传说》晚半年,而当时已经达到26篇,按这一速度,如果没有迫于外在压力而停刊,全年的篇数甚至可能打破前一年的记录。

图1:《旅行与传说》中国内容篇数变化图

图2:《民间传承》中国内容篇数变化图
其实,不仅是这两份中央的民俗学杂志,我们在岐阜县的地方民俗杂志《飞騨人》*『ひだびと』岐阜:飛騨考古土俗学会,1935-1944年。上也可以确认以1939年为界关于中国的内容大量增加的事实。该杂志是“飞騨考古土俗学会”(岐阜县高山町)的会刊,1935年1月创刊,每月发行,直到1944年5月停刊。柳田曾多次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如1937年的「団子浄土」(5-3)、「飛騨と郷土研究」(5-8)、1938年的「耳たぶの穴」(6-8)、1939年的「女と煙草」(7-2)、1942年的「文化と民俗学」(10-10)等。。柳田十分注重日本各地的自主性民俗研究的意义,对于地方发行的民俗学杂志,也会寄发文章给予声援和支持,但给一本地方杂志多年持续寄发文章的情况极为少见。与其他地方民俗学杂志的执笔者大多仅限于当地的研究者不同,在《飞騨人》上刊登了大量以柳田为首的中央民俗学者,以及其他地区民俗研究者的文章,具有全国性的视野。也许这正是柳田比较重视这本杂志的原因吧。
以柳田为中心的全国规模民俗学会的会刊《民间传承》、在民俗学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央的民俗学杂志《旅行与传说》、具有超越一地的广阔视野的地方民俗学杂志《飞騨人》,都不约而同地从1939年左右开始,关于中国的内容大量增加,这无疑显示着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以1939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二、日本的中国占领与调查的展开
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在1939年左右出现重要转折,是与中日间战局的变化,以及日本战争支持体制的动向一致的。
1938年攻陷武汉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铁路、河流等交通沿线的重要城市,但距离交通线路较远的地域及西北、华北的广阔地区仍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原计划速战速决的对中战争,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沼。
竹制建筑严格依地势而建,可以为游客提供庇护所,在400 m之外的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这个特色建筑。建筑设计使用2个双曲线抛物面做屋顶,中间以具有张力的中心构件连接,抛物面屋顶长18 m,高高地悬挂在空中,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图5、图6)。竹制结构采用直径为8~12 cm的毛竹建造,使用的毛竹总长度约3 500 m。毛竹是从南方购买。
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一般偏重于历史、制度、文章、典籍等。虽然不少在中国旅行或生活过的日本人留下了大量游记、日记等记录,但出于对现代中国的兴趣而开展的实地调查,却是在日本的近代国家逐步形成的明治时期以后的事情。早在1875年,当时的劝业寮就曾组织对清朝的“物产调查”。之后在日本推进所谓“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及民间的诸多机构以中国为对象进行过为数众多的调查。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日本上至政府及军部,下至学者,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是一个似乎早已有所了解,却还不曾真正知晓的对象。于是通过实地调查来理解中国的现实,便成为当务之急。
1938年12月,日本在中央机构中新设了一个部门,叫做兴亚院。其目的,一是打破中央各部门的纵向分割格局,实现中国占领地区事务的一元化管理;二是在中国当地设置超越外务省驻外机构的,拥有综合权限的常驻机构。*[日]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兴亚院成立后,迅速在中国各大地区设立了联络部或事务所,并着手对日本在中国的调查活动进行整理和重编。
1939年4月,兴亚院设置华中联络部(总部在上海),“作为事变善后机构,致力于中支新政权的培育、以及文化及经济等各项建设。第一步就是统合官民各调查机构,创设‘中支调查联合会’”,“在中支那地区官民主要调查机构的相互合作下,展开为确立我国对中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所必需的实地调查。”*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編『上海要覧改訂増補1939』,1939年8月。
在张家口,1939年,出现了以陆军为中心,统合蒙古自治联合政府、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满铁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会社、蒙疆银行、华北交通会社张家口铁路局、蒙古善邻协会等组织活动的动向。其结果是1940年1月“蒙疆调查机构联合会”的创设。*『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26-221,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几乎是同一时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总部在北京)管理下的“华北联合调查委员会”、青岛的“青岛调查机构联合会”先后设立。*『支那調査関係機関聯合会会報』1-2,1940年12月。
而在日本国内,为了协调对中国的各调查机构,在兴亚院的推动下,1940年10月在东京设立了“支那调查相关机构联合会”。其成员有兴亚院、北支那开发会社、台湾银行、台湾拓殖会社、台湾南方协会、东亚海运、东亚研究所、中支那振兴会社、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银行、日本商工会议所、三菱经济研究所、满铁、横滨正金银行等,进入12月后,东洋拓殖会社、朝鲜银行也加入了该联合会。*『研究所旧蔵記録/茗荷谷記録』E-106、E-108,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的民俗学、人类学领域为大家所熟知,其成果也受到高度评价和积极利用的满铁“华北惯行调查”,也是在1939年开始计划的。这一年,东亚研究所第6调查委员会制定了“华中商事惯行调查”及“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计划。后者在东京成立了以末弘严太郎等东京帝国大学相关人员为中心的研究小组。而几乎同时,满铁调查部北支经济调查所第3班(1941年改称为“惯行班”)也独立地制定了从1939年起开始“华北土地惯行调查”的10年计划。为避免重复,经过协调,决定最初的3年,由满铁向东亚研究所提供资料。1940年,满铁成立了杉之原舜一领导下的调查组织,在华北的满铁调查部负责调查,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学者负责研究的分工体制正式成立。*『中国農村慣行調査』(全6巻),東京:岩波書店,1952年等。
此外,长期以来在“对支文化事业”项目经费下对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研究给予大力支持的外务省,也于1939年正式决定在文化事业部内设置“支那民俗刊行会”,开始刊行永尾的研究成果《支那民俗志》(计划13卷,含索引1卷,各卷约600页,实际只出版了3卷)。*[日]永尾龍造:『支那民俗誌』第1、2、6巻,東京:支那民俗刊行会,1940年。
三、日本民俗学面临的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些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调查活动中,几乎找不到有影响的日本民俗学者的名字。“一国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专注于国内的研究态势,使得日本民俗学在直接参与对殖民地和占领区的调查方面,存在着比其他学问领域更大的阻力。通过对具体内容的考察可以知道,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关联的增加,首先是作为会员个人对中国民俗的兴趣得以显现,然后逐步上升成为会员对民间传承会的希望与要求。
据笔者所见,在日本民俗学内部,最早呼吁进行中国民俗研究的文章,是1938年12月《民间传承》4-3上刊登的大阪会员大桥富枝的来信。在题为《研究支那民俗》的这封来信中大桥说“从8月上旬起,我从新京到北京旅行了约1个月。听说支那的民间传承与我国相比,有很多奇怪之处。我没什么时间研究,非常遗憾。如果哪位能就此在本杂志上有所发表,则实为我幸。”
而1939年1月《旅行与传说》12-1上发表的太田陆郎《行军中所见之支那习俗》,涉及的是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民俗,仿佛正是对大桥要求的回应。虽然并非如大桥所愿刊登在“民间传承会”的会刊上,但太田的文章开启了凭亲身经历和观察来记录与思考中国民俗,并在日本中央的重要民俗杂志上刊登发表的先河。此后,这两本中央杂志上陆续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民俗的会员来信或是投稿。但与学会会员或是一般民俗研究爱好者的要求及实际行动相比,柳田国男和木曜会等日本民俗学指导层的意见依旧十分保守。
1939年3月《民间传承》4-6刊登了标题为《时局下的民俗学》的刊首语,执笔人是柳田的得意弟子、杂志编辑的中心人物之一仓田一郎。文章开篇即指出时局对民俗学带来的冲击:“昨天还在愉快地议论着民俗学之未来的青年,今天却以心神动摇的语调,说什么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之下无法悠闲地研究民俗,年轻人的大志应在大陆。”
“动荡的时局”,自然指的是与中国的战争。在关心局势变化的青年眼中,与中国没有关系的日本民俗学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对于他们的疑惑,仓田的回答简单明快:民俗学才是学问对时局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民俗学的贡献绝非对个别民俗的刨根问底,而是“旨在对日本民族生活所有方面进行根本性研究”的“国学”,并且是能够“立即加以运用”的,对将来的“殖民政策”也能有所贡献的实学。
整篇文章的基调还是强调要立足于日本国内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具体论述,只有“有待依托彼此两国民俗学对两民族生活的解明与比较”一句,实际上贯彻了“一国民俗学”的基本思路,并未体现出对中国的实践性意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一丝松动:即面对日本民俗学视为学问之未来的青年们在时局中的动摇,民俗学的指导层也不得不开始似实而虚地提及日本民俗学关与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了。
1939年3月,柳田为《亚洲问题讲座一政治军事篇(一)》而执笔的序言《寄语亚洲》,是藤井隆至的《柳田国男的亚洲意识》*[日]藤井隆至:「柳田国男のアジア意識」,『アジア経済』16-3,1975年。以来,经常被引用的内容。柳田在文中说“支那故事的贮藏量惊人的丰富,但虽然往来已久,关系亲近,我们却一直袖手旁观,而让西洋人占了先手。其实对于我们,那四四方方的汉字,要容易理解得多。不只是支那,潜藏于常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可以借此(引用者注:故事的比较研究)相互对照。为了五族协和的理想,这也应该是必要的工作。东亚新秩序的基石,也许意外地存于这样的地方。”*[日]柳田国男:「アジアに寄する言葉」,『柳田国男全集30』,東京:筑摩書房,2003年。
这段话初看似乎可以理解为柳田对研究中国民俗的直接提倡,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
《亚洲问题讲座》这一序言的基础,是同年1月柳田应丸善书店的杂志《学灯》之约而执笔的《续打火石山》*[日]柳田国男:「続かちかち山」,『昔話覚書』,東京:三省堂,1943年。。比较这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在《续打火石山》中的具体所指“前年出了英译版的W.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在《寄语亚洲》中变成了“让西洋人占了先手”这样的抽象表述。
柳田在1939年3月执笔的《猿与蟹》中,提到“翻阅前年5月德国人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的英译版……”*[日]柳田国男:「猿と蟹」,『昔話覚書』同上。,而1940年发表于《朝鲜民俗》的《学问与民族结合》及其草稿《比较民俗学的问题》中,也都提到了“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日]柳田国男:「学問と民族結合」,『柳田国男全集30』,東京:筑摩書房,2003年。「比較民俗学の問題」,『定本柳田国男集30』,東京:筑摩書房,1964年。
30年代,德国学者艾伯哈特(也译为艾伯华,W.Eberhard)从德国到中国避难,与中国学者密切联系,埋头中国故事神话研究,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出版了名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aerchen,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120, Helsinki,1937)。
柳田一直认为中国是民俗的宝库,但出于其“一国民俗学”的理论,主张其研究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去努力。但如今德国人却利用这一宝库,拿出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出色成果。这一事实,对于一直对西欧民族学、民俗学抱有强烈对抗意识的柳田国男,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西洋人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也能。而且我们与中国之间还有着历史、文化的渊源,以及共同使用的汉字,应该更有优势,这应该是柳田的心声。了解了这一背景,再回头看前述柳田的文章,无论是显现出强烈好胜心的行文,还是限定在民间故事范围内的话题,都可以让我们基本判断,柳田的发言与其说是对当时政治军事等具体时局的迎合,不如说是对西洋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新成果这一刺激的强烈反应。
仓田面对的是日本青年在时局下的动摇,柳田面对的是西洋学者先行一步的事实,虽然性质和意义都迥然不同,但似乎构成了推动态度保守的日本民俗学指导层面向中国的合力。1939年1月,由科学知识普及会出版的杂志《科学知识》面向各界名人进行问卷调查,题目是“最近阅读的书目”,被访者的回答刊登于2月的杂志上。柳田国男在回答中,一共列举了6本书,其中2本都是关于中国的专著:内藤湖南的《支那绘画史》和梅原末治的《支那考古学论考》。*[日]柳田国男:「最近読んだ書」,『柳田国男全集30』,東京:筑摩書房,2003年。联系柳田答应以中国为主要论述对象的《亚洲问题讲座》(共12卷,1939年1月-1940年4月)担任其编辑顾问的事实,我们不难窥见当时柳田个人对中国抱有的兴趣。
而与还暂时缺乏实践意欲的柳田或是《民间传承》的论调相比,日本社会的要求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都要积极得多。例如《旅行与传说》值得纪念的总第150期(1940年6月),其刊首语的标题就是《支那大陆民俗调查的必要性》。
文章虽未署名,但应该是编辑部的意见。文章认为“支那民俗的调查,在日本还完全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既往日本学界的态度,反映了当政者的对支政策”,“衷心希望能够尽早对支那民俗的调查研究投入精力”。而与刊首语相呼应,这一期杂志的开篇论文,是乡土史研究家藤原相之助以与中国的比较为主要内容的《马蚕神话的分布——与大白神的关系》。编辑后记中也特别提到“藤原先生提到的马蚕神话,是早就应该有人论述的课题,但将比较过于限定在国内的日本民俗学,却一直将之束之高阁”,实际上是在敦促日本民俗学扩大其研究领域,积极面向中国。
结 语
以1939年为分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的要求日益高涨,以《民间传承》、《旅行与传说》为首的中央及地方民俗杂志上涉及中国的内容也开始大量增加。日本民俗学一方面与伴随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区的扩大而增加、升级的带有国家政策性质的调查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开始需要面对来自学问内外的,将中国纳入研究范围的强烈要求。是否将中国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日本民俗学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一国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以及在日本社会快速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中抢救和收集日益消逝的民俗资料的危机感,使得当时以柳田为首的民俗学高层指导者对直接关与日本以外地域的态度依然保守。但尽管对直接关与中国还是缺乏积极的实践性态度,在面对青年的变化及西洋学问的刺激下,已经开始提及研究或比较的可能性,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反映了促生变化的力量正在蓄积之中。
而民俗学整体的变化,既需要以实践为前提的逻辑、理论转换,也需要与之相应的组织体系的整编,这些绝非是漠然的所谓“时局影响”的结果,而需要更为实在的具体契机与摸索过程。本文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在此展开论述。
但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抗战开始后日本民俗研究者对中国关与的与日俱增。仅民间传承会的会员中,就有中央指导者之一折口信夫、地方民俗学团体指导者太田陆郎、泽田四郎作、木曜会重要成员石田英一郎、大间知笃三、守随一、青年一代中的重要人物直江广治、千叶德尔、和歌森太郎等在内的中央及地方的民俗学者以记者、军人、调查员、学者、教师等各种身份来到中国。其中一部分人长期在中国生活,或公或私地从事着对中国民俗的调查研究,并且与日本国内的学界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如「会員通信」「会員だより」,『民間伝承』4-6~10-5,1939年3月-1944年5月。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知道,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日本民俗学研究中国的意愿与实际行动,并非始自是二战以后甚至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日本民俗学确立初期的1939年,“一国民俗学”便迎来了必须开始认真面对中国的重大转折。
战争期间日本的民俗学者在中国从事着怎样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又对日本国内民俗学指导层的认识与决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日本民俗学在关与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怎样的立场变化?其计划或尝试的具体内容和结果如何,有何意义?日本民俗学战争期间的动向与战后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重要的问题,都还在等待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责任编辑]王霄冰
王京(1975-),男,湖北武汉人,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ZDA16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K890
A
1674-0890(2017)03-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