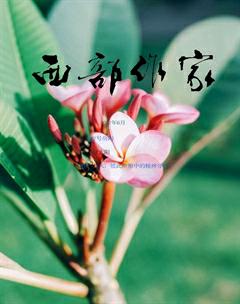507号房间
编者按:几年前,在某网站写一个人物系列,排到4,有些踌躇,怕有人不喜。不想贴出后,被写人大为激动。他说:“我与4最有缘。读书时是四班,宿舍是404号,学号是4号,我与我女朋友生日都是初四,不想您又给我排在系列4,太感谢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难忘的数字,数字后是故事。不管你承不承认。正如,罗锡文老师的507号房间。
倘若一声响动,使时光回过头去,看见的,一定是507号房间的门打开了。随着门打开的,还有落锁已久的记忆,以及在体察了诸诸世象后仍不肯上闩的心灵。我总还能逮住时间披在无数景物上的光影,伫立在门前凝视着黑白杂糅的村庄、错落起伏的庄稼地、长坡上的树木和坡下那条让思绪变得深刻情愫变得典雅的金沙江。
这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门外是一条过道;屋子后面,还有一座精致的阳台;从阳台看过围墙去,是一所中专学校,叫经济学校,袖珍极了,时下已经搬迁到南岸去了;由于其办学性质,我把它说成是在算盘珠上滚来滚去的校园。我见过很多简陋的屋子,也读过关于陋室的很多文章,领略了每个作者在写出他们居住的那些弹丸之地的唯美感受和对生命及其价值的思索,但我的这间小屋子大概比他们的还简单,但明净,也规则,墙面的粉刷和地板的平整还算那么一回事。门口两侧的壁柜说明这儿曾经是用作学生宿舍的,而我也顺便让这六个壁柜分别保存一些杂什,但壁柜门显得非常单薄,一关一开,总觉得要掉下来似的。我刚住进这屋子时,除了一张简易的木床和靠近后门的一张写字桌以外,别无其他摆设。但见天花板上摘掉了日光灯的几根电线,就象老鼠的尾巴,在寂静的空间里扫来扫去。我很快就发现这一切酷似我的性情,简单,明亮,爽快,也符合我的居住原则:只要有一间处所,我就能拥有一个世界。从此,这间被标为507号的房间就归我使用,同我度过了八个春秋;它庇护着我,我拥有它,它的声色气息与我的感知在相当的时期内非常融洽。
我弄来几张课桌,放在屋子中央,把经常阅读的书籍和写作用的纸张全放在上面。起初,桌面上还算整洁,久了,便凌乱得非常壮观,常让来者皱紧眉头,他们虽然不至于当面露出鄙夷和厌恶的神色,但那哦啊哦啊的声音和触及桌面立即弹开的眼光,我便明白了他们崇尚富贵。只是几个经常来的学生和一些在社会上打拼而迷恋纯粹精神生活的人,在桌子旁边和我瞎侃一通后,半真半假地说,凌乱有什么不好?凌乱美啊!话倒是说得不错,但究竟谁能从凌乱中爬梳出秩序,找到美,尤其是我经常对他们提及的接近抽象的秩序和成为抽象的美?他们如若进行这项工作,怕是不肯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不必在乎桌子什么时候该整洁,该打扫,该重新排列序目,也不必在乎桌子是课桌还是什么老板桌,也不在乎油漆脱落,抽屉抽动的声音如何奸污了耳廓,也不在乎和桌子成亲家的椅子够不够档次。我喜欢的就是那点随意,随意抽一本书读上几个小时,把写好的文章随意往桌上一扔,而需要时即刻就能找到,随意在垫在桌面上的报纸或白纸上写一些更随意、甚至是庸俗的文字或一些单线条画,或者把一些购买东西后别人找补的零钞丢在上面,不必担心它们会突然失踪,疲倦了随意往上面一趴,就能睡个黑白不辨死活不知,随意将信件放在桌上,阅过的和没阅过的一目了然,也能在随意的情绪间拆读和回复。这样一来,全乱了,但绝对不是某个老先生说的杂乱无章,他进门时小心翼翼到了蹑手蹑脚的地步,十二分可笑;我内心早已经为这几张桌子和上面的东西编排了程序,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一些老友的脸和性子,熟悉自己身体的每个机件一样。别人自然会以他们的见识和意见来看待我这屋子中央的庞然大物,时常喋喋不休,我自然不作计较。倒是有几个好心的女生曾经在某次来访时把三张桌子拼成的台面给细致地整理了一通,害得我在她们有序的排列中去寻找我无序的组装,结果可想而知,我累得腰背都要佝偻了,才找到两篇写在散纸上的文章和几封要汇出的信。几乎每个深夜,我都坐在这堆凌乱之物的旁边,看文字如何舞蹈,看时间如何被夜晚一口口吞下,看人生如何在有梦和无梦之间痴呆地坐着,看睡态中的众生虔诚地朝岁月深处飘去。
我之所以不使用那张写字桌,是因为它过于的方正(若放在现在,它早是文物了)和沉重,伏在桌上写字看书,我感觉相当异样和笨拙。只是在某些时辰,坐在它面前,单单是因为它靠近窗户,在黄昏时节能很好地看到西边天上的太阳,而对面那座山包很像猴子弓着背时的模样,那轮红得要化的残阳,酷似那只泥猴子的屁股了。
在写字桌旁边,有一只凳子,凳子旁边是一张当时比较流行的学生单人桌。凳子上是一只小巧的电炉,深夜肚子嚷嚷时,我就随意煮点粥和面条什么的。白天里什么饮食都调不动胃口的积极性,倒是深夜里,即使是一碗素油面条或一只白水鸡蛋,也成了美食。倘若没有可煮的东西,便到底楼守门老头那儿去买方便面,有时是买香烟,那善良的老头即使睡得如何痴迷,都是有求必应。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老人。除了吃的,还得有听的,那张小桌子上就摆放着一台从学校音像室借来的录音机,先是一台小的,后来换成了一台大的,尽管机身已显老态,但效果非常好,是上海货。那牌子忘记了,但那质量和名声,同当时在中国极度流行的永久牌自行车一样响。音乐是一种让人快活的精神享受,工作和生活的劳累只要在旋律的纠缠和抚慰中,很快就会得到恢复,而从小就喜欢音乐,致使我必须有这样简单的设备,来制作我的生活和享受廓远的精神世界。梁实秋是不欢喜音乐的,除了他说他自己没长出一双属于音乐的耳朵之外,恐怕还在于他对音乐的某种偏见和对自我精神领域的过于自恋。那时,既喜欢民乐,也喜欢流行歌曲。民乐主要是二泉映月江河水高山流水梁祝春江花月夜之類的,流行歌曲是有所选择的,主要喜欢当时让年青人没心没肺地传唱的台湾歌人的作品,如王杰姜育恒童安格潘美辰赵传费玉清等,而我听得最多的是王杰的作品,盒带也买得最多,至今还好好地保存着。听多了,便有了共鸣,实在感慨极了,便写了一本散文诗集,为老王写的。那是一些忧郁孤独到骨子里的歌曲,唱这些歌的人,仿佛就是一个在夜深人静时,与你共对一盏青灯,共饮一怀愁绪的老哥。我始终相信,当年从每个文字到每个音符都将听者打动的人,在今天是难以找到了。一段时间里的情绪,如那段岁月里的歌,只能回到当时才能找到真正的应答。这507式的音乐,往往只在别人被梦俘虏时播放,声音低得只有我能捡拾到,感知到。是的,来自灵魂里的所有声音,也只能让自己在安谧中聆听,并让自己精心储存。
我经常出神地望着两面空空的墙壁和贴在上面的影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壁画,被深深地镌刻在无数日常生活里,多年以后,如此这般观望,有些许感动的人,除了我,还有谁呢?不久,我在墙的一侧贴上了几张自己用炭精条画的素描,几个人不一的神态成了我观察和体会的第一对象,也在很多时候使我无意间将他们当成了活着的人,我们彼此凝视,彼此体味内心,尤其是在独自一人,被寂寞的川南之夜包裹着的时候,这些靠在我生活一面墙上的人,就成了娓娓相叙的友人。在墙的另一面,挂着几张体育明星和歌星的图片。呵,那年月多么年轻,即使朝那些生动的人那生动的眼睛投去一道光,青春就灿亮起来,晨昏也活泼起来了。
一些杂什和几只在大学毕业时托运用的纸箱,还有几件运动之后一直扔在报纸堆上的球衣,床头的粘贴画和一只蓝色风帽,一把已经只能瘪着嘴发音的吉他,以及一地的灰尘,都是我的生活,我的财产。如果在善于抛弃和善于过高档生活的人眼里,我这简单的居所简单得接近于荒芜了,但我看中的就是这点简单,就像痴迷于自由轻松的人生。
在以购买房子为极大乐趣,以艰辛的劳苦为代价得到的房子,以房子的高低档次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现代社会里,蜗居的内涵也许正在日渐收缩,甚至在变异,这和今天讲究激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或者只求一夜之欢、甚至只在钟点房里快餐式的现代爱情模式,拿来同巴山夜雨式的、连理枝比翼鸟式的爱情相比是一个原理。也许,空间不必煞费苦心地越拓越宽,只要能容纳自身便可。但真正能包容一颗心的,该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在我看来,只要有心有梦,哪儿都是你的蜗居、你快乐生命的栖息之地。倘若心无法放宽,即使把整个地球给你,你的物质世界和心灵空间也是小的。心胸狭窄者,在哪儿都感到拥挤,被生活所羁押,都会睁着两只圆圆的但空洞的眼睛,使自己的心灵无神。
很多人同我一起分享过507号房间里的青春时光,包括友谊、爱情和当今社会里越来越稀罕的师生之情。我们都是507的匆匆过客,而一生中,我们还要经历无数个507号房间,最大可能地享受那些自在时光,最大程度地抒写生命的意会,包括年深日久之后的回味。
后来,我离开了川南。临走那天早晨,我来到了楼下,长时间地朝五楼望去。几年前我就不住在507号房间了,它被重新改装成了学生宿舍。冬天柔曼的阳光同往日一样将整个大楼拥在怀里。远游与别离的感伤很快被龙眼树叶轻微的摇曳所撩动,随目光上升到蓝色天空映衬的楼顶,慢慢地扩张到我的每根神经。
我多想在每根神经的末梢都装上性灵之眸,在羁旅中回首那块诗意的空间和始终居住在我灵性世界里的缤纷的青春。
作者简介
罗锡文,男,四川省仁寿县人。文学创作以小说、诗歌和散文为主,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散见《星星》《读者》《当代文坛》《当代小说》《飞天》《诗林》《文化月刊》《四川文艺报》《青年作家》《散文诗》《散文诗世界》《旅游世界》《西部文化旅游周刊》《四川新书报》《音乐探索》《贡嘎山》《人之初》《学生之友》《蜀峰》等全国各级报刊杂志。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著作共计20部。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纸刊合作:《當代人》《长城》《诗选刊》《河北作家》《散文百家》《小品文选刊》《当代小小说》《小小说百家》《唐山文学》《兴安文学》《包头晚报》《邢台日报》(合作期刊陆续添加中)
《西部作家》微信平台,坚持最新原创作品推介,欢迎各大文学期刊合作选稿!
投稿邮箱:xibuzuojia@126.com
创刊宗旨与理念
《西部作家》是西部联盟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学双月刊,创办于2012年1月,是非营利的公益性文学期刊。
宗 旨:以交流文学为主要目的,探索前沿文学,追求文学新理念,审视当下文化。不搞征订、不以任何手段收取作者费用,为文学爱好者和作家搭建交流平台。
理 念:提倡文学多元化,鼓励超前性写作,积极探索新的创作模式,以人文关怀为基础,关注当下现实。发掘具有现代性内核、地域性特色的优秀作品。
顾 问:韩石山、熊育群、秦岭、洪烛、陈启文、邓九刚、余继聪、阮直、王克楠、帕蒂古丽、李荣
社 长:张柏青
主 编:邓迪思
副 主 编:梅 纾
微信平台编辑: 阿兮、王存良、章远初、冷秋、朱辉、记得、一朵女子、高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