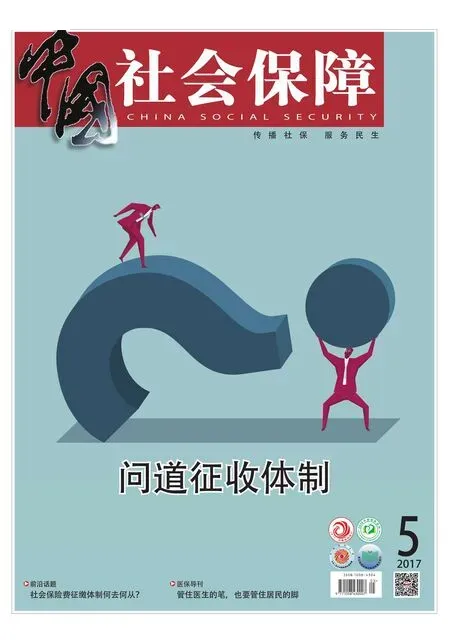总额控制的问题与局限
文/谢祖平
总额控制的问题与局限
文/谢祖平
新医改以来,随着总额控制的全面实施,以及其他支付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特别是加上相应的医疗服务监管不断加强,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幅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全国来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出增幅就从2009年的35.9%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13.4%。不过,也要看到,虽然以总额控制为基础的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取得了不小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同时也有一些相关制约因素影响了支付方式改革的作用发挥,需要将来在完善支付制度改革中加以克服和解决。
总额控制的指标与医疗费用发生的实际出现较大差距,引发医疗机构的消极应对。影响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总额的因素复杂多变,如患者自由流动就医、病种结构动态变化、价格增长、人才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等,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导致医保管理部门很难根据既往的医疗费用数据科学、准确预测出某一特定医疗机构的年度医保预算总额标准。各地普遍的做法是运用历史数据来确定下一年度医保预算总额,但历史数据仅代表过去,不反映未来,而且数据本身可能包含了不合理的医保预算分配结构,有的地区在实行总额控制、确定总额标准时,没有考虑医院等级、专科特色、科室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未能将上述差异作为主要的参考因素纳入确定总额标准的设计之中。因此,采用这种方法得出的预算总额分配结果可能会与某些医疗机构的实际运营出现较大偏差,医疗机构难以接受甚至拒绝执行;或者即使被迫接受,也往往通过费用转嫁(从医保支付的费用转移成个人自付或自费)、推诿病人的方式来规避自身经济风险,最终损害参保患者的利益。
在医保政策调整、患者就医需求变化、疾病谱变化以及不受限制的流动就医的背景下,年初就能准确预测出一个年度一家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总额,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一些地方对预算总额采用季度、半年为期的期中动态调整,但只能接近实际而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而且频繁动态调整也使得总额预算约束失去了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将预算总额控制指标分配到每家医疗机构确实存在定不准的缺陷,这是国际上很少采用的原因(特别是在住院费用支付方面),也是我国之所以不把它称之为一种支付方式而仅仅视为一种医疗费用控制手段的原因。
医疗保险机构对医疗服务质量的监控还很不足,支付制度改革缺乏系统性。实行总额控制之后,医疗服务的经济风险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转向了医疗机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控制费用的压力相对较小,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重心应该从费用控制转向服务质量监管。每一种预付制支付方式都有各自的缺点和不足,这就要求在实施某种预付制支付方式过程中设置一些针对这种支付方式的缺点的监管指标和相应的监管办法,来避免医疗机构利用这些缺点来钻支付方式改革的空子。不过,在一些地方推行总额控制的实践中,往往没有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价体系,通常医疗费用得到了控制而医疗质量却受到一定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实行“总额控制、超支不补”的政策,这种刚性约束的措施,使得医疗机构的医保支付不能随服务量的增长而有所调整,导致医疗机构出现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质量、推诿病人等现象。一些地区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往往没有对医疗服务实施严格的监管,未能采用有针对性的监管指标和监管办法来约束医疗机构的行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从而使得支付方式改革的约束医疗机构、减轻个人负担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

重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控制,轻个人负担的控制。虽然一些地区开展了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但预先确定的总额、病种或人头的支付标准大多是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标准,并不是全口径的所有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往往没有对个人支付的部分进行控制和约束。即使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医保支付费用和总医疗费用的“双控”,但总医疗费用往往不包含医保目录范围外自费项目的费用,虽然“双控”能够同时控制个人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但却不能控制政策范围外的个人自费,也难以防范医疗机构将医疗费用向个人自费转移转嫁的问题,从而加重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负担,这显然不符合支付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由于支付方式设计缺陷而造成医疗机构可以实行费用转嫁,也使得通过支付方式改革促使医疗机构转变行为方式和运行机制(主动进行成本控制和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难以实现。
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覆盖范围还比较小,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比较缓慢。总额控制是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也仅仅是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初级阶段。根据相关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文件要求,应该在实施总额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住院、门诊大病实行按病种付费、门诊实行按人头付费。不过,不少地方的支付方式改革往往止步于总额控制,不仅总额控制不够科学、精细,而且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也没有实质的推行。即使不少地区也在总额控制的基础上开展了单病种付费,但是实行单病种付费的病种范围还比较小,发挥控费和约束医疗机构主动控费的作用还非常有限。而全面实行住院按病种付费的地区非常少,国际通行的根据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付费还仅仅在北京少数几家医院开展探索试点。门诊付费实行按人头付费也是在少数实行门诊统筹的地区有所采用。可以说,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度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滞后影响了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和管理效应的发挥。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疗保险单方面能够实现的,支付方式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配合和合作。另外,支付方式的支付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确定的整体支付价格,支付方式改革与现行医药的价格制度密切相关。因此,支付方式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医药卫生体制这一外部环境的支持和配合。然而,现行的医药卫生体制(包括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医药的定价制度)却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本身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内容。医药卫生体制这一外部环境的缺陷也构成了支付方式改革的障碍性因素。
就医疗服务提供方来说,公立医疗机构是我国医疗服务提供的主体,但公立医疗机构(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改革进展缓慢。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缺乏竞争,以及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僵化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用人、分配机制不活,这种行政化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在新医改实施的几年里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由于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的滞后,支付方式改革往往难以得到公立医疗机构正面的积极应对。失去公立医疗机构的配合,支付方式改革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其管理效应。另外,以全面实行基本药物、收支两条线管理,强调行政化管理的基层医改,不仅没有实现强基层,反而进一步弱化了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能力,导致患者进一步向上的就医流动,基层的弱化也反过来促进了大医院的扩张,从而进一步扭曲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扭曲(头重脚轻)也使得微观的支付方式改革很难从根本上发挥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就医药定价机制来看,虽然政府定价已经取消,但市场化的医药价格机制远未形成。行政性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仍然继续存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仍然以行政性价格调整的方式在进行,医药价格的扭曲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医药价格或者虚高或者虚低、与其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医药价格的扭曲也扭曲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行为,造成以药养医、以检查、以材料养医的格局,从而使得疾病治疗路径偏离了正常、合理的轨道,这也给预付制支付方式(总额预算、按病种付费等)的支付标准的科学测算和合理确定带来很大的障碍。
待遇提升过快,筹资能力与需求释放存在落差,使得以总额控制为核心的支付方式改革难以平衡供求矛盾。医疗保险的筹资能力和基金支付能力决定了医疗保险的待遇水平。不过,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往往为了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而提高待遇水平、扩大待遇范围,致使大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快速释放,使得筹资和基金支付能力与快速增长的基金支付需要存在较大落差。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却仅仅寄希望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比如总额控制)控制医疗费用,维系基金收支平衡。实际上,支付方式改革可以发挥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的作用,但合理的医疗费用支付还是需要相应的筹资增长来满足,而无法通过支付方式改革的控费来实现。强行将不足支付的医保基金按总额控制的方法分解到医疗机构,往往带来医保与医疗机构、医疗机构与患者的矛盾和纠纷。此外,老龄化、疾病谱变化(慢性病发病率的快速上升)以及技术进步、物价上涨等因素也会带来合理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也不是支付方式改革所能消化的。
作者单位:人社部社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