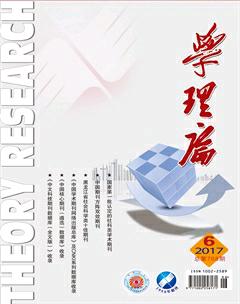试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
周彦霞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核心思想是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理性自由中抽象出人的本质到从感性直观中考察人的类本质,继而从生产劳动出发并同现实的物质基础相联系在社会关系中确立人的本质,最终找到在实践中实现人的解放道路的演进过程。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中,唯物史观随之形成和确立。通过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进路的梳理和解读,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谛,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关键词: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58-02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渊源就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集中体现,有一个从萌发到形成到最终确立的过程。正如“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必须要有正确哲学思维的指导”所言,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也是伴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得以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的。
一、理性自由下人的解放的迷失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萌发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都被基督教所笼罩,神权高于人权。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他们从“自我意识”出发,致力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基督教,为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的资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提出把“人”从宗教束缚和专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政治要求。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布鲁诺·鲍威尔曾说,“自我意识”是绝对自由、合理的,而现存的宗教、现存的国家是不合理的,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受时间制约的暂时的异化形式。为了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必须消灭基督教和专制制度。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自我意识”是有生命的人或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把社会主体的人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用理性批判信仰,借自由批判专制,不可避免带有唯心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试图从古希腊哲学中寻找到同“自由个性”和“自我意识”相类似的理想追求,对德国专制制度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以便为人的解放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莫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把自我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的本质,指出“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1]233。显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将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从自由和理性出发批判宗教,称宗教是无知和迷信的产物,那么,人的解放的实现也就是破除宗教对人的精神控制,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开始接触大量社会现实,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但依旧把理性、精神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认为事物所以存在是由于其合乎理性,自由则是合乎理性的本质,并且指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1]63。马克思在此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主题文章,如:对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争取出版言论自由的权利等都是基于人们的意志自由是客观的、永恒的、不证自明的立场。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看到了私人利益对人的言行的影响,诸侯、貴族为了各自的私利反对出版自由,但依然认为只有出版自由才能使人们遵循理性来解决问题,“出版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1]62。马克思以人类理性为依据,以理论的批判为武器,认为只有消灭现存的宗教和专制制度,建立理性国家,才能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发展的早期,认为实现人的解放主要通过张扬自我意识,实现个性解放、理性自由。青年黑格尔派提出人是理性的人,必须按照理性办事,国家是人格的最高实现,是理性和自由的产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马克思却发现人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者,国家和法并不能代表私人利益;诸侯、贵族为了自己的私利反对出版自由,林木占有者为维护个人私利,把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普鲁士国家也不是理性的体现(或者说实现),而是封建贵族地主等疯狂掠夺劳动人民的“物质手段”和工具。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在国家和人的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产生怀疑,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思考国家和人的本质,以便找到实现人的解放的正确道路。
二、“类本质”下人的解放的凸显
对人的本质的确认是回答“人的解放”的理论前提。基于意志自由的立场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冲破了神权对人权的束缚,然而,意志自由并不必然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由。《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存在决定思维的观点,不仅对黑格尔的“理性的人”的观点进行了清算,批判了黑格尔所谓“构成群体的个人本身是精神的存在物”,代之以“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的论点;而且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倒置过来,提出决定国家的不是理性而是市民社会。至此“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途径被打开。马克思不仅借助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而且找到了进行人的研究所需要的理论突破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这里“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自此以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索逐渐由黑格尔式的自由理性精神向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跨越,不再把理性、自由作为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人的本质,从人本身寻求人的解放的实现。这已经蕴含着唯物主义的萌芽。费尔巴哈从生物学的角度,把“类”看作是一个物种,一个群体,现实的人也就是过着群居生活的自然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并没有将“类本质”局限在生物学范围内,而是将其扩展到社会领域,提出人的类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群居生活,而是人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团体、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成员,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人的社会特质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发现人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现实生活中人的类本质并没有实现,人不是作为国家、社会中自由自觉的一员,而是过着一种异化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象征,而是异化成人的外在约束,不但使劳动者从“类本质”异化出去,也从自然界异化出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4]既然异化劳动是形成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的根源,那么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消除异化劳动产生的经济条件——私有制,才能使劳动者从奴役性的生产劳动中获得解放,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里的“共产主义”,其中心问题是人怎样从克服异化状态中实现人的解放。到那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
马克思通过阐述异化劳动理论深化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指出人的解放就是实现“人本身是人的本质”,但此时马克思还仅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也没有意识到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才是人成为真实的存在和自然界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不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抽象性。
三、唯物史观的确立与人的解放的实现
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开始深入到“现实的前提”中来寻求人的解放。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抽象物,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存在下产生和形成的,是人的对象性的物质创造和精神道德创造的结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83。作为人的解放的逻辑起点的现实的人,不外乎存在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与外在自然界的关系;二是与其他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三是与其自身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的形成都是在生产实践中确立的,因此,对人的解放的追求也需要从生产实践中寻求答案。人类的生产实践毋庸置疑地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的解放的实现也必然是来自于现实历史条件、植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场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分工克服了原始人简单协作的落后状态,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但劳动的分化也造成了人的活动的异化,分工把人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分工造成不同的阶级和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37异化的消灭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消灭。到那时,也就是人的解放的实现。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标志着唯物史观正式问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下,人类社会实现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这一科学认识的前提下,马克思将对人的解放的探索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得人的解放的实现不再是一种价值的应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6]。生产力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是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总和。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不仅仅是指人类某个个体的劳动能力,而是存在于每个个体及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客观的力量,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运用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这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言的仅仅是财富积累的手段,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物質基础,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就不能消灭奴役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不仅如此,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还和生产关系的解放程度密切相关,只有生产关系解放了,人们在生产中才能形成一种平等协作的友好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把生产关系作为人们借以进行物质生产的关系,是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只有结成人与人的一定社会关系,才有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才有现实的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决定着特定社会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深刻论述,深刻指明了其他社会关系对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生产关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预测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与阶级对立会消失、国家将消亡、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人人将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最终诉求,不仅渗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而且是伴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不断完善。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实现人从自然界的解放,才能为人的解放创造物质前提;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解放,才能创造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只有消除了来自外界(自然界、人际关系)的外在束缚,人才能实现自身解放,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当前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也务必秉承“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引领作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号召力。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结合我国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生活条件来谈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刘同舫.从思想解放走向人的解放[J].理论月刊,2009(4):38-40.
[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