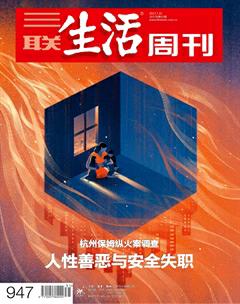教育的生意:成都“学而思”下架调查
葛维樱

这场“地方教育部门与全球上市机构的正面对决”,看起来是教育部门的胜利。“学而思”被成都教育局下架,这家近百亿美元的上市公司股价暴跌。培训机构在学校素质教育之外,构建的选拔、应试体系,揭开的是学校减负的现状之下,家长对于教育的消费需求和心理期待,以及催生出课外辅导机构的巨大市场。
下架博弈
暑假前最关键的招生时间,开在成都闹市区路边的一栋旧大楼里的“学而思”门庭冷落。作为中小学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的代表,“学而思”果然和传闻一样,没有销售,只有前台。即使是风口浪尖上已经开始整改,仍有家长来咨询报名。自从今年5月开始,成都市教育局接到举报后,携5个区教育局,联动消防部门,责令“学而思”9个教学点整改,停止招生或教学。这是学而思第一次受到教育部门公开惩罚,当天它的母公司好未来股价下挫5%。
今年3月举行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开考前,一位老师收到学生发来的一道奥数题求解,开赛后老师发现,那道题出现在考卷上。去年华赛,也有家长反映比赛题目在辅导资料里出现过,辅导资料作者周春荔是华赛的主试委员之一。华赛作为全国统一命题的考试并不是封闭命题,而是由命题组成员春节后到中科院数学所命题,在考前提交。以前组委会过去提前一周发题到各地,两个成员单位一个保存试卷,一个保存密码,现在改成了提前一天把电子版发往各地印刷。
此次华杯成绩公布后,成都获得一等奖学生总共394人,其中331人来自学而思和盛世英才两家华赛委员机构。数学素养本来是拓展思维的兴趣爱好,却已经走进了应试教育的功利怪圈。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是1986年始创的全国性大型少年数学竞赛活动。2015年以前华赛成都区赛,由成都市少年宫举办。此后北京组委会到成都组建了成都赛区的“管委会”,管委会成员单位中,包括成都新星飞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学而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和成都盛世英才资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这个比赛已经完全成为民间组织、民间管理的赛事。
4月学而思在官方微信上说,除了组委会发布的公开复习资料外,从未在考试前获得华赛相关考题。在学而思和盛世的网站上,一等奖获得者依然是光荣榜上的佼佼者。学生们被各名校录取,在小升初战役中这又是一场“辉煌的胜利”。自从2012年学而思进入成都市场,奥赛和华赛获奖人数和比例连年升高。学而思自从2012年进入成都,以奥数起家在这个二线城市站稳了脚跟。
2016年末四川省教育厅曾经连发三道文件,严禁公办、民办学校组织选拔性考试和测试。2017年针对民办学校,专门出台了“禁止笔试,不开展提前报名、面谈和录取,录取不与培训机构挂钩,不收学生的个人简历和获奖证书”的政策。然而事与愿违,“关门”,导致奥赛华赛含金量更高。“哪个名校招生会拒绝一等奖?”参与此次“清剿”活动的一位教育局干部无奈地告诉我。学而思的课程表上,从小学到初中的课程以理科为主一应俱全,是另一个校外校。曾经相对公平的私立校考试,被“禁试”阻断,义务教育阶段取消排名,孩子处于什么水平、哪个梯队,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都越来越模糊。
调查结束后金牛区教育局“关于成都金牛区学而思培训学校存在的问题报告”里显示,学而思的主要问题,在于违反以下规定:“一是严禁委托或变相委托其他主体,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考试或培训班,二是严禁举办、承办和组织中小学生参加非政府部门举办或未经政府部门认可的各类竞赛、考级或活动。”
这场正面对决看起来应该是教育部门的胜利,在随后学而思向成都市教育局提交的自查报告中,除了各方面资质自检,也专门拎出竞赛,承诺“从即刻起绝不主办、承办、协办参加华杯赛、国奥赛、学而思杯等非政府部门举办或未经政府部门认可的各类竞赛、考试或活动”。
学而思2004年起从单纯的家教中介向课外辅导机构转型,家教辅导班小作坊开始正规化经营,此外较早介入该行业的还有巨人教育等。自从小升初考试被取消,学校选拔人的方式将奥赛作为重要的标尺。2008年学而思在北京的奥数班一战成名,几乎整个班都被人大附中录取,使当年被称为北京小升初的奥数元年。学而思开创的奥数之路,后来拓展成为其看家的思维拓展训练的方法。在新东方等机构享受着留学相关培训的红利时,以学而思为代表的课辅机构,开辟出了中国教育培训的另一个巨大的细分市场——K12。
爆发式增长
K12课辅被称为近两年来最大的教育投资风口。K12原本是对幼儿园(Kindergarten,通常5~6岁)到十二年级(Grade12,通常17~18岁)教育阶段的统称,在中国投资界成为中小学课外辅导的代名词。以学而思2011年上市为标志。课辅这个门槛低、离钱近的行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目前近1.4亿中小学生,德勤的报告显示K12教辅的市场规模在万亿元以上,学而思加新东方总共占领了不到5%的市场份额,每个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的机构,数量难以统计。“这个蛋糕太大了,谁也垄断不了。”持续数年在K12领域投资成功几个项目的投资人丽君告诉我。
根据学而思财报,2016年11月30日之前,当年累计入学259万余人。这比2015年时的统计数字,增长超过100万人,增长率70.8%。學费增长一倍,2016年净收入7.26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了63.4%。目前,学而思市值接近99亿美元,两年时间翻了4倍。
2007年开始逐渐取消小升初考试后,在一线城市学区房这样性价比极低的对照下,家长对于课外辅导价格的敏感度正在降低。近两年内,二线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学区房”苗头,成为课外培训大力开发的市场。中考是城市学区房价的风向标。每一年中考模拟成绩一出,初中连带小学周边的房价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杭州和成都的学而思是二线城市K12的代表。小升初在这些城市家长心中,也开始成为焦虑的核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商机,2015年学而思在全国仅有19个城市落地,有289个教学中心,近一年多里爆发式增长,2017年进入30个城市,教育中心达到507个。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行业集中度较高,进入品牌化竞争阶段,市场结构已经相对稳定。杭州、南京、重庆、西安、成都等二线城市是上市公司进行业务扩展争夺的主要区域。K12把学校减掉的负担加了回来,按照考试测验成绩给学生分不同的等级。尽管标准化难度高,进入门槛却相对较低。对于资本,K12在预付模式下现金流良好,使得热钱不断涌入,机构遍地开花。
在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渐渐不再进行竞争分级,而名校有自己极严格的升学体系,使“上课”和“选拔”变得南辕北辙。一个年龄段的学生到底应该对应什么水平?
中考是硬指标。一方面是课辅一直宣传的孩子“吃不饱”,另一方面名校提高了考试的标准。进入名校的家长,反而瞧不上老师们轻飘飘的素质课堂,开始各种花样翻新的“思维拓展”“情商训练营”。相对于学校,辅导班严密的教学机构、排位和竞争体系的架构,以“体系”被认可的学而思有一套独到的教育方式,对学生“七大能力”提高的标准化教学模版。主备课老师带下属教师一起备课。家长可以坐在课堂后听讲,教师不断针对学生水平做调整,老师讲课也比很多课堂有趣。一位家长告诉我,辅导班更注重对学生的鼓励,“让孩子感受到被关注。看看考试题目,谁敢依赖那40分钟的教学”。
一位自称“海淀最朝阳的妈妈”告诉我,她的孩子三年级,课外辅导的一年费用在10万元以上,这是以三门主课各上4000元一学期的普通班为计算标准。她的孩子就读于中关村一小。四年级以后,进阶高级课程的基本费用在30万元一年左右。海淀“学霸培养学霸”的模式下,课外辅导机构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虚妄。“学霸妈妈会比孩子更前一步领会融合所有奥数、逻辑思维等课程的精华,然后带领孩子一起进入学霸思考模式。她们对于学校的考试随便应付已经可以得优,就是那种智力超群的极少数人。”这位放弃加拿大国籍举家回国创业的母亲说。

相对于拼搏有限的升入名校的比例,更多的K12消费,源于对教育资源平等的怀疑和家长自身的焦虑感。在采访成都市教育局时,一位领导告诉我,他自己的外孙正在学而思学习,比起那些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和良莠不齐的师资,学而思这些年在教育局的家长投诉次数为零。尽管成都正在整改学而思,但另一个事实是,学而思的教师大多出自一本院校,上课有章法。能考入学而思尖子班的孩子,在每个小学里都凤毛麟角。成都名校录取择校生,400人中不过20来人。私立择校还相对公平,嘉祥在九思冬令营中已经选优完成,到面试阶段已经录取的非常少。另有巩固加强、与学校同步的班级更需要老师的耐性,达到学校以外的效果。传统意义上初三、高三才出现的升学考试需求,但是现在,K12掌握的是从底层用户开始捕捉的策略。
教育消费越来越高。投资人丽君引用了教育部5月发布的数字,“2016年中国教育财政经费是3.8万亿元,达到GDP的5%”。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57%。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37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36%。教育经费总投入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间的分配占比分别为5.65%、7.21%、45.29%、15.84%、26.01%。“每个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达到可支配收入的20%~30%。一线城市公立学校的孩子上辅导班每门主课一年费用按1万元算,二线城市5000元,还有艺术体育培训市场,和四年级开始的刚需。”家庭投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支出,而是一个消费指数。这个指数反映的是家长对于教育,尤其是课内教育的不满足。
“在分数以外,学校没有提出更有信服力的素质。”竞争、培优体制在一个程度、一定人群以内确实有效。2007年进入学而思尖子班的刘周岩,小学和初中都在差校。他正好赶上学而思以竞赛起步的时间点,在课外辅导班打开了另一扇门。竞争并不是坏事,“只要我愿意做,就可以做得很优秀”。北京崇文区最好的学生都集中在这个校外校里,老师不少是北大、清华刚毕业的大学生,除了上课还能聊天,学生也很喜欢。初中阶段的优等生,在培训班如鱼得水,是教育和学生之间的互利。
“只有当课外辅导机构的师资好于学校时,才有必要购买这个服务。”他在北京崇文区一所普通初中里成绩优异,而初中老师却是“思想僵化照本宣科的大妈”。模拟考试他有一次考了全区第三名,在学校里备受夸赞,他想在学而思辅导班里炫耀一下,数学班上,同桌很平淡地说:“哦,我第二。”他不服,又去英语班,结果碰到了第一。“因为学习、竞争产生的快感,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中考“失利”进入北大附中后,刘周岩说自己对于海淀搞竞赛出身的同学,等于是“玩泥巴”长大的。高中老师几乎没有师范院校毕业的,很多是北大附中加北大的双校友。
在层层下压的培优压力下,公立小学的短板就显示了出来。一些要求高的家长会认为,“英语普遍很‘水”,“如果不能在五年级学完小学,六年级学习初中课程,上了最好的初中一样会跟不上”。
风口上的教育
营利性通向“应试”的课外辅导机构,和以“素质”为导向追求普惠的学校教育目标,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为焦虑买单的热潮。几乎和家长的消费需求同步,人民币开始关注教育产业。2013年投资教育资金量百万美元以上还是新闻,而2016年获得亿元以上的投资已经比比皆是。
“很多投资教育的资金来自传统行业,为了把企业资产盘活,优化资产结构,所以经常看到一个中国最大的钢化膜企业、印刷公司,开始进行对教育领域的大笔投放。这个与国家近两年鼓励资本进入实业有关,曾经的游戏文化之类的领域冷却了。”丽君说另一方面,教育的不标准化、门槛低,恰恰使这个大蛋糕细分,被切了不同年龄、地域、科目的“N多刀”。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教育机构从过去只能设立为非营利的民办教育机构,申请牌照只能申请非营利,变成了可以有合理回报。一个教育机构,可以实施盈利和非营利要两种管理办法。既然可以分红给股东,投资人觉得,这个事可以把回报赚回来,不用非得去美国上市。”丽君分析近两年传统产业为了优化资产,加上国家政策鼓励投入实业,纷纷找项目进入教育服务业。到今年,主板加新三板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百家。“教育纯粹是内资需求。”
参照美国教育科技市场,90%的公司都是B2B的企业,由美国公立学校选择采购适用的教育科技产品。然而,在国内K12教育领域,无论在传统教育在线化,还是新兴在线教育机构,基本都是围绕课外辅导做文章。2013年拍题为主的作业帮,虽然达到了千万用户量,但学生流量不是家长流量,变现压力很大,市场转化率低。“拍题找答案对于学生来说很实用,流量很高,但不排除一部分学生就是用来抄作业。”丽君说,2014年大量线下课辅机构,把存量转到了线上,交费报名用APP。2015年是题库类的爆发点,是曾经的题海战术的延伸,2016年火的是北美外教用QQ聊天的形式进行一对一口语训练。丽君投的项目处于这个风口:“在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学方式,口语一直是短板,一个星期大多只有两节课,达不到目前城市家长的国际化要求和对英语的期待。”
资本让课外辅导机构数量猛涨。在线教育机构选择从教学大数据、翻转课堂乃至教师服务进入公办学校,试图以B2B、B2C的模式,将在校学生引流到线上或线下课外辅导之中。B2C的公司针对学校,开发帮助教师批改作业,和将知识点拆分到最细并进行不断强化训练的信息元。B2B的课外辅导机构则用于满足减负带来的升学刚需。可是父母并不期待学生用iPad做题,这也是很多教育机构希望进驻学校做硬件设备和应用程序出现的阻力。“老师连卷子也不用改,机器直接阅卷,老师和学生之间更加互不了解。”矛盾依然在人身上。
教育本质在一波波投资热潮中并沒有变化。在传统教育机构,教学质量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的教学水平和负责任程度,教育机构对教学过程的参与、管理和提升都非常有限。“时代变化了,老师的职业专业度提升了多少?我们的同学谁在做老师?我们身处的行业的竞争程度远远高于教师,家长对学校里老师确实缺乏敬畏之心。”丽君感叹。
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抱有期待,学校难以改变,培训机构却能把握战机。在这个以“学习”为名的军备竞赛里,曾经的学校主导权,变成了家长联合培训机构主导的“超前学习”,学校的试题也越出越难。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K12已经成为一个孩子从6岁到18岁持续的马拉松。就算没有培训机构,家长的纠结和孩子的奋斗会停止吗?